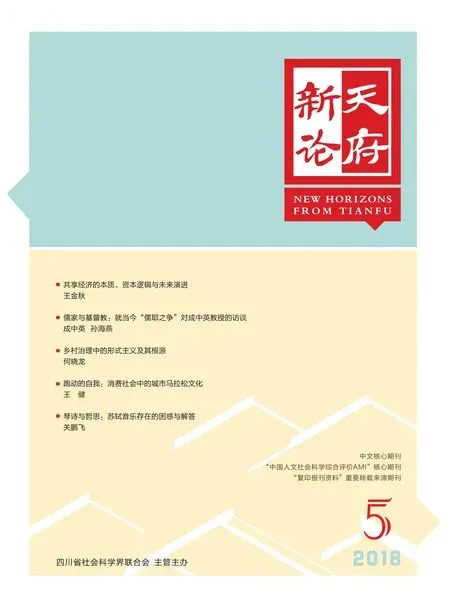論《資本論》的勞動主體性問題
——基于日本宇野學派的理論
尤歆惟
勞動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在馬克思的學說里,勞動究竟是否擁有主體性地位?關于這一點,學界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有著不同的觀點。中國傳統的實踐唯物主義曾經試圖基于早期馬克思的實踐和物質生產概念來建立一種主體性原則,其中最核心的原則就是人對自然的能動的改造,也就是勞動的主體性原則。這樣,就把馬克思的理論理解為一個基于勞動主體性原則的理論。但不同意這一解讀范式的學者也大有人在。比如仰海峰認為,馬克思的理論中存在著生產邏輯和資本邏輯的兩條邏輯,前者可以說是勞動主體論,但后者是資本主體論,它主要體現在《資本論》中。在這里,勞動主體只能被視為是資本增值的工具。*參見仰海峰:《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胡岳岷也指出:“到了《資本論》,馬克思只將勞動視作具有‘特定形式’的功能性活動,是從非本體論的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的。”*胡岳岷:《〈資本論〉中是勞動本體論嗎?——兼與譚苑苑博士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17年第1期。由此可見,一部分學者認為,至少在《資本論》的理論中,勞動是不具備主體性的。
在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也存在著類似的分歧。比如市民社會派的望月清司認為,馬克思的史觀是關于“勞動有機編成的各種形式”的理論,這是一個“直面自然、改造自然、領有自然,人通過這一過程將自己陶冶成類的個人,人類史就是將既存的生產力重新編成的歷史。”*望月清司:《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韓立新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即可以說,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一個基于人對自然的勞動關系而形成“市民社會”的歷史。而且在望月清司看來,這一論點是貫穿馬克思一生理論思考始終的。將市民社會學派介紹到國內的韓立新教授則更加直接地認為,要通過勞動的外化(或者說“異化勞動I”)來理解私人所有,并基于此,將《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異化論理解為馬克思最初的資本積累理論。*參見韓立新:《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究竟是不是循環論證》,《學術月刊》2012年第3期。也就是說,馬克思的整個理論應該建立在基于最初的勞動的外化的異化勞動理論來加以理解。與之相反,日本的宇野學派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通過對《資本論》的研究認為,在《資本論》的原理論*宇野弘藏把經濟學研究分為原理論、階段論和現狀分析三大階段。其中,原理論是關于純粹資本主義的理論,闡明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律。對三階段劃分的論述可以參考宇野弘藏的《經濟原論》序論。體系中,勞動作為人與自然物質代謝的基本原則,要納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規律中來闡明,因而它只能作為一個消極的東西而存在,不具有主體性的地位。而且在這一問題上,宇野學派的觀點比國內主張《資本論》無勞動主體論的學者更加徹底。可惜的是,雖然我國的一些學者已經開始向國內陸續介紹日本市民社會學派的學說,但關于宇野學派的介紹還非常匱乏。本文的目的即試圖從宇野學派的理論出發,對《資本論》中勞動的主體性問題進行闡述,同時也填補國內宇野學派研究領域的這一空缺。
一、在《資本論》的原理論體系中勞動所處的地位
《資本論》中對一般性的勞動的論述主要集中在第五章第1節,即著名的“勞動過程”一節。這一節在《資本論》中處于一個奇特的位置。作為唯物史觀開創者的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社會時,不是從人類社會最基本的人對自然的物質代謝過程出發,而是從商品和貨幣的流通出發,在論述完貨幣轉化為資本和勞動力的商品化之后才開始論述這個最為一般的勞動過程。這樣一個奇特的論述結構表明,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是有意識地把勞動過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環節而進行論述的。
宇野學派創始人宇野弘藏將這一理論發揚光大。他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理論加以純化,形成了經濟原理論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宇野弘藏于流通形態理論完結之后和生產論理論開端之處,介紹了一般性的勞動生產過程。從這一論述的位置來看,宇野弘藏原理論體系中對于勞動的態度和《資本論》是一致的。不過,在宇野弘藏關于一般性勞動過程的觀點中,有如下兩個創造性發揮:
首先,宇野弘藏在流通論的最后,將資本明確定義為G—W—G′這樣一個一般形式,資本即貨幣通過購買商品并賣出商品以實現增值這樣一個價值增值的運動體。但這一價值增值過程在流通過程中,還只是一個流通形式,尚不具備它的內容,或者說,尚不具備它的“實體”。因此,通過賤買貴賣來獲得利潤的商人資本是最符合這一資本形式的。但很顯然,這樣一種商人資本形式只能是一種偶然的形式。在這里,資本還無法以一種必然的方式獲得一種基于主體性的自立性。只有當這一資本的一般形式把握了作為物質生產的勞動過程本身之后,資本才能以產業資本的形式,即G—W…P…W′—G′這一形式,實現自立性,而這樣一來,流通論也就過渡到了生產論。因此,宇野開始論述一般性的勞動過程時,很顯然是將勞動過程視為產業資本這一自主、自立的運動體的一個重要環節來看待的:在宇野弘藏那里,勞動生產過程構成資本的“實體”性規定。正因為資本一般形式即G—W—G′把握住了作為人類一般物質生產過程的勞動過程,資本才能以產業資本的方式成為自主、自立的東西。
其次,宇野弘藏區分了“經濟原則”和“經濟規律”。“經濟原則”指的是那些“規定人類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這個一般性經濟生活”的原則*參見宇野弘藏:《経済學方法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第4-5頁。,即人通過勞動作用于自然并進行最基本的物質代謝過程的原則。它是貫穿于一切人類社會形態之中的。而“經濟規律”則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人們的經濟生活所表現出來的規律,是“經濟原則”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表現形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五章第1節“勞動過程”中所論述的那些基本原則,就是“經濟原則”。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是消極、被動的東西,必須納入資本增值的目的中,構成資本增值的實體性根據。在宇野看來,馬克思的做法,正是明確地把“經濟原則”放在“經濟規律”中去論述。
不過,“經濟原則”并不是一個獨立于“經濟規律”之外的、僅僅因為資本主義的產生才以“經濟規律”的形態表現出來的東西。毋寧說,“經濟原則”作為“在所有社會中所共通的勞動生產過程,只有在闡明資本生產過程的經濟學原理論的這一生產論里,其自身才得到闡明”*宇野弘藏:《経済原論》,巖波全書,1964年,第48頁。。作為“經濟原則”的人類一般性的勞動生產過程,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而被我們積極地理解;相反,只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規律”中,其自身才能獲得理論上的闡述。這是因為,人的一般性的勞動生產過程這樣一個物質代謝過程,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中不是獨立的,而是或多或少依附于上層建筑等非經濟因素而存在的;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人類的物質生產過程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獲得了物質生產的自立性和自律性。這種物質生產的自立性和自律性就表現為經濟的“規律”。因此,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原則”才以“經濟規律”的方式實現了自我理解。也只有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的“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這一著名命題的內涵:我們必須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來理解貫通人類歷史一切社會形態的生產的原則。
因此,宇野弘藏認為,勞動并非僅僅在資本主義中才喪失自己的主體性,不如說,它從來就不具有規定歷史的主體性意義。宇野學派學者大內秀明引用列寧關于唯物史觀的“假說”理論,認為唯物史觀中那種用人的物質生產勞動來規定上層建筑的觀點不僅不能支持《資本論》的理論,相反,它作為一個理論假說必須被《資本論》的理論支持。*參見大內秀明:《宇野経済學の基本問題》,現代評論社,1971年,第127-129頁。簡而言之,不是勞動的主體性決定資本邏輯,而是勞動主體性的性質必須被資本邏輯決定。當然,這種徹底站在《資本論》立場而否定唯物史觀哲學意義的觀點未必是符合馬克思的原意的,但宇野學派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無主體性的立場由此可見一斑。
立足于這樣一種將《資本論》的邏輯徹底化的觀點,我們只能從一種無主體性的角度出發去重建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哲學。宇野學派的學者對勞動的哲學態度是明確的,即勞動不是一個能夠積極構建人類社會形態的積極的要素,因而它在哲學上是一種“無”。
二、作為“無”的勞動和基于流通形態的異化理論
開創這種“無”的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解讀范式的學者是宇野派學者清水正德。他在《從自我異化論到〈資本論〉》一書中,把馬克思以《資本論》中的勞動理論為代表的勞動觀概括為“無”的哲學:“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勞動的概念擁有無法用物質或精神這樣的‘有’概念來規定的結構,如果要用邏輯來把握的話,就必須使用‘無’這個規定。”*清水正德:《自己疎外論から『資本論』へ》,こぶし文庫,2005年,第86頁。它不同于黑格爾哲學中的勞動觀。在黑格爾的哲學中,一切主體性的行動都必須納入“形相”中去把握。但在馬克思的勞動哲學中,勞動主體性可以被把握為作為可能態的“質料”,而且不同于亞里士多德通過形相來考察質料,馬克思的行動、實踐的原則可以說是“質料的質料”或“第一質料”。在這個意義上,勞動只能是“無”。
基于這種理論,清水正德重新理解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宇野學派的學者傾向于將馬克思早期創立的唯物史觀和后期的《資本論》的勞動觀對立起來,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視為試圖通過勞動主體性原則來積極構建歷史的理論,從而否定早期馬克思的理論貢獻。但清水正德擁有不同的觀點,他試圖正面評價馬克思早期的勞動觀和唯物史觀。在清水正德看來,馬克思早期的唯物史觀與其說是一種積極的勞動主體歷史觀,不如說是自然主義的勞動觀,在馬克思早期的唯物史觀中,勞動只是充分地發揮著維持人類物質代謝的基礎作用。唯物史觀的積極意義正在于把這一物質代謝的基礎過程凸顯了出來,從而實現了對黑格爾哲學的顛倒。由于黑格爾哲學用邏各斯把握了一切,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無”的空間。但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哲學的顛倒,開辟了一個非邏各斯的純粹物質生產活動的領域,因而開拓了一個作為“質料的質料”的“無”的空間:唯物史觀就是這樣一個“無”的空間。可以說,清水正德積極地把馬克思早期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從費爾巴哈那里吸收來的自然主義提取出來,作為唯物史觀理論的積極要素發揚光大,并納入《資本論》的勞動觀的立場中。就這一點來說,他和另一位日本馬克思理論學者山之內靖有異曲同工之妙。山之內靖正是通過充分發掘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手稿中對勞動者作為“受苦者”的論述,尋找著超越近代化的理論資源。*山之內靖的思考可以參見他的著作《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馬克思的復興》第四章第四節和第六節。
不過正因為如此,在勞動過程本身中是尋求不到異化的根源的。異化的根源在于勞動力商品化,但勞動力商品化是不能從勞動過程本身中推導出來的。作為事件,它是歷史的產物。然而,這并不妨礙我們以理論的方式對這一事件進行把握。把握異化的理論即宇野弘藏的經濟學原理論中的“流通形態論”。 宇野弘藏經濟學原理論中的流通形態論對應于《資本論》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內容,但其論述更加純粹化,主要內容即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純粹流通過程中商品、貨幣、資本等范疇概念上的過渡進行闡述。在流通形態論中,宇野弘藏論述了商品是怎樣必然過渡到貨幣、貨幣是怎樣必然過渡到資本的。在這個過程中,體現“異化”問題的最重要的環節即“一般價值形式”。因為,每個商品作為能夠通過別的商品表現自己價值的能動的主體,到了“一般價值形式”出現時,就只能通過一個特定的等價形式表現自己的價值。本來,每一個商品的所有者都通過自己的商品這個主體對社會的一整套商品體系有著欲求,而現在,所有商品所有者都只對某一個特定的商品有著欲求。“價值表現的能動主體從個體轉化為普遍。”*清水正德:《自己疎外論から『資本論』へ》,こぶし文庫,2005年,第73頁。一般價值形式這一顛倒的結構,進一步發展出了貨幣和作為增值貨幣的資本,而資本則要求能夠控制物質生產這個社會的實體領域以實現穩定的價值增值過程。這樣,勞動力商品化也就成為資本進一步發展的題中之意了。
于是,按照宇野弘藏的“流通形態論”,《資本論》中的異化理論就可以理解為和早期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異化理論。在早期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中,勞動的對象化和外化被視為異化產生的根源。但在《資本論》中,商品流通過程本身創造著異化的條件,勞動作為一個消極的東西只不過被納入這樣一個資本主義所訴求的條件之中而成了異化勞動。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先論述商品、貨幣(第一章到第三章)和勞動力商品化(第四章),再論述一般性的勞動過程這一論述結構,也同時意味著,馬克思已經把一般性的勞動過程置于異化的邏輯中去對待,而不是像早期異化勞動理論那樣,從勞動過程本身中引出異化了。
三、勞動與《資本論》范疇體系之間的關系以及對勞動價值論的反思
既然勞動作為一個單純消極的、“無”的東西不能構成資本邏輯的理論上的前提條件,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勞動和《資本論》的范疇體系之間的關系呢?
清水正德認為,“馬克思的原理論中,存在是創造性的勞動-生產力,它是無限性。但原理論的諸范疇是有限的、歷史的東西,即在這一存在的自我對象化的形態中的東西,它是個體自由展開為全體的必然性時的形態的邏輯。”*清水正德:《自己疎外論から『資本論』へ》,こぶし文庫,2005年,第18頁。也就是說,在清水正德看來,《資本論》中的范疇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對象化活動展開時所表現的必然性形態。雖然勞動作為“無”不能積極地展開為這些范疇,但人們在全面地展開自己的勞動時卻不得不以這些資本范疇的方式表現出來。因此,勞動這樣一種對象化活動不能直接被我們從理論上加以把握,相反,它必須作為“價值”這一對象化活動過程的產物來加以把握。換句話說,理論的思維過程不是從勞動到價值,而是從價值到勞動。勞動這樣一個作為“無”的過程要通過價值這樣一個作為“有”的范疇來把握。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宇野學派以一種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完全不同的方式,構建起了勞動和資本范疇體系之間的關系。
基于這樣一種勞動與資本范疇體系之間的關系,我們就必須要對勞動價值論進行反思和重新理解。按照宇野學派的觀點,因為不能從作為對象化活動的勞動本身出發來構建資本主義的范疇體系,所以,《資本論》一開始試圖通過投入勞動量來決定商品價值的論證就是很難成立的。勞動過程必須理解為被納入了以資本增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之中的勞動過程,它并不是一個先驗地規定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價值量的一個積極因素。因此,我們只能在論述資本主義生產即原理論中的“生產論”時,才能給出勞動價值論的論證。而這個時候的勞動價值論已經不再是基于單純作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勞動的投入勞動價值論了,毋寧說,它是被納入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關系中的“勞動力價值論”。在這一意義上,宇野派學者岡部洋實主張重新評價亞當·斯密的支配勞動價值論,并重新構建聯結亞當·斯密理論中的支配勞動價值論部分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橋梁。*參見岡部洋實:《価値概念の再考》,《季刊経済理論》,2016年第53巻第2號,第25頁。對勞動價值論的更進一步的考察屬于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已經超出本文的范疇,這里不再贅述。但很顯然,宇野學派對傳統的投入勞動價值論的反思,不僅僅是為了回應西方經濟學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攻擊,更是有著他們對勞動主體性的觀點本身這一哲學視角為指導的。
四、資本主義的揚棄何以可能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已經被納入了資本的邏輯,因而不具備主體的主動性,那么資本主義的揚棄又何以可能呢?
在這一問題上,宇野學派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有著重大分歧。他們否定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那種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和領有的私有性之間的矛盾的觀點。宇野弘藏認為,“作為經濟學的《資本論》闡明了,構成資本主義社會自我運動之根源的矛盾在于勞動力商品化,而勞動力商品化構成了資本的社會再生產的基礎。”*宇野弘藏:《経済學方法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第129頁。這一點可以說是宇野學派關于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問題的核心觀點。因此,揚棄資本主義社會,并不在于是否簡單地推動生產的社會化乃至國有化,也不在于是否僅僅充分發動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進行革命,而必須將以勞動力商品化為基礎的資本邏輯徹底廢除才得以可能。
在這一問題上,宇野學派學者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里還殘留著理論上的不徹底性。例如,在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7節“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中,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辯證法式的揚棄理論,即,資本主義私有制作為對基于個體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現在要再一次被否定,這種“否定之否定”即對資本主義的揚棄,即重建基于共同占有的個人所有制。*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頁。在宇野學派看來,這一揚棄的途徑并非基于《資本論》的科學邏輯,而是基于辯證法的哲學方法得出的,因而忽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源即勞動力商品化的問題。宇野弘藏認為,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是用“過渡的邏輯”代替了“循環的邏輯”,即把辯證法用在了論證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上,而不是用在了闡述資本主義作為歷史上一個自律的社會的展開邏輯。大內秀明在批評平田清明的社會主義觀時,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這一論述容易讓人陷入勞動-所有、勞動-所有的喪失、勞動-所有的復歸這樣一個早期異化勞動理論的結構,而這樣一種解釋路徑由于未能理解資本主義得以建立的邏輯,結果產生了平田清明的那種把資本主義邏輯還原為個體勞動=所有關系的傾向*參見大內秀明:《宇野経済學の基本問題》,現代評論社,1971年,第五章,『資本論』と市民社會論の復位——平田清明氏への疑問。。
如果我們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的邏輯是有效的和具有統治性的,那么,資本主義的揚棄在理論上就必須回到勞動力商品化的揚棄這一點上。但這一點并不是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部能夠實現的。它的實現需要借助“他者”的力量。宇野學派學者青木孝平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個體系是一個自足的全體,但并不意味著它沒有“他者”,這一他者存在于這個體系的外部,外部擁有一個無限的可能性。青木孝平將這個外部的他者同列維納斯的“臉”和親鸞的“他力”進行了類比,試圖從這個外部的他者中尋找揚棄資本主義的積極的力量。*參見青木孝平:《「他者」の倫理學——レヴィナス、親鸞、そして宇野弘蔵を読む》,社會評論社,2016年,第299-300頁。而關于這個“他者”具體落實點,青木孝平寄托于非原理論所能把握的“階段論”和“現狀分析”。也就是說,如何揚棄資本主義這一問題并不是一個通過《資本論》這樣的原理論就能給出答案的,它需要落實到資本主義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政策上,并進而最終落實到對現狀的分析上。資本主義的不同歷史階段和現狀,其本身就是資本主義不能將全部社會歷史納入其體系中的表現。而我們在階段論和現狀分析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地去改變資本主義的面貌,這也是一個在自足理論的外部存在的一個作為“他者”的實踐問題。
到這里,宇野學派和馬克思本人的訴求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背離。對理論的純粹性的訴求要求他們堅持勞動非主體性的觀點,而這樣一種觀點又導致他們不能把揚棄資本主義社會的希望寄托在勞動主體性的變革力量中。很顯然,馬克思很可能不會認同這一結論。馬克思的《資本論》雖然可以說是一個闡述資本邏輯的科學著作,但馬克思一生都在訴求著勞動正義觀和勞動者地位的提高,而這一點在馬克思那里顯然只能通過勞動者自己的主觀努力才能實現。
盡管如此,宇野學派的觀點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在一個資本邏輯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中,勞動者真的能夠基于其勞動主體性來扭轉這一資本邏輯嗎?對這一問題恐怕并不那么容易給出肯定的答案。在當今西方社會,勞動者不僅在物質生產的意義上被納入資本的邏輯中,而且在倫理價值觀上也接受著資本主義價值觀,他們不斷投入到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中并引此為豪。這是一個勞動全面納入資本邏輯的時代。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把這種現象稱為“新新教(Neoprotestantismus)”文化*參見沃爾夫岡·施特雷克:《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常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6-37頁。。這一現象是伴隨著二戰以后小農和小經營生產方式的真正瓦解而形成的。也許馬爾庫塞正是基于這一現象而得出了無產階級已經被體制化的結論。如果馬爾庫塞親眼看到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資本主義價值觀突飛猛進的回歸,他也許會更加驚嘆自己觀點的正確。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無論在世界范圍還是在我國,對以《資本論》為代表的中后期馬克思關于資本邏輯的研究在悄然升溫。國內的數位學者也在積極向國內介紹在理論視野上和宇野學派相近的國外價值形式學派的觀點。可以說,宇野派學者試圖通過“他者”來訴求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揚棄的觀點,對今天的我們無疑是有非常大的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