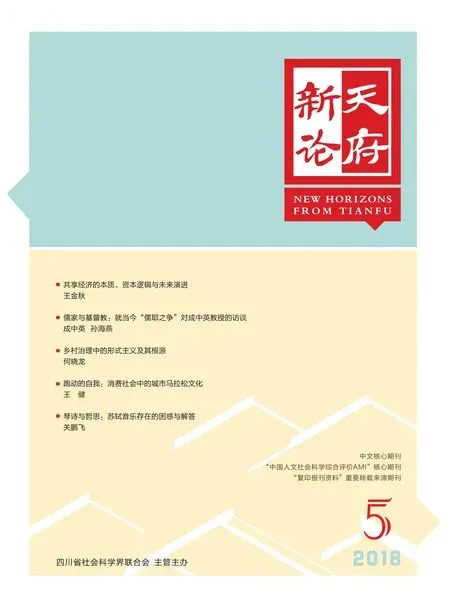刑事訴訟中的假認罪現象探究
——從聶樹斌認罪說起
閔豐錦
“在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被追訴人的認罪率很高,然而,這種高認罪率有多少是出于自愿卻不無疑問。”*左衛民:《認罪認罰何以從寬:誤區與正解》,《法學研究》2017年第3期。鑒于打擊犯罪的價值追求在相當長時間內遠大于保障人權的價值需要,認罪成為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第一要求。在偵查中心與口供中心的雙重作用下,個別被追訴人基于自身利益,或者“被認罪”或者“認假罪”,刑事訴訟中出現了一定的假認罪現象。“被認罪”體現了認罪的非自愿,“認假罪”體現了認罪的非真實,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工作中應當尤為注意。本文試圖揭開聶樹斌多達13次的認罪之謎,并以此為切入,對假認罪現象進行深入探究,以期找到保障認罪自愿性與真實性的有效對策。
一、最可怕的“被認罪”:聶樹斌案
2016年12月2日,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案被平反。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判決書表明,聶樹斌到案后共計有13次有罪供述,其中有“訊問筆錄11份(偵查階段8份,審查起訴、一審、二審階段各1份)、自書《檢查》1份、一審當庭供述筆錄1份”。雖然判決書也指出,“聶樹斌被抓獲之后前5天的訊問筆錄缺失,嚴重影響在卷訊問筆錄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但對于為何認罪,則稱“聶樹斌有罪供述的真實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誘供可能”,“刑訊逼供的意見,因無證據證實,本院不予采納”。可以推斷,聶樹斌在偵查階段的前五天可能存在無罪或者罪輕的辯解、但不知為何沒有入卷,在入卷之后的所有13份筆錄包括接受檢察院、法院訊問時都表示認罪,連上訴的理由都是“年齡小,沒有前科劣跡、系初犯,認罪態度好,一審量刑太重,請求從輕處罰”*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刑再3號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再審刑事判決書。,甚至家屬委托的辯護律師張景和在回憶時也稱“聶樹斌3次會見中都承認是自己所為”*趙凌:《“聶樹斌冤殺案”懸而未決,防“勾兌”公眾吁異地調查》,《南方周末》2005年3月24日。。
矛盾顯而易見:命案之中,明知自己被冤枉,為什么聶樹斌會認罪?如果說對警察認罪還能理解,為什么聶樹斌會對不是警察的檢察官、法官,甚至對屬于自己一方的律師也認罪?作為成年人,難道聶樹斌不知道涉及命案極有可能遭受的極刑后果?如何揭開聶樹斌持續認罪的謎團,就連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合議庭法官也不得不承認,“聶樹斌從開始作有罪供述,直到最后也沒有翻供,即使是在提出上訴的過程中也是如此,這確實會給認定相關事實帶來一定的困惑。”*李敏,荊龍:《讓正義不再遲到——聶樹斌再審案紀實》,《人民法院報》2016年12月3日。
曾經在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聶樹斌案中擔任申訴代理人的陳光武律師,在平反后也撰文思考“聶樹斌為何不翻供”。其以坐冤獄長達9年的山東李少奎故意傷人錯案為例,指出一直認罪態度極好的李少奎稱“我招供以后,他們真的就不打我了,但他們警告我,‘你選擇了坦白從寬的道路,這很好,政府很歡迎,我們已經向領導匯報了,給你留條命,但是不許翻供。只要你日后翻供,肯定殺你’。對他們的話雖然仍半信半疑,但為了不再受折磨,也為了能僥幸活命,我就一直沒敢翻供”,甚至在被判處死緩后,李少奎“不僅未吐怨言,而且還當即磕頭拜謝,感謝政府不殺之恩!心想:政府真的說話算話,果然給自己留了條命,慶幸自己選擇了坦白從寬的路”*陳光武:《聶樹斌為何不翻供》,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aeaff70102vqch.html,訪問時間:2016年12月3日。,暗示同涉命案的聶樹斌是否也持有同樣心態,即“坦白可能保命,抗拒必然槍斃”,尤其在上訴狀的“認罪態度好,請求輕判”似乎能夠印證此種心態。
筆者以為,必須以聶樹斌案所處的時代背景為依據,進行換位思考。正如同被錯判的念斌在平反之后又被列為犯罪嫌疑人,有評論稱“在新證據呈現之前,自然會讓坊間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那些實權人士”*文曄:《念斌案的新證據在哪里》,《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11月27日。。追根溯源,在聶樹斌案發的1994年,在客觀上法制不健全、有罪推定思維深入骨髓、公安機關“命案必破”口號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原本就很強大的公權力更加肆無忌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功能變異成為“偵查、起訴機關行使裁判權力,審判機關承擔追訴職責”*孫長永:《探索正當程序——比較刑事訴訟法專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5頁。。性格內向、毫無法律知識的聶樹斌在面對偵查機關的前五天究竟經歷了什么已經無從知曉——那肯定是如坐針氈、度日如年的五天。當年有關聶樹斌案的紀實報道如是說,“干警們巧妙運用攻心戰術和證據,經過一個星期的突審,這個兇殘的犯罪分子終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攔路強奸殺人的罪行”*張法生,焦輝廣:《青紗帳迷案》,《石家莊日報》1994年10月26日。。問題來了,這里所謂的“巧妙運用攻心戰術”到底何意?只是個別文字上的渲染升華,還是另有所指?通常意義上,“繼續、強化、加大審訊力度”“限期破案,不問過程,只看結果”等措施都在潛意識上隱含著以刑訊逼供、疲勞審訊、欺騙引誘等方式進行預審、訊問的意思,正如有基層公安局長給下屬下達“繼續加大審訊力度,三天之內要結果!我不問過程只要結果!出了事我負責!”*韓宏,王榮忠:《丹鳳縣原公安局長獲刑2年》,《文匯報》2009年11月25日。的命令、導致涉案嫌疑人猝死后被判處濫用職權罪,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的復查專案組負責人也透露“加大審訊力度,其中大有名堂”*田北北:《內蒙小伙被槍決9年后,疑似真兇被緝捕歸案》,《法制晚報》2013年11月28日。。潛規則中,“加大審訊力度”就是“變相刑訊逼供”的柔和說法,潛意識就是一旦出事,下令者就可以把自己摘出來,“我沒說要打,只是說加強訊問力度,是你自己領會錯誤”。當然,在聶樹斌案中,由于時過境遷、證據缺失,刑訊逼供處于證據不足、無法證實的狀態,官方層面上已然無法確認。
之所以聶樹斌會選擇認罪、供認不諱、永不翻供,根本上是個人私權利與國家公權力之巨大反差所致。公檢法三機關聯合打擊犯罪,實則為追訴職能的實踐異化。單就公安機關肩負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雙重職能而言,一旦公安機關將一個自由民抓捕歸案,毫無疑問,就意味著公安機關代表政府對該自由民的人身自由進行了一定限制。在“政府既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傳統思維下,犯罪嫌疑人的無罪辯解往往會被扣上“狡辯不配合”甚至“對抗政府”的帽子,這一切偵查人員往往不用明說,僅僅一句“說不說、認不認,后果你要想好”,基本上就達到“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思想攻勢效果,更厲害的不用多說話,一個眼神就足以表達盡在不言中的一切。此外,不說聶樹斌案發的1994年,時至今日大多數群眾對檢察院、法院的司法機關性質認識不清。正如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所表現的那樣,在老百姓眼中,檢察院、法院就是與公安局平級的大政府職能部門之一,公安局認定的就是政府認定的,政府認定的“對的就是對的,錯的也是對的”。聶樹斌案中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現已無法查證,但其對并非指定辯護的律師也連續三次認罪,在當時辯護體制并不成熟的情況下,除了受到各種壓力影響的違心自誣外,筆者實在想不出為何聶樹斌的認罪態度如此之好,深感這種對自己的律師也數次違心認罪的表態,才是刑事錯案中最為可怕的“被認罪”現象。
二、辯訴交易下的“認假罪”:不能承受的審判風險
美劇《金裝律師(Suits)》中,男主角羅斯因為無法律資格冒充律師被控詐騙罪、堅稱不認罪、接受陪審團審判,在庭審已經結束、陪審團已經達成一致意見、陪審團主席即將宣判的前一刻,因害怕被判有罪后被處以雙倍以上刑罰,羅斯與出庭檢察官簽署了認罪協議,法官詢問了認罪的真實性后,認可了該認罪協議、直接處以五年監禁、指出服刑一半后即可申請保釋——吊詭的是,事后羅斯的律師斯帕克特私下去詢問陪審團主席判決結果時,得到了“無罪”的答復,陪審團主席稱“你應當對我們的司法制度有更大的信心”,意即“選擇了無罪答辯、接受了陪審團審判,就應當相信我們陪審團會作出公正裁判”。
此案件充分體現出“事實有罪不等于法律有罪”的美國司法理念,典型如全國人民都知道是他做的、卻被陪審團判決無罪的辛普森案。實際上,雖然羅斯冒充律師辦案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損害了國家的司法制度,但由于羅斯以律師名義幫助了眾多弱勢群體甚至蒙冤人士、沒有其他危害社會行為,即以假身份做好事。因此,在代表所在社區的陪審團成員看來,羅斯的詐騙行為不具有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社會危害性、不是犯罪;程序上,陪審團之所以得出“無罪(not guilty)”的一致意見,是因為美國法律存在“陪審團廢法(jury nullification)”制度,即“在陪審團審理的刑事案件中,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檢察官已經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被告人違反了刑事法律,應依法裁決有罪,但陪審團依然裁決被告人無罪”*高一飛,賀紅強:《美國陪審團廢法的正當性考察》,《學術論壇》2013年第6期。,美國法律秉持尊重民意的理念,賦予陪審團在個案中廢法的權力。問題在于,沒有任何刑訊逼供、沒有受到威逼利誘、沒有處于羈押狀態,為何深諳法律的羅斯依舊作出了認罪選擇?難道羅斯不知道以不認罪的姿態接受陪審團宣判,可能會像辛普森那樣被判無罪嗎?
歸根結底,這是選擇辯訴交易與接受公正審判之間的矛盾:風險與博弈。認罪之后交易所得的量刑,遠低于不認罪、被判決有罪后處以的量刑,而作為辯訴交易主體的被追訴人,有著自主的程序選擇權,體現了訴訟主體的地位。正如有美國刑事辯護律師指出,“如果上庭的風險是100%的話,那么進行辯訴交易只是上庭的50%”,“這其實就是一個風險和保證收益之間的一個博弈。”*約瑟夫·A. 海登:《美國辯訴交易中的律師作用》,http://www.king-capital.com/content/details11_12172.html,訪問時間:2016年12月5日。霍爾巴赫指出,利益是人類行動的一切動力。本案中,從內心深處考察羅斯認罪時的考慮:在不認罪可能被判處十年、認罪只是判處五年且服刑一半后即可假釋的情況下,是放手一搏、追求概率較低的無罪判決,還是認罪了事、爭取早日出來陪伴新婚燕爾的妻子?畢竟又不是辛普森認罪可能面臨的死刑后果,再精明不過的律師進行理性選擇時,也是在各種利益之間加以平衡,認罪與否的選擇并非僅僅自己作出,而需要考慮自己背后的家人、親友等相關因素,“關進去”的時間長短至關重要。換言之,只要你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有利益糾葛顧慮因素,無論是真犯罪還是被冤枉,都有極大可能在刑事訴訟這一政府與個人之間最尖銳的利益沖突之中,敗下陣來。以2003年被平反的李杰故意殺人案為例,在李杰拒不認罪時,當地派出所副所長抓來李杰母親,對李杰說“李二娃,你媽在那邊受不住審訊,暈倒了。如果你不承認,我絕對不會把她送醫院”*劉志明:《四川宜賓“11·28”殺人冤案調查》,《鳳凰周刊》2005年第19期。,聽完后李杰立即認罪、其母親也被釋放,足見親人因素對認罪與否有多大殺傷力。
這就是人性,永遠捉摸不透。當有罪判決已經板上釘釘,如果不認罪認罰、不交易協商就可能遭受更為嚴重的刑期;當監禁刑罰已經十拿九穩,如果認罪認罰、交易協商有可能取保候審、量刑減讓甚至宣告緩刑……中國的司法現狀證實,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尚未完全建構之際,傳統的“公安做飯、檢察端飯、法院吃飯”的追訴犯罪流水線模式依舊有著巨大的生產力及慣性力。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為例,“從被告人角度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效果直接體現于量刑上,所以被告人可能想方設法利用認罪認罰以達到逃避嚴厲處罰的目的,但可能會出現被告人無中生有、亂認罪情況的發生。”*謝作幸,陳善超,鄭永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現實考量》,《人民司法》2016年第22期。縱然被告人在法庭脫下囚服,但深埋內心的囚意豈能輕言脫下。從自由民到犯罪人,打擊犯罪的國家機器一旦開動,必將轟隆隆一往無前,沒有極為特殊的原因,注定無法停止。
三、利益權衡:假認罪的思想根源
“人們在為自己的利益而考慮時,都是最聰明的。”*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40頁。當被追訴人與偵查人員獨處一室,“在訊問中,對于犯罪嫌疑人來講,是一個權衡利弊得失、作出判斷,選擇供與不供的心理過程。”*楊耀杰:《反貪審訊秘籍》,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0頁。實踐中,出于利益權衡的原則,存在以下幾種“被認罪”“認假罪”的假認罪現象。
一是冤假錯案中的被逼認罪,如被刑訊逼供、親人說服、誘供騙供等。早在18世紀,貝卡利亞就指出了刑訊的巨大威力,“痛苦將提示強壯者堅持沉默,以便使較重的刑罰換為較輕的刑罰;并提示軟弱者做出交代,以便從比未來痛苦更具有效力的現時折磨中解脫出來。”*貝卡利亞:《論犯罪獄刑罰》,黃風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33頁。云南錢仁鳳投放危險物質案平反后,坐冤獄13年的錢仁鳳稱其在案發17歲時受到刑訊逼供而認罪,“當時的心情就是感覺很黑暗很絕望,沒希望”*上游新聞:《17歲女孩坐冤獄13年,曾經被逼認罪》,http://d.youth.cn/shrgch/201512/t20151222_7447900_1.htm,訪問時間:2016年11月28日。;內蒙古王本余強奸殺人案平反后,坐冤獄18年的王本余稱其在偵查階段認罪原因在于“我一看女兒都說是我了,肯定活不了了,于是我就說是我是我”*茍明:《王本余親述被逼認罪:“女兒指認我是兇手,我只有認了”》,《華西都市報》2016年4月22日。;安徽劉明河故意殺人案平反后曝光,當年預審人員不僅欺騙劉明河認罪后可以定性過失致人死亡,而且編造“測謊儀就是科學結論、可以直接作為殺人證據”的謊言,使得大學文化、身為副教授的劉明河相信“違心認罪能夠活命,拒不承認必死無疑”*王亞林:《五年六審,死囚辯無罪——劉明河故意殺人案》,http://blog.sina.com.cn/s/blog_802253480100rb7q.html,訪問時間:2016年12月2日。,坐冤獄長達5年。在被逼認罪的案件中,由于可能面臨肉刑、變相肉刑、精神折磨等非人道處遇,行為人對冤獄的害怕程度已經遠遠小于對身體、精神傷害的害怕程度,在利益平衡之下,寧愿選擇在監獄完好無損,也不愿意在外面體無完膚。何況,在舉證責任錯位的情況下,“如果犯罪嫌疑人辯解自己沒有實施任何犯罪行為,那么他必須要證明自己無罪,并且要證明到令偵查人員滿意的程度,否則就會因抗拒而視為認罪態度不老實、頑固不化、有意狡辯、抗拒偵查,甚至會招來直接的或變相的刑訊。”*孫長永等:《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87頁。
二是假自首,以規避強制隔離戒毒、收容教育等處罰。有利益就有市場,“強制隔離戒毒人員主動供述未被掌握的罪行,被判處輕刑后不再執行強制隔離戒毒的現象,在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閔豐錦:《強制隔離戒毒人員自首現象研究》,《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強制隔離戒毒系行政處罰、期限為二年,由于刑事處罰優先行政處罰執行的緣故,只要被強制隔離戒毒的吸毒人員因為犯罪被判處小于二年的刑罰,由于刑滿釋放后刑罰執行機關與公安機關之間尚未建立有效的銜接機制,導致吸毒人員刑罰執行完畢后、原強制戒毒決定的執行無人監督落實的現象,或吸毒人員已經脫毒、不符合戒毒所的收治條件,極可能成功避開剩余戒毒期限。在以勞教戒毒為主的2008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了有吸毒人員為了逃避勞教編造販毒假案、企圖通過短期徒刑“以小換大”的惡性案例。例如,C市B區檢察院在辦理葉某販賣毒品案、陳某販賣毒品案時,發現二人主動交代的購毒人員都是陳某,三人曾在戒毒所被關在一個舍房,經查詢關押記錄、詢問證人,證實了彭某、葉某為逃避勞教編造假案的事實。*秦力文:《檢察官剖析假自首背后法律漏洞》,《法制日報》2006年10月24日。
三是考慮被害人因素,如躲避被害人打擊、與被害人慪氣等。在涉眾類經濟犯罪中,由于被害人眾多、涉案金額巨大,犯罪嫌疑人在無法還款的情況下,“關進去”面臨的各種壓力、滋擾甚至人身危險明顯小于在外,典型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筆者曾在訊問時得到“錢又還不完,出去要挨打”的嫌疑人答復。在個別故意傷害致人輕傷案中,因為矛盾不可調和,無論賠償與否、被害人都不會諒解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寧愿坐牢也不賠償。筆者也曾在訊問時得到“犯法坐牢可以,就是不賠錢不輸理”的嫌疑人答復。可見,在個別涉及罪與非罪、罪輕罪重的案件中,嫌疑人基于被害人因素,主動認罪、寧重不輕、愿意坐牢。
四是基于個人原因,如衣食無著、心理偏激、悲觀厭世等。有的老年人因為無人照料主動犯案要求在監獄內“養老”,如“日本很多老年人認為,監獄是個養老的好地方,于是爭先恐后地犯罪”*袁金會:《用坐牢換取免費食宿,日本監獄逐漸變成“養老院”》,《華商報》2016年3月29日。,以便管吃管住管治病;也有青年人因為“得不到父母關心他想坐牢”,*王梓涵:《這個18歲的小伙子為什么想“主動”坐牢啊……》,《重慶晨報》2016年10月11日。最終被檢察院不起訴;還有無證醉酒駕駛員連續報警五六次,“說家里煩,只想找個安靜的地方關個兩三年”,*鄭振國:《無證醉駕男開車至交警隊,強烈要求把自己抓起來》,《現代金報》2013年5月31日。甚至對可能判處的拘役刑罰不認可;至于未成年人因心智發育不全,一氣之下要求坐牢等事件更是時有發生。寧愿被貼上犯罪的污名化標簽,也要基于自認為更高利益的生活所迫,實施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犯罪,這種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帶來的犯罪選擇引人深思。
五是不符合邏輯、前后矛盾的形式化認罪。接受訊問時表態認罪、認罪態度較好,但面對訊問時與認罪應當的供述內容不一致、對所涉罪名的內容完全予以否認,并且在之后的檢察訊問環節、拒絕回答或者回答不出為何與之前供述不一致,甚至在被問到是否有刑訊逼供等被迫行為時表態“沒有”。理論上表態認罪就應當如實供述犯罪經過,但這種有些不符合邏輯甚至胡攪蠻纏的“形式上認罪、實質上不認罪”現象在司法實踐中卻有發生,充分體現了行為人避重就輕、試探逃避、見風使舵、心口不一的思想態度。
四、變異邏輯:認罪不等于有罪
(一)邏輯之一:表面認罪,實則認錯
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中,何為認罪引起了一定爭議。張建偉教授認為,“認罪就是承認指控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且系其所為,相當于英文admission 包含的內容。”*張建偉:《認罪認罰從寬處理:內涵解讀與技術分析》,《法律適用》2016年第11期。有法院則認為,“被告人認罪應當是對主要犯罪事實和罪名的承認,如果只承認其具有犯罪事實(進行了公訴機關指控的行為),但是并不承認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構成犯罪),被告人不能構成認罪。”*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三庭課題組:《關于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調研報告》,《山東審判》2016年第3期。實踐中,不少被追訴人的認罪,實質是一種認錯——“自己做了這件事情”即認可事實本身,而非“自己懂得這項罪名”即認可指控罪名。這是由被追訴人對具體罪名的犯罪構成不了解所致,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被追訴人大多是社會底層人士,文化程度并不高,法律知識欠缺,可能對事實和法律規定存在認知上的錯誤。”*韓旭:《辯護律師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有效參與》,《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6期。從犯罪構成的四要件出發,出于個體認知的局限性,只會對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及客觀要件中自己行為的一部分予以承認即“認錯”,而對于主客觀要件在某一部分的專業化認識則無法達到。一是主觀條件上,對自己患有的精神病是否影響刑事責任能力,對自己的真實年齡是否達到14歲、16歲、18歲等關鍵節點,往往需要多方證據證實、專業醫學鑒定,不少犯罪嫌疑人無法認知應屬正常。二是客觀要件上,對于盜竊、搶奪、搶劫、詐騙等侵財犯罪所非法占有財物的價值鑒定,對故意傷害、過失致人重傷等侵權犯罪所致被害人身體損傷程度,對非法集資、職務侵占等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所涉賬目、財物等,對交通肇事、危險駕駛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所承擔責任、血檢等,往往需要價格認證中心、物證鑒定中心、審計事務所、交警部門、醫院等專業機構進行鑒定,犯罪嫌疑人缺乏相應專業知識,在重新申請鑒定需要自己選擇鑒定機構、承擔鑒定費用的條件下,對鑒定意見往往只有服從、認可。三是案件定性上,犯罪嫌疑人往往沒有主導性的發言權。如行為人實施了盜竊但實際上已經構成了“轉化型搶劫”,又如行為人實施了拘禁他人索要合法債務但自認為是合法追債不是非法拘禁,再如對假裝做法事趁機調包財物的行為長期有盜竊與詐騙的認識分歧——“事情是你做的,但事情的性質由我們來定”是公安司法機關面對犯罪嫌疑人不認可被指控罪名時的常用回答,以至于出現了同一行為人在不同地區實施“假借手機趁機溜走”的行為、被分別判處盜竊罪和詐騙罪的“同案不同判”*閔豐錦:《同案不同判的理性思考》,《中國檢察官》2016年第10期(下)。現象。筆者曾訊問長期以“假借手機趁機溜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秦某,其認為自己就是詐騙,但對部分地區定性“盜竊”也表示認可,用其原話就是“反正事情是我做的,認就認了吧”,全然不知盜竊與詐騙在“數額較大”客觀方面的不同標準。雖然不懂法律并非排除犯罪理由,現行法律體系更不要求行為人對其行為是否涉嫌具體犯罪有明確認識,但總而言之,無論采納四要件說還是三階層說,行為人對涉嫌罪名的犯罪構成各方面的認識程度確實存在局限。在這種認識下,行為人所言的“認罪”就是認錯,自己做了錯事就應當承認、應當承擔。
(二)邏輯之二:表面認罪,實則認命
筆者自2012年8月從事檢察工作至今,共訊問各類案件犯罪嫌疑人近600人,從在看守所、訊問室與犯罪嫌疑人的親歷性接觸,筆者深刻體會到不同犯罪嫌疑人所持的不同心態。其中有一種貌似矛盾的說辭并不罕見:“進都進來了,我認,但你要說我真的做了嗎?我確實沒做……”。如果再次追問,往往都會馬上端正態度:“我認我認,就當我沒說過”——吊詭的是,此類案件往往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有罪判決并無障礙,畢竟從卷宗來看,都是板上釘釘的認罪鐵案。每當想到此,筆者總會感嘆:有的真相也許就是假象,有的假象也許就是真相;也許假象才會浮出水面,也許真相永遠沉沒水底……*實際上,這就是“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的區別。經筆者觀察,多數證據不足、處理不下去的案件,往往形成這樣的“邏輯悖論”:在案發一段時間后,面對靜態、冷冰冰的卷宗、材料時,以證據裁判規則為依據,綜合分析后確實是證據不足,多數公訴檢察官、法官持這種觀點;但如果在案發后第一時間就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接觸,在動態、活生生的人證之前,以內心自由判斷為依據,憑直覺就是這人干的,不少偵查人員、批捕檢察官持這種觀點。這絕不是簡單的有罪推定思維作祟,而是各方面因素所致,如證據制度等。筆者就多次遇到“盜竊人贓俱獲只是找不到被害人,認罪言之鑿鑿、就是無法處理”的情況,哪怕憑借自由心證“就是他干的”,也不得不“到點放人”。
一般而言,面對“認罪與否”的問題,會有三種回答:認罪、不認罪、不置可否(不予回答)。既然回答認罪,為何出現這種不干脆、很猶豫甚至有些模棱兩可的答復?常理上,做了就做了、沒做就沒做,要認就認、不認就不認,為何面對批捕檢察官會有所反復?要知道,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階段沒有獨立的偵查權,只有通過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被害人和證人、聽取辯護人意見等方式對提捕案件進行核實,審查逮捕階段的檢察訊問功能是核實偵查機關提捕的證據而非另行偵查。通常情況下,在審查逮捕檢察訊問時,若犯罪嫌疑人欲言又止,批捕檢察官往往會向其說明檢察機關的性質、闡明對公安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責。以筆者為例,此種情況往往告知“沒事,你有什么說什么,我們是檢察院的、是監督公安機關的”,試圖以此打消對方顧慮。當然,也有少部分犯罪嫌疑人在筆者解釋后表態“不認罪”,更多的認罪了事——這種認罪,實則認命。
犯罪嫌疑人的認命心態,在批捕階段中較為多發的“試探性翻供”也可窺見:先對偵查人員認罪,再對批捕檢察官翻供,又對偵查人員認罪。具體而言,在公安機關的提捕卷宗中,犯罪嫌疑人有二次以上的供述全部認罪,筆者去提訊時犯罪嫌疑人翻供,翻供理由往往既不是刑訊逼供也不是誘供騙供,而是當時亂說。在將疑問反饋給公安機關后,承辦民警再次前往看守所訊問并進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不少犯罪嫌疑人再次認罪并說自己對檢察官才是亂說或者狡辯。筆者一方面對承辦民警的訊問功力十分佩服,另一方面也對犯罪嫌疑人是否真的信口開河產生疑問。在詳細查閱同步錄音錄像的基礎上,若仍有懷疑就會再次前往看守所親自訊問——吊詭的是,再次檢察訊問的結果,就變成了認罪。筆者曾經懷疑,由于在看守所訊問室無法刑訊逼供,民警是否有過不當言論使得犯罪嫌疑人違心認罪?但再次訊問犯罪嫌疑人的過程表明,不少犯罪嫌疑人都是在審查逮捕的檢察訊問環節抱著“試探性翻供”的僥幸心理,即突然翻供可能不會逮捕,繼續認罪肯定就會逮捕,反正對批捕檢察官翻供不會產生任何不良后果,不如翻供試一試、搏一下;如果批捕,就在民警的逮捕訊問中繼續認罪,反正到了起訴、審判等后續階段認罪就是態度良好。可見,犯罪嫌疑人在審查逮捕檢察訊問階段的“試探性翻供”心態,說到底就是兩個字:搏命。
一言以蔽之:于人于己,認罪的“好處”太多了。如果說到案是偵查階段的開始標志,那么就絕大多數刑事案件而言,逮捕就是偵查階段的中心任務。很多情況下,“偵查人員甚至不需要采用刑訊逼供這樣極端的方法,就能做到迫使其作出虛假供述”*王敏遠:《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疑難問題研究》,《中國法學》2017年第1期。。即使個別在公安機關提捕之前辯解無罪、在審查逮捕檢察訊問時依舊不認罪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批準逮捕后的24小時訊問筆錄中,多數也轉為認罪。這既是逮捕制度異化出的定罪色彩所為,更是犯罪嫌疑人在被逮捕之后的認命思維所致:“連檢察院都逮捕我了,我能是無罪的嗎?我之前還能以一己之力對抗公安機關,現在還要再對抗檢察院,不是雞蛋碰石頭嗎?早知如此,不如認命,認罪態度好、還會少判。”畢竟,在我國不起訴率、無罪判決率極低的精密性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試圖以不認罪的答辯換來無罪處理的可能性極低,還會因為抗拒而被從嚴處理,此謂“抓都抓了,怎能不認”的認命邏輯。
五、警惕假認罪:確保認罪認罰的自愿性
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推進,辯訴交易制度正式進入了中國視野。正如孫長永教授提出“從實現刑事程序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學化著眼,我們應當珍視正當程序、拒絕答辯交易”*孫長永:《探索正當程序——比較刑事訴訟法專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545頁。,辯訴交易制度自誕生之日起就充滿了爭議。在認罪自愿性上,辯訴交易制度客觀上的威脅甚至逼供效應確實存在,某種程度上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潛在威脅成分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如果以不認罪的態度不接受辯訴交易,雖然有可能審判后被判無罪,達到“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的效果,但這種可能性極小,更大可能性是有罪判決且量刑遠大于認罪后答辯交易的量刑幅度。從這個層面來說,辯訴交易制度的不合理元素——對認罪自愿性的潛在逼供,是我國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需要極其警惕的。“為防止被告人在被脅迫或受利誘的情況下做出錯誤的認罪認罰,也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冤假錯案,有必要建立一種保障被告人認罪認罰自愿性的制度機制。”*陳瑞華:《“認罪認罰從寬”改革的理論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運行經驗的考察》,《當代法學》2016年第4期。
一是筑牢防線。在學界多年呼吁的法院直接制約偵查的司法審查機制尚未建立之際,為了防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偵查階段變異,有必要進一步強化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大到命案要案、小到輕微案件,以偵查監督為抓手,以審查逮捕為重點,筑牢嚴防假認罪的第一道防線,將訴訟效率僭越公平正義的潛在風險降到最低。面對提捕案件,既要運用口供補強規則,禁止以口供作為有罪與否的唯一判斷依據,綜合其他證據尤其是客觀性證據予以統籌判斷,更不可輕信偵查卷宗里白紙黑字的認罪筆錄,而要發揮司法的親歷性,堅持審查逮捕“每人必訊”,面對面核實犯罪嫌疑人認罪的自愿性、真實性,防止犯罪嫌疑人假認罪。正如“在王玉雷案中,正是檢察人員提審中的一句‘是你殺的也跑不了你,不是你殺的也冤枉不了你’,讓王玉雷徹底打消顧慮,推翻了在偵查階段被逼迫作出的供述”*卞建林:《發揮偵查監督職能,把好防范錯案關口》,《檢察日報》2015年6月17日。,一起可能冤錯的命案成功避免。
二是守住底線。嚴守司法作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以審判為中心、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夯實法院的居中裁判職能,既要堅持、完善當庭訊問被告人、被告人最后陳述等相關不可簡化的法定程序,也要創新性提出一些打消被告人顧慮的舉措。如開庭前,被告人被提押到法院后,在休息室內,由合議庭成員、法警與身著便服、去除戒具的被告人單獨見面,對其申明法院居中裁判的職能、公正司法的立場、“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理念,告知其在即將開始的庭審中認罪的后果、享有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出于誤解為威脅的考慮、不告知不認罪后果),以杜絕控方在場時可能發生的“之前對我們認罪、現在怎敢翻供”“以眼神相暗示、威脅”等認罪要求。
三是強化監督。“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試點經驗顯示,在看守所和法院分別設置法律援助律師值班室,使接受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能獲得法律援助律師的法律咨詢和其他法律幫助,這是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自愿性的關鍵制度安排。”*莊永廉:《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與程序完善》,《人民檢察》2016年第9期。借鑒美國辯訴交易制度中律師參與的做法,在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設計中,加大律師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的參與率,進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公職律師、值班律師制度,做到律師與犯罪嫌疑人在法律框架內一起商議、為其出謀劃策。“律師的角度和法官、公訴人是不一樣的,從被告人的角度,他可能更相信律師,相信律師是為他說話的,他更容易和律師講真話”*張軍,姜偉,田文昌:《新控辯審三人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89頁。。正如王敏遠研究員指出“認罪認罰的前提是自愿真實的,為了保障自愿和真實,就需要辯護律師的參與,在我看來,這是必不可少的底線”*王敏遠:《認罪認罰從寬改革不僅要“謀其利”還要“慮其害”》,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x?id=4979,訪問時間:2016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