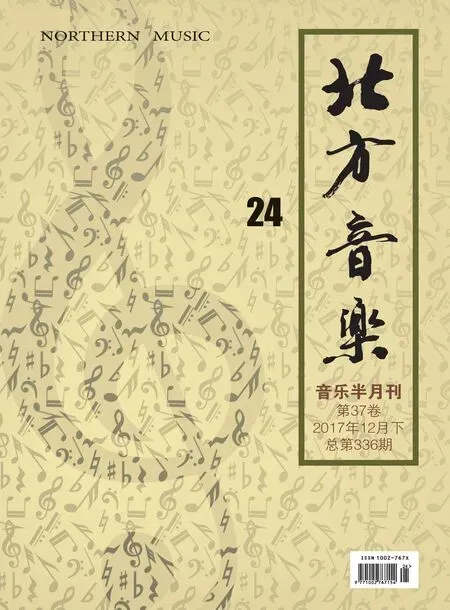土沃老花鼓舞臺化傳承思考
周 赟
( 山西大學音樂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不斷地加速發展,現代民間舞的生態環境有了很大變化,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對于民間舞形成了新的要求和新的審美觀念,受到這些方面影響,民間舞蹈的生存面臨著危機,很有可能即使挖掘、整理出來也沒有觀眾愿意買單,因為這樣的民間舞脫離了現代人們的生活。基于這樣的現狀,我們在做民間舞舞臺化的工作過程當中,不僅要考慮如何保留民間舞蹈的原貌,還要考慮怎樣才能符合當代人們的審美和思想等問題,這樣對民間舞蹈的舞臺化創作就增加了難度。
一、土沃老花鼓的基本概況
據傳承人講,土沃老花鼓最初是受到鳳陽花鼓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汲取本土文化茁壯成長起來的一種舞蹈藝術,到現在為止已經有360多年的歷史。土沃老花鼓歷史悠久,作為山西民間舞的一種,它的表演形式同樣獨具特色,它集“打、跳、唱”為一體,道具繁多,道具即樂器,樂器即道具。其中土沃老花鼓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小丑的口銜鼓,我們常見到的鼓多是綁在胸前、跨前或者放于舞者正對面的地上,比如稷山花鼓、踢鼓子秧歌、安塞腰鼓等,而土沃的老花鼓是唯一將鼓銜在嘴里進行表演的。這一點是一把雙刃劍,雖然獨特,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舞蹈動作的張力以及舒展程度。我們說要保護歷史傳統文化,但是不代表要全盤接受一成不變的東西。例如山西大學將左權的小花戲進行了藝術化傳承,在保留了其雙手扇的同時將很多民俗性動作進行提煉、創新、引入課堂。同樣,我們可以借助舞臺、燈光、音響以及改變口銜鼓的打擊方式來改善現存的問題,讓土沃老花鼓在保留自身特質的同時發揮其最大的藝術價值。
二、土沃老花鼓的物質構成
小丑是土沃老花鼓最有特點的人物,在表演中,小丑口銜“口銜鼓”穿行于整個表演隊伍中間,它所使用的“口銜鼓”,已經成為了演員肢體和五官的一種延伸,傳達著土沃人聰明、勤勞、富有創造力的特質。
小丑一的扮相是三花臉,黑色羅帽,帽邊扎有粗皮電線盤成的圓狀,再用黑綢纏繞的英雄圈。黑色夸衣,袖口處扎一寸寬天藍色綢。所用的道具口鼓用一節桐樹桿,將樹干的心挖空做鼓身,兩頭釘豬皮或羊皮做鼓面,在鼓腰的中端穿一鐵絲彎成環形,用紅綢纏緊做成口銜鼓。最初小丑的口銜鼓就是口銜鼓幫上的小環,后來經過四代傳承人的改良,會在上面裹紅綢來減緩牙齒的酸痛感。同時雙手各握一根用四根軟皮條編成長20厘米的軟鼓槌,槌頭挽有疙瘩,再用紅綠條纏繞,槌尾留綢帶。
口銜鼓的打法十分花哨,體現的就是土沃老花鼓的第一個“花”。主要動作有“單、雙點擊花”“單點交替擊花”“單、雙立圓擊花”“丹鶴前彈勢”“弓步打花勢”等。

以上這些元素只是以傳統民間舞蹈的方式進行呈現,動作、服飾單一粗糙,并不美觀。如果將土沃老花鼓搬上舞臺,勢必就要將它更深層次的內容以及相關的元素進行挖掘、提取、整理、創新。
三、老花鼓的舞臺編創
如果想要將土沃老花鼓引入舞臺,我們就要正視“民間舞”本身就是動態發展的這一現象,因為無論是跳民間舞的人還是編創民間舞的人都會受到現代意識的影響。人的思想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生變化的,人們更加追求個性、追求自我意識的抒發,而讓傳統的民間舞蹈進行舞臺創作,勢必會重重困難。
(一)整體風格把控
民族舞蹈有其民族的特性,同樣的民間舞蹈歸屬于民間地區,不同地域的民間舞蹈與生俱來也有其地域的獨特性,所以民間舞的舞臺創作首先離不開風格上的把控。而現代元素與現代意識隨著時代的變化,我們可以嘗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去融入、體現。所以土沃老花鼓的舞臺創作首先要注意的是風格上的把控,在合理把握風格的前提下嘗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去融入、體現現代元素,讓它更適合舞臺藝術。
(二)取其精華 提煉加工
土沃老花鼓傳承遇到瓶頸,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逐漸發展的現代意識與一成不變的傳統舞蹈格格不入,老生常談,如果全部拋棄從頭編創,就失去了民間舞的意義,但一成不變就勢必會造成斷代問題。山西民間舞蹈小花戲,其保留了山西民間舞蹈的哏、俏等特點,發揚只屬于山西民間舞的雙手扇,提取扭擺甩等經典動作加以改變。在音樂上選擇了經過加工后具有現代藝術氣息的民間音樂,通過改變節奏、詞曲等體現它的創新。不完成挖掘、收集、整理、分門別類、理論總結等工作,舞臺化民間舞蹈的結果就是沒有民族特色和個性,是不被觀眾認可的民間舞蹈。將元素提取進行創新后進入舞臺,還依然保留了原民間舞的大量素材及其文化內涵。并且在舞蹈作品中將動作、情感、人物性格的刻畫、主題、題材、體裁、結構等元素融為一體,使土沃老花鼓的藝術性得以提升。
四、土沃老花鼓舞臺傳承的意義
在城市化進程的背景下,對于民間舞的創作、現代的交匯,既要保留傳統意義的民間舞,也要融入時代意識才能讓民間舞有新時代的注解,在尊重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產生新的藝術表達,也讓更多活在當代的人更好地理解民間舞。老花鼓進入舞臺后,從一定程度上使它從民間的舞動達歡、通宵達旦、樂此不疲到有隊形、有結構、有時長限制的舞蹈作品,將功能由自娛表演轉向了藝術表現,帶來民間舞蹈另一種舞蹈形式的存在。這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也就是對老花鼓進行了傳承保護。
在中國和西方國家民間舞都經歷過從民間走向舞臺的過程。西方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進入當今舞臺,而中國將民間舞搬上舞臺也僅僅比西方晚了約10年左右。從這點來看我們已經有意識地將民間舞蹈傳遞在現代舞臺上,將這一傳遞方法作為傳承的有效手段,從根本上解決將土沃老花鼓難以傳承的難題,也進一步提高了土沃老花鼓的表演藝術檔次,使它能有一個長遠的發展和傳承,通過將它的優秀元素提煉、創新,可以增加它的“輻射面”,做到后繼有人。
文獻參考
[1]張晶.沁水土沃老花鼓的文化學思考[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S5):55-56.
[2]楊盼.論“口銜鼓舞”的表演形態及其教學價值[D].山西大學,2013.
[3]吳青瑤.民族民間舞限定下的舞臺創作[D].北京舞蹈學院,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