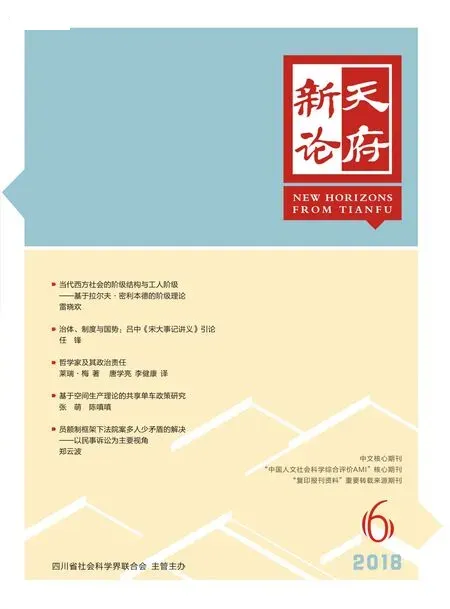延施與文明:《詩經·葛覃》析義
李 靜
畢達哥拉斯說這個世界有兩個本原, “一個產生了秩序、光明和男人的好本原,一個產生了混亂、黑暗和女人的壞本原。”①轉引自波伏娃:《第二性》,鄭克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頁。波伏娃引用這句話來證明女子不是與男性相區別的女性,而是被男性塑造的第二性。不管波伏娃對西方傳統的解讀中肯與否,但這用來解釋中國的男女,多半不恰切。與西方相似,中國傳統社會的女子也主要生活在家庭內部,然而中國的女子卻很難說是第二性。拋開某些陳陋的習俗,僅從經義上看,她們實實在在就是女性。這其中的關節,主要在中西方對家庭的看法差別太大。《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②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3頁。家庭是邦國的根本,齊家乃治國平天下的前提。要想齊好家,就得正心誠意以修身,男子如此,女子也如此。男子的修身古今談論很多,而女子當如何修身呢?對此,《葛覃》一詩給我們指明了方向。
一、《葛覃》中的延施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覃》是 《詩經》的第二篇,緊跟在 《關雎》之后。《關雎》以動物雎鳩鳥起興,《葛覃》以植物葛起興;雎鳩鳥一出場就在動,以 “關關”音聲相和,而葛一出場卻偏于靜,它在靜靜生長蔓延。同樣講齊家,《關雎》從君子的角度講夫婦之道,而 《葛覃》卻從淑女的角度談家庭之道。有夫婦才有家,有家才有邦國天下,而要成就一對好夫婦,女子就得先長成,而且是好好地長成。
《葛覃》以葛起興。葛并非什么難得之物,南方的山谷中、樹叢中常常可以見到。葛既常見也很實用,葛的莖可以用來制鞋做衣,葛葉可以入藥,葛根既可食用也可藥用。《葛覃》以葛起興不只是因為它實用,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的生長習性特別。葛為藤本植物,莖細長而不能直立,只能依附他者蔓延開來。覃者延也,葛在幽靜的谷中靜靜地生長,莖蔓延得廣遠,葛葉繁盛。在葛靜靜生長之時,黃鳥飛來了,駐足在灌木叢上,“喈喈”地叫著。葛的蔓延安安靜靜,黃鳥又飛又鳴,驚動了這種安靜,葛勢必要 “抬頭”看看那音聲相合的黃鳥。葛的鮮綠,黃鳥的鮮黃,葛的靜,黃鳥的動,構成了一幅鮮亮的畫面。
“葛之覃兮”,或為賦,或為興。若如朱熹所言為賦,此章便是一個女子追溯她幼時在父母之家所看到的情景①朱熹:《詩集傳》,中華書局,2011年,第4頁。;若如毛傳所說為興,那么此章便重在以葛之蔓延起興女子的成長②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17頁,第18-19頁,第20頁。。葛為女子專有之事,所以無論是賦還是興,講葛的蔓延總離不開談女子。葛長得正好時,黃鳥來了,它飛來干什么呢?《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黃鳥好像很會找地方駐足。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5頁。為人君為人臣,為人父為人子,甚至與國人交都有所 “止”。然而,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應該如何 “止”?黃鳥為 “應節趨時”之鳥,每當麥子黃了、桑葚熟了,便會來到麥地桑間。葛在谷中靜靜地生長,女子在父母之家漸漸長大,這時黃鳥飛來了。魯說曰: “葛覃,恐其失時。”黃鳥 “應節趨時”,似乎在暗示,女子也當 “應節趨時”。葛順從自然之性,從此地蔓延到彼處,黃鳥飛來,提醒女子,當像葛一樣適時順性蔓延出去。
除了 “應節趨時”的特性外,黃鳥的形貌也很特別。此鳥又名離黃,“其色黎黑而黃”,“其為鳥柔易而近人,其頸端有細毛雜色”,有 “文”貌。④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17頁,第18-19頁,第20頁。黃鳥 “黎黑而黃”而非周身遍黃,有雜色便意味著鮮明的紋理,不是普遍同質。有文便有差別,就需要從此處延伸到彼處。如同黃鳥的 “文貌”,女子長大之后,就得離開父母之家,出嫁到夫家。葛與黃鳥,葛與女子,黃鳥與女子,就這般勾連在一起。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毛傳言 “萋萋”為 “茂盛貌”, “莫莫”為 “成就之貌”,鄭箋解 “成就”為 “可采用之時”。朱子進一步解釋首章為初夏,次章為盛夏之時。無論哪家,都以 “莫莫”為 “萋萋”的發展,以次章為首章的遞進。葛在此已經長成,可以為人采用,女子也的確適時地取來煮了,分別制成粗葛布細葛布,最后加工做成衣服。無論是葛之賦還是葛之起興,最終都要說女子。葛成熟了要適時地為人采用,女子成熟了也要順其自然、合其目的。此詩首章談女子在父母之家成長,睹物思人,以蔓延的葛和有文的黃鳥相提醒,女子依自然性情需得及時出嫁蔓延出去;此章女子如 “莫莫”之葛,成熟了便出嫁了。
關于本章的理解,諸家分歧較大,究其緣由,主要是對 “服”的理解不一樣。毛傳曰:“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鄭箋進一步解釋:“服者,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來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⑤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17頁,第18-19頁,第20頁。毛傳以 “服”為 “穿衣”,鄭箋直接解為 “整治”,毛傳認為女子采葛練習做衣服是給未來丈夫穿,鄭箋認為女子只是在預先學習女功,反復練習不厭倦。二者都認為這是女子在父母家練習女功的畫面。而三家詩卻認為本章在寫女子出嫁后實實在在為丈夫做衣服的情景。丈夫穿著女子親手做的衣服,“服之無斁”。朱子或許也看到毛傳與鄭箋的解讀有些牽強,所以他直接將此解釋為后妃出嫁后仍不辭勞苦采葛為自己做衣服,知道自己勞作的艱辛,所以她們穿著自己做的衣服無所厭倦。“服”字的解釋不同,此章的整體意蘊就會大有分別。如若是后妃在預先練習制作衣服給未來的丈夫,此章便只是未出嫁的女子在辛勤練習女功。《葛覃》首章以葛的靜靜蔓延起興女子在父母之家長大,此章葛成熟了都被采摘做成衣服了,女子若還在父母之家,延施二字便沒法展開,立意便不如三家詩了。更恰當的理解似乎是,《葛覃》從葛的延施特性出發,首章女子在父母之家培養德性漸漸長大,準備及時出嫁;次章女子已嫁為人婦,為丈夫辛勞做衣,丈夫服之無厭,最終達至夫婦和順。葛為女子所用,女子辛勤為夫家操持,葛與女子各順其性。
二、女子的二歸之道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葛覃》的第三章不見了 “葛”,又新出現了兩個人:師氏和父母。 《葛覃》全篇的安排與葛的蔓延一樣,是在逐步展開。首章只有葛和黃鳥,明里沒提到人,卻又暗示著女子的存在;次章沒了黃鳥卻仍有葛,明里談的是 “是刈是濩,為絺為綌”的女子,暗里卻又提到了另一個人:“服之無斁”的丈夫;末章沒了葛,沒了動物也沒了植物,只有人,而且還是兩位長輩。
女子出嫁,為夫家操持家務,這并不是女子生命的全部。嫁出去的女子并不是潑出去的水,她總在念著父母之家。女子告訴女師她該回家探望父母了,得到肯定回答后,女子便把休閑衣服都拿出來,看看哪些臟了哪些需要清洗,洗好了衣服,整齊了儀容,便回娘家問候父母去了。
此章出現了兩個 “歸”字:“歸”與 “歸寧”。諸家對 “歸寧”的解釋一致,而對 “歸”的看法卻大相徑庭。依著毛傳的解釋,次章還在父母之家學習女功之事,那么末章的這個 “歸”便是 “女子出嫁曰歸”的 “歸”。經過首章的鋪墊和次章的勞作,女子在末章終于出嫁了。出嫁之后,她在夫家仍舊如同在父母之家一樣辛勤勞作,忙著 “澣我衣”,清洗自己的私服。鄭箋解釋此章 “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女子的辛勤勞作才是持家的常道。據此,前一個 “歸”為 “出嫁”,末了便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 “歸寧父母”,沒有任何鋪陳。如此解釋,《葛覃》的延施便會顯得過于倉促。若按三家詩,節奏就明朗多了。這里的兩個 “歸”同在一章,不必強做區分,都是 “歸寧”之歸。次章女子出嫁,末章女子歸寧,節奏十分明晰。將心比心,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也同樣可以想象,女子要回娘家了,總是會先洗漱打扮一番,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自己的父母,表示自己在夫家過得好,讓他們安心。寧者安也,歸寧父母便是要讓父母安心。
《葛覃》共三章,首章在父母之家,次章出嫁到夫家,末章又從夫家返回到父母之家。此間,我們看到了女子的 “二歸之道”。《春秋》:“隱公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何紹公注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①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5頁。父母之家與夫家,出嫁與歸寧,便是女子一生的所有路程。
在 《葛覃》的前兩章,葛的出現都十分耀眼,到了末章,葛卻不見了。從表面上看,葛的延施從此處到彼處,女子從父母之家出嫁到夫家,就已經完成了任務。然而,葛蔓延出去卻不是終結,它還需要回到根本,否則就真成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葛的莖葉在谷中蔓延,這延施的力量來自葛根。葛莖細而長,葛根卻粗而壯。有了粗壯厚重的葛根,才有葛莖的廣闊蔓延,葛根有多厚重,葛莖的蔓延就有多廣闊。《葛覃》的第三章明里沒有葛,實際卻有葛。女子的出嫁如同葛莖的蔓延,是順性而為,女子是一條緯線,可以廣闊蔓延,然而蔓延的根本力量卻來自父母之家。如同葛莖的蔓延、葛葉的繁盛需要葛根的滋養,女子的出嫁、女子在夫家的榮辱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父母之家的給養。當然,這種給養除了有形的物質,更多則體現為一種精神力,體現為父母之家對女子德性的培養。毛傳解 《葛覃》曰:“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②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16頁。毛傳認為首章、次章都是女子在父母之家從事女功勞事,最后一章出現的兩個長輩 “師氏”、 “父母”,為的是卒章顯志。這樣 《葛覃》全篇的重量就落在了 “父母之家”上,“重本”也就變成了 “重父母之家”。
《葛覃》的確講女子要 “重本”,但要明晰地理解這個 “本”卻不那么容易。《左傳》里講了一個故事,桓公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可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 ‘謀及婦人,宜其死也。’”①劉勛:《春秋左傳精讀》,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168頁。在丈夫與父親的生死之間,雍姬選擇了父親,這是否就是重本?鄭厲公把雍糾的慘死追究為 “謀及婦人”,實際上,婦人并非不可與謀,關鍵是與什么樣的婦人謀。雍姬的選擇主要受其母親的影響,看來女子的根本很可能在父母之家。葛以根支撐莖葉的蔓延,父母之家靠什么來支撐起女子的延施呢?不難看到,在 《葛覃》中,父母之家對女子的教誨主要集中在女功上。
與 《關雎》中的 “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不同,《葛覃》通篇都充滿了辛勤的勞作。“是刈是濩,為絺為綌”,雖身在富貴,卻要親手去采葛來織布做衣,“薄汙我私,薄澣我衣”,雖身份尊貴,卻需親手洗衣清潔。葛之莖 “覃兮”,葛之葉 “萋萋”,如此廣闊茂盛之葛為的是給人采用。葛之性何其無私。女子在父母之家勤學女功,出嫁后辛勤勞作以事人,歸寧又以孝道安寧父母,與葛一樣無私。朱子曰:“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于此可見其己貴而能勤,己富而能儉,己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②朱熹:《詩集傳》,中華書局,2011年,第4頁。《葛覃》里的女子有勤儉之德,有敬孝之德,這些德性大都建立在勞作的基礎之上。在現代社會,勞動成了普遍勞動,也大多變成了異化勞動。在這樣的勞動中,人大多只感覺到艱辛與痛苦,很少能體驗到快樂,更不用說從中養成德性。然而,《葛覃》中的勞作卻很難說成是艱辛,因為其間總是伴著歡樂,而且,它還能培養出女子特有的德性。
王夫之在 《詩廣傳》中說:“《葛覃》,勞事也。黃鳥之飛鳴集止,初終寓目而不遺,俯仰以樂天物,無惉滯焉,則刈濩絺綌之勞,亦天物也,無殊乎黃鳥之寓目也。以絺以綌而有余力, ‘害澣害否’而有余心,‘歸寧父母’而有余道。故詩者所以盪滌惉滯而安天下于有余者也。‘正墻面而立’者,其無余之謂乎!”③王夫之:《詩廣傳》,中華書局,1964年,第3頁。王夫之由黃鳥而生出了別樣的理解。葛在谷中靜靜生長,黃鳥駐足于灌木叢上,看著女子辛勤勞作,而女子在勞作間不時俯仰,看看飛鳴集止的黃鳥,于是勞作的艱辛便消解了。這就是 “有余”。我們現在常常把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對立起來,為了追求自由時間,去努力減少甚至消解勞動時間,以為這樣才能達到人的自由狀態。殊不知, “有余”源于人心,有 “余情”、“余心”自然就有余力,有余力才會真正有余暇。心有余暇,勞作自然就有余力,有余力人就會有歡樂,自然也就不會生出愁苦惉滯的情緒。也只有如此,才能避免 “正墻面而立”的壓迫和緊張。《坤》之六二曰: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④來知德:《周易集注》,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39頁。坤德在內為直,在外為方,內中正而外柔順,自然就“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女子常常勞于家務,家務又多繁瑣細碎,便很容易走向 “無余”的緊張境地。女子若勞心竭力于細務,身心操持于瑣碎繁雜,看不到心中的 “黃鳥”,長此以往,她的視野就會變得越來越窄,最后只能 “正墻面而立”,變成要么喋喋不休地抱怨,要么如奴仆般無原則地順從。無論成為哪一種,都不過是惉滯與心塞。女子通常被指責為眼界小、氣量小,原因多半在此。因而,女子對待 “絺綌煩辱之事”尤其需要心有余暇,只有培養出 “余心”,才會在勞作中蕩除惉滯之情,才會 “安于所事之中,余于所事之外”。不必徒勞地在勞作之外另求閑暇,因為閑暇始終在勞作之中。有余心的女子自然會內直外方,自然會 “大”得蕩滌愁悶與惉滯。如此 “直方大”的女子去齊家自然不在話下,她會給父母之家和夫家都帶去歡樂。 《葛覃》首章的黃鳥,次章的 “服之無斁”,末章的 “歸寧父母”,都是 “樂”的表現。心有余,勞作自然有歡樂,女子在勞作中培養出了坤德,自然有求就有應。因著這樣的德性,丈夫會穿著她辛苦做成的衣服無所厭倦,夫婦因而和順;父母也會因為她的歸寧心有所安,真正達至歸 “安”父母。夫家與父母之家,都在余心余暇中得到安定。《葛覃》中處處充滿了女功和勞作,卻又處處飽含著歡樂的回饋。樸實無華的 《葛覃》,卻生出了最壯麗的文采,女子的二歸之道因著這樣的文采而得到了詳盡表達。
三、異質與文明
《葛覃》既講 “及時”也講 “重本”。及時出嫁延施出去是女子的自然天性,出嫁后,女子的生活重心自然挪到夫家,這也就是三家詩強調 “及時”的原因。然而,嫁到夫家并不意味著切斷與父母之家的聯系,葛的蔓延始終都要依靠葛根的支持。在 《蝃蝀》里,女子愁嫁與人淫奔,延施出去卻忘了本,切斷了與父母之家的聯系,真正是 “遠父母兄弟”。而 《泉水》和 《載馳》,無論是思歸寧還是真歸寧,都得到了君子的贊美。
《葛覃》重本,重父母之家的教導培養。只有在父母之家養成了 “直方大”的德性,延施出去才可能出現 《關雎》的琴瑟鼓鐘之樂。葛以根滋養著莖葉的蔓延,父母之家以德性給養著女子的延施。只有重本,延施才能開出更燦爛的花來。雍姬母女的不智之舉,恰是不重本,沒能在父母之家培養好女子的德性。而缺失德性的女子延施出去,只會把禍患蔓延出去。延施的力量因著父母之家這個根本變得可好可壞。
《葛覃》講 “二歸之道”,講 “延施”與 “重本”,都是在順女子之性,其中延施是目的,重本則為基礎,延施是文,重本是質。“二歸之道”表達了兩個方向:一個朝向父母之家,朝向過去;一個朝向夫家,朝向未來。女子的一生總是在父母與夫家、過去與未來間穿梭。然而,這兩個方向從一開始就分別了主從。沒有延施,女子便永遠無法走出父母之家,去表達她的珍貴,而如果只有延施而不思本,她又成了沒有根的葛。在西方,女性出嫁后就丟掉了父母之家的姓氏,完全隨了夫姓。這在我們看來實在難以理解,因為沒了根,也就沒了 “本”,蔓延也便談不上了。延施和重本,構成一組有主有從又相伴相生的關系。女子的 “二歸之道”,延施與重本,一為 “東北喪朋”,一為 “西南得朋”。①來 知德:《周易集注》,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6-23頁。走出父母之家,從表面上看是 “喪朋”,實際上卻是以生育的方式開啟了新的人類文明;留在父母之家,雖有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護佑,卻沒法由內而外,去開拓更廣闊的天地。留在父母之家,是在保持同一性;走出父母之家,延施到夫家,是在建立異質性,是在開拓新的 “文貌”。
延施或異質性在中國宗法社會最直接體現為 “同姓不婚”。《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為何要 “合二姓之好”?合同姓之好親上加親豈不更好? 《左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②劉勛:《春秋左傳精讀》,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440頁。看來古人早就看到近親結婚會影響后代,然而如果僅僅是為了“其生不蕃”,大可籠統規定幾代血親內禁止通婚,如此便可一網打盡,避免生物學上的近親繁殖。《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無禮的禽獸可以父子聚麀,人若不自比禽獸便得循禮。看來同姓不婚的背后道理極深,它講述了一個從叢林狀態走向文明狀態的過程,它能把人從動物中分離出來,避免人墮落為野獸。
《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傳》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解詁曰: “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 ‘吳孟子’。《春秋》不系吳者,禮,婦人系姓不系國,雖不諱,猶不系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葬,深諱之。”①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77-1178頁,第1178頁。無論是 《禮記》還是 《春秋》,都說同姓不婚是人區別于禽獸的大倫,是人類走向禮法文明的重要一步,但要邁出這一步,著實不易。
對禽獸而言,既談不上父子,也談不上夫婦。禽獸的繁殖只需雄性與雌性的隨意結合,所以它們可以 “父子聚麀”,共用同一個雌性。由 “父子聚麀”而生的下一代也不必分清是父子父女還是兄弟姐妹,它們的世界只有雄性與雌性的差別,不必有倫理來分殊上下左右。甚至,許多植物和動物連雄性雌性之分都可以不談,它們自己就是雌雄同體,可以同性繁殖或者自我繁殖。然而,對于人來說,不分清男女,不分清父子,根本就沒辦法生活,更不用說組成人類共同體。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人們很早便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索福克勒斯的 《俄狄浦斯王》里,俄狄浦斯一出生就被預言會殺父娶母,他的父親丟棄他,他自己也千方百計想擺脫那個神諭,然而機緣巧合他最終還是應了殺父娶母的預言。俄狄浦斯娶了母親,成了 “父子聚麀”,一雙子女既是他的弟妹,也是他的兒女。作為一個人,俄狄浦斯沒法接受這樣的命運,也沒法繼續在人類社會中生活下去,所以他只能刺瞎雙眼自我放逐。人類要組成社會,建立共同體,必定得有人倫,而最基本的人倫就是夫婦、父子和兄弟。要保住父子和兄弟關系就必須建立穩定的家庭,使男子和女子過穩定的婚姻生活。而要讓男女過上穩定的婚姻家庭生活,就必須定下標準來嚴格分別男女。要分別男女,最簡單有效的方式就是同姓不婚。
在同姓不婚的規范之下,一個家庭里除了祖母、母親不同姓,其他父子叔伯兄弟姐妹全是同姓。以姓來辨別男女和親親,簡單而易行。除了明面上的男女不同姓,同姓不婚其實一開始就暗含著另一個前提:女道外成。如果沒有女道外成,男女就談不上實質上的分別,即便不同姓,血親姻親不做分別,籠統住在一起,也終究沒法避免 “父子聚麀”的危險。只有男女異姓外加女道外成,才可以保證婚姻生活的穩定,夫婦固定了,父子關系、兄弟關系也就固定了,相應地,其他各種人倫也才能穩定下來。所以,同姓不婚首先是對父子兄弟的保護,是對宗法社會里作為經線的血緣親親的保護。《昏義》云:“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②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第1418頁。同姓不婚實在是人類文明的根基。
對于現代女性主義者而言,講男女有別和女道外成似乎顯得不合時宜。殊不知,同姓不婚一開始也是對女子的保護。在建立人倫之前,人類社會 (其實還不算人類社會)男女不別、父子聚麀、兄弟相爭。沒有人倫的社會就是霍布斯筆下的戰爭狀態。在戰爭狀態里,男女結合的法則只能是叢林法則,男性由于體力上的自然優勢,很容易勝過相對弱勢的女性,男女的結合因而多半是力量對比的結果。在叢林法則下,可以想象大多數女性的生活實際會更差,她們既沒有固定的男性伴侶,也沒有婚姻家庭可以庇護,弱肉強食之下很難保證基本安全。因此,鑒于女性在體力上的劣勢,外加生育的自然限制,在同姓不婚的法則下,只能女道外成。
同姓不婚既保證了男女的分別,也保證了父子的親親,它一邊穩固著父子兄弟的血緣關系,一邊也保護著女子不受強力欺凌。它將父子的經線和夫婦的緯線串聯起來,組建成一個有序的共同體。中國的宗法制度包含著同質與異質兩種關系,它的內里既有血緣的親親也有非血緣的結合。父子的血緣關系嚴格來說只是一種同質關系,它沒法產生新東西,而夫婦的非血緣結合則是一種異質性的關系,它將兩個不同姓的人結合在一起,通過婚姻生育可以締造出新的人倫關系。異質產生文明。
在夫婦的異質性關系中,女道外成是關鍵。女子在父母之家長成,然后延施到夫家,這就是女道外成。延施給同質性的血緣親親關系注入新的活力,從而創造文明。向外延施可以締造文明,向外的動力卻由始至終來自父母之家。在 《公羊傳》的 “諱取同姓”之下,徐彥疏曰:“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③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77-1178頁,第1178頁。中國的女子即便婚后也不改姓,除了方便識別她的姓,顯示 “不適同姓”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 “不忘本”。女子只有不改姓,才能保住她的根。不管女子延施多遠,她的根始終是她向外擴展的源泉,她在夫家的一切作為都將影響到父母之家,她在夫家的所有榮辱也會影響父母之家的榮辱。只有意識到這一點,她才會在夫家盡心輔助丈夫齊家,為夫家的繁榮而努力。“人盡可夫,父一而已”,雍姬母親的說法只是一種同質性的表達,雍姬其實從來沒有延施出去,也便談不上重本。而魯昭公一生,總是在 “犯大禮而取同姓”①蘇 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8-9頁。,娶同姓便注定開不出異質性,所以最后落得個 “身死子危”的下場。
同姓不婚保證了延施的異質性,保證了人類文明的延續。然而,延施并不只是女子外嫁、與夫家共同生活那么簡單,它內里還包含著德性的延施。《葛覃》中的女子在父母之家養成好德性,在勞作與余心中保持中道,修身的功夫好了延施到夫家,才可能幫助丈夫齊家,輔助丈夫治國平天下。這樣的女子既能避免 “龍戰于野”,也可免于 “以順為正的妾婦之道”②姚永概:《孟子講義》,黃山書社,1999年,第97頁。。能在煩辱的勞作中保持余心余力,也便能在夫婦生活中保持中道。很多女子的婚姻生活要么充滿喋喋不休的抱怨,要么就只能是奴仆似的順從。殊不知,《理想國》里,那最佳政制走向衰敗,最開始就是源自一個母親對父親的抱怨;殊不知,莎士比亞的 《馴悍記》里,那個把妻子馴服得違背理性跟著他說 “太陽從西邊升起”的丈夫,自己也因為妻子的奴性變成了 “崟岑絕人”的丈夫,從而失掉了創造異質文明的可能。
延施,在傳統宗法社會主要表現為同姓不婚、女道外成,在現代社會它更是延及同性婚姻是否正當等新問題。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延施,是締造文明的根基、延續文明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