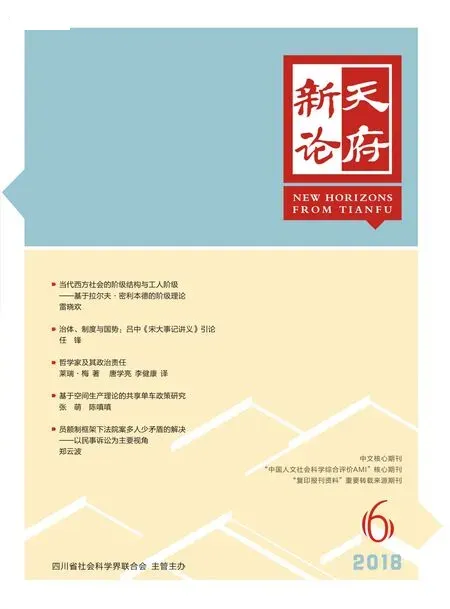商品價值范疇內涵新探
宋愛忠
勞動價值論作為揭示資本主義經濟迷宮的 “阿里阿德涅線”——剩余價值理論——的核心基點,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曼德爾指出:“沒有勞動價值論,便沒有剩余價值理論,也沒有辦法把利潤、利息、地租歸到唯一的根源上來”①曼德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下)》,廉佩直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53頁。,從而,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必將陷入含混不明的淵藪。因關乎兩種經濟理論之命脈,百年來圍繞勞動價值論的學術爭論之激烈,亙古未有。交鋒結果卻是:在國外,即便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亦是 “沒有勞動價值論的馬克思經濟學”盛行②阿蘭·弗里曼:《沒有馬克思經濟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沒有壯大起來?》,《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1期。;在國內,勞動價值論肯定派內部 “爭論紛紜”而西方經濟學卻聲名顯赫。實言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面臨著 “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
在外部,西方經濟學秉承卡爾·波蘭尼 (Karl Polanyi)所批判的經濟之 “形式”概念③指僅囿于經濟學科從 “從邏輯關系上來定義和把握人類的種種經濟活動。”但經濟實際是 “經驗性的”,是豐富的 “人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之間變換或交換。”詳參:栗本慎一郎:《經濟人類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42-44頁。,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似乎實現了基于數理主義語境下的 “證偽”。面對薩繆爾森對 “價值轉形”技術困境的 “揭批”、瓊·羅賓遜對價值范疇形而上學性的指摘等西方經濟學步步緊逼的技術性挑戰①參見其流布甚廣的文字:“熟視兩個互換而又不相協調的系統。寫下其中的一個。用擦子將它抹去,以進行轉化。然后填入另一個。瞧!你已經完成了你的轉化算式。”Paul A.Samuelson,“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A Summary of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p.400.瓊·羅賓遜則認為,“我們無法采用簡單地計算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小時的總和的方法,估算出一年之內生產出的商品的總價值”,故 “價值仍然沒有實際內容,價值不過是一個詞而已。”瓊·羅賓遜:《經濟哲學》,安佳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8-53頁。,勞動價值論肯定論沒看到勞動價值論的 “社會理論屬性”和 “技術規范屬性”之間張力的原在性,又把兩者真值邏輯混為一談,更多的是套用 “現象學”歸屬的實證主義真值邏輯去評判 “本質論”歸屬的勞動價值論的真值邏輯,在技術主義話語層面必然陷于疲于應對的窘地。在內部,勞動價值論肯定論又呈現另一種吊詭:一方面,具體問題爭論周期性重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學界在總體肯定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各種具體問題的爭論大的就有五次②張萬余:《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歷史爭論與現實擴展》,《甘肅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小的爭論一直未停。所涉及問題廣泛而深刻。另一方面,這些爭論卻對問題產生的理論前提和地基—— “商品價值”范疇的本質性涵義及其重大分歧——懸置不談。殊不知,具體問題爭論的周期性爆發昭示的常是根本矛盾病灶的隱而不彰。這個病灶正是商品價值范疇核心涵義的含混不清。
因此,揭批數理主義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證偽”的邏輯,呼喚著對商品價值概念的再澄明。只有立基于該范疇科學性內涵,才能充分展示勞動價值論作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真值屬性;消弭勞動價值論肯定派內部的諸多齟齬與抵牾,需要對商品價值概念的迷誤再去蔽。不闡明指涉物的本質性內涵去探討關涉該物諸種具體問題的真理性,注定會陷入迷霧與混亂。這要求我們對勞動價值論給予“本體論”意義上的理論充盈與合理重塑③特 別指出:本文 “本體論”非指形而上學之 “終極真理”,只是 “理論研究把握世界的一種認識論范式和據點”。詳見本文“二、 (一) ”。,以形成統一的、整合的、發展的新解釋。
一、內在張力: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兩種理解范式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首先構筑于 “商品價值”范疇之上。然而,確如李嘉圖所感慨:“在這門學科中,造成錯誤和分歧意見最多的,莫過于有關價值一詞的含糊觀念。”④李嘉圖:《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9頁。在 《資本論》中,經典作家亦沒有對其做出本體論意義上的厘定。對原著文本進行深層耕犁,我們發現,“商品價值”范疇凸顯出兩種涵義異質、內含張力的思想規定。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兩種理解范式
1.價值實體論
此種思想規定把商品價值本體歸結為一種物質性的實體范疇,即人的活勞動耗費。馬克思的文本指出,價值可 “純粹歸結為勞動量……價值本身除了勞動本身沒有任何別的 ‘物質’”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頁。, “價值實體不外是而且始終不外是已經耗費的勞動力,而價值生產不外就是這種耗費過程。”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8頁。就價值多少的判定而言,“價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頁。這些經典表述使我們不難得出 “勞動耗費=價值”、“勞動耗費量=價值量”的公式。意即,活勞動耗費與價值是完全等同性而非對應性范疇,二者同生共死且可互代互換。肯定論學者大抵認同價值本體之實體論內涵,并將其作為具體問題的立論之基。蔣學模教授編著的流傳甚廣的教科書定義是實體論觀點的明確和經典表述:“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①蔣學模:《政治經濟學教材 (第13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頁。更有學者對此進行深入加固論證,認為,由于 “與平均勞動消耗是對應關系的價值既不能被人感知,其存在和大小也不能被人所證明,那么我們可以說與平均勞動消耗是對應關系的價值是不存在的”,因此,“價值就是平均勞動消耗本身,所謂勞動產品中的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正是凝結了平均勞動消耗本身,除此外不會有任何其他的東西”②靳毅民:《勞動價值論的新認識》,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3-41頁。。樊綱教授也斷言:“勞動價值論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將勞動視為商品的內在屬性,是將勞動確認為價值的物質內涵”③樊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三聯書店,1990年,第172頁。
2.價值關系論
與價值實體論范式的理解相反,價值關系論對經典文本做出了另樣解讀。馬克思指出: “勞動……不是作為價值本身,而是作為價值的活的源泉存在。”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3頁。在劃清勞動與價值的界限后,經典作家把價值歸結為一種經濟交換關系:“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代表人們在其生產活動中的關系。…… ‘價值’的概念的確是以產品的 ‘交換’為前提的。在共同勞動的條件下,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關系就不表現為 ‘物’的 ‘價值’。產品作為商品的交換,是勞動的交換以及每個人的勞動對其他人的勞動的依存性的一定形式。”并且明確反對把 “價值變為某種絕對的東西,變為 ‘物的屬性’,而不是把它僅僅看成某種相對的東西,看成物和社會勞動的關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社會勞動的關系。”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第三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8-139頁。而 “商品的價值的大小……是由耗費于、體現于、凝固于該商品中的相應的勞動數量或勞動量決定。”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頁。價值關系論者認為,這些論述可總結為三點:其一,價值在本體論上是人們之間交換經濟成果的關系;其二,價值與勞動耗費之間是測量與被測量關系,猶如身高和米;其三,價值和勞動耗費是一種對應性關系而非等同性關系。這就把商品價值為的本體論內涵歸結為另一種物質性范疇——人的勞動交換關系。據此,價值關系論認定價值非某物 (比如勞動)的實體受創物,“商品中并不物理地存在著 ‘價值’,‘價值’只是人們將社會關系賦予它的”⑦魯品越:《價值新概念與唯物史觀新境界》,《西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7期。。作為一種衡量交換價值 (關系)的范疇,說勞動創造交換價值 “是一種合成謬誤,是典型的語言學和語義學上的錯誤。”⑧李克洲:《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3頁。價值關系論認為,商品交換的本質是勞動交換,“商品價值不是單方面確定的先驗的實體,而是不同主體之間交換勞動的關系,只存在于商品交換之中,可以用社會勞動量 (有效勞動量)來評定或表現。要確立勞動表現為商品價值的科學提法,擯棄勞動 ‘創造’價值的不科學說法。”⑨鄭怡然:《發展勞動價值論的另類思維》,《江漢論壇》2012年第7期。
經典文本中的上述情況似乎表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內部存在著某種巨大的張力與分裂。
(二)兩種理解范式的內在統一性
然而,只要眼光中正和不激不隨,可知勞動價值論的統一性本質意涵本是經典作家文本中隱含的理論預設。因為,在確定客觀情境下,一事物的本體論內涵不可能有二,任何針對該事物具體問題的討論與推演均須以此為前提。無視勞動價值論內涵的本體統一性而對前述兩種價值內涵的單方強調,均會產生各自解釋中的邏輯缺環。
1.價值實體論的 “硬傷”
價值實體論的 “硬傷”主要有三:其一,實體論對 “勞動”一維的極化強調,使發生于生產領域的勞動成為必然關涉生產和交換兩個領域的事物的本體,在實踐和理論層面均難以自洽自證。晏智杰教授正是針對實體論此弱點,認定勞動價值論的缺陷之一 “表現在它與市場價格論 (供求關系決定,筆者注)的脫節,因為它不足以說明市場價格的各種決定要素及其變動的普遍規律,商品價格僅僅由勞動這一個要素決定畢竟只是一種特例,而不可能是通則。”①晏智杰:《勞動價值論:反思與爭論》,《經濟評論》2004年第3期。其二,實體論把價值歸結為實體范疇而非關系范疇與事實不符。因為價值并非某種物的內在固有事實屬性,而必然是一種關系屬性。實體論源于無法忽視交換關系維度而對其所做的部分承認,又僅把它定位于勞動價值論的必要補充而非本體論范疇之內,這種理解路向在實踐中悖逆了價值根源于商品承載的主客關系向主體間關系轉化的基本事實。馬克思早有確言:“任何生產者,不管是從事工業,還是從事農業,孤立地看,都不生產價值和商品。他的產品只有在一定的社會聯系中才成為價值和商品。”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9頁。其三,在學理上更致命的是,價值實體論難以回答勞動永存而價值卻趨亡的詰問,往往倒果為因地用商品消亡導致價值消亡應付了事。但與之恰恰相反,商品消亡不是價值消亡的原因而是結果。基于 “等同性”理解,實體論無法想象勞動和價值間的張力與分離性,機械地把勞動與價值進而與勞動時間無縫隙永久綁定甚至融合,從而陷入了既承認二者為同一物又不承認其中一個為多余物的邏輯悖論。
2.價值關系論的窘況
價值關系論亦窘況環生。其一,現實中把交換關系做價值范疇的本體定位,使勞動價值論極易滑向供求決定論,從而與否定論陣營只有一步之遙。供求當然是一種交換關系,但把供需關系歸結為決定商品價值從而價格的唯一因素則是對價值的關系屬性做了機械、直觀和淺化強調。有供求決定論傾向的關系論盡管也承認 “勞動”的作用,但和實體論看視 “交換”作用的做法相似,只是把勞動當作價值不可或缺的表現物和基礎,而非本體或本質因素。其二,把關系作為商品價值本體,混淆了邏輯學的概念 “下屬關系”與 “全同關系”范疇③金岳霖:《形式邏輯》,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37頁。。商品價值是一種關系,“商品價值”與 “關系”有下屬關系,但并不能因此把關系一般定義為商品價值這種具體范疇的本體,從而把 “商品價值”與“關系”變為全同關系。猶如夫妻是一種關系,但非所有關系都是夫妻。其三,在學理層面,以關系為本體必難以闡明價值量的衡量與變動問題。從價值歸屬交換關系范疇的質的規定性無法推導出其量的大小,在無法揭示價值范疇中勞動和交換的實質關系的同時,又看不清 “交換”發展的限度與軌跡的 “勞動”根據。并且 “關系”范疇無法度量大小多少,難以作為需要量測的價值本體的承載物。
3.兩種理解范式的內在統一性
事實上,對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這兩種理解范式,以任一方為本體兼顧另一方的言說,均背離于事情本原。前述文本引證表明,商品價值范疇中的勞動和交換在經典作家那里猶如人之雙腿鳥之兩翼,具有不可分割性。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和內在尺度,交換是價值生成的必要環節。離開勞動談價值,就會得出所有有交換價值的物均有價值的錯誤結論;而拋卻交換談勞動,必導致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的現實不實在性,使勞動價值論對市場需求側尊重不足,從而難以兼顧交換環節的作用。二者“對壘”著 “互嵌”才是其真實之在。其實,支持價值關系論的文本證言,就是馬克思對 “交換”的強調;支持價值實體論的文本言說就是對 “勞動”的強調,二者有機統一才構成勞動價值論的完整內涵。“勞動-價值”論這一簡潔有力的范疇本身—— “勞動”指向生產而 “價值”作為交換關系內含著交換——即是標示商品經濟條件下人類生產和交換相統一的完美表達。
囿于種種原因,尤其是經典作家理論構建旨歸在于揭示剝削的根源,這勢必要對 “勞動”進行極度強調。加之資本主義上升期的市場需求強勁,交換和商品實現基本不成問題,而問題在于勞動,故經典作家并未從涵蓋勞動和交換的路向對勞動價值論本質涵義進行明確界定,而是在對兩者進行分別強調的基礎上,不甚精確地以現在眾所周知的方式使用了價值概念。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只是由于馬克思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探索宏觀的社會發展規律,特別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的規律,所以他主要探索了勞動價值論的根本方面,……而對勞動價值與市場供求的關系一直沒有充分展開。”①王天思:《創新勞動價值論的探索及其啟示》,《哲學研究》2011年第3期。后來學界又對交換維度地位認識不足,為前述分裂性認知提供了誘因。然而,隨著消費社會和資本主義發達階段的到來,“交換”實現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繁多事關勞動價值論具體問題之辯日益迫切地要求著對勞動價值論種種有意無意地割裂性認知范式進行再審視。因此,闡明商品價值范疇本質意蘊,進而還原和再發現統一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就成為本文的邏輯出發點。
二、本真揭示:商品價值范疇本體性內涵闡明
實際上,價值實體論和價值關系論的多數觀點并非拒斥另一方存在的合法性,而是未確言二者具有統一性的本質意蘊基礎,以及以何方式進行統一。推進這項工作,以商品價值范疇本體論內涵的澄清為核心事件。
(一)商品價值范疇內涵把握向度
本體論 (ontology)由logos(theory)和ont(being)構成②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08頁。,直譯即 “是論”、 “實是論”,以探索 “是之為是”或 “實是之為實是”為歸旨③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120頁。,回答的是 “世界歸根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旨在塑造一種新型哲學思維方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反對任何 “本體論主義”的,因為本體論主義追求所謂終極存在和永恒真理,并以范疇構設脫離現實的獨立本體世界,從而必然產生預設本質解釋現實世界的前定論和先驗論的絕對論思維方式。然而,對 “本體思維方式”的否定不等價于對 “本體”問題研究范式的廢止,猶如不要 “實證主義”不等于要拋棄 “實證方法”一樣。任何理論抽象都具有某種 “超驗性”和 “形而上學”性。揚棄了傳統 “本體”的至高無上、解釋和宰制一切的絕對性,本體論研究可轉變為一種把握世界的認識論范式和據點。此視闕下,“本體”范疇在本文的適用意義即可獲得限定范圍:當我們 “從現象入手去尋求現象背后作為現象的承載者時”,可用 “本體”概念指稱 “現象背后、引起現象但不具有現象屬性、被認為是唯一實在的那種東西。它是理性……對現象世界所作的本原性或本真性重構,……包括本原的事物及其相互關系”④江暢:《論本體的實質》,《江海學刊》2008年第1期。。依此,勞動價值論的本體論內涵則指向 “商品價值的邏輯構成要素的承載者到底為何物”的追問。
論究該問題需把握以下向度:其一,商品價值首先屬于物質性而非精神性范疇。從本體意義上看,體現為人腦功能的精神運動僅限于人腦之內。運動于生產、交換諸環節的商品價值顯然是外在于人腦意識之物,自然歸屬于客觀物質范疇。其二,此物質性范疇需有 “量”的維度。并非所有客觀物均可 “量”測,那種無法定量的客觀范疇難以成為商品價值本體。其三,該范疇必須包含勞動因子。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定活勞動是形成商品價值的源泉和內在尺度,排除了勞動的價值論是不可想象的。其四,該范疇必須包含交換關系。不用于指向需要從而交換的活勞動及其物化形不成商品及價值,是一個同質于 “時間不可倒流”的經驗事實。其五,符合對人的經濟有用性的價值一般規定。一般地,價值是 “以主體目的、需要為尺度的一種主客體關系,是客體與主體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適合、相接近的關系,是客體屬于與主體尺度的統一”⑤李德順、孫偉平、趙劍英:《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86-387頁。。簡言之,在經濟領域,價值即是對人的經濟交換的有用性。
但在做出正式定義前,我們仍有必要正本清源回到商品交換事件的本真過程思考。商品交換并含著有機關聯的兩大領域和六個環節 (見圖1):(1)確定交換主體:人與人;(2)確定交換物:使用價值及勞動 (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統一體),此為生產層面;(3)市場供需影響;(4)形成商品實際交換能力;(5)確定交換價值;(6)確定市場價格:交換比例的貨幣化。其中,(2)發生于生產領域,(3)(4)(5)(6)發生于交換領域。分別回答:誰在交換、交換什么、根據什么交換 (包含(2)(3)(4)、交換到什么、交換多少等問題。

圖1 商品交換的環節
從圖1可知:首先,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實體論所強調的 (2)環節中的交換物——物化為使用價值的勞動,主要在生產領域的成本耗費層面發揮作用。而價值——不管它可能會是什么——卻是超出生產領域之物,不可能和生產領域中的勞動是等同性、同質性范疇,因而勞動無法成為價值的本體(但可說是其源泉、根據)。其次,關系論所強調的交換關系主要限于與生產關聯不大的交換過程,在無法說明自身根據的同時又不具備可測量性,因而與可度量大小的商品價值范疇異質,亦無法成為價值本體。那么,商品價值到底是什么呢?即是說,這種價值本體是經濟領域一種既非勞動耗費又非交換關系、立足于二者之上又有機涵蓋它們的可量測的客觀范疇,這個范疇排除了對人的消費而言的有用性,保留了對人的交換而言的有用性,合乎現實和邏輯的,它只能是一種由勞動內在地決定的商品的交換能力。即所謂商品價值,是由當下社會平均勞動耗費決定的、在供需競爭中實現的、作為勞動物的商品的基本交換能力①無特別指出,本文中的 “勞動耗費”均為 “社會必要勞動耗費”;“價值”指作為勞動物的 “商品的基本交換能力”(二者完全等同)。。這個范疇與勞動價值論本體論內涵的五個把握向度完全契合,同時又可將 “勞動”與 “交換”內在地融為一體,作為商品在交換領域的 “價值有用性”的選擇性物質承載物更具競爭力。下面從價值生成的具體過程做進一步確證。
(二)商品交換能力生成的序參量環境
前述實體論和關系論,大多是在簡單性視域下因對商品價值范疇內涵的理解不同而生發。它們對價值概念的考察僅僅立基于經濟系統的某個環節或方面,而沒有看到現代商品經濟系統是一個包含生產、交換等諸環節及其生成條件的復雜之物。價值是在復雜經濟系統的運動中演化生成的具有非單一屬性之物。若以還原主義的方式把價值歸結為某種單一屬性之物 (如 “體力勞動”、“廣義活勞動”、“關系”或 “勞動價值與均衡價格的簡單加權”),勢必掩蓋經濟系統及價值的復雜本真形相。因而,對商品價值的探賾需要有新的理論視域出場。作為人類最新科學形態 (復雜性科學)核心成果的系統自組織理論,在科學上證明 “物質以系統的形式運動演化著”,被拉茲洛認為 “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規律”,并 “為科學中的還原主義綱領敲響了喪鐘”②E.拉茲洛:《系統哲學講演集》,閔家胤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34頁。,因而十分適合用來分析復雜經濟巨系統的運動演化規律。這或可為我們剖析現代商品經濟系統中價值的運動演化提供可行性關照視角。在自組織理論視域下,商品交換能力在經濟系統的生成首先需要一些基本的序參量條件③在系統運動中有許多控制參量,分為 “快變量”和 “慢變量”,而 “慢變量”——序參量才是處于主導地位,支配子系統的行為,主宰著系統演化過程。。正是在這些序參量提供的環境條件下,商品交換能力才得以現實地生成,其中最重要的序參量條件至少有四個,分別屬于物的維度和人的維度 (見圖2)。

圖2 商品基本交換能力即價值的生成
①r并非指商品售出比例 (其值≤1),而是指在供需影響下商品中勞動耗費的補償程度。
第一,效用必須存在 (物的維度)。效用即使用價值。就某物的交換能力的產生而言,要實現憑該物換取他人所有物之目的,該物必須具有某種有用性,這是其交換能力產生的物質前提。這是從物的屬性的維度生成商品交換能力的序參量條件之一。第二,對效用有需要 (人的維度)。某物有一定的效用,但這種效用必須能夠滿足目標交易人的某種需要,為其所需要;否則,該物具有再多可能的效用有用性,但不為目標交易人所需要,也就不具備生成特定交換能力的可能性。這是從人的需要的維度產生的商品交換能力生成的條件。第三,利益區隔存在 (人的維度)。即交易者是一個個利益彼此獨立的主體,他們的利益相互區隔。這是確定利益邊界從而形成交換主體的前提。若利益高度一致,猶如母腹中的胎兒和母體那樣,就不存在交易主體,也就不可能發生經濟交易行為。同理,由于機器人是非獨立的利益主體,由其 “制造”的待售商品雖有交換能力及事實,卻無法 “屬于”機器人,故不能生成對機器人而言的 “價值”。第四,產品相對稀缺 (物的維度)。該條件形成了交換的必要性和動力。即便是有利益彼此區隔的主體存在,若效用豐富如空氣,也不會產生交換的動力。此四者缺一不可,并要求換回具備同樣條件之物。凡滿足者即獲得 “交換能力”而成為 “商品”——不管此物是否為勞動有用物②若無特別指出,本文中 “商品”均指勞動有用物。。正是以上四個序參量條件,為交換的產生和商品交換能力的形成提供了基礎。
價值本體是一種 “交換能力”,而這種交換能力有多大,則取決于現實供求這種隨機性力量。就發生過程來講,任何商品交換能力的具體生成和確定,毫無例外地以交換價值的比例的形式遵循供需機制由供需博弈決定,這是一般的、絕對的、根本的原則。當作為非勞動物商品進行交換,經供需博弈即具備交換能力并形成交換價值。當考察作為勞動物的商品的交換能力的生成,則由凝結在商品中的勞動耗費決定。固然,作為物的交換能力的直接來源和物質載體只能是效用,但除極特殊條件下效用源于自然外,人類社會絕大多數有用物一般均為勞動形成。當然,這需自然物參與——即不加任何人力的自然物 (為簡便計我們從生產源頭考察)。勞動生成了效用、效用經過供需形成了交換能力、無勞動則無效用也就無交換能力。這與其說是效用的交換能力毋寧說是勞動的交換能力。因此,勞動便成了人造有用物交換能力的根本來源。量化講,勞動對交換能力大小的決定又遵循如下機理:同量勞動耗費可形成不同的效用,因此,異質效用間的這一同量勞動耗費自然成為它們比對交換的基礎和法則,并決定著某效用兌換其他效用的比例——越大則交換能力越強——從而成為該效用交換能力的內在尺度。當然,勞動耗費的這種 “抽象”決定作用必須在活生生的供求博弈交換活動中實現和外化。
正是在上述序參量控制下,在勞動耗費的決定下,商品生成了具體的現實的交換能力。而商品表現出的一般的交換能力即價值。
(三)商品價值生成的過程
具體而言,商品具體交換能力必經由兩大步驟形成:勞動耗費環節和供求博弈環節 (詳見圖2)。單純有供求或勞動耗費均無法形成商品價值,前者只能形成交換價值,而后者只形成使用價值。
第一,勞動耗費環節。商品交換能力的形成以勞動耗費 (L)為深層根源和本質根據、其衡量以勞動耗費為根本尺度。這是活勞動對商品交換能力發揮影響的 “質”和 “量”兩層面的個規定:前者指明了商品交換能力的來源,后者明確了其大小的測量依據。但活勞動耗費本身并不是交換能力,二者是形成與被形成、表現與被表現、測量與被測量的對應性而非等同性關系。此前提下為便于實踐中對交換能力的計量,才可把二者做具有超高關聯度和等同度的類似同一物對待——對一個的測量即是對另一個的測量,就像實體論一直做的那樣。顯然,單純的勞動耗費絕不能單獨地在生產領域中自然地生成交換能力,后者必須在交換中由供需博弈具體地現實地被量化塑造。
第二,供需博弈環節。在供求博弈中,勞動耗費首先影響著使用價值的質量和數量,后者又影響著需求對使用價值的依賴程度從而影響商品交換能力:使用價值量越少、質地越好,需求對其依賴程度越大,則使用價值越具有優勢市場地位和較大市場權力,商品的交換能力越大;反之,則交換能力越小。故交換能力與使用價值的數量成反比而與其質量成正比。勞動耗費正是通過影響使用價值的質與量決定使用價值對需求的市場地位和權力進而生成商品交換能力的。供需博弈的結果由商品勞動耗費實現程度r來指示。勞動耗費正是在此過程中通過使用價值展現為現實的具體的交換能力:若供需相當,供給對于需求的滿足不多且不少,則r等于1。在此條件下,意味著商品效用的每一筆交換都以其平均勞動耗費為尺度進行,商品獲得了由平均勞動耗費決定的交換能力,即其基本交換能力——價值;若供不應求,則r大于1。供給方從需求方那里得到超過平均勞動耗費額決定的效用兌現——并非真的兌換到別人已永遠消失在效用中的生理支出意義上的 “勞動”——獲得超過自身的交換能力;若供過于求,則r小于1,供給方從需求方那里得到小于平均勞動耗費決定數額的效用兌現,商品獲得小于自身的交換能力。
第三,商品基本交換能力的生成。交換能力的大小正是以勞動耗費為基礎、在交換中經供需博弈,具體地現實地波動著生成,并具體化為諸種交換價值、貨幣化為各種價格 (如圖2所示)。但是,只有祛除了供求對這種具體的交換能力放大或縮小的影響后,商品所展現出的較穩定和一般的交換能力,才是其基本交換能力,即價值。其展現機理是:勞動根本地決定著所供給效用的質和量,從而從供給的角度對商品供需平衡系統產生決定性影響——使供需平衡的態的變動從隨機偶然性中表現出某種穩定性、一般性。于是,該物的交換能力也從隨機偶然性中展現出某種穩定性、一般性和必然性。這個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在隨機變動的交換能力中展現的穩定的交換能力就是價值,而前者就是價格。從發生學的角度講,不是價值決定并生成價格,而是價格展現為價值。二者是同一個事物的不同的態,是把握商品交換能力的兩種范疇形式:價格是現實的、具體的、生動的交換能力,價值是從這個具體、現實和豐富的交換能力中展現出的較為穩定的、基本的、一般的交換能力,是前者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不過是將 “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后的 “剩余物”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頁。。在此意義上,晏智杰教授關于 “勞動價值論所說的價值不過就是市場價格的一種較長期的穩定的價格而已”、“企圖在價格之外還去尋求什么價值,不過是搞神秘主義”等觀點是成立的①晏智杰:《燈火集:勞動價值學說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49頁。。現實中動蕩的交換能力之所以能夠展現出穩定性,即根源于勞動的決定作用。
第四,交換能力的變動。商品交換能力由平均勞動耗費內在地決定又受著r的放大或縮小作用,因此,其歷史性變動決定于L和r及其關系的存在與演化。其一,r的存在規定著L的方向及其對需求的有效性。L能否形成v、具體形成多大v必經r的規導。若r=0,平均勞動耗費形成效用完全不滿足市場需求,L只能是毫無意義的人力消耗從而無法形成任何交換能力。其二,L的存在變化根本地決定著v變動的趨勢。從而對L的考察即是對商品基本交換能力的考察。其三,L的變動導致r的消亡進而v的消亡。當平均勞動耗費減少到一定程度 (但永遠非0),r將自然消亡②這與r=0意義迥異:r=0表明勞動交換存在,但由于不滿足市場需求而無法產生交換能力;r消亡則表明勞動交換消亡。。意即使用價值的豐富使經濟需要相對滿足,從而 “經濟利益”的區隔性消失,勞動耗費失去了作為私有物和交易物的交易屬性;L將不被區隔為一個個用于交易的私有物,并回歸為社會公共物從而不再是形成交換能力的根據。此時,商品交換能力因 “相對稀缺性”和 “利益主體存在”兩序參量條件的消失而消亡。即是說人與人之間勞動的交換不再以 “商品”為媒介從而展現為共產主義的形式。在實質意義上,平均勞動耗費正是通過影響交易必要程度——商品 “稀缺性”——來對商品交換能力發揮決定性影響的。從公式v=L.r看,r若闕失v必坍塌,交換能力即自然消亡。這更直觀地確證了交換 (實質為供需博弈)對價值的本質構成性,而不能僅僅被當作價值的一種不可或缺的附屬條件。因此,商品交換能力實為表征商品存在性的歷史性經濟學范疇。若某商品交換能力及其基本交換能力自然趨零,這即等意于其價值和商品性的歷史性消亡。因此價值作為一般經濟范疇,不過是人與人之間經濟利益區隔性從而分裂性、對立性存在的表征,是人們之間經濟交易發生、發展、消亡歷程——即共產主義運動——的動態指示器。
三、走向統一:商品價值內涵的整合
應當說,奠基于商品基本交換能力范疇的統一商品價值內涵,是立足于價值實體論和關系論理論闕失進行整合的邏輯當然。
(一)“實體論”與傳統勞動價值論的勾連
實體論首先導源于勞動價值論思想家們對勞動由來已久的強調。在配第那里,“勞動”已和 “土地”一起成為評定價值的一種尺度③配第:《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貨幣略論》,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45頁。配第:《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貨幣略論》,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45頁。。斯密認為,公有制社會 “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種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④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6頁。,但不否認私有制條件下其他因素亦形成價值,并提出了著名的 “價值悖論”: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無關,從而為后來者把價值源泉唯一歸結為勞動提供了理論前提。李嘉圖接受了這一前提但反對 “多重價值論”,認為 “所謂勞動不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而且也包括凝結在使該勞動有效的一切器械上的勞動”。⑤李嘉圖:《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7頁。這就把資本看作死勞動的凝結并將其驅除出價值源泉范圍,從而把商品交換價值的來源唯一歸結為勞動。馬克思在承認交換作用的基礎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在把價值的尺度和源泉歸結為勞動的同時,“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1頁。價值實體論則將勞動之于價值的作用作空前提升。不但對勞動進行 “一家獨大”式極化強調,且直接把勞動耗費本身當作價值本身。實現了價值的 “根源”、“尺度”和 “本體”在勞動范疇中的 “三合一”。
顯然,實體論犯了還原主義的謬誤。它將非單一屬性的價值化約為 “勞動”,又將 “勞動”化約為 “勞動時間”。實體論忘記了價值不是物的屬性,而是包含著物的交換關系的綜合性范疇,因而招致廣泛質疑而難以自證。其理論闕失反映的恰是傳統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內在的 “二律背反”。傳統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雖然也強調交換對價值的必要作用,卻將其當作獨立的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分離出價值范疇,沒有意識到勞動不能和價值建立即時直接的聯系,以及交換對價值范疇的本質生成具有根本性意義;沒有對勞動和交換之間關系做出統一性解說,進而把價值本體定義為涵蓋二者的綜合性范疇;也沒有認識到價值是由勞動形成的商品的基本交換能力,從而把勞動和這種由其決定的能力間的關系明晰化,因此,始終在 “勞動”與 “交換”、“勞動”與 “價值”到底是何關系的無限糾繞中搖擺不定。
(二)“關系論”與西方經濟學 “供求決定論”的耦合
導源于對供需交換強調的關系論斷言:“認定商品交換價值和市場價格背后一定先驗地存在著一種支配它們的抽象價值,并以研究這種抽象價值為主要目的,是形而上學先驗論的思維在以往價值論研究中的共同表現。”①鄭怡然:《發展勞動價值論的另類思維》,《江漢論壇》2012年第7期。這確實擊中了實體論的要害。但關系論卻秉承同樣的還原論思維——將價值化約為一種 “關系”,陷入了另一個極端。對于勞動價值論中極其重要的勞動與交換關系若何,怎樣將勞動具體地、現實地融合進關系范疇等問題,關系論除正確指出價值范疇的關系屬性外似乎并沒提供太多。價值到底為何物仍未得到透徹表達。這種懸置價值本體承載物,僅對交換關系屬性指認的做法,在實踐中又極易與價值供求決定論相耦合從而滑向否定論陣營。以馬歇爾的 “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價值供求決定論倒是徹底的供求 “關系論”。均衡價格論認定由生產費用決定的供給與由邊際效用決定的需求形成的均衡價格即價值,這就將價值等同于交換價值即價格。正如馬歇爾所言:“一個東西的價值,也就是它的交換價值,在任何地點和時間用另一物來表現的,就是在那時那地能夠得到的、并能與第一樣東西交換的第二樣東西的數量”②馬歇爾:《經濟學原理 (上卷)》,陳良璧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9頁。,從而對商品交換能力生成、表現和確定的直接交換環節進行唯一化強調固然,任何商品交換能力的現實形成必經此步驟,但把價值唯一歸結為交換環節作用結果,也就無法揭示作為勞動物的商品 (非勞動物商品適用于馬歇爾理論)價值的最終根源只能來自生產它的必要勞動耗費的事實,以致在 “童車供不應求也不可能比供過于求的轎車交換價值大的一般事實”面前陷入解釋困境。所以,西方經濟學理論割裂地、片面地只看到供需環節(r)所得出價值供求決定論,由于不考慮平均勞動耗費 (L)形成的基本交換能力對商品價格的決定性作用,可以肯定必然沒有準確反映事情的真相。
總之,關系論對價值交換維度的重視以及對交換與勞動關系的語焉不詳,從 “交換”方面凸顯了傳統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內在的 “二律背反”。
由是,傳統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對價值兩個核心本質要素分別強調的基礎上分裂為兩個對立物:實體論和關系論。雙方均沒意識到二者均非價值范疇之本體。與之恰恰相反,兩者的統一才構成價值本質性內涵。
(三)統一商品價值內涵的整合
將價值決定之勞動根據和價值形成之物理交換過程做分離性考量的做法所導致價值范疇的現實不實在性,呼喚著對二者須做統一性體認。作為包含主體間勞動的生產和交換環節因素的總體性、綜合性范疇,商品基本交換能力范疇則是對 “實體論”和 “關系論”范式的整合的產物。
統一商品價值內涵認為:作為非勞動物的商品的交換能力,由于供給方來源于天從而供需博弈的權力結構也決定于天,最終交換結果只能由供需這個交換的直接環節唯一決定,這種交換能力不能形成價值,只能形成交換價值;而作為勞動物的商品,供給取決于勞動耗費,從而供需博弈權力結構與結果最終由勞動決定,其交換能力和基本交換能力也最終通過供需競爭由勞動決定。綜言之,交換價值決定于交換能力,而后者又決定于平均勞動耗費和商品實現程度并最終形成基本交換能力。此過程中,L指向生產者的勞動,從勞動耗費維度影響商品的交換能力;r指向需求者的需要,從需求者愿意和能夠付出多大補償的方面影響商品的交換能力。在r=1條件下展現出商品的基本交換能力,即價值。這就比較清晰地揭示了從勞動耗費到價值生成的內在理路與過程,祛除了傳統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視勞動為價值的不精確性。既強調了勞動作為價值的源泉與根據的決定性作用,又將交換關系內在地、本質性地融入價值范疇之內;既避免了實體論在實踐中懸置交換而孤立地強調勞動耗費的不足,又把關系論強調交換關系的正確性貫徹到底。因此,商品基本交換能力范疇作為勞動和交換的統一體,能夠成為價值之承載本體。
更重要的是,揭示資本對工人的剝削也因此有了全新視闕。傳統觀點由于把價值化約為勞動耗費本身,忘記了勞動耗費——無論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作為人力耗費的物理過程在商品中只有“過去式”形式,一經付出即永遠消失而不能被轉移和分割。資本對工人的剝削不是對其勞動本身的分割和榨取,而是通過 “勞動力商品”與 “勞動力形成商品”之間交換能力之差額——把此差額變現為使用價值并占有之——實現,資本剝削物之本體只能是使用價值。為更形象地表達和衡量,我們可用交換能力的體現物——勞動耗費的量——分析:通過交換能力,資本兌現了商品中的勞動耗費,并劈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從而獲得了剩余勞動而非剩余價值。這并不影響 “把利潤、利息、地租歸到唯一的根源”——剩余勞動上來。
因此,統一商品價值內涵,不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標新突破,而是對它的本意澄明。正如有論者所言,“可以看到勞動價值與人的需要的發展、從而與市場供求的內在關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僅內在地包含效用價值論、生產要素價值論和供求價值論等合理要素,而且避免了把價值和最基本的要素——勞動割裂開來的根本局限。”①王天思:《創新勞動價值論的探索及其啟示》,《哲學研究》2011年第3期。同時兼顧生產和交換兩大環節因素對商品價值生成的作用、又絕不放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基點——勞動對價值的根本性決定、且不給要素或效用價值論留下地盤的統一商品價值內涵,正是這種統一性邏輯的言明。應當說,這并非源于對傳統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解構或遮蔽的主觀故意,而是對經典理論中 “勞動實體”和 “交換關系”兩本質因素的合理綜合。這與其說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創新發展,毋寧說是其本體論層面的本意言明和重新發現。

表1 三種價值內涵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