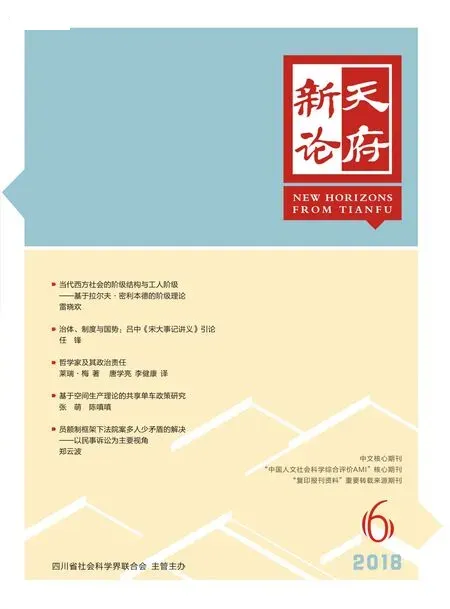由“私”及“公”:民間信仰與鄉土社會的公共生活
——河北龍牌廟會的個案研究
王媖嫻
導語:“私盛公衰”的鄉村
在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的 《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閻云翔在針對黑龍江省下岬村開展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當代中國農村的 “個體化”傾向進行了生動的呈現與深入的分析。他認為,伴隨著二十世紀國家介入鄉土社會的方式的變化,鄉村生活發生了明顯的變遷:舊有的各種傳統尤其是道德觀念被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不斷地沖擊乃至摧毀,農民的私人生活受到明顯干預,幾乎全被納入集體的統一管控之中;而在20世紀80年代集體化終結、國家漸漸減少對鄉村社會的干預后,社會主義道德觀隨之缺少了維系的支持而面臨困境。但也就在此時,農民被裹挾進商品經濟與市場之中,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費主義為特征、“將個人欲望合理化”的晚期資本主義道德觀,從而 “擺脫了傳統倫理束縛的個人往往表現出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張個人權利的同時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很可能成為極端自我中心的無公德的個人”。①閻云翔: 《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 (1949—1999)》,龔小夏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自序第5-6頁。由此,他不無憂慮地認為,在鄉土社會中,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斷裂還將繼續擴大,個人難以平衡社會義務與一己私利之間的關系。①閻 云翔: 《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 (1949—1999)》,龔小夏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260-261頁。
盡管閻云翔的觀點乃是基于個案研究提出的,但其分析卻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同及其他個案的支持。比如,吳理財就認為:“在當下,沒有權力強制的、也沒有情感的、更沒有理性的力量,促使農民參與到社區的公共事務中來”,“農民在私性領域逐漸生長出個體權利和利益意識,但是并未同時在公共領域培育出公民意識或公共理性,相反地,農民的公共生活卻急劇衰落,私性意識在沒有任何公共理性的節制下得以肆意膨脹,人們簡單地按照功利化原則處理彼此之間的關系,農民之間原本親密的互助關系被赤裸的利益關系所取代,農民在日漸功利化的同時,也日益原子化、疏離化,傳統社區走向瓦解”。②吳理財:《農村社區認同與農民行為邏輯——對新農村建設的一些思考》,《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年第3期。
然而,與此同時,各種新聞報道及不少學者的研究成果卻顯示出,作為鄉土社會公共傳統的廟會正在各地迅速復興,甚至成為動員村民參與村落公共生活最為有效的力量。比如,范麗珠通過對河北某些農村及陜北黑龍潭廟會的考察,認為廟會管理組織可構成鄉村社會公益活動的重要社會資源;③范麗珠:《公益活動與中國鄉村社會資源》,《社會》2006年第5期。李華偉在河南的田野調查指出,“在中國鄉村,公共空間主要是由宗教信仰或者與信仰有著關聯的組織建構起來的,公共空間的走向與各種信仰自身的機制及其與民眾生活秩序的關聯程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④李 華偉:《鄉村公共空間的變遷與民眾生活秩序的建構——以豫西李村宗族、廟會與鄉村基督教的互動為例》, 《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趙旭東基于對華北村落廟會的調查認為,廟會在很大程度上能夠 “把分散的、自私自利的個體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大家相互認可的共同認同”⑤趙 旭東:《從交流到認同——華北村落廟會的文化社會學考察》,《文化藝術研究》2011年第4期。;而筆者在魯中地區的調研也發現,民間信仰作為鄉村公私領域之 “裂縫間的橋”,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當代鄉土社會在日益 “原子化”、個體化的情況下構建積極的公共生活的可能與潛力;⑥王 媖嫻:《民間信仰與鄉土社會公共生活的構建——基于魯中地區顏文姜信仰活動的考察》,《西北民族大學學報 (哲社版)》2012年第5期。等等。在各種材料中,鄉民在參與廟會的各項事務時所展現出的積極主動的態度、不計利益的付出、團結合作的精神,甚至令有些學者認為 “一個處于國家與家庭之間、并外在于市場的 ‘公共領域’正在中國農村出現”⑦約 翰·弗洛爾,帕米拉·利奧納:《中國鄉村的文化生活:以川主廟為例》,陳永革譯,張敏杰主編: 《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西方學者看中國》,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320頁。。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似乎 “矛盾”的情況?在學者們眼中 “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日益原子化、疏離化”的當代鄉民,這些在波普金看來總是 “從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出發權衡”的“理性的小農”⑧S amuel L.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31.,真的能夠在廟會的各種公共事務中不計回報地自愿付出、傾力奉獻并有效合作?其背后的動員力量又是什么?本文將借助在民俗學界頗負盛名的河北范莊龍牌廟會⑨無 論在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中還是在學界的表述中, “龍牌會”都涉及彼此相關但并不等同的兩個所指,如高丙中所言,它“在組織上是一個草根社團,在活動上是一個地方廟會”。為了行文方便,本文將服務于龍牌的會頭組織以 “龍牌會”稱呼,而圍繞龍牌信仰舉辦的廟會則以 “龍牌廟會”稱呼。的個案⑩本文的研究發現及觀點乃基于龍牌信仰此一特殊個案,這一個案可能與其他不少地方類似,但卻不能囊括和代表所有民間信仰和廟會的情況。予以回答。
一、入會與幫會——因 “事兒”而許的謝神之舉
自古以來,河北趙縣的范莊就保持著對于傳說中的祖先——龍牌的信仰。每年從農歷二月初一至初四,該村都會為龍牌舉辦聲勢浩大的廟會 (俗稱 “范莊節”),其影響力輻射至周邊數村,甚至有不少信眾自外鄉、外縣甚至外省市專程而來。據村委會估計,廟會期間一天中接待的各地信眾恐有萬人之多。規模如此之大,前來進香的信眾又如此之多,龍牌廟會該如何承擔繁重的接待任務、確保各環節各項目有條不紊地進行呢?這與村民的廣泛、積極參與有直接關系。
在人力方面,由于共同的龍牌信仰,該村久已形成了一個名為 “龍牌會”的管理組織及會頭輪伺制度。所謂 “龍牌會”,指的是范莊數位民眾自發形成的 “侍奉”龍牌的組織,其核心成員稱為“會頭”。會頭的身份大多為世襲,但也可經由本人 (往往需為廟會服務過一段時間)主動提出申請、龍牌會加以考察并通過一定的考驗儀式后成為會頭。一旦加入龍牌會成為會頭,便需承擔一定的義務。這些義務主要包括:以抽簽決定順序的方式輪流在兩次廟會之間的一年時間里日日 “伺候”龍牌①伺候龍牌的方式前后有過巨大的改變:本世紀前,是由會頭在廟會結束時將龍牌法身迎至自己家中 “伺候”至來年廟會舉行之時;而伴隨著上世紀末龍牌廟的落成,龍牌有了固定的安身之所,其方式也隨之轉為輪值的會頭夫婦搬至廟旁特設的龍牌會辦公樓里。,參與龍牌會一年三次的集體會議,分工合作、分別承擔與廟會相關的各種繁瑣事務,無償為與龍牌有關的各種事務貢獻財力、物力和人力。會頭之外,還有大量 “幫會”之人。幫會者不限本村,僅在廟會期間自愿前來承擔各種雜務,但絕大多數年年到場。而在物力和財力方面,除了龍牌廟會本身收入的香火錢外,村民的貢獻亦不可或缺:除金額不等的捐款外,廟會提供的飯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 (主要為白菜、豆腐和饅頭)均由村民主動捐助,各種車輛也均由村民尤其是會頭主動免費提供。
那么,范莊的村民,為什么會選擇入會和幫會,并為了廟會這一村落公共事務鞍前馬后、不計得失地出錢出力?
在問及村民加入龍牌會組織或者前來幫會的原因時,有一個字眼—— “事兒”頻繁出現。慣常的 (多夾雜有一些無奈)說法是:入會及幫會的 “都有 ‘事兒’”, “還不都是為了 ‘事兒’許的啊”。因此, “事兒”這個在現代漢語中相當通俗的字眼,作為訪談過程中出現的一個 “言語標記”②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91頁。,在這種情境下的具體意義就成為我們洞察當地人信仰行為的一把鑰匙。以下擇取的陳述或許有助于我們在具體語境中理解該詞的含義:
俺父親那時候是有病,就是覺著身體不壯實、有病去的,許了 “叫我沒病壯實點,我就來當會頭”。后來病好了,就成了會頭。(2012.6.15對老會頭汪己的訪談)
干這個的身上都有點事兒,人家 (指龍牌)都牽著你哩。入會都是為點事兒,沒事兒誰干這個?沒點事兒不攬這活兒,攬了這活兒你這一輩子就 (耗在那兒吧)。(指著家屬說)她鬧騰,跟那精神病似的,一連鬧了三年,到醫院里檢查不出病來。人家說她這是虛病③當地人將疾病分為 “實病”與 “虛病”兩種。“實病”是實在的身體疾病,是通過中西醫尤其是西醫醫治便可治療的;而無法歸入 “實病”體系的便往往自然而然地被當地人視為 “虛病”,其表現常常或類似精神病發作時的癲狂、混沌,或看似“實病”而難以查找病因無法醫治,從而常被視為與仙家和神靈有關,必須找香頭依靠巫術手段禳解——與仙家有關的,往往是該仙家想要求財、物或者于此人家中接受常年供奉;與神靈有關的,則是神靈與其有緣而對其進行 “打磨”、助其修行,不少人往往經此成為香頭。,叫我領她看看,實際上我不相信那,我也不給她看。后來石家莊三院有個姓白的大夫,他成分高,人家說,這吃藥可好不了,找個香道的給看看吧,這是虛病。他這么說我還不相信,什么虛病!后來鬧騰啊鬧騰,她嬸子行好,就領著她去找明眼兒 (指香頭)。去了一磕頭,人家說誰叫你不去跑噠(指繼續做會頭服務龍牌)了?你去跑噠,入了臘月就好了。——俺家原來是會頭,后來老人上了年紀,沒有接的就斷了一兩輩子。我這才入的會。嘿,一進臘月,(她)不鬧騰了,你看人家說的可準。她要不這樣,我咋也不能干這個活兒。(2012.6.17對中年會頭苗巳的訪談)
我丈母娘身體一直不太壯,找人看,說是虛病。人家還說,你守著范莊的龍牌你還來俺這里干啥?當時我就很納悶,他怎么知道我是范莊的?挺神奇的。我去了好多地方,人家都這么說。包括一些和尚尼姑,都看過。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年俺家小子,你看他胸口上叫開水燙的。北邊有個住持叫我皈依,說我殺氣太重。我本來挺不在乎,他說你家幾輩子都是會頭,都是管事的,你不入會,對你家老人和后代都有影響。就從那時候我開始去幫忙,幾年以后,會長說叫我入會。入會就入會唄,本來咱家就是老會頭,我就入了會。(2012.6.19對中年會頭苗辰的訪談)
這日本進中國,我爸爸那時在村里干著什么事我就不清楚了,叫鬼子給逮住了,捉了他們兩個人,綁著他們。他在心里念叨龍牌:“叫這繩子自己開了,叫我跑了,我立時就接班當會頭。”結果那繩子就開了!這事兒絕對跑不了,這是真事兒!(他的繩子)開了,把另一個 (人的)也給解開,他倆躲到莊稼堆里,趕鬼子走了以后,他倆作伴跑回來了。回來正好過廟,立時就參與了會,當了會頭。(2012.6.16對老會頭柳子的訪談)
有一年,我做了個夢,夢見那神駕著云過來了,放下一個皮箱。使那甩子一指,那皮箱就打開了,出來個大虎,看著我,掉著淚。我知道這不是好事。我就和俺娘說這事兒。俺娘說,石春(村中的香頭)會看這個,咱去找人家問問。那時候石春才供上神,還不認得俺。石春問俺俺家這個 (指配偶)叫嘛?俺說叫顧戊。那時候俺家顧戊還沒接會頭,俺公公干著,顧戊也就是管著記記賬,還沒正式干,也不是很積極。石春說人家這是叫他給圣里干事兒去,這是叫他來了。我說,喲,這叫給圣里干事兒,這不就死了?俺孩子們這還小哩,家里離不了他,還有別的法兒吧?人家說,還能沒法兒啊,有法兒,給圣里也是給龍牌干,你答應伺候就行。我這不就和龍牌許,在圣里干也是一樣,在凡里干也是一樣,都給你好好干。(2012.6.18對中年會頭顧戊家屬石梅的訪談)
俺爹四十五那一年有了病,醫生給他判了死刑。他回來在龍牌這兒對龍牌說:“醫院里給我判了死刑了,你要是能叫我活過來,我給你好好干。”打那他就一心一意的幫會,誒,他活到了七十三。(2012.6.18對盧黔之子的訪談)
根據這些陳述,“事兒”這個詞大致與這兩種情況最為相關:自身或家人生病而求健康,諸事不順而求平安。在當事人因 “事兒”向龍牌許愿的過程中,其在龍牌前許愿的內容根據 “事兒”的大小及嚴重程度,會有所差別。一般而言,情節較輕、“事兒”較小的,可以物質類的供品和香油錢許愿;事態較為嚴重的或是實物許愿均不奏效時,便常常需要以自身的長期投入作為交換的砝碼——輕則幫會、重則入會。在后一種情況下,比之其他信眾,會頭和幫會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乃至物力和財力來服務龍牌 (如上文所述)。在安土重遷的傳統鄉土社會中,恪守對龍牌的承諾、隨時遵照龍牌的旨意行事并不是難事,甚至成為這些村民務農之余的精神寄托。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襲來,社會流動加強;另一方面,在務農之外,尤其是伴隨著村中商城大街的修建,當地人有了更多的產業可以從事,這使其在時間上常常不由自主。于是,堅持在固定的時間甚至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始終堅持對龍牌的盡心侍奉,便成了一件 “自討苦吃”的事。
我們該如何看待入會及幫會這種似乎有些 “得不償失”的許愿—還愿行為呢?如有學者所言,“民眾是從私人關系的角度去理解并建立和神界的關系的,其基本的原則和差序格局的人間社會并無二致,是從己出發的 ‘攀關系、講交情’。”①彭牧:《祖先有靈:香火、陪席與靈驗》,《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2期。從主位的角度看,這種做法,實質上都在會頭和幫會者這些信仰及實踐主體與龍牌之間建立了更為具體、直接而密切的關聯,從而令其與龍牌的關系更近一層,在其需要神助時,能夠得到更多的神佑。
那么,對神明龍牌而言,它又該以何種方式來維系信眾對它的信服,不斷約束他們認真踐行諾言,動員他們積極投入與龍牌相關的各種公共事務之中呢?
二、恩威并舉——來自神明的公共動員
每逢廟會,關于龍牌的靈驗傳聞總是被鄉民們煞有介事地反復提及。其中最主要的,莫過于因拒絕或消極幫會而招致的龍牌的懲罰。以下試舉幾例:
我有個叔叔原來不信龍牌,叫他去龍牌會上做飯,他說我要去犁地。他喂了個小牲口——一個馬,套著個小車,他就套不上,就不能套。
南營村有個趙家,有一年去接神,要路過他家的地,他說先去地里澆上一車糞再去接神。那時候都是木頭獨輪車,他就是說啥也推不動。(2012.6.12對會頭柳乙的訪談)
我小時候聽老人們講,二月初二,有一個人叫道印,叫他去扛桿子搭棚,他說我賣完洋油我就去。他說這話時把擔子一撂——那時挑著擔子賣洋油,一撂,桶咕嚕咕嚕倒了,把洋油都透了了。他 “好了好了我去吧”就去了。(2012.6.15對會頭盧庚的訪談)
你心眼不正,(龍牌)到時候就給你顏色看看。過會的叫他去搭龍棚,他上地里去套騾子,套不上犁,小騾子都驚了,好沒把他拉死。三旦,叫他去搭棚,他沒去,他去趕集賣羊,到了一看羊沒了。過去,誰也不敢說個劣字,你敢說個劣字這 (龍牌)就發話;誰也不敢說個劣字,在屋里都不敢說。(2012.6.15對會頭汪己的訪談)
沒點事兒不攬這活兒 (指加入龍牌會當會頭),攬了這活兒你這一輩子就 (耗在那兒吧)。你看人家出去打工,刷盤子刷碗,叫我去我不敢去。你 (去了)身上這個事兒誰管啊?你走了人家 (龍牌)干啊?還有這事兒牽連著哩,人家有點事兒,你到了時候家里活兒撂下也得給人家做去。你看看,你說干這個容易啊?不容易。跟你說吧,好行好的少啊少。磕閑頭的少,人家是愿意磕頭就磕不磕也沒事兒;你這,磕也得磕,不磕也得磕。這初一十五得去念佛、得出去趕會,二月二也得去伺候著,有了事兒叫你到你接著就得到。你對他心服口服了他就沒事了。你牽連著這事兒,該給他服務就得服務去,他就不差你了。(2012.6.17對苗巳、盧蘭的訪談)
龍牌叫你來幫忙,你放下活兒、放下家里的事兒,都得來幫忙。我在外頭給人干活一天80,(廟會)這四五天也不能去干了,說叫來立刻就得來,不然 (龍牌)就鬧騰俺老的,俺爹都84了。我那時候就是為了俺爹長病許的,來了好幾年了,不來俺爹就摔跟頭。神叫你來你不來不沾。再說,來幫會的、來趕會的都有好處,都不白瞎、都沾光。 (2013.3.13對某男性幫會者的訪談)
除此之外,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有個關于龍牌早年顯靈復仇的故事也不斷地被范莊的老人們提起:
為嘛信龍牌?就因為那一年還沒解放,剛剛開始解放,那是在40年代初那個階段,我才七八歲,那一年俺家正好當值,趙慶印領著兩個人來俺奶奶家把龍牌的牌位砸了。他這一砸,從俺家三進院當中起來一個有幾丈高個火星似的,上了東北了,從村里西南角到了東北角,人家都看到了。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俺親眼見到的,俺記得啊。砸了以后他們走了。結果,(一拍大腿)領頭的這個趙慶印三天之后死了——他砸了龍牌的牌位,龍牌在他家鬧騰不能安寧,睡覺睡不了,他就往外走,走到賢門樓那,那地方那時候住著日本人哪,他就叫日本人捉住了,用刺刀扎死了。剩下那倆,其中一個,在家里就不能合眼了,一合眼滿屋里凈長蟲。這倆人以后通過村里商量,賠了一個新牌位,他們才安生。(2012.6.13對會頭盧丁的訪談)
也有訪談對象提到,法身被砸的龍牌曾經傳旨給彼時村中的香頭,“報不了仇永不上天”,這一賭咒后來化為了現實:盡管為首的趙慶印不得善終,但趙家的災難并未結束——其遺腹子尚未滿十八歲便得病去世,自此血脈中斷。這個故事被很多會頭和村民講述,盡管具體細節和熟悉度不盡相同,但訴說者均以篤信不疑的語氣和神態鞏固著這樣的集體記憶。另外,在調查中,龍牌對于曾任龍牌會“當家人”林丙的懲罰也被不少人提及。根據這些說法,林丙在六十歲出頭時的早早離世及其家人的不幸都與林丙貪污了龍牌會的巨額香火錢有直接關系。
盡管這些傳聞或經歷往往只 “發生”在有限的個體身上,但對于龍牌懲罰的忌憚卻在 “信息過濾機制”①陳彬,劉文釗:《信仰關系、供需合力、靈驗驅動——當代中國民間信仰復興現象的 “三維模型”分析》, 《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4期。的作用下,通過口耳相傳傳播到了每一個鄉民那里,加深著信眾對龍牌的畏懼。從而,之前許下的那些 “只具信仰約束力不具法律效力”的、單方面的 “嘴口愿”②瞿海源,張珣:《民間信仰的基本特征與奉獻行為》,載瞿海源著:《臺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臺北:桂冠圖書出版社,1997年,第115頁。,也因此獲得了令人人自危的外在監督、制約乃至管束——慮及信眾在談及這些傳聞之時的神情,我們不得不懷疑,如若不是出于對龍牌懲罰的忌憚,不少人很可能會對龍牌 “違約”或忤逆龍牌的神意而拒絕對龍牌廟會這一村落公共慶典的投入。
不過,龍牌的靈力并不僅僅體現在其嚴厲的 “有過必罰”上,對于那些經年對他虔誠供奉、事無巨細積極投入的會頭和幫會者來說,他也會以溫情脈脈的一面回報他們的付出。
俺在那兒耽誤了功夫了、投了錢了,別人不知道老人家知道,你別看老人家在那兒坐著,心是活的。俺這龍祖靈得很!趕有個三災兩難你起來求就沾,頂事得很,不叫你白跑,不叫你白費心。(2012.6.17對苗巳夫婦的訪談)
龍牌也記著賬哩,你干啥事他都有一本賬,他可知道哩。他要是知道你不正干,厲害得很,就能置人于死地。(2012.6.17對梅秋的訪談)
龍牌可靈哩,要不這片兒的人都信的沒法兒。 “有求必應”,可是有一樣,你得信人家,你的心得在這兒,你辦壞事人家嘛事不管。俺這里有一個,別人去套娃娃,緣分大的一下子就套上了,她套了幾年都不行,你不行正人家就管你啊?俺這個孫子,人家問俺是不是套的,我說俺一天到晚伺候著,俺還需要套?!(2012.6.18對石梅的訪談)
此外,據說,在輪值的那一年,有些會頭雖然忙于侍奉龍牌而耽誤賺錢甚至造成了經濟損失,但龍牌在事后都予以了一定的獎賞。比如:盧庚夫婦輪值的那一年正值蓋廟,夫妻倆顧不上園里成熟的蘋果,一心撲在龍牌的事務上,導致當年的蘋果爛掉大半而賠本,但第二年家中的果園獲得了大豐收,結出的蘋果比往年都大都好;顧戊、石梅夫婦輪值時,夫妻倆也顧不上照看自家的生意,一心以龍牌為重,過后龍牌也為其帶來了滾滾的財源;而長期負責整理龍牌會資料的盧丁,早年眼睛老花得厲害,卻在接手此事后神奇地徹底丟棄了老花鏡……這些關于龍牌靈驗的言論及 “體驗”成為維持會頭們為龍牌的公共事務效力的有力支撐。
可以看出,在關于龍牌這一神明恩威并舉的各種傳聞中,所謂的過錯都體現為拒絕或消極為“作為公共生活的鄉村廟會”①劉鐵梁:《作為公共生活的鄉村廟會》,《民間文化》2001年第1期。服務,而獲得福佑的人也往往是積極虔誠地投入廟會公共事務之中的人。因而,這類靈驗傳聞實際上隱含的規訓是:作為社區的一份子,在廟會這一 “非常”的公共時刻來臨時,每個個體都應積極主動地投入到圍繞龍牌信仰展開的各類公共事務之中去,在跨越家戶的公共生活中排除私心、按照公共秩序行事;只有如此,才能蒙神恩、避神懲。如是觀之,因 “事兒”許愿并進而在愿望實現后義務參與公共的廟會事務甚至將此后余生與龍牌相捆綁以盡力還愿,這種看似 “非理性”的舉動,實際上飽含著主體在作選擇時對其所預計的回報和代價的充分權衡②羅德尼·斯達克,羅杰爾·芬克: 《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楊鳳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04頁。,從而充滿了工具理性的色彩。而這種理性的背后,便是對于一己或一家之福的祈求。
討論:“追尋一己之福”的民間信仰何以走向 “公共”?
臺灣學者蒲慕州認為,中國古代宗教信仰中最根本而持久的目標是 “如何得到個人和家族的福祉,個人又如何能接觸,甚或控制超自然力量”,亦即其所說的 “追尋一己之福”。③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6頁。而事實上,盡管歲月更迭、世事變遷,中國人在信仰實踐中所持有的這一追求卻經久不絕。桑高仁 (Steven Sangren)也主張,盡管民間信仰的實踐尤其是儀式活動產生了整合當地社會、激發不同層級的共同體感之社會學意義上的影響,但對于個體崇拜者而言,其參與其中所帶來的這種影響實屬無心插柳之舉——信眾并非出自社會或群體的需要而參與儀式,其動機都是以達成個人目標為指向的;不少人參與公共的儀式活動乃是為了博得某些神明的偏愛或是引起上天的格外注意,而且他們相信神明極有可能在這種慶典活動中顯靈。④P.Steven Sangren, “Dialectics of Alienation: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 Man, New Series, Vol.26, No.1,Mar., 1991, pp.69, 71, 79.
在這種情況下,追尋一己 (家)之福的民間信仰何以走向 “公共”呢?李向平在論及宗教信仰的 “公共”性時,曾經指出:“毫無疑問,信仰或信仰宗教是個人的事情,但信仰的實踐,特別是信仰群體的社會實踐,以及宗教對于一個社會的影響,肯定就是公共的事情。關鍵的問題是,私人的、個人的信仰,如何能夠成為公共的社會信仰,如何構成社會的公共認同,尤其是在不同的信仰之間能夠建構為公共的、共同的價值共識。”①李向平:《公共信仰與社會共識》,《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8期。在以龍牌信仰這一個案具體回答這一疑問之前,我們需要借鑒一下桑內特 (Richard Sennett)的觀點——當人們將某些非個人的行為和事務誤認為是個人的事情時,才會投入熱情②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2003, p.6.。而由此引申出去,我們或也可以說,人們對那些看似屬于個人事務但可能通向集體性、公共性的事務,也極有可能投入較多的情感與精力。這樣一來,追求一己 (家)之福的私人信仰便可能走向 “公共”,只不過,這種情況下的 “公共”乃是不完整的、打了折扣的 “公共”。
對于依托民間信仰而形成的這種有限的公共生活,我們或許可以借用涂爾干的經典分析來重新思考。在 《社會分工論》一書中,涂爾干提出了 “機械團結”與 “有機團結”兩種人類的團結方式。涂爾干認為,“社會凝聚力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所有個人意識具有著某種一致性,構成了某種共同類型,這類型不是什么別的,只是一種社會心理類型。在這種條件下,所有群體成員不僅因為個人的相似而相互吸引,而且因為他們具有了集體類型的生活條件,換句話說,他們已經相互結合成了社會”。而所謂的 “機械團結”,正來源于這種相似性,其作用 “不僅在于能夠使普遍的、無定的個人系屬于群體,它還能夠使人們具體的行為相互一致”。③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328頁、67-68頁,第89頁,第89-90頁。在這種團結方式中,“個人不帶任何中介地直接系屬于社會”,從而 “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所有群體成員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組成的:即集體類型”。④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328頁、67-68頁,第89頁,第89-90頁。而 “有機團結”,指的是存在差別的成員之間分工合作、互相結成有機統一體的團結方式。在這種團結形式中,“個人之所以依賴于社會,是因為它依賴于構成社會的各個部分”,從而 “社會是由一些特別而又不同的職能通過相互間的確定關系結合而成的系統”。⑤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328頁、67-68頁,第89頁,第89-90頁。
循這一思路,我們可大致將公共生活劃分為 “機械的公共生活”與 “有機的公共生活”。其中,“有機的公共生活”對應的是哈貝馬斯、漢娜·阿倫特等政治學意義上的 “公共生活”。在這種公共生活之中,人們所談論交流的更多的是現實的集體、公共事務,其統一行動亦往往有共同的指向性——謀求公共福利、捍衛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成為個體獲得及維護自身權益的前提、保障,因此每個個體及家庭都自覺地、積極地投身其中。而范莊如今依托龍牌信仰所形成的這種公共生活,可稱為“機械的公共生活”。在這種 “徒有其表”的公共生活中,參與其中的個體具有趨同性——他們的參與懷有相似的動機,這種動機更多地在于追尋一己 (家)之福的私利,而不在于交流對于現實公共事務的看法,通過采取共同行動以達成共同的公共利益。
因此,雖然一眾鄉民得以借廟會這一契機匯聚于村廟這一公共的神圣空間之中,但這種采取了“公共”、“集體”形式的廟會公共生活僅是政治學意義上公共生活的雛形或初始形式:它盡管實現了跨越家庭的互動乃至合作共事,但其內在指向并不在于公共利益、公共價值、公共訴求。因此,這種公共生活只能算作一種極其有限的 “公共生活”,而很難作為 “民主得以確立和運行的重要社會基礎”⑥林尚立:《有機的公共生活——從責任建構民主》,《社會》2006年第3期。。以追尋一己 (家)之福為最終目標的民間信仰及其儀式活動如何提升為 “鄉村公民文化”⑦南剛志:《中國鄉村治理模式的創新:從 “鄉政村治”到 “鄉村民主自治”》,《中國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進而作為當代鄉村民主自治的有效基礎,仍是一個棘手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