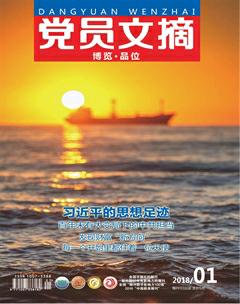子午嶺的星星之火
萬曉林
子午嶺原是北方一脈普通的山系,居黃土高原腹地,占地三萬多平方公里,因與本初子午線方向一致而得名。它北起甘肅東部的華池、合水、正寧等縣,向南、東南延伸400多公里至陜西黃陵、耀州、旬邑等縣區,其主峰又稱橋山,支脈有香山、馬欄山、石門山等。山間松柏密布,雜木相陳,灌喬兼備,郁郁青青,還有一些原始森林,人跡罕至,珍禽異獸出沒,頗顯神秘。
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時,子午嶺燃起了紅色革命的星星之火。一座子午嶺,為單調的黃土高原增添了無盡的生機,為一個民族、一個政黨的發展埋下了生生不息的根脈。
悠悠的照金
子午嶺中段往南延伸至香山便是照金鎮。照金河由北向南緩緩流過,陽光照耀下的河水,閃著金波,照金鎮或許由此得名。
上世紀30年代初,照金一夜之間變得熱鬧起來。
劉志丹等率領的陜甘游擊隊一路南下,攻城拔寨,開進照金。打土豪,分田地,照金成了為數不多的早期紅色革命根據地。
此時18歲的習仲勛,在發動“兩當兵變”失敗后,回到家鄉富平繼續革命。之后奉組織安排喬裝打扮,跋山涉水來到了照金,出任邊區特委軍委書記和指揮部政委。這支部隊一方面深入農戶組織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另一方面積極組織壯大紅軍力量,開展軍事斗爭。
他們將紅軍指揮所等機構建立在鎮東側的薛家寨,此地雄踞山中腰,上有天然形成的四五個洞穴,洞中分別建成了紅軍醫院、兵工廠、服裝廠、指揮所和倉庫,前后均有山門、索道,依此天險開展革命。
照金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震驚了國民黨,遂調集重兵進行“圍剿”。面對敵強我弱的形勢,黨組織決定將紅軍主力轉入外圍作戰。習仲勛等領導率領部分干部群眾,堅守根據地與敵周旋。
一次外出籌集糧草時,習仲勛和數名干部被幾股敵軍團團包圍,在突圍之中,他腰部中槍滾下山坡。一位名叫鄭老四的農民救了他,在家里給習仲勛搟面條,做荷包蛋,并以土法為他止痛,最后送到隊伍上。
1933年6月下旬,紅二十六軍第二團三百余名官兵,離開照金,南下渭華。
南下隊伍抵達華縣一帶便被國民黨重兵圍追堵截,一度被打散,百余名紅軍戰士飲恨渭華,僅有劉志丹、王世泰等少數同志轉入秦嶺打游擊。四個月后,劉志丹等收攏失散受傷的戰士不足百余人,回到照金。
照金像一位慈祥的母親將這些受傷的孩子輕輕地攬在懷中,撫慰著傷口。
那時候,劉志丹、習仲勛等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他們憑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用生命書寫著一個政黨和民族奮進的歷程。
紅紅的南梁
子午嶺北端有座山叫大梁山,其南麓延伸出幾道山梁,分別有南梁堡、荔園堡、豹子川、二將川等村落,中心是位于華池縣的南梁堡,這一地區故稱南梁。
照金失守以后,劉志丹、習仲勛等努力尋找建立新的根據地,后經多方討論選擇在南梁,建立紅色政權與敵人長期斗爭。
1934年初,病體初愈的習仲勛來到了南梁一個叫荔園堡的小村堡。此地沒有一棵荔枝樹,但它就叫荔園堡。
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荔園堡一座大廟中舉行。歷時七天,代表們熱烈討論根據地的政治、軍事、土地、財政、糧食等主要問題,形成決議,并選舉成立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21歲的習仲勛當選為蘇維埃政府的主席,被老百姓稱作“娃娃主席”。
就是這個“娃娃主席”,帶領著年輕的部隊組織鄉親們鞏固紅色政權,開展民主選舉,發展生產,與敵斗爭。
面對許多不識字的老百姓,他們想出了一個很有用的選舉辦法:在每一個候選人的背后放一個碗,旁邊放一袋黃豆,選民排成隊往前走,同意誰當選就去誰的碗里放一顆黃豆。最后數黃豆報票數,當場宣布結果。翻身農民第一次嘗到當家作主的味道。
他們將農村那些好吃懶做、游手好閑的“二流子”集中起來,組織學習教育,集體勞動。改造“二流子”活動,讓群眾看到了新政權的希望。
他們創辦了陜甘邊紅軍干部學校和列寧小學,積極培訓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還讓村上的孩子們一個個背起書包走進學堂。
他們興辦集市貿易,讓群眾的物資交易活起來,同時集市又成為聽取民聲民意的很好場所。
那時候,南梁的天是紅彤彤的天。
時隔60余年之后,已經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的習仲勛住在深圳,依然惦記著南梁、荔園堡,甚至能說出誰家有幾個孩子、誰的婚姻狀況如何,并一直想回南梁等地走走看看,但由于身體原因不能前往。他專門安排夫人齊心和幾個兒女帶著南國的荔枝等,看望南梁、照金等地的鄉親。
當鄉親們見到齊心,吃著荔枝,眼睛里淚光閃閃,嘴里喃喃地說:“仲勛真好,這么多年了,還記著咱們。咱們荔園堡里真有荔枝了!”
火火的馬欄
旬邑縣馬欄鎮是子午嶺北段馬欄山下的一座小鎮,一條清淺的馬欄河穿村而過。
1941年秋,隨著關中分區的遷入,靜謐的馬欄火了起來。
時任關中分區區委書記的習仲勛已經是兩下關中。這次他率領關中分區機關和部隊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激烈的反摩擦斗爭,從旬邑縣馬家堡到長舌頭、劉家店、陽坡頭村,轉移至馬欄鎮。
在這里,他們挖窯洞、修橋梁、辦學校、建劇團、出報紙、練隊伍、抓經濟、興商貿,一派興旺景象。
過去,馬欄河上一座橋也沒有,村民在河面窄處隔一步擺一塊較大的石頭(俗稱列石),靠此過河。為了方便百姓生產生活和分區、隊伍運輸物資,習仲勛找技術人員設計,組織大家運來沙子、石條等材料,數月時間就建起了一座“七孔石橋”。
70多年過去了,這座橋巋然不動,穩固如初,造福著這里的百姓。
從1941年遷入直到1949年解放,馬欄鎮一直是關中分區機關所在地。習仲勛離任后,先后有張德生、高錦純、趙伯平等同志出任書記。其間,此地也成為陜西省委、河南省委、山西省委駐地,小鎮人口最多時有好幾萬。一批又一批奔赴延安的熱血青年途經馬欄到達陜北。
那時候,馬欄之夜常常是沸騰的。八一劇團的演員們在一支支火把或汽燈下演出《小放牛》《做軍鞋》等自編劇目,還常常演出傳統的秦腔戲《三滴血》《逼上梁山》等。
馬欄的清晨是激昂的。自1943年關中第二師范學校(習仲勛曾任校長)遷至馬欄,每天清晨師生們都迎著朝陽,唱著嘹亮的關師校歌等抗日歌曲出操上課。
馬欄的日子是鮮亮的。溝坡山梁河川間常常傳來勞動的號子和歌聲。大生產運動期間,分區的干部和群眾一起,開荒種田、紡線織布。分區院子的工字房成為大生產成果的展室,里面擺滿了糧食、農具。蠟版石印的《關中報》在干部軍民間廣為傳閱。
1945年六七月間,抗日戰爭勝利在望。國民黨又公然挑起摩擦,侵占我關中分區子午嶺南端的爺臺山附近的40多個村莊。中央決定組織戰斗予以反擊,任命張宗遜為司令員、習仲勛為政委,指揮部設在馬欄。
習仲勛又一次來到馬欄。他同張宗遜等同志一起,運籌帷幄,調集八個團兵力及萬余名群眾投入戰斗,一舉殲滅來犯之敵,全面收復被占區域。
1949年四五月間,彭德懷率領第一野戰軍南下,在馬欄居數日,召開了扶眉戰役部署動員會。第一野戰軍幾個縱隊在子午嶺間穿梭,而后揮師南下,解放西安、咸陽,最后將胡宗南主力包圍于扶風、眉縣一線,一舉殲滅。
從北端的大梁山,中段的小橋山至南端香山、馬欄山、爺臺山,子午嶺的山山嶺嶺、溝溝川川,留下了一批又一批共產黨人的青春、熱血乃至生命。他們的精神將與黃陵同在,與民族永隨
(胡世民薦自《學習時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