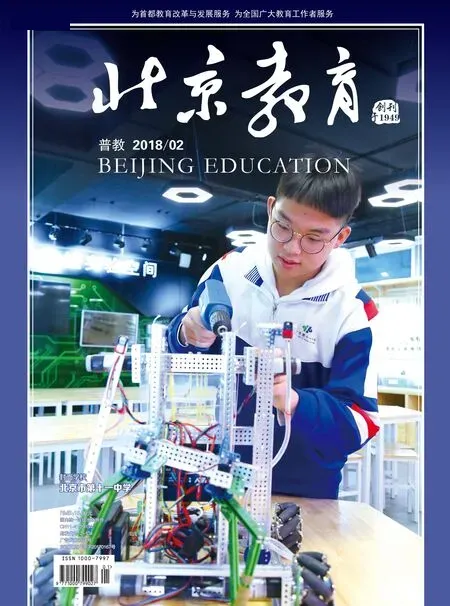新高考背景下普通中學轉型的路徑選擇
李希貴 _ 北京市十一學校校長 郭學軍 _ 北京市十一學校
2017年秋季學期,北京市進入高考綜合改革的實施階段,此次改革最大的特點就是突出對“具體個人”的尊重。“具體個人”意識的凸顯,即對每一個人的幸福人生和生命價值的關愛。高考改革使傳統學校面臨著從教育理念到課程結構,從教學內容、實施方法到管理機制等各方面的變革要求。在原有框架內的修修補補已經無法應對變革的要求,學校必須實現全面的轉型。那么,學校應該如何“轉型”呢?經過幾年的實踐摸索,我們歸納出學校轉型的基本思路。
學校價值的轉型:目中有人
“人的回歸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條件。”“從傳遞知識為本轉向以培養人的健康、主動發展的意識和能力為本,是現代型學校價值的核心成分。”在對傳統教育的反思過程中,我們逐漸認識到學生作為人的地位的存在。當把對人的關注和尊重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時,學校教育的目的就不應該只追求分數,而應該關注分數以外的、與學生的終身發展有關的綜合素養。我們提出“創造適合學生發展的教育”,這里的學生,其一,不是全體學生,而是每一位學生;其二,不是觀念層面的學生,而是一個個鮮活的學生個體。
當我們目中有人的時候,在具體的教育實踐過程中,具體的學生個體便進入了我們的視野。學生是存在差異的,他們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學習基礎水平、學習方式、興趣特長、發展的潛質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等方面,而且也表現在智力上。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的教育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在探索人類潛能的本質與實現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論。他認為人的智力是多元的,人除了有言語智力和邏輯數理智力這兩種基本智力以外,還有視覺空間關系智力、音樂節奏智力、身體運動智力、人際交往智力等其它七種智力,它們分別代表個體身上不同類型的九種潛能。正是這九種智力間的不同組合方式和結構形式構成了個體間的智力差異和潛能差異,使每個個體表現出自己的獨特性。
面對學生的個體發展差異和需求,我們認為,發現和尊重每一位學生的不同,喚醒每一位學生的潛能,啟動每一位學生自主發展的內動力便成為現代學校的責任擔當和價值追求。這種價值選擇為學校轉型奠定了思想基礎。
學校課程的轉型:自主選擇
對于普通中學而言,課程是學校育人目標、辦學理念的載體。從某種意義上說,課程決定著學校的形態,只有改變課程,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校。所以,課程變革是學校轉型的關鍵。
“課程”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教育家斯賓塞的《什么知識最有價值》一書中,它是從拉丁語“Currere”一詞延伸出來的,它的名詞形式意為“跑道”,可見課程就是為不同學生設計的不同跑道;而它的動詞形式意為“奔跑”,這樣一來,課程的著眼點就會放在個體認識的獨特性和經驗的自我建構上。如此理解,課程的更深層次價值在于,尊重每一個特定學生的需求和不一樣的成長方式。如果我們能夠在可能的情況下更多地開辟適合每一位學生“奔跑”的道路,就能夠幫助每一位學生找到自我。
以滿足每一位學生的需求為主旨,我們通過國家課程校本化,在融合國家課程必修要素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套可供學生選擇的分層、分類、綜合、特需課程體系,既有理科的分層次課程,也有文科的分類型課程;既有綜合的藝術和綜合實踐課程,也有專項的技術和藝術課程;既有理性思辨的課程,也有實踐體驗的課程;既有補弱的課程,也有提升的課程。除此之外,我們還設置了一對一的特需課程,如小學段的援助課程、書院課程等。這些課程的設置,有的立足于學生不同的發展方向,有的立足于學生的興趣愛好特長,有的立足于未來專業或職業傾向的引導等,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自主選擇。
學校教學組織形式的轉型:走班上課
與選擇性課程相適應的教學組織形式是走班上課,每位學生按照自己的課表安排,到相應的教室上課,而教師,則各自在固定的教室里等待學生上課。走班上課打破了以行政班為單位的上課方式,轉變為以不同的課程形成的教學班。與行政班授課方式相比,這種教學組織形式,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行政班教室轉變為學科教室。為了讓資源更貼近學生,更好地服務于學生的學習,我們把傳統的教室建設成了集上課、閱覽、實驗、討論、教研等多功能為一體的學科教室,學生每天在不同的學科教室之間流動。學科教室以任課教師的名字命名,它既是學科教師授課和學生上課、討論、閱讀、上自習的地方,也是教師備課、辦公和答疑的地方。
第二,學生沒有固定的教室和課桌。為方便學生存放學習用品,學校在教學樓的走廊里為每人準備了1-2個柜子,供學生放置個人學習、生活用品之用。學生每天帶著課堂需要的學習用具和學習資料,按照課表,在不同的教室之間流動。
第三,以教學班為基本單位進行集體授課。由學生選擇課程而形成的教學班,成為學校的基本單位。通常情況下,一位學生本學期選擇了幾門課程,就會有幾個教學班。同一年級的不同學生,甚至不同年級的學生因選擇同一門課程而走進相同的教室,成為一個教學班的同學。教學班存在的時間長短隨課程而定,課程的結束即教學班的結束。
第四,學生處在各種教育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影響之下。選課走班擴大了學生的交往范圍,同一教學班級不同學習層次的學生間,專業任課教師與學生之間,導師、咨詢師與學生之間以及家長與學生之間等存在的關系構成學生成長的環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對學生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
學校管理模式的轉型:從管理到領導
課程及其實施過程的變革,凸顯了學校教與學的需求,迫使學校管理重心下移,形成扁平化組織結構,實現從管理到領導的深層次變革,為可選擇的課程體系提供實施的空間,真正實現學校的整體轉型。
1.建立師生導向的扁平結構
選課走班帶來了教學組織形式的變革,同時,也對學校的組織結構提出了變革要求。要讓師生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得以反應,就需要調整組織結構,壓縮學校組織結構層級,建立“扁平化”組織管理結構。在扁平的組織結構中,校長直接面對學部,副校級的干部兼一個年級或部門的主管。這樣,確保師生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得以反應。
這種扁平結構有如下三個特點。第一,強調服務第一,師生導向。我們倡導管理者就是服務者的理念,強化服務意識,充分尊重教師與學生的發展需求。第二,以“舒服”為取向。扁平結構強調發揮每一位成員的創造才能,讓每一個人都感到很舒適。第三,營造“簡單”的學校文化。學校一切的活動和資源都圍繞教與學而展開和安排,學校教育的目光聚焦在每一位學生身上。
2.建立多種激勵機制
在學校變革的過程中,我們非常注重組織成員的參與,強調喚醒組織成員的主體性,調動人的潛能和主觀能動性,從管理走向領導。為此,我們通過各種平臺和途徑,構建一套多元的教師激勵機制。
第一,把檢查和評價分開,淡化和慎用評價。一方面,將評價轉變為診斷。評價需要進行價值判斷,而診斷主要是幫助教師查找問題,目的是為了改進工作。例如,學校每個學期組織一次學生層面的調研,這項工作在過去叫“評教評學”,淡化評價后,我們改為“教育教學情況調查”。另一方面,將檢查與評價分開。在學校工作中,有些事情可以檢查,但不要評價,如教師的備課;有些檢查需要認真仔細,但評價卻不要太計較,如對學生的常規檢查。
第二,搭建各種平臺,讓每一個人的長項和創造才能都能得到施展。學校創造各種機會,運用多種方式,發現并展示每個人的閃光點,促使其自覺、持久而穩定地提高工作績效。例如,在管理模式上,學校借用管理大師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提出的“分布式領導”的理念,在年級實施“分布式領導”的管理模式,將各種管理事務進行項目分類,形成咨詢師、過程性評價主管、終結評價與診斷主管等崗位。這些分布式領導項目由年級的任課教師根據自己的專長主動承擔。此外,學校的職業考察課程、學生社團以及不同類型的學生研究性課題指導教師、學校課程研究院的學科兼職研究員、教育家書院的兼職助理等崗位,也為各學科學術拔尖的教師搭設了施展才能的平臺。
第三,重視教師的職業規劃和專業成長。學校充分考慮教師發展的不同需求,設置多層次、多類別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供教師選擇。為了減輕行政命令式的專業成長可能帶來的壓力和負擔,因此,學校盡量以學術的而非行政的方式推進,激發教師自主提升的愿望和需求,變被動成長為主動成長。學校還充分挖掘各種資源,牽線搭橋,創造條件幫助教師進入各種學術組織、研究機構等,讓他們在校外的學術領域中快速成長。
第四,建立溝通、對話、協商的機制。與管理的行政命令不同,領導更注重通過與組織成員建立關系,運用這種人際影響力去達成目標。在學校,我們一般不太主張提“執行力”,因為在學校轉型性變革中的大多事情需要商量著來做。例如,學校建立的導師、咨詢師和教育顧問制度與過去的班主任管理方式不同,這些崗位更注重通過溝通、協商的方式,一對一地為學生提供各種幫助、服務、咨詢和引導。
學校教師的轉型:從教到學
葉瀾教授指出:“學校轉型不僅是教育實踐的變化、培養目標的重新構建和實現,而且是教育者自身的發展變化過程。沒有一線教育實踐工作者自身的變化,要實現轉型是不可能的。”在學校轉型性變革中,教師需要經歷從教到學的轉型,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觀念之變。當課程變革觸及到每一間教室、每一個課堂的時候,當學生的自主選擇性被調動起來之后,教師的觀念必須轉變。經過痛苦的蛻變,越來越多的教師逐漸認識到,教師要從一個教育者轉變成為學生成長的服務者,但人的觀念轉變是最深層的變化,需要很長的過程。
第二,思維方式之變。變革更多的是對舊的思維習慣的挑戰,在挑戰中必然會面臨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可以參考借鑒的經驗。面對改革中出現問題,我們倡導用改革的方式解決,項目研究便是一種改革的方式。項目研究不僅讓學校的教科研取得豐碩成果,而且真正貼近實踐一線的需求,幫助教師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項目研究幫助教師形成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即從課堂的微觀層面跳出來,站在課程和學科等宏觀的立場上思考問題。
第三,專業素養之變。過去,教師只是一個單純的任課教師的角色,現在要承擔科任教師、導師、咨詢師和分布式領導等角色,而多重角色需要相應的多種素養支撐;過去,教師管好自己的課堂就行了,而現在每位教師的教育和管理的責任大大增加;過去,教會學生就行了,而現在要教學生會學,要管理和領導學生的學習,幫助學生做計劃、檢測,掌握方法,還要幫助學生描繪愿景、確定目標;過去,教師只是課程的實施者,而現在,教師不僅要研究教與學的方式,還要設計和研發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課程,開發相關的學習資源,這需要教師具有相當強的課程研發能力和專業學術能力。
第四,管理與教育方式之變。過去,教師常常是以“警察”的身份,靠行政權力,以自己認為合理的方式去管理學生。而選課走班之后,當學生與我們平起平坐了,當學生有了自主發展的愿望和動力后,他們需要的不是“管”“堵”“罰”等管理手段,而是咨詢、服務、引導和陪伴。過去,我們總是對學生不放心,不敢放手,而真正給學生提供空間之后,學生表現出的能量讓我們感嘆。這樣的看法在慢慢改變著過去對教師學生的很多固有認識,并重新思考教與學的關系。
第五,職業尊嚴之變。過去,教師的職業尊嚴來自教學設計的環環相扣,以及教師個人多年的教學經驗散發的個人魅力,等等。而現在,當把課堂還給學生,當教師成為學生成長的服務者,教師的職業尊嚴能從哪里尋找?首先,新的“權威”需要從了解走向理解,從理解走向信任。如果我們只是僅僅了解學生,而不是深深理解他們,那就沒有信任,沒有信任就沒有教育。其次,我們的職業成就感還存在于對國家課程標準進行可操作化的分級分解,給學生提供能抓得住的“拐杖”,讓學生自主學習時心中有數。第三,尊嚴還在于幫助學生喚醒沉睡的潛能,厘清未來的發展方向;在學生遇到困難和問題時,隨時提供有用的咨詢和建議;成為學生成長的陪伴者和看護者……
本文系2013國家科技部軟科學研究重大項目(編號2013GXS3B047)和北京市綜合教育改革實驗(京教函[2010]702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