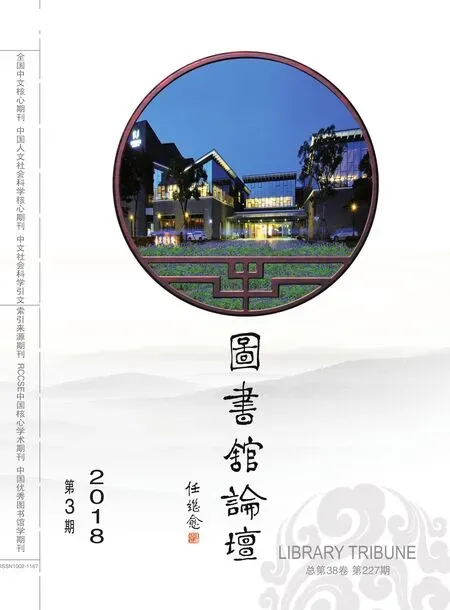觀念、形態、功能視閾下的圖書館空間重組*
王正興,徐紅玉
0 引言
20世紀末,我國大部分圖書館建筑的新建與改造,完成了紙質文獻從“藏閱分離”到“藏閱一體”“流閱分離”到“流閱一體”以及不同載體文獻從“分離”到“一體”的空間重組。當今互聯網+環境帶來了后數字圖書館(Post Digital Library)時代[1],“第三空間”理論使圖書館空間觀念不斷更新,功能定義不斷被拓展,圖書館的“空間重組熱”①再度興起。目前我國眾多圖書館正在投入熱情和經費進行新一輪的空間重組,但也出現了一些不符合自身辦館宗旨的跟風和不切實際的“高、大、上”追求現象。本文從哲學視角的觀念空間、建筑學與信息科學的形態空間以及圖書館學理論的空間布局3個方面研究圖書館空間重組中的若干問題,試圖厘清圖書館在空間重組中應秉持的理念、堅持的原則、把握的方向,以期為各級各類圖書館空間重組實施提供多視角的理念借鑒和決策參考。
1 觀念空間特點
觀念空間是屬于認識論范疇的一種主觀與客觀的意識(精神)空間[2]32。圖書館觀念空間是人們對圖書館空間形態與功能的主觀與客觀認識的系統化集合。這種集合在圖書館空間重組的理論與實踐當中,又表現為一種對空間創設的功能理解、對空間再造的理念追求和空間重組的思路拓展。圖書館社會性質特點及圖書館職業能力優勢決定了圖書館觀念空間3大基本特性。
1.1 優越性
圖書館觀念空間具有顯著的優越性。首先,表現為圖書館空間重組具有鮮明的社會規定性:(1)圖書館是人類創設的一種空間。(2)在人類創設圖書館之始,已經賦予了它文獻存貯空間功能。(3)國際公認的圖書館保存文化遺產、實施社會教育、傳遞科學情報、開發智能職能,規定了圖書館對應不同用戶需求重組的各類服務空間都應圍繞這4項基本職能展開。這3方面的規定性,保證了圖書館空間重組的概念不易產生分歧,也就不存在方向性含糊。其次,“知識是當代圖書館學的核心概念”[3],闡明了圖書館在人類信息—知識—智能轉換[4]活動中的“知識空間”屬性和獨特的“樞紐”地位。這樣的屬性和地位使圖書館觀念空間有了一個比較高的理論起點,也決定了圖書館空間重組“觀念上”的原則立場,驅動著圖書館在不同社會人文和科技環境下關注空間變革,尋求適應時代變化的功能定位。
1.2 敏感性
圖書館觀念空間具有強烈的敏感性。這種敏感性表現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圖書館對空間形態功能不斷完善的職業化探索過程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圖書館走過了從靜態文獻載體在實體空間的保存、組織、管理、揭示,到動態數字文獻在虛擬空間的存取、整合、挖掘、發現歷程;經歷了從實體空間到虛擬空間、復合空間的形態發展與轉換。近年來,一方面,圖書館不僅重視物理空間的容量,還關注空間環境建設與人的精神空間關系,強調通過注入文化元素,讓知識傳播在一種美好的文化環境里進行[5-6]。在技術層面上,通過現代技術運用,特別是網絡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發展了智慧圖書館的探索[7],這種文化的,智能的空間研究,讓圖書館的空間重組又注入了新的內涵。另一方面,針對新一代用戶需求的特點,從傳統閱讀空間轉向體驗空間、從學習空間拓展到創客空間,重視并提供“新型學習工具”[8]以服務用戶間交流互動,也成為一種趨勢。正是這種職業敏感性,為圖書館空間再造與重組植入了與時俱進,理論與實踐不斷創新的良好基因。
1.3 包容性
圖書館觀念空間具有廣闊的包容性,表現為理論探索與實踐操作的多元化取向。
第一,哲學上的空間觀為圖書館的空間重組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索加建立的“第三空間”概念②,從根本上回答了圖書館空間重組的多元性問題。哲學上的空間價值觀強調空間的價值需要落實到社會活動中才能真正展現,“忽略了行動者對于空間存在的價值,空間觀念必將被重塑”[9]60,解釋了圖書館空間重組的社會價值意義。享利·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三層次理論③,指出了人類空間創設(包括圖書館空間重組)的現象、過程及一般趨勢。
第二,建筑空間觀是圖書館空間重組的主要依據。建筑空間的整體觀,強調根據建筑各功能空間的使用人群、活動類型、私密性等要求,進行合理有據的歸納分類,成組成群,并設定符合要求的空間單元……通過聚集、組織形成彼此聯動的網絡整體[10]56[11]。在空間單元重組中,并列空間的“分離”、共用空間的“疊加”、層級空間的“嵌套”都要遵循“序”“元”論[10]56,構成新的空間秩序,這些都為圖書館空間重組的布局與整合理清了思路。另外,實驗建筑觀念空間的“場所論”[12],啟發圖書館空間從“藏”的功能實現向“用”的功能發揮,再向人性化“場所”功能重組拓展,是圖書館空間重組趨勢在建筑學意義上的有力闡釋。
第三,信息空間(INFOSPHERE)是一個三維空間,將是人們進行交流、活動的一個新的場所[13]。正是信息空間的這個基本概念與當代圖書館追求的空間目標功能的契合,使信息空間觀成了圖書館空間重組的始作俑者。一方面,信息空間理論主張對空間的認識應該從物理視角向社會視角、關系視角和行動者網絡視角轉換[9]59,拓展了圖書館人的研究視野,擴大了圖書館對互聯網時代空間概念的理解,移動圖書館、泛在圖書館、虛擬圖書館的研究和實現,使圖書館徹底從實體空間走向了復合空間。另一方面,信息空間有著將所有的人與所有的知識集中到一起(Vlahos,1998)的潛力,信息空間的內聯互動對真實世界就像放射性對大氣層一樣(DerDerian,1996)[14]有著巨大魅力,引導著圖書館學在知識積聚、知識關聯、知識交流、用戶互動方面探索,推動圖書館致力研究網絡社會中的虛擬社團,專家網絡、網絡聯盟,以及共享空間、創客空間。
觀念形態上的優越性決定圖書館對待空間重組的態度與立場;敏感性反映了圖書館人對空間重組的創造性和熱情,也確保了重組與時俱進;包容性決定空間重組的豐富和多元,也給圖書館空間重組帶來開闊的視野和活躍的思維。優越性、敏感性和包容性共同構成圖書館空間功能重組的理念與動因,也是圖書館空間重組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的源泉和觀念支撐。
2 形態空間關系
圖書館的空間形態,決定圖書館運營情境和空間服務方式。可以運用哲學上的范疇概念,對目前圖書館空間的一些空間組織形式進行一番梳理,進而研究圖書館的各種形態空間關系,指導空間重組實踐。
2.1 “靜態空間”與“動態空間”重組的辯證認識
廣義的圖書館靜態空間,是指圖書館空間內的聲靜、人的心靜和設施布置的相對靜止。聲靜是圖書館作為公共空間上的環境要求,是為人的心靜創造條件。傅斯年說過,“一天只有21小時,其余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沒有安靜的環境,學者的沉思,習者的反省是不可能的。設施的相對靜止是指圖書館的空間布局從書架安裝到圖書定位,再到服務空間組織要相對穩定(因為畢竟設備的大動是勞命傷財的,更是不利于用戶習慣性利用公共設施的)。
在傳統圖書館里,一個“靜”字幾乎成了圖書館空間的特色符號。然而,“靜”又是相對的,“動”才是絕對的。從人的行為上區別傳統圖書館與未來圖書館空間,本質就是“靜”與“動”的轉變。傳統圖書館的靜囿于傳統文獻載體和圖書館服務方式的單一性,現在圖書館的“動”,則是源于信息的“流動性”、知識的“交互性”和圖書館啟發人的“智力創造”要求。現代圖書館專家認為,好的圖書館空間是指圖書館經過反復調整,并將其調整到讀者認可的最理想狀態的圖書館物理空間的集合[15]。在這個意義上,圖書館空間重組的追求是永動不停的。當代圖書館學對用戶行為認識的突破,在聲音上對空間的要求也不是絕對強調靜的。比如,在面向廣大學習型公眾的圖書館空間里,從用戶的學習習慣考慮,專門設立討論區,朗讀區,制造一種動態的學習情境也同樣有很好的空間效果。另外,在面向思想碰撞、科研創新的圖書館公共空間里,則需要為用戶提供更多的交流互動機會,讓知識、思維、精神流動起來。還有,從空間的可組合角度看,空間組織的多元化、復合式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更表現為一種“靈動”。所以,圖書館的空間重組,應該在傳統的“動靜分離”不合理布局上做文章,要從圖書館的主動服務、參與式服務和用戶的自我服務、相互服務角度去重組舊空間,創設新空間,而不是一味強調“內外分開”“鬧靜分開”“不同讀者的閱覽室分開”的原則[16]7。
2.2 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組合從資源特點考慮
關于圖書館的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Victor Zverevich曾先后下過兩個定義:實體空間是“所有存放印刷資源及傳統圖書資料載體,并提供讀者服務的物理空間的集合,在這個空間里也進行所有圖書館的業務運行,是各種技術及通訊活動的發生場所”;虛擬空間是“包括web服務器、計算機內存及存儲空間、通訊頻道、無線wifi等用于支持讀者訪問圖書館的數字化資源的不可見的圖書館空間”[17]。仔細推敲Victor Zverevich表述的這兩個空間區別,一個是空間形態的“功能類型”,另一個是資源類型的“利用形態”。它啟發我們:圖書館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的重組就是要歸結到有形與無形的資源在有形與無形的空間里的合理組合利用。
20世紀末,圖書館實體空間建設曾經為有形資源的快速增長和用戶的大量增加經歷過一個新建與擴建高潮。經過近20年的發展,圖書館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的收藏比例、用戶的資源利用方式和空間利用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圖書館的空間價值已經從收藏利用轉向場所服務[16]5。從這個角度看,圖書館的空間重組需要從館藏資源的利用特點考慮。在面向廣大學習型用戶的圖書館里,應該將建設重點仍然放在實體空間組織上,一般學校圖書館應以滿足讀者學習,中小型公共圖書館應以適應全民閱讀的實體空間建設為重點,而不是一味追求虛擬空間建設的高大上。這是因為圖書館虛擬空間只有在強大的數字資源支撐下才能凸顯人的主體性、想象力和構造力。如果一個中小型圖書館并無重要國內外數據庫,而花大投入建設虛擬空間,無疑是舍本逐末的。反之,在重點大學與研究機構圖書館的空間重組過程中,則應強化虛擬空間建設,強化重要學術資源數字化服務的技術含量,著力在虛擬空間重組上做文章,向機構知識庫、智庫,虛擬學術團隊方向組織實施。當然,中小型公共和學校圖書館積極創造條件加強虛擬的移動圖書館、數字圖書館報導性服務,重點大學與研究機構圖書館實體空間的不斷優化也是圖書館事業整體發展的需要。
虛擬空間在空間上總是同時與實體空間、想象空間相互關聯的。圖書館的實體空間體現為“實在性”,能夠讓人類的知識獲取有一個平等、自由的公眾場所,是圖書館定義的本源。圖書館的虛擬空間表現為“自在性”,能夠讓人類的知識活動表現力得到極大的顯現和張揚,使創造者和被創造者融合為一[2]34,是圖書館概念的擴張。將“實在”的圖書館建筑空間與“自在”的圖書館虛擬空間有機結合,科學重組,這是當今圖書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2.3 物理空間對精神空間作用與服務對象特點關聯
圖書館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它的文明精神、文化精神表現為一種特定的“場”[18],這個“場”就是圖書館物理空間表現形態。圖書館的精神空間是圖書館用戶對圖書館物理空間的“場效應”的精神感受,包括視覺的、心理的認知體系。研究圖書館物理空間對用戶精神空間的作用,要從強調人對空間的構建到注重空間對人的精神的影響出發,關注從傳統空間的文化形態之間的沖突到重建多元文化形態的和諧共處,追求圖書館社會功能滿足“高質量的物理空間與實體感官的需求”的人文性特征[19]。
在圖書館空間重組設計中,第一,圖書館物理空間的“場所精神”④體現要有對象性,要針對不同對象的方向感,認同感,歸屬感[20]去建構各具特色的物理空間體系,發揮空間影響人、塑造人的功能[21],而不是一味追求氣派豪華,跟風雷同,誤入盲區。國內圖書館的同仁們到國外一些圖書館參觀,常常最感嘆的就是國外圖書館建筑空間的獨特場所精神,這是我國圖書館界在新一輪空間重組中應當借鑒的。第二,精神空間的效用主要是通過人的審美情趣在物理空間實現的,圖書館空間重組應特別注重室內陳設的“氣質”和“個性”把握,應以體現服務不同用戶對象的人文精神內核為依據設計室內主題,合理地把握材質、色彩、燈光等設計要素,讓空間傳遞出不同的情感氣氛,創造情感空間以影響塑造人的精神空間[22]。近年江蘇地區南京師范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圖書館的空間改造正是秉持了這一理念,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受到了廣大讀者熱烈歡迎。第三,強調物理空間與精神空間的契合,倡導將圖書館物理空間的社會性和交互性最大化[23],即根據不同類型圖書館的性質和與服務對象,以物理空間的開放性、多元性、關聯性組織(如展覽空間、講座空間,Living Library空間,閱讀輔導空間、閱讀治療空間),促進各類用戶和圖書館人精神空間的豐富,形成連接一切的理念,包容一切的胸懷,繼承傳統的信念。真正使圖書館成為物理空間與精神空間虛實關聯的社會“文化教育廣場”[24]。這將是我國圖書館空間建設的一個重要探索方向。
3 功能空間定位
傳統圖書館的設計被早期的標準化圖書貯藏辦法和閱讀設置所左右,在功能分區上緊緊圍繞著藏書數量和閱覽流通方式展開,其結果形成為書用和為人用的兩種截然不同特征的空間,書和讀者在一種靜態的狀態下互不相關。現代網絡通訊和計算機技術顛覆了這兩種不同空間獨立存在的形式,并將改變圖書館空間的社會化功能,也暴露出目前一些圖書館空間存在的幾個具有普遍性的矛盾:超高氣派、不適用的物理空間與日益完善的虛擬空間應用的矛盾;研究包間的功能萎縮與共享空間崛起的矛盾;大開間孤島式包圍工作臺、流通借閱臺的過份寬敞與用戶自由活動空間擁擠的矛盾;大規模電子閱覽室的冷落與全媒體互動式學術文化空間缺失的矛盾。針對這4對矛盾,圍繞空間重組策略,本文從功能空間的定位視角展開討論。
3.1 目標功能空間與圖書館性質的呼應
如前所述,圖書館空間從社會職能角度可以分成4個層次的目標空間:一是對應保存功能的檢索空間;二是教育功能的閱讀空間、學習空間;三是情報功能的研究空間;四是智力開發功能的創意空間、智能化空間。但是,不同圖書館的目標功能空間又因辦館性質任務不同有其側重。
就檢索空間而言,現在傳統的卡片式目錄柜基本不用了,圖書館大廳更寬敞了,在保證機器檢索必要空間的前提下,重組大廳空間,加強人文化裝飾、增加休閑活動區、增設人性化設施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然而,這里有一個與圖書館性質呼應的問題,比如,大廳空間的人文化裝飾,在一些大型公共圖書館里,卡片式目錄柜其實就是一種具有歷史感的人文裝飾;在一般公共圖書館里,電子報紙、新聞性電子屏又是首選的普適性人文裝飾;在高校和研究機構圖書館里,揭示大學精神、反映文化底蘊,鼓勵科學探索的裝飾主題能使其人文價值更能凸現。因此,不應所有圖書館不分類型、不顧性質都去追求“賓館化”“高大上”。又如,教育、情報、智力開發功能空間是不同性質圖書館各有側重的三種基本空間,圖書館根據用戶變化的需求、辦館任務的要求調整和變革這些基本空間,進行一些空間重組無可非議,但也有一個與圖書館性質呼應問題。例如,在全民閱讀熱中,一些公共圖書館擴大了專門閱覽室,設立國學經典閱覽室、必讀書目閱覽室,增加了老年、兒童讀書空間,但在高校和研究機構圖書館是不是就一定有必要擴大閱覽區域或者針對某一專門活動開辟專門閱覽室呢?以高校圖書館為例,現在多數高校館各種大型閱覽室動輒上千平方米,但使用情況并不盡如人意,不管你用何種方式組織室內藏書,多數學生讀者還是把它當作自習室,可見高校圖書館的目標功能空間重組的切入點,并不一定要在閱讀空間重組上做文章。還有,在當前的創客空間熱中,不僅研究圖書館、大中型公共圖書館在建,普通高校圖書館在建,甚至一些小型館也在建,并且都以3D打印機等現代技術運用為追求。Slatter和Howard分析認為,并不是所有的圖書館都需要建設創客空間,況且創客空間也只是吸引了一部分圖書館用戶而已[25]。再者,現在社會上以及許多高校的創業指導機構、實驗、實踐基地也都在創設創客空間或類似功能的空間,這些空間在設備配置上比圖書館更專業,在實驗、實踐條件上比圖書館更優越。圖書館究竟應該建設什么樣的創客空間?什么性質的圖書館應該建設什么樣的創客空間?這是當前圖書館功能重組中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但有一點毋庸置疑:目標功能空間重組不僅要“與時俱進”,更要“量身定制”。
3.2 特色功能空間對辦館特色的彰顯
特色功能空間是指圖書館圍繞辦館宗旨,針對不同用戶需求創建的具有本館特色的空間設置與組合。從活動范圍上可分為公共空間、私密空間;從活動形式上可分為交流空間、體驗空間、休閑空間、展覽空間等,這些空間在不同類型的圖書館里又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彰顯圖書館的辦館特色。
特色功能空間的“特色”可以從兩個方面考察:一是圖書館目標功能實現在空間組織上的特色化,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科學圖書館[26]11沒有設置單獨的大型閱覽室,而是將閱讀座位分散分布在整個建筑空間的各個角落,且座位都臨窗而設,以便讀者自己選擇合適的位置和適宜的學習環境,做到既可投入多人學習的氛圍中,也可獨處一隅靜心研讀,以適應當代大學生自主式、多元化學習方式。像這樣的一種有特色的空間組織設計方式,對重組圖書館閱覽空間就是一種啟發。二是超越、延伸圖書館“書文化”核心服務功能的“空間服務”的特色化,如公共圖書館根據社區民眾的特點,以社團組織活動和社區集會場所的目標功能進行的一些空間服務;高校圖書館以教育模式和學習方式的轉變為基礎,為教師、學生和其他研究者創造的各種更適宜的學習空間、Living Library空間、閱讀輔導空間、閱讀治療空間、創意空間、體驗空間等空間服務,在江蘇大學圖書館,擁有數百臺電腦的“電子閱覽室”被改造成了ACCA(國際注冊會計師)、HSK(漢語水平考試)等專門閱覽室和考點,一些研究包間也被改造成了研究生工作室、信息行為實驗室等,既解決了一些不合時宜的功能空間長期閑置問題,也體現了該館新的辦館特色。這方面新加坡各類圖書館有很多經驗可供參考借鑒[27]。
相同目標功能的空間創設與重組,也應追求特色。還是以創客空間建設為例,美國許多大學的圖書館都有創客空間,但他們的各自的特點又十分鮮明[28],我國的一些公共圖書館在這方面也探索出了一些經驗。例如,上海圖書館的“創·新空間”、成都圖書館的“閱創空間”、長沙圖書館的“新三角創客空間”[29]集閱讀、討論、共享、展示、制造等功能于一體,強調圖書館創客空間作為信息交流分享中心的特色。總之,圖書館只有圍繞辦館特色,通過塑造“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特色空間,才能體現空間重組的目的意義和社會價值。
3.3 組合功能空間與建筑特點結合
圖書館空間重組的狹義“重組”就是融合多視角的新理念,根據圖書館服務方式的新變化要求,形成對原有建筑空間整合的新思維,實施多重功能空間組合的新布局。
以共享空間IC為例,就有若干種理念引導的不同組合方式:如學習共享空間(LC)、學術共享空間(RC)、知識共享空間(KC)等。不同類型的共享空間組合,最根本的是要從創設互動型服務空間的新思維出發,以空間、資源、館員融為一體的互動形式,組合個性化服務與學習交流相結合空間,去解決前文提及的現有建筑空間設計布局存在的4種突出的矛盾現象。第一,從建筑空間的組織方式角度研究空間區劃的重組,在原建筑結構允許的情況下,將大小、尺度、形式各不相同的信息空間,采取一些改造措施,使空間實現最自由的組織形式,形成多維豐富的空間層次。比如,荷蘭烏德勒支大學圖書館利用地型地貌特點,將空間劃分為若干區域,設計若干分散好比云朵的藏書庫,圍繞書庫擺放閱覽座位,各種大小和比例的閱覽空間穿插在同一個完整的空間中,形成多維變幻的空間組合,值得借鑒。第二,針對原有建筑空間“全程服務”的線性服務流程設計特點,向“即時服務”的點式[26]12服務進行重組。實體空間的格局也許形體固定,難以改造,但在細節的重組上可以補救,如在每一個服務點都考慮信息技術利用與圖書館服務的有機整合共享,讓OPAC電腦遍布各個角落,甚至可以將液晶屏幕的OPAC安裝在書架上,并將電腦屏幕保護設計為新書書評或熱門圖書介紹。第三,建筑學意義上以空間功能劃分的服務空間與被服務空間整合理論[30]對于圖書館空間重組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許多圖書館在服務空間改造的同時考慮被服務空間的拓展和優化,通過一些設施改造縮小服務空間,在樓梯轉角、走廊增設閱覽椅,既增加了被服務空間,又做到服務空間與被服務空間的融合。在南京大學杜廈圖書館、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以及新近改造的江蘇師范大學圖書館,都能看到這些結合建筑特點重組服務空間與被服務空間的成功范例。從圖書館以讀者為中心宗旨角度看,可以通過服務水平的提高來調整以對象劃分的服務空間和被服務空間,加強兩種空間的相互聯系與轉換,并追求兩種空間界限的消融。現在許多圖書館拆除大開間孤島式包圍的工作臺、壓縮過份寬敞的流通借閱臺(如江蘇的淮海工學院圖書館),正是這種思想在空間重組中的表達。
3.4 拓展功能空間與發展規劃匹配
“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會生產出自身的空間。”[31]圖書館的拓展功能空間是圖書館在網絡時代協同創新生產方式下,功能定位和變革的趨勢空間和愿景空間。隨著新空間理念的引入,新的圖書館空間形態將在以下幾個方面拓展:(1)場所化拓展:后現代建筑觀念空間的“場所論”[12]110強調,作為場所的建筑不僅是某種圍合的空間,而且也是某種文本、符號,是通過建筑整體中人的參與,強調人的“到場”,以創設一種發現人的價值的“場所”。即,未來的圖書館空間將突破“館”的概念,而立足于行動者角度的社會空間。今后以用戶的活動方式、參與方式為“場所”的空間形態將不斷涌現,如公共圖書館的文化廣場、研究圖書館的嵌入式協作化知識實驗室[32]等。(2)流空間引入:場所空間的交流是有限的,流空間理論打破了固定空間的局限性,讓信息時代圖書館的空間具有了“彈性”,激勵圖書館借用開放且無限延展的網絡力量,將人、活動、空間及其關系放到一個大背景下去組織不同空間尺度的流動和共享型空間[9]62。一些創新型空間,如虛擬團隊空間、合作網絡空間,將通過要素的快速流動來實現不同行動者占有不同的信息資源等關鍵性要素,獲得建構關系空間的先機,它帶給用戶的將是超越文獻信息服務、知識發現服務的“關系空間”服務。(3)智能化趨勢:韓國延世大學“U-服務圖書館”,是集U-休閑、文化和IT設施等為一體的復合智能空間,被認為是世界首家圖書館智能空間[33]。在新一輪空間重組中,我國諸多圖書館開始采用RFID、探索物聯網等智能技術運用,如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在IC2理念成功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到2020年實現觸手可及、靈活感知的“泛在智能圖書館”,該館的自助服務的整體設計框架在實踐嘗試中取得了良好的應用效果[34]。
圖書館拓展功能空間取向是多元的。具體到某一類、某一所圖書館,空間重組的拓展究竟應從哪個角度首先拓展突破,受到眾多客觀條件限制,也與辦館方向和目標緊密相關,需要做到既有前瞻性,與本館的發展規劃匹配、發展目標一致,又要接地氣,立足當前圖書館的性質、任務,與辦館實際及具體條件接軌,還要注意傳統統功能的堅守,在保留圖書館“書文化”核心服務功能的基礎上拓展,切不可脫離人力、物力、財力實際,追求時尚與高端。
4 結語
任何一所圖書館在空間重組實施時,都應以一種明確的觀念空間為主線,一定要圍繞圖書館的基本職能,以一種包容的心態、前瞻的胸懷,腳踏實地去創設重組新空間;做到在空間限定上從清晰到模糊,空間組織上從靜態到動感,空間界面上從藝術表達到為人設計。圖書館空間布局上不僅跟隨功能和技術的發展不斷演進,更要聽取用戶意見,努力滿足用戶行為方式,經受用戶和館員的評鑒并適時調整。惟其如此,圖書館的空間重組才能伴隨圖書館這個有機體的生長,充滿多元發展的活力。
注 釋
①本文討論的空間重組為廣義概念,包括空間創設、空間再造與空間重組。
②索加在Third 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中認為,第一空間是固定在具體物質性上的;第二空間是在觀念中的構想;第三空間是真實性和想象性并存的多性質空間。
③《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揭示了空間的社會關系:一是空間實踐;二是空間表現;三是再現的空間,再現后的空間是數量的、流動的和動態的。
④“場所精神”乃古羅馬的一種觀念,即任何“獨立”存在的事物都有自己的守護神,場所也一樣。它是由自然環境和人造環境所結合的有意義的整體,具有自己的獨特氣氛,場所所聚集到的意義構成了場所的精神。
[1]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post digital library future workshop[EB/OL].(2013-10-04) .[2017-04-12].http://www.Sis.pitt.edu/~dlwkshop/.
[2]張之滄.論空間的生產、建構和創造[J].學術月刊,2011(7):30-36.
[3]王子舟.圖書館學基礎教程[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59.
[4]鐘義信.知識論核心問題——信息—知識—智能的統一理論[J].電子學報,2001(4):526-530.
[5][21]段小虎.重構圖書館空間的認知體系[J].圖書與情報,2013(5):35-38.
[6]Will Sherman.ReasonsWhy Librariesand Librariansare StillExtremelyImportant[EB/OL].[2015-03-10].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12/13/18020_364778.shtml.
[7]王世偉.論智慧圖書館的三大特點[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2(6):22-28.
[8]Janet L. Balas. Do Maker spaces Add Value to Libraries?[J].ComputersinLibraries,2012,32(9):33.
[9]董超,李正風.信息時代的空間觀念——對流空間概念的反思與拓展[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2):59-63.
[10]杜小輝,宋昆.空間單元的雜陳藝術——一種建筑空間解構重組的設計邏輯[J].新建筑,2015(3):56-59.
[11]林嶸,張會明.探究建筑空間組織方式——論空間單元的重復與組合[J].建筑學報,2004(6):35-37.
[12]王彥章.觀念空間的情感交流——實驗建筑的理念闡釋與審美反思[J].天津社會科學,2006(5):108-111.
[13]信息空間—搜狗百科[EB/OL].[2017-04-08].http://baike.sogou.com/v7793543.htm?fromTitle=%E4%BF%A1%E6%81%AF%E7%A9%BA%E9%97%B4.
[14]華薇娜.基于信息的三個空間理論述要[J].圖書館雜志,2003(4):2-4.
[15]肖小勃,喬亞銘.圖書館空間:布局及利用[J].大學圖書館學報,2014(4):103-107.
[16]肖瓏.后數圖時代的圖書館空間功能及其布局設計[J].圖書館情報工作,2013(20):5-10.
[17]Victor Z.Real and Virtual Segmentsof Modern Library Speace[J].Libraryhi techNews,2012(7):5-7.
[18]高新陵,王正興.生命不會終止——圖書館存在下去的N個理由[J].圖書館雜志,2012(2):10-13,59.
[19]趙乃瑄,王正興.基于空間整合的交互式高校圖書館網站設計理念與框架[J].圖書情報工作,2015(11):42-47.
[20]許建業,楊亮,張天穎.基于場所精神的圖書館空間應用之理論模型研究[J].圖書情報研究,2013(2):15-17,12.
[22]胡玲玲.論室內陳設藝術的精神空間構建[J].設計,2016(7):80-81.
[23]Will Sherman.33 Reasons Why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are Still Extremely Important[EB/OL].[2015-03-10].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12/13/18020_364778.shtml.
[24]Aabo,S,R.Audunson,A.V rheim.How do public libraries function as meeting places?[J].Library&InformationScienceResearch,2010,32(1):16-26.
[25]Slatter D,Howard Z.A Place to Make,Hack,and Learn:Makerspacesin Australian PublicLibraries[J].The Australian LibraryJournal,2013,62 (4):272-284.
[26]陳劍飛,任偉璐.現代高校圖書館空間的區劃與重組[J].城市建筑,2008(9):11-13.
[27]王正興.重新解讀新加坡經驗[J].圖書館雜志,2010(9):31-34.
[28]陳婧.高校圖書館創客空間建構研究——以美國學術圖書館為例[J].圖書情報知識,2016(3):47-55.
[29]劉茲恒,涂志芳.圖書館“創客空間”熱中的冷思考[J].圖書館建設,2017(2):43-46.
[30]鐘曼琳,李興鋼.結構與形式的融合——路易斯·康的服務與被服務空間的演變[J].建筑技藝,2013(3):24-27.
[31]Henri Lefebver,Oxford(UK).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1.
[32]張曉林.研究圖書館2020:嵌入式協作化知識實驗室[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2(1):11-20.
[33]鄭海燕.當代世界的U-圖書館模式建設與實驗[J].圖書館雜志,2012(1):29-32.
[34]邢卓媛,孫翌,曲建峰.多終端環境下圖書館實體場館自助服務的設計與實踐——以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為例[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6(4):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