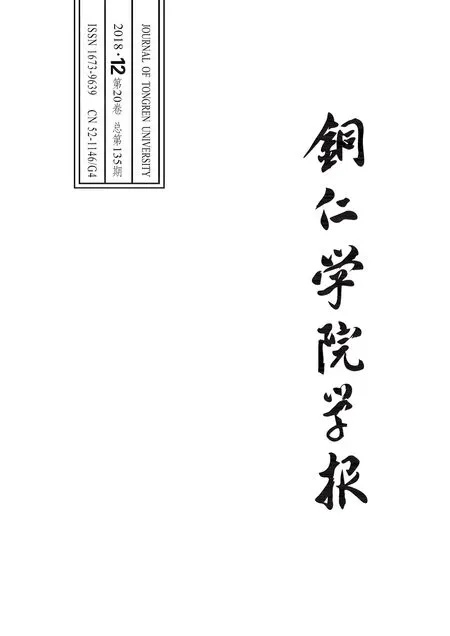西南鄉兵宋代成因及作用考略
廖靖宇
?
西南鄉兵宋代成因及作用考略
廖靖宇
(中南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宋代軍種分為禁軍、廂軍、鄉兵以及南宋“屯駐大軍”。西南鄉兵作為宋軍的重要構成部分經歷了傳統期、改制期和重塑期三個階段。它的形成與發展并非偶然,而是同宋代的邊防戰略、經濟狀況和戰斗能力息息相關,鄉兵在邊遠復雜的自然社會環境中,承擔著戍防、鎮撫、勤王、開邊、征討等多重使命,在加強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統治的軍事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穩定地區局勢的重要武裝力量。
鄉兵; 宋代兵制; 西南邊防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積貧積弱的朝代,由于長期奉行“守內虛外”的消極戰略,終宋一代的邊防形勢都十分嚴峻。在軍隊建制上,北宋的軍種大致分為禁軍、廂軍、鄉兵三種,南宋時又在此基礎上增設“屯駐大軍”,并列為正規軍。鄉兵是宋代官軍的重要補充,多設置于邊境地帶,采用軍農合一的方式,協助禁軍戍守和作戰,并在日漸頻繁的戰事中逐漸凸顯地位,成為鞏固邊防和維持少數民族地區統治的重要力量。
一、鄉兵的歷史沿革
宋代鄉兵形成發展大致分為傳統期、改制期和重塑期三個階段。
(一)傳統期:北宋開國(960)至熙寧(1068-1077)初推行保甲法前
鄉兵制度并非宋代所創,后晉時為抵御契丹,“命諸道州府縣點集鄉兵,率以稅戶七家共出一卒,兵杖器械共力營之”(《五代會要》卷12《軍雜錄》)。至于后周,“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教習武技,逃死即以佃地者代之”(《長編卷16開寶八年》)[1]73。因而,北宋鄉兵制應該是對唐五代遺制的延承。
熙寧以前,西南地區鄉兵主要有荊湖路義軍土丁、弩手,夔州路義軍土丁、壯丁,施州、黔州、思州義軍土丁,渝州懷化軍,廣南西路土丁,邕州、欽州溪峒壯丁等。其來源分為征兵制和募兵制兩種,《宋史·兵志》中載:“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2]4569所謂征兵制即以戶籍為單位進行選征的義務兵役制度。這種制度具有強制性,如宜州、融州、桂州、邕州、欽州等多地土丁,“成丁已上者皆籍之”[2]4744;荊湖路土丁、弩手也“皆選自戶籍”[2]4741。嘉祐七年(1062),廣南西路凡不服差役者,五丁征一丁為兵,至皇祐(1049-1054)時改為“以第四等戶三人取一人為土丁”[2]4744。募兵制為北宋獨創,是中國古代社會兵制的一大變革,招募的對象一般有三種,一為州縣土人,二為營伍子弟,三為饑民流民,并大多就近安置在所屬地的兵團、軍團或兵寨中。西南地區鄉兵多來自征兵,但亦有少數來自募兵。
宋初,鄉兵編教之法各地不一,但一般都不脫離生產,農閑時根據規定接受教閱,農忙時則放散務農,不違時令。宋仁宗時,荊湖路義軍土丁、弩手分設正副都指揮使、指揮使、都頭,軍頭,頭首,十將,節級等職級,或按年、或按季、或按月“番戍寨柵”[2]4741。廣南西路土丁每年冬季十一月集結舉行教閱,習練槍、鏢、牌等軍械,次年一月放散歸農[2]4744。宋英宗(1064-1067)時,設置邕州、欽州峒丁,“以三十人為一甲”,每甲置節級,五甲置都頭,十甲置指揮使,五十甲置都指揮使,遇有寇匪侵擾,溪峒反叛時才召集抵御,每兩年舉行一次教閱[2]4746。
(二)改制期:熙寧初至建炎南渡(1127)前
熙寧初,王安石認為募兵制弊端甚大,軍中混雜,許多“浮浪不顧死亡之人”[3]5299喜好禍亂,難以調度,建議實行保甲法恢復征兵制,得到宋神宗允納。
保甲法規定每十家為一保,選主戶中“有干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威望高者二人分別為正副保正。所有主戶、客戶有兩丁以上者,出一人為保丁,可自置兵械,習學武藝,接受訓練。每一大保每夜安排五人輪流警戒,使得衛戍任務常態化。[2]4767熙寧六年(1073),荊湖路全州、邵州土丁、弩手、弩團與本村土人共為保甲,以原正副指揮使為保正,軍都頭、頭首、節級等為大小保長,分兩番防守邊寨[2]4742。邕州、欽州也行保甲之法,并以獎勵的方式鼓勵峒丁勤于閱習,武藝出眾者可授以職級[2]4747。
保甲法雖是王安石針對宋初募兵弊端而提出的,但也只是對征兵制的部分恢復,而不是全部替代。如王曾瑜在其著述《王安石變法簡論》中指出:“王安石只是主張部分恢復征兵,‘與募兵相參’,而不是完全取消募兵制……誠然宋朝的募兵制不可免地有很多弊端,但因此而要恢復征兵制,卻只能是倒行逆施”[4]461。故而,西南地區鄉兵仍有來自募兵者。熙寧七年(1074),經制瀘州夷事熊本募得土丁五千人[2]4741。熙寧九年(1076),趙離征討交趾,招募勁兵數千人,以脅諸峒[2]4747。
保甲法的實施并未使宋代兵政擺脫故有的亂象和困境,反因嚴重擾民遭到司馬光等守舊派人士的強烈反對,甚至斥責保甲法是一種“驅民為盜”、“教民為盜”和“縱民為盜”的制度[5]315。因而到北宋末期,一些地方兵政業已恢復舊制。
(三)重塑期:建炎(1127)以后
靖康之后,宋高宗南渡,遷都臨安,兵力銳減,內外大軍兵不滿萬,此期間經歷了一個從潰散到重組的過程。至紹興(1131-1162)初增至19.4萬[6]404,宋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3)增至41.8萬[6]405。南宋官軍體制有較大變革,除禁軍和廂軍外,另設地方“屯駐大軍”。此時,“大軍”已取代禁軍成為正規軍,而禁軍則淪為與廂兵類似的地方性役兵。
相反,鄉兵的體制則無太大改變。湖南鄉社延承舊制,以鄉豪進行統領,每一鄉豪統領二三百至數百不等[2]4791。各地土丁仍然沿襲宋初舊法,每年冬季十一月至次年一月講武,余月放散務農[2]4790。
南宋鄉兵番號較之前則有所增損。紹興(1131-1162)末,增設荊鄂義勇,仍沿用保甲法,主戶有兩丁以上者取一丁為兵,每十戶為一甲,五甲為一團[6]410;增設夔州路義軍,從保甲中選置,以縣令為軍正[6]418。淳熙時(1174-1189),又增設湖南飛虎軍[6]420、成都府義勇軍[6]421,就近更戍,御盜防叛。淳熙中,罷湖北刀弩手、兩廣保丁[6]4790。
二、宋代鄉兵興起的原因
宋代之所以會形成西南鄉兵這支勁旅,并作為宋軍重要構成部分原因諸多,大致歸結以下三點。
(一)穩定宋代西南后院的需要
終宋一代的邊防大患幾乎都在北方,雖然在戰略上一直都實行重北輕南的政策,但作為中央王朝的后院,西南地區的社會穩定問題不可小視,若該地區動亂不定加上本就岌岌可危的北方邊防,就會使宋王朝腹背受敵。
由于西南地區地理、氣候環境惡劣,“重山復嶺”、“罕嬰瘴毒”[2]4741,遠戍當地的正規軍因不能適應水土,“一往三日,死亡殆半”,而且地方土著叛服不定,一方剛剛平定,沒住上幾月,一方寇鈔又起,又復出軍,人情郁結。所以,靠長期大量地派遣中央軍遠戍西南根本不切實際。
針對這種情況,王安石就曾指出,其他地方“民兵則可漸復,至于二廣尤不可緩。”[9]1360當地鄉兵一方面適應氣候環境,同時熟悉山川道路,又“與夷獠雜居”、“便于馳逐”,一旦征募為兵,可以就近戍守州縣寨團,遇到緊急情況又能隨時調度征發,故西南地區歷次少數民族叛亂的平定,幾乎都藉助于鄉兵,他們在加強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統治的軍事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當時穩定局勢的重要武裝力量。
(二)減輕財政壓力的需要
宋代國力羸弱,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虎視眈眈,頻頻進犯,迫使宋王朝不得不征募大量兵士。據統計,宋太祖開寶年間(968-976)全國共有禁軍19.3萬,廂軍18.5萬。到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為對西夏用兵和加強對內鎮壓,各路廣寡兵士,共計125.9萬,其中禁軍82.6萬。宋英宗即位后,又從各地征募兵士,并選廂軍中的壯勇之士補充禁軍,全國總兵士計116.2萬[2]4576。如此規模巨大的軍隊,無疑加重了宋王朝的財政負擔。英宗治平四年(1067),張方平在上疏中說:“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靖康之后,內外大軍兵不滿萬,乾道年間(1165-1173)增至41.8萬,其后雖有增減,但都不低于40萬,如按當時所養一兵平均每年需要錢糧衣賜等各項支出二百緡錢計算,40萬兵每年共需花費八千萬緡錢,“宜民力之困矣”[6]406。
相比之下,鄉兵則無如此巨大開支,養兵模式也十分獨特。一是以田養兵,即“入耕出戰,遞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困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3]3167。熙寧七年(1074),川峽土丁子弟自行耕種防務,“更無廩給酬勞”[2]4741。乾道時(1165-1173),四川弓箭手得授官田耕種,馬軍每丁給二頃半,步軍給二頃[6]407。二是以力充役,鄉兵在服役期間,大多只出力出任務,本應承擔的苛捐雜稅得以免除。南宋初,利州路義士每丁免“家業錢”三百緡,成州忠勇軍免稅賦,西和、鳳州皆免租[6]407。三是花費極少,鄉兵無需巨額給養,僅配給少量生活必需品。夔州路義軍土丁職級以上者“冬賜綿袍,月給食鹽、米麥、鐵錢”,無職級的只“月給米鹽而已”[2]4743。渝州懷化軍、溱州江津巴縣巡遏將,一年發一次“料鹽”,三年所轄地區無寇警給“襖子”。涪州賓化縣夷人義軍職官,每月配發給鹽[2]4744。如立戰功,則會給予少量的“特支錢”作為獎賞。
寶元二年(1039),夏竦在上奏陳述陜西防秋之弊時,指出禁軍“廩給至厚,倍費錢帛”,而征募而來的土兵卻能“歲省芻糧鉅萬”。據乾道四年(1168)荊南府王炎上奏所載,給養八千四百名官軍,每年需輸出“錢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綢絹布四萬馀匹”,若養同樣數量的義勇民兵,一年只需消耗米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7]3741。相比之下,使用鄉兵要廉價許多,在不減軍隊規模的同時,還為宋王朝節省了大筆軍需開銷。
(三)提升戰斗力的需要
宋代軍隊雖然規模龐大,但作戰能力卻不強。自公元1004年宋遼訂立澶淵之盟后,宋王朝進入了持續將近40年的太平年代。此間兵將安于無事,缺少訓練,不識戰陣,不修武備,即使領取糧餉,也都要雇人挑運。朝中缺少有見識的謀臣,軍中沒有驍勇的將士,根本不能統兵打仗,“器械朽腐,城郭隳頹”[3]4936。宋夏戰爭之初,北宋西北沿邊雖屯有重兵,但可戰之士,十無二三。有志憂國之士屢次進言,宋神宗更是采用了王安石提議的保甲法,對軍政大興改制,并一直沿用到哲宗、徽宗年代。雖能作“一時之氣”,但卻不能“盡拯其弊”,至崇寧、大觀年間,兵將雖多但無精銳可用,“故無益于靖康之變”[2]4570。
相較之下,西南鄉兵卻更能發揮作用。首先,在規模上不輸官軍。乾道年間(1165-1173),四川禁軍、廂軍總數為4.8萬人,西蜀大軍14.6萬人,而土兵、義軍、保丁、良家子、弓箭手等各路廣寡鄉兵共計8.4萬余人[6]407,其規模已接近官軍之數。其次,戰斗力也不弱。宋遼戰爭時,“皆云契丹不畏官兵而畏土丁,蓋天資勇悍”[3]3007。
西南鄉兵身處邊地,按時教閱,編制嚴密,和正規軍交錯駐屯,“施之西南,實代王師”。他們平時就近防務本地,遇寇匪作亂、溪峒反叛,臨時取旨加以鎮撫。遇有戰事發生,則服從調遣,出征作戰,既當向導,又作官軍前鋒。紹興二十一年(1161),大將姚仲于散關阻金人南侵,驅利州路義士2.1萬余人行在官軍之前,“其人勇健善戰,亦屢有功”[6]408。
三、宋代西南鄉兵作用
宋代西南鄉兵的作用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戍防
鄉兵的首要任務便是戍防,戍防分兩種。一是戍守內地,主要抵御當地少數民族的反叛和盜寇的侵擾等。如大觀元年(1107),宜州有土丁三百人更戍,河池土丁,分為兩番戍防,一季輪替一次。宜山、忻城二縣,三丁抽一,分為三番戍防,每月輪替。二是戍守邊境,主要抵御境外軍事力量的入侵。如欽州與交趾為境,設抵桌寨,鄉兵與官軍共同戍衛,安遠縣土丁有百人更戍,每季輪替一次[8]132。
(二)鎮撫
宋代西南羈縻地區少數民族叛服無常,常會因為反抗賦稅,爭奪土地、人口、錢糧等原因為寇邊地,鄉兵往往成為平叛這一地區少數民族叛亂,維護中央王朝統治的中堅力量。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施、黔、高、溪四州生蠻借抵御益州亂軍之機侵襲漢口,高州義軍務頭角田承進等擒獲生蠻六百六十余人,將漢口奪回,并相與盟約,于施州邊界設尖木寨予以控扼。有生蠻違約寇擾者,州府既命田承進率眾擒獲,“焚其室廬,皆震懾伏罪”[2]4175。
宋仁宗慶歷年間,桂陽徭人據眾為盜,屢屢寇擾內地,官軍因不熟山川險隘,五、六年都無法攻克。六年(1046),令衡州“頗習溪峒事”者黃士元,率敢戰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進行逐捕。徭人畏懼,逃遁至郴州黃莽山之中,依山自保[2]14183。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宜章峒李金寇亂郴州,焚劫桂陽軍,州將棄城遁逃,衡州調常寧縣官軍前往救援,不能攻克,世忠峒李昂霄等率溪峒壯丁前往支援,將賊亂平息[2]14190。
(三)勤王
靖康年間,金人攻破京畿,數路大軍從全國各地積聚京師勤王,西南鄉兵也在此列,并對保衛中央王朝做出了犧牲。靖康元年(1126),金左副元帥完顏宗翰圍攻太原意在汴京,辰、沅、澧、靖四州九千余土丁刀弩手全數調往河東勤王,至太原陷落僅存一千五百人[6]414。武岡軍溪峒義軍[2]14187,邕州峒丁靖康年間也調以勤王[8]135。
(四)開邊
除了因背困西夏,對河湟地區進行開發外。熙寧時,還為平定少數民族叛亂,對西南羈縻地區進行了開發,開發中大量借助了當地土著居民和鄉兵的力量。
熙寧間,兩湖察訪使章惇開發湖南地區,對當地少數民族進行招撫,鄉民、土丁“爭辟道路以候”,有效分化了逃竄至此的亡命之徒同當地少數民族的結合,維護了社會的穩定。熙寧七年(1074),瀘州熊本招募土丁五千余人進入夷界,捕殺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蕩平其地,并于小溪口寧遠寨西置二寨,平治險隘,開修道路,建置橋閣、里堠,募人墾耕所得土地一百四十里[2]4741。
這些開發,對穩定西南邊陲、堅固后院卓有成效,至南宋時,西南少數民族叛亂已大大減少,使中央王朝能脫身專注于抵御金元的北方戰事中。
(五)征討
遇到戰事,官軍也會征調各地鄉兵隨同出征,有時驅使在官軍之前,沖鋒陷陣,或在軍中從事各種勞役。熙寧間,新興的越南李朝集團率兵十萬,“水陸并進,分三道入寇”,交人圍攻邕州,知州蘇緘率城中禁、廂軍二千八百人奮力拒敵,但因外援不至,在堅守至四十二天后,邕州城破,蘇緘戰敗自盡,交人入城“屠其民五萬余口”[9]2592。熙寧九年(1076),趙離奉詔征討交趾,宋神宗曉諭其“用峒丁之法”,招募勁兵數千人,以脅諸峒,左右江諸蠻夷皆來歸投。趙離攜眾蠻夷兵將出征,擊潰交趾侵略軍,收復邕州[2]4747。
四、結語
宋代中央王朝之所以依賴鄉兵,一是因募兵產生的弊端已無法克服,軍隊實力羸弱,難以應對周邊少數民族的頻頻侵襲。鄉兵征稽于民、兵農合一,數量十分龐大,極大地提升了軍事力量。二是基于對南方少數民族一貫奉行的羈縻政策,使本就自顧不暇的中央王朝只能放手西南,借當地勢力鎮撫邊陲。姑且不論宋代兵制是否問題重重,但就西南少數民族的反叛活動來看,規模及數量到了宋代后期皆已大有減少,不能否認西南鄉兵在其中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可以說,終宋一代,西南鄉兵作為宋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經歷了熙寧變法、建炎重組等多個變革階段,但仍與宋王朝始終相伴,其作用和地位日益凸顯,對維護邊防安全和地區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1]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4]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鄧廣銘.王安石對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C]//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7.
[7] 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
[8] 周去非.嶺外代答校注[M].楊武泉,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
[9] 馬端臨.文獻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Militia in Southwestern China in Song Dynasty
LIAO Jingyu
(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
Military services of Song Dynasty are composed of imperial guards, local troops, militia and cultivating soldie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ilitary services of Song, militia in Southwestern China have a history of three stages: tradition stage, restructuring stage and reformation stag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ia is not an acciden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order defense strategy, economic situation and fight ability of Song. In remote and complicated social environments, militia assume a role of defending, pacifying, emperor protecting, border expanding, and rebel suppressing. It is important in the military actions to enforce the management in the ethnic regions of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s a significant armed force in the regional stabilization.
militia, southwestern border defense,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of Song Dynasty
2018-11-27
廖靖宇(1985-),男,苗族,貴州都勻人,講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方少數民族史。
K289
A
1673-9639 (2018) 12-0047-05
(責任編輯 黎 帥)(責任校對 車越川)(英文編輯 謝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