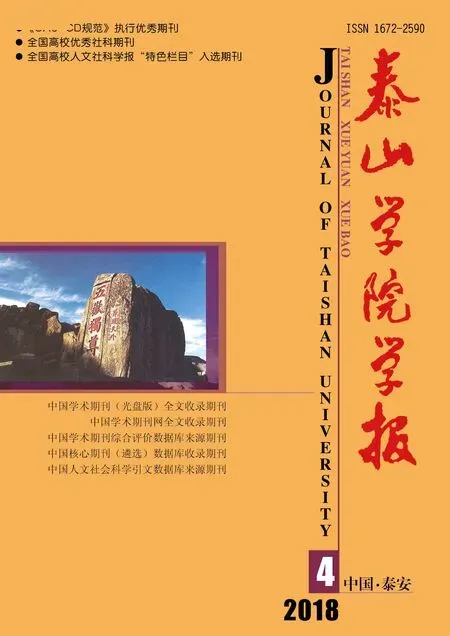書場內外:女彈詞藝人的“職場”互動
劉思瀚,秦箬茜
(1.蘇州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2.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上海 200234)
評彈藝術是深受江南地區民眾喜愛的一種曲藝形式,不過,自明清以降,評彈演藝事業長期處于男性藝人主導的狀態。直至民國時期,職業女彈詞才逐漸出現,打破了男性主導下的評彈演藝市場的性別格局。這一變化,引起了男性藝人的抵抗。1935年,以蘇州光裕社為首的男性藝人群體為維護其在業界的壟斷地位,對女彈詞進行排擠打壓,禁止男女拼檔。女彈詞藝人為求生存,以男女職業平等為由與光裕社展開斗爭,終以普余社的成立以及女子登臺說書合法化取得勝利[1]。不過,在女彈詞登上書臺之后,她們所要面臨的社會關系依然復雜。對女彈詞而言,尤其需要謹慎對待的,無疑是與書場諸角的互動關系。有學者指出,“演員、聽眾、場東構成了書場‘小社會’”[2],這正對應了職場中同事、客戶與資方的角色。從這一角度而言,書場便是彈詞演員“職場”之所在。因此,本文擬分析女彈詞藝人的“職場”互動,以探討女彈詞藝人是否如同獲得演出權一般,在職場上也獲得了平等的權利。
一、同行之爭——女彈詞與競爭者的互動
書場并非一個太平之地,各種沖突屢見不鮮,同行之爭更屬“家常便飯”。這一現象是由評彈演出的特性決定的,畢竟對于一個評彈藝人而言,搭檔少,對手多,而你的搭檔,隨時可能轉化成為你最大的對手。因此,評彈藝人之間的沖突,屢見不鮮。輕則口角不絕,在自己演出的內容中對他人進行“扦講”;重者甚至拔拳相向,定要分個“你死我活”。若是兩個男性藝人大大出手,或許令人見怪不怪,但男女藝人之間發生的肢體沖突,則真是讓人嘖嘖稱奇了。事實上,在女彈詞走上書臺之后,這類現象并不少見。
擅說《萬年青》的盲目評話家王抱良,曾與普余社錢家班的女藝人錢醉仙同在上海三北輪船公司接演長期堂會。王抱良的演出時間原本定于每日午后四時半至五時,錢醉仙緊隨其后,由五時起演至五時半。不過,王抱良常常需要趕場,不能準時到達開演。錢醉仙則趁此機會搶占先機,提前上臺演出。導致王抱良姍姍來遲之時,卻只能在臺下“欣賞”錢醉仙的演出。日積月累,王抱良心生不滿也在情理之中。
一日,王抱良準時到場開講,卻聽見錢醉仙在臺下與男聽客談笑風生,遂認為錢醉仙存心與他搗蛋,破壞他的演出,再加上王抱良早就對錢醉仙心懷怨氣,積攢的怒火一觸即發。下臺后,王抱良即罵錢醉仙:“你又不是向導社,說笑吵鬧,搗什么蛋。”[3]錢當然不甘受辱,馬上回嘴。誰知王抱良此時已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竟揪住錢醉仙一頓拳腳相加。雙方經人調解之后,方才作罷。不過,錢醉仙事后每每想起此事,心中的怨氣難以平息。于是約了幾位“動手朋友”,待王抱良在光裕公所茶敘時,娘子軍一轟而至,將王抱良團團圍住,錢醉仙更是上前“一記耳光”,報了此前的“一箭之仇”。事已至此,雙方都難以善罷甘休。只得由王抱良的師父與錢醉仙的丈夫錢景章出面調停,才將此事化解。
男性在公眾場合毆打女性,本身已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女藝人錢醉仙即便有錯在先,但遭到男藝人毆打的遭遇,理應得到社會輿論的同情。不過,因為她身為“拋頭露臉”的女藝人,大眾卻常常將這類女性與“生性不檢點”、“喜好惹是生非”等特點掛鉤。在此之后,盡管錢醉仙身為錢景章的妻子,卻也受到多方指摘,難以在上海書場中繼續立足,女藝人的弱勢與無助,可見一斑。
除了與男藝人的沖突,女藝人之間的摩擦也不在少數。雙方矛盾的焦點大多在于某個聽客專門為了一個女彈詞家捧場而冷落了同場的另一個女彈詞,遂使后者心生不快。女彈詞家徐雪月和沈玉英之間便曾發生此類事情。
中南書場曾于1936年組織過一場賀壽演出,邀請徐氏三兄妹與沈麗斌、沈玉英一同演出。此時,徐氏三兄妹正是風頭無二,尤其是是雪月,表演功力遠超她十五歲的年齡,“聽客們多歡喜她的口齒老練”[4]。因此,他們演出之時,竟有五個聽客,點了五只開篇,把他們規定的時間唱過了多時,原定十一點鐘下場,直延至十二時才歇。臺下沈玉英早已等不耐煩,本想離開棄演,最終被眾人勸回。而待到她登臺演出之時,卻未急于開場,對聽客說道:
現在有位×先生×先生,他們情愿每人拿出五塊錢來,點兩只開篇,并且指定星期日晚上在中西電臺唱給他聽,現在我在此謝謝兩位先生,星期天那天,一準在空氣中孝敬他聽。[4]
不難發現,沈玉英這番話是說給徐雪月聽的。為了表明自己不差于有人點唱的徐雪月,沈玉英不得不說上這么一段如此“刻意”的陳述,自己心中的“醋意”。
與之相類似的,某歲年尾,普余社留滬諸男女彈詞家,為籌募該社經費串演書戲。準備上演《雙珠鳳》,早先已經定醉疑仙出演女主角霍定金,但這部書中還有一位充滿正義感的丫鬟秋環,在文相府中規行矩步,目睹主婦文張氏私戀俊仆,寫信告訴了在外問花尋柳的主人文平章,卒遭陷害入獄。秋環這個角色在戲中的戲份亦是相當重要,主辦方本定沈玉英飾演,但醉疑仙因為也想出演丫鬟秋環一角,“被主持劇務者不允,羞憤填膺,在后臺放聲大哭。”[5]
錢醉仙的這一表現,與前文所述她在與王抱良爭執中的舉動可謂大相徑庭,顯得相當克制。而沈玉英在已經準備棄演而被人勸回的情況下,也僅僅只是說了幾句略帶“醋意”的自白,并未撕破臉皮,當場傾瀉自己的怨氣。可見,女彈詞藝人顯然不具備男性藝人能夠在同行之爭中“肆意妄為”的條件,社會輿論的支持更是無從談起。就這一層面而言,男女評彈藝人距離“平等互動”,尚有不小的距離。
二、“捧損之間”——女彈詞與聽客的交往
評彈藝人在書臺上說書,聽客在臺下聽書,是一種互動關系,聽客能夠對于藝人的表演做出直觀的反饋。尤其是一些老聽客,不僅對書情較為熟悉,往往還能從專業角度出發,對藝人的水平進行恰如其分的評價。對初登書臺的藝人來說,老聽客的意見對他們提高自身的藝術水平十分重要。如果某個藝人在臺上說的那一節書有不合理的地方,或是唱詞運腔不得當等等,聽客還會當面“扳錯頭”。普余社中的女藝人文化素養都不高,常常會出現別字亂讀,虛字瞎用的情況。“如‘鬼鬼祟祟’,讀‘鬼鬼崇崇’;‘棘手’讀‘辣手’,諸如此類的字,不勝枚舉。”[6]偶爾有些聽客會不留情面地指出來,這讓女藝人下不來臺。譬如女彈詞家謝樂天,“她可說是女說書中的翹楚,但是對識字,實在是太不幸了。她常常有別字讀出來。”所以她的女弟子謝小天,常常在一上臺唱開篇的時候,先對聽客打一個招呼,說:“有別字請諸位原諒。”[6]
除了對評彈藝人的技藝進行反饋,聽客也對藝人在書臺上的行為進行監督。若是藝人為人處世較為謙遜有禮,對聽客提出的意見虛懷如故,那么即便是剛出道的小先生也能獲得聽客的好感與追捧。但若是藝人“恃寵而驕”,目中無人,那么即便是再紅的藝人也不會得到聽眾的喜歡。外號“走油肉”的女彈詞家鄒蘊玉,說書時嗲聲嗲氣,以嬌媚巧笑取悅聽客,一時聽客眾多,人氣頗旺。這位嬌滴滴的鄒蘊玉卻有煙霞之癖,某天因戒絕嗜好,請醫打針,導致誤場二十分鐘,被座客當面責問。不知是否是自我感覺過于良好,鄒蘊玉登臺后非但沒有向觀眾致歉,居然還表示“此間共有書場三家,意謂:愿否來聽,悉聽客便”[7]。引得在場聽眾勃然大怒,一場演出即將化為鬧劇。場東見眾怒難犯,恐怕事態擴大難以收場,便出面調解,囑蘊玉向座客大打招呼,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對彈詞藝人水平的反饋與對其行為的監督,無疑是女彈詞與聽客之間的良性互動。但在此之外,兩者的非常態互動也多有例證。由于在傳統社會中,評彈藝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尤其是女藝人,可能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在跑碼頭的過程中,女彈詞就常常遭到達官顯貴、地痞流氓的任意欺辱。
1940年,剛滿12歲的徐麗仙跟著師姐醉仙到蘇州城郊木瀆的一戶姓石的人家做堂會。兩姐妹結束了一天的演出,已過午夜,當她們拖著疲憊的身子準備離開時,突然從旁竄出兩個大漢。這兩個滿臉怒氣沖沖、醉氣熏熏的無賴自稱是隔壁鄰居,說是麗仙姐妹倆唱堂會影響到他們休息了,所以攔住她們要她們也去自己家里唱上幾段算是補償損失。醉仙與麗仙自然想拒絕這無理的要求,但見二人來勢洶洶,又無處尋求幫助,只得順從。剛進家門,那兩個無賴便把房門落了鎖,居然拔出手槍威脅麗仙姐妹唱到天亮。她倆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把會唱的全唱完了,只唱到口舌發干,嗓子冒煙。兩個家伙還不放她們走,讓她們會唱的唱,不會唱的也得唱。最后只得等到兩個家伙睡熟了,發出了重重的鼾聲,姐妹倆才敢偷偷逃走。
女彈詞的生存環境便是如此險惡。為求自保,女彈詞認“寄爺”的現象就多了起來。“寄爺”也稱“過房爺”,是近代以來十分常見的一種社會現象,與如今的認“干爹”有異曲同工之妙。據時人介紹,拜寄爺這一舉動最初興起于京劇行當,隨后才在曲藝界流行開來。有錢有勢的先生認藝人為干兒子、干女兒風行于當時的都市文化圈。過房的關系是公開的,對于雙方都有一定的利益。對于過房爺來說,能夠充當紅極一時的藝人的保護傘是自己社會地位和財富的體現;對于藝人來說,有錢有勢的過房爺可以為自己的演藝生涯保駕護航,一定程度上改變任人欺壓的被動局面。更為重要的一點,這是藝人們接近上層社會財富和權力的標志。以至于有些女藝人沉迷其中,連拜多個“寄爺”:
拜過房爺若干女說書偏亦東施效顰,今日拜先生明日拜寄爺,一個寄爺不算,再拜一個,兩個不夠,再拜第三個,以至四個、五個,多者有至半打以上,甚有不問此人有名與否,能夠買雙皮鞋,送一件旗袍者,都是寄爺。嘗見某女說書一腳踏進書場,連叫五聲“寄爺”。[8]
過房爺除了在經濟上給予藝人幫助,在社會關系上也會給予藝人各種支持。“彈詞皇后”范雪君在常州初登書壇之時,便得到當地名耆遜清遺老“錢親王”的垂青,每日必定蒞往書場聆聽。不僅如此,這位“錢親王”還動用關系,每日為她作文一篇刊登于報。范雪君成名之后,為謝其恩,便“拜錢親王為寄爺”[9]。在眾多女彈詞所拜的寄爺之中,老聽客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些聽客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學修養的文人,他們時常會寫一些揄揚文字來品評女藝人技藝的優劣[10]。有時文人聽客間甚至會針對一位女藝人是應該“捧”或“不捧”打起筆墨官司,女藝人則通過文人聽客的“捧角”來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例如被稱為“書壇小鳥”的張麗君就曾拜評彈專欄的作者張健帆為義父。“書壇小迷湯”周蝶影也因為技藝受到常州報人范秉毅先生的賞識而被收作“過房囡”,并舉辦了隆重的儀式。
三、“利字當先”——女彈詞與場方的糾葛
藝人與場方之間的互動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舊式的書場聘請藝人說書,主要采用拆賬制度,場方根據每場聽客人數按照比例將每場的演出收入與藝人分成,或四六分,或對半分。藝人自身的名氣也是影響收入的因素,等到每場結束,藝人下臺后,場方老板會將現鈔包在紙里,上面標注賣座人數,當面交付給藝人,稱為“拆簽”。到了民國后期,上海的新型書場轉而采用“包銀”的辦法,即按月支付藝人的酬勞。
一般情況下,藝人與場方之間是相互幫持的關系,因為彼此間有著共同的經濟利益,在藝人與聽客產生矛盾的時候,場方往往會從旁調解。但若牽涉到各自利益的時候,藝人與場方之間的矛盾卻往往難以調和,甚至需要對簿公堂才能解決。女彈詞家范雪君和大華書場老板張作舟就因《秋海棠》一書的彈唱權問題,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經濟糾葛。
范雪君素有“彈詞皇后”之稱,20世紀40年代走紅于上海各大書場。1944年,上海大華隆記公司開設了大華書場,大華書場的經理張作舟很是看好范雪君,認為她“‘皮子挺’,色相光鮮,能說各處方言,起角色逼肖,還能唱幾支流行歌曲,在書壇上善拋眼風,為場下聽眾癡迷。”[11]有鑒于此,張作舟決定為范雪君量身打造適合她的評彈腳本。而早在這之前的幾年,鴛鴦蝴蝶派的代表文人秦瘦鷗曾寫過一部名為《秋海棠》的小說,這部被稱為“民國第一言情小說”的文學作品,以民國初年為背景,講述了梨園名旦秋海棠與天津女子師范學校出身的羅湘綺之間悲慘的愛情故事,在上海淪陷后吸引了大量的讀者。張作舟看中了《秋海棠》改編為評彈腳本的潛力,為此,他請來將張恨水《啼笑因緣》改編為評彈腳本并大獲成功的陸澹安,請他為范雪君量身打造《秋海棠》彈詞腳本。
陸澹安的改編很是順利,范雪君也對此十分滿意。在范雪君登臺說唱之前,張作舟提出,陸澹安所編的《秋海棠》之說唱權歸大華隆記書場所有,未經書場負責人張作舟的同意,范雪君不得在其他書場彈唱此書。只有在范雪君于大華書場將《秋海棠》唱滿四遍的情況下,該腳本的永久彈唱權才歸范所有。在合同期間,范雪君除了要在大華書場彈唱《秋海棠》,也需應書場要求彈唱其他篇目。大華書場則每月為范雪君提供國幣二萬元作為報酬。而陸澹安作為腳本的改編者,無論范雪君在何處演出,他均享有提成演出收益作為“編導稅”的權利,具體數額,由張作舟與范雪君協商決定。
以上雙方的約定,看似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但都建立在《秋海棠》演出十分順利的基礎之上。實際的情況卻不似書場與藝人想象的那么樂觀。1945年元旦之后,范雪君在大華、仙樂(征得張作舟同意的)兩家書場說這部書的時候,聽客的反響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上座率不是很理想,范雪君不得不提前剪書離去,并未在大華書場“唱滿四遍”。至1946年10月,范雪君從蘇錫等地的書碼頭返回上海,在新仙林和同孚兩家書場開書,說的卻正是陸澹安改編的《秋海棠》,這樣一來明顯違背了當初和大華隆記的約定。張作舟便向范交涉,要求范履行契約,因范前未滿四遍之約,應依約繳付版稅。而“范方則以在滬雖僅彈唱未滿約定,但后在蘇續唱,已唱滿四遍,當時曾在蘇交付陸偽幣五百萬元、法幣五萬元以作版稅,故契約業已全部履行完畢,自可自行彈唱,不受干涉,致事遂成僵局,雖經人調解,卒無效果”[12]。雙方僵持不下,張作舟便一紙訴狀將范雪君告到了上海地方法院。
陸澹安作為《秋海棠》的改編者,也不得不牽連其中。為了贏得輿論,范氏父女在《新聞報》上連續兩天刊登啟示,聲明自己在去年已經將彈詞的版稅一次性付予改編者陸澹安,并指出《秋海棠》原著作者應為秦瘦鷗,張作舟讓陸澹安改編《秋海棠》也是一種侵犯著作權的行為。范雪君方面強調自己已經向陸澹安支付了買斷版權的費用,并支付了大華書場偽幣五百萬、法幣五萬作為彈唱四遍的費用,他們認為陸澹安對張作舟隱瞞了此事。但實際上上述所付款項與陸澹安是毫無關系的,范玉山是曾托蘇州的宣乃鼎向陸澹安轉交了兩萬五千元作為酬勞費,陸澹安“因不明其計算之方法,乃逕去函詰問,旋據被告之父范玉山復函,約至上海再算。”[13]所以雙方之間因此有了誤會。“廿二日《新聞報》又刊雪君再度聲明廣告,對陸更不客氣,竟有‘斯文掃地’等字句。”[14]這樣一來又惹惱了陸澹安,他也在報上刊登啟示回擊,并將之前與范玉山往來的書信、范雪君在報上刊登的啟示、原始合同全部拿出作為證據,以“故意誹謗、妨害名譽”為由將范雪君告上法庭。陸澹安公開表示,自己與秦瘦鷗交好,改編《秋海棠》純屬“友情難卻,寫作技癢”,還公開發表聲明若是此案勝訴,即將名譽損失的補償款以及版稅余額全部捐助慈善機構。
陸澹安此舉一出,大眾的輿論導向由同情范雪君被場方盤剝、受壓迫轉而認為范雪君“人紅是非多”、“不知報恩”,光裕社的男藝人朱耀祥就認為范雪君對陸澹安的所作所為太“不近人情”,因為陸澹安早先曾幫朱耀祥、趙稼秋雙檔將張恨水的小說《啼笑因緣》改編為彈詞,范雪君也曾說過此書,所以朱耀祥就在警告范雪君的信函中稱《啼笑因緣》彈唱權,為其所有,不準他人奏唱,應立即停唱,并須賠償過去數年間擅自彈唱并侵略彈唱權益之損害費。[15]如此一來,范雪君作為被告將被三方告上法庭,官司纏身,且輿論的傾向大多傾向于陸澹安一方,對于范雪君的指責也越來越多,三面夾攻讓她焦頭爛額,嚴重影響了她的演藝生活。
1946年11月26日下午,范玉山作為范雪君的代理人出席了上海地方法院的開庭。范雪君一方的兩位辯護律師桂裕、鄂森將辯護的重點放在了《秋海棠》作品版權的歸屬權上,他們認為陸澹安僅是此書的編導,而真正的著作權應該屬于原著作者秦瘦鷗。言下之意即陸澹安對作品的改編本身就構成了一種侵權的行為。再者,范雪君在書場所說的《秋海棠》彈詞已經根據自己的演出實踐加以改變,并非陸澹安的初稿。最后,范雪君方面表明通過經濟方式已向著作權所有人陸澹庵取得永遠彈唱權,張作舟不過當時之傳達人,自無權過問,與大華書場訂立之四全遍,亦于大華閉歇后在蘇州補足。上海地方法院對案件進行審理之后,認為張作舟要求范雪君禁止彈唱的請求依據不足,理由在于:其一,雙方簽訂的合同當時已經逾期,失去效力;其二,大華書場尚未待到范雪君彈唱四遍,已自行避歇,沒有為范雪君提供演出場所,“依據原契約原告尚有未盡之責,何得更禁被告在他處演唱”[16];其三,《秋海棠》的著作權不屬大華書場所有,原告無權要求被告禁演;其四,范雪君此次演出的《秋海棠》,已與陸澹安的改編腳本有“根本不同”,“陸澹安亦無主張權利之余地”[16]。
根據以上四條理由,法院最終駁回了張作舟要求范雪君禁止彈唱《秋海棠》的訴訟請求。與法院的判決結果大相徑庭的是,輿論對范雪君的指責聲卻更加激烈,有的報道認為范雪君“不是東西”,是個“爛小人運氣派”;陸澹安與范雪君打交道也是“倒了霉的,會和爛小人繞不清起來,怕是前世造的孽吧”[17],甚至有人將范雪君斥為“書妖”。在這種情況下,范雪君方面不得不請人出面調解,《秋海棠》原著作者秦瘦鷗與雙方都有交情,所以愿為雙方調解,他主張范雪君刊登啟事向陸澹庵道歉,最后范雪君在《新聞報》上刊登了道歉啟事,陸澹安也隨之撤訴表示對妨害名譽一案不予追究,雙方各讓一步,此事才算平息。
《秋海棠》彈詞一案是藝人與場方之間關于經濟利益的博弈,但也反映出評彈藝人,尤其是女藝人在演藝生涯中所要面臨和處理的各種復雜的問題和關系。范雪君雖是官司的被告人,但實際上所有的合同都是其父范玉山代她所簽訂,范玉山扮演著女藝人經紀人的角色,幫她打理演出外的一切事務。但在出現問題的時候,社會大眾會選擇將范雪君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而非其背后的始作俑者范玉山。在與大華書場的交涉中,范雪君雖也有處理不當的地方,但總的來說范的行為是合乎法律規范的,法院的判決也支持了這一點。反而是場方張作舟在經濟利益驅使之下,有意為難范雪君以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由于陸澹安的社會影響力較大,輿論便紛紛將矛頭指向了范雪君,認為她不懂得知恩圖報、忘恩負義,在大眾的眼中,范雪君就是一個“無恥的書妖”[17]。大眾的非議似洪水猛獸,在這種情況下,被推到臺前的女藝人承載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但為了能繼續在書臺上謀生,也只能以低姿態向公眾道歉。
通過對女彈詞三組“職場”互動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即便是在女彈詞獨立登臺演出之后,女性仍然處于弱勢地位,不僅受到男性的欺辱,更多的情況下女彈詞還需要依附于男性,無論是師父、“寄爺”還是父親,都成為她們謀求生存的保護人。因此,女彈詞登臺權利的合法化,只是眾多女彈詞所期冀的男女平等的起點,而非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