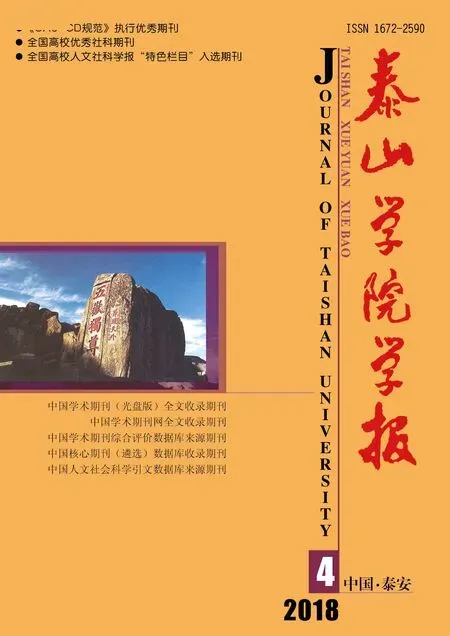簡評《評彈藝術的輕騎兵之路
——十七年書目傳承研究(1949-1966)》
劉 曉 海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20)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后共計17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歷了從新民主義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變革,也經歷了初步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程,對自此之后直至今天的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簡稱國史)研究逐漸在學術界興起。“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長期以來是國史研究中的熱點,對這“十七年”的認識存在著諸多不同,正如金光耀所言:“‘文革’十年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大動亂的年代,與之相比,對毛澤東領導下的‘十七年’卻沒有像‘文革’十年那樣容易加上一個定語。”[1]作為中國史研究中相對年輕的學科,國史研究最先是在政治史、外交史等領域取得一系列成果,“而法制史、經濟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會史等領域的研究比較薄弱,影響了研究的全面發展”[2]。近幾年來,伴隨著學者對“十七年”社會、文化等領域研究的深入,諸多成果促進了國史研究的深化與拓展。
金坡博士《評彈藝術的輕騎兵之路——十七年書目傳承研究(1949—1966)》(以下簡稱“《書目傳承》”)便是有關“十七年”社會文化史的新著,筆者以此文就這本著作進行簡介并從具體研究角度略陳淺見。
一、整體與區域:國史研究領域的新拓展
徽學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唐力行教授曾經指出:“社會史的研究必然導向區域史研究……以往的史學研究側重于中央王朝、典章制度的研究。但這涵蓋不了歷史研究的全面的空間……只有對各個區域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把一個個區域研究透了,才有可能對各個區域進行綜合的研究,我們的整體研究才有可能提升到一個新的層面上。區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小可至一村、一鎮、一縣、一城,大可至一省或數省,以至一國、一洲。全面的空間,不僅是指區域之大小,或區域之相加整合,而且包含另一層意思,即區域社會是整體社會的細胞形式,認真解剖一個區域社會,可以獲得整體社會的全信息。”[3]雖然“對中共來說幸運的是,近代交通運輸、火力和警察網絡等方面的發展,已給人民共和國新政府提供了各種控制中國形勢和暫時控制社會的手段”[4](P21),但是這種能力仍然是相對的,中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地域文化差異仍然十分明顯。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回答整體與區域的關系問題。在這一方面,金坡博士的著作在兩者之中找到了一個較為恰當的平衡點。
在《書目傳承》一書中,作者頗為關注1949年后的全國開展的戲改工作,而評彈書目的改造恰是這一全國性的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書目傳承》第一章中特別指出“新政權希冀通過戲曲改革來建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重塑現代民族國家理想和人民主體形象”[5](P36)。得益于作者對于整體史的把握,他沒有將思維局限于1949-1966。例如在考察戲改歷史時,把這一段歷史置于更長的時間范圍內加以考察。作者注意到改造舊戲的運動,并不是在1949年后才開始的,早在抗日時期的陜甘寧邊區便已開始推行。這一運動的開展也不是空穴來風,是中共所構建的新社會建設方案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之下,才開始了對于江南地區傳統曲藝——評彈的改造。
作者隨后對傳統書目“第一次斬尾巴”前后歷史的梳理,十分注重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微妙的互動關系。中央一方面力圖盡快推進評彈書目的改造,另一方面卻對由此可能引起的藝人生活困難頗為擔心。反觀之,更為激進地要求禁絕傳統書目的是最為了解藝人群體生存狀況的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除此之外,作者也關注到全國開展的思想批判運動對于蘇州評彈深刻影響,他通過對于“九藝人聲明不再演出傳統書目”前后中國文藝界的最新動態,發現了全國批判《武訓傳》這一運動所營造的“大氣候與上海對傳統書目指責愈來愈嚴重的小氣候共同作用”[5](P73)才是導致藝人如此表態的原因。
除舊和布新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新書創編同樣是中央與地方互動的產物,作者通過對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為代表的建國初期新書目編演的研究,認為“積極配合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開展編說新書目工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評彈界所開展工作的重要內容”[5](P51)。從《書目傳承》的目錄編排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對于江南地區評彈書目創編的深刻影響,從建國初期“傳統抑或現代”抉擇過程中引發的評彈書目傳承的動蕩,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新舊書目并存的“兩條腿走路”,再到“大寫十三年”時期現代書目全面占領評彈演藝市場。
當前中國的社會史研究之中,存在著“碎片化”的傾向,由此引發了諸多學者的討論。李長莉教授認為史學研究的碎片化在社會史和社會文化史領域表現尤為突出,存在“論題小而微,缺乏大關懷與大問題”、“論題細碎而零散,缺乏大聯系與大序列”、“論題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論與大闡釋”的問題。[6]《書目傳承》采用了社會文化史的思路,從微觀的評彈書目史著手,題目雖看起來很小,卻將之與歷史重要事件的內在聯系揭示出來,管中窺豹,通過評彈書目這一小切口,拓展了我們對于“十七年”整體史的認知視野。
二、繼承與突破:社會文化史與政治史研究的有機結合
高華教授曾經說過:“在‘當代’和‘現代’之間并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的長時段因素還在對歷史的進程發揮著深刻的影響,當代史從久遠的過去而來,以往的結構、制度、思想、風俗、文化情趣并沒有一夜之間消失,它們和新因素相依相隨,構成了當代史的復雜斑斕的畫面。”[7]即使是誓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文革”時期,也仍然有傳統文化的影子得以保留,例如錢杭教授在關于“文革”期間所修族譜的研究,就發現“在狂飆之下,中國大陸一部分民眾仍然以不間斷的重修族譜方式,通過整理自己所在宗族各成員間的世系聯系和文化聯系,表達和確認了該宗族的歷史連續性與存在合理性”[8](P219)。
評彈作為江南地區流行數百年的曲藝文化,在疾風驟雨之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續著其傳統。在《書目傳承》一書中,作者認為評彈傳統書目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載體之一”[5](P394),傳統書目在1949年后不同歷史時期境遇的不同,是由于政府對于傳統文化態度前后不一造成的,評彈傳統書目被現代書目完全取代,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而現代書目的創新之處,最直觀表現在階級斗爭以及工農兵等形象。在家國、審美、愛情以及忠孝節義等觀念上現代書目也與傳統書目大相徑庭。作者認為這“絕非評彈藝術內在發展的必然結局,也并非國家政治權力在推動大眾文藝改造過程中的偶然所為,而是中國共產黨為確立并鞏固在戲曲領域中的領導合法性而有計劃、有步驟地積極運作的結果”[5](P395)。作者的研究,從政治史的角度切入,以社會文化史的視野與方法開展研究,從而揭示了1949年后政治與藝術之間的密切聯系,既避免了傳統政治史研究高高在上、往往實證不足的缺陷,又避免了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的就文化談文化、缺乏對政治回應的問題。通過最后的比較分析,《書目傳承》中直言“上海評彈界創作演出的評彈現代書目大部分沒能取得成功。尤其是在‘以現代劇目為綱’以及‘大寫十三年’號召下,評彈界創作演出的現代書目,幾乎無一部可流傳”[5](P395)這一論斷恰好回應了唐力行教授所說的“藝術和政治本是兩個概念,它們有聯系也有區別。當政治要與藝術合而為一,當藝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時,一系列的問題也隨之凸顯”[9](P824-825)。
江沛教授在談及如何推進改革開放前中國當代史研究時,曾經指出:“除了關注高層政治何以如此之外,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才是描述歷史的關鍵所在,而社會政治化形態也才是歷史的表征。我們應該摒棄那種高層文件下達——省市級傳達——下層動員——反響廣泛的單線式歷史記述思維,在強調政治社會化的強大力量同時,要看到因諸種條件產生的復雜性,看到底層民眾對于政治理解的不同對上層政治的反作用。”[10]在《書目傳承》一書中,對于政治社會化問題的研究頗為考究,可以通過書中文字了解到很多歷史的細節。如對于評彈書目“翻箱底”運動的考察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有中宣部領導袁水拍出席的上海評彈團座談會,也可以看到上海區級評彈團體對于上演傳統書目“折子書”表現出的高度熱情,還可以看到來自觀眾對于傳統書目上演過多、現代書目邊緣化的意見。[5](P192-196)政府、評彈團體、藝人、受眾在一個事件中的不同觀念和發揮的作用都得以體現出來,歷史所還原的內容不再枯燥乏味,社會生活的眾生相躍然紙上。
三、思索與求真:獨到的學術視角與豐富的歷史資料
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1]陳寅恪先生希望歷史研究者洞察新材料與舊材料、舊問題之間的關系,兼容不同領域、不同文化的學者對同一問題的不同看法,從而推動學術的進步。在《書目傳承》一書中,作者沒有局限于傳統上對于評彈在1949年后歷史的判斷,而是以豐富多樣的材料為佐證,以獨到的學術視角對材料進行解讀,從而獲取了對于相關問題的新認識。
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馬克·布洛克曾經說歷史學“是一種以認識的深化為皈依的思想活動,因而也是一種運動中的事業”[12](P36)。史學著作的寫作,既不能刻意標新立異,但更不能因循守舊,在《書目傳承》一書中,可以看到作者對傳統認識的新突破。以1949年后的中共文藝思想為例,常見的敘述、研究僅僅關注到毛澤東一人的文藝思想對于整個文藝界的影響,而毛澤東之外其他的中共領導人在文藝思想方面的情況往往語焉不詳,而《書目傳承》的作者通過對于史料的認真解讀,較為完整地還原了陳云有關評彈的論述,分析了陳云關于評彈本體與市場規律的認識,進而歸納總結出陳云文藝觀。
李良玉教授對于重要歷史人物在1949年后歷史中的作用有過高度概括:“歷史的主人當然是人民群眾,離開人民群眾,既不會有英雄,也不會有英雄的歷史。但是這并不是說英雄人物可有可無,或者無足輕重。英雄人物和領袖人物不是一個概念,某一個歷史時期可能沒有出現英雄人物,但必定有領袖人物。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關頭,人民群眾不一定能起到扭轉社會發展方向的作用,這時候,領袖的作用就是決定性的。”[13]《書目傳承》作者認為陳云的文藝觀“在一些重要方面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文藝思想”[5](P207),陳云對于評彈書目整舊與創新的關心“不僅是出于個人愛好,更是為了保存和發展這門傳統藝術”[5](P241)。作者對于陳云文藝觀的再發現,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固有文藝研究思維定式的突破。
除了對于重要歷史人物的再度發掘,《書目傳承》中對于評彈書目與評彈其他要素之間的關系互動,也做了較為細致深入的考察。作者將“藝術表達”這一概念運用到評彈書目研究之中,“藝術表達”主要有兩層含義,其一指的是評彈書目的創作過程,其二是評彈書目的演出過程。在研究書目創作史,作者很注意對評彈書目整理創編過程中藝人之間的討論的還原與分析。蕭冬連教授曾說當代史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文獻編排和文本解讀上,文件的形成過程更加重要。一個重要文件從動議到調研、起草、討論再到通過,是黨內逐步取得共識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鮮活的歷史話題”[14],雖然這是對黨內政治活動研究的觀點,但是也同樣適用于1949年后與政治發生密切聯系的評彈書目創作活動之中。如《書目傳承》第三章對于上海市評彈團1963年9月有關評彈“鬼戲”“鬼書”問題的座談會的研究,首先是將有關“鬼戲”討論出現的時代背景予以介紹,進而對這次座談會上藝人表達的觀點進行整理概括,最后得出結論:“與其說是對評彈傳統書目中‘鬼戲’‘鬼書’以及忠孝節義的討論,不如說這次討論其實是對廣大評彈藝人的一次思想改造,而這一討論的結果就是廣大評彈藝人自覺地接受傳統書目被徹底斬斷‘尾巴’的現實”[5](P322)。通過這種整理創作細節之處的還原與解讀,使得我們能夠更深刻地了解這一時期文藝作品是如何產生的。
而作品產生之后的演出效果究竟如何,作者對此進行了細致解讀。受眾分析往往是文藝研究過程中比較難以深入開展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受眾群體是“失聲”的,他們屬于“沉默的大多數”。了解一部作品何時在何地上演、創編人員信息乃至創編過程可以運用一些直接材料,唯獨在受眾分析過程中,這種直接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缺失的。《書目傳承》的作者沒有滿足于從作為宣傳喉舌的報刊中得到的“深受群眾歡迎”、“觀眾反響熱烈”等空話,而是有著自己解讀的視角。如作者對于《王孝和》演出過程的考察,不僅注意到輿論宣傳的情況,還通過對上海檔案館和上海評彈團檔案室相關檔案的分析,揭示出《王孝和》“雖然連續上演3個月,貌似轟轟烈烈,然而工人聽眾基本上是團體訂票的。在演出中,書場里即有部分聽眾表示‘不習慣’,亦有人公然認為‘這個作品一定要失敗’,甚至在演出過程中聽眾與場方發生毆打事件。在該團(上海評彈團)的檔案中可以顯示,該中篇在演出過程中也遭遇了相當數量的退票……藝術造詣的一般或許是廣大聽眾退票的真正原因”[5](P98-99)。
作者沒有拘泥于“評彈在20世紀50年代經歷黃金時期”的傳統論斷,而是以書場的情況為切入口,提出了與傳統論斷不同的新見解。作者通過1954-1961年上海市檔案館有關書場及工作人員的統計數據,發現這一時期上海的書場和工作人員的數量是逐年下降的。書場情況是評彈演出市場中最為重要的風向標,一般情況下通過書場數量的興衰變化就可以了解這一時期評彈的發展情況,作者以數據為支撐,大膽推翻了傳統論斷,提出“從1954年開始到60年代初,評彈藝術的發展是較為緩慢的,甚至是停滯乃至逐步萎縮的”[5](P81)。
研究當代的歷史,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材料的制約,沒有足夠的材料作為支撐,就容易出現“以論代史”的情況。求真應是當代史研究的第一要義,李良玉教授就認為“當代史研究的根本方法是以真實為原則,以事實為基礎,以材料為根據”[13]。求真的基礎就是盡可能多地掌握不同材料,這一方面《書目傳承》一書的作者付出了很多心血。作者在后記中說道:“2013年時,上海檔案館可以免費復印檔案,每人每天限50張,每個卷宗復印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記得當時,很多師弟師妹跑到上海檔案館幫我復印資料,甚至最多時,每天可復印幾百張,最終我搜集到了幾箱子評彈檔案。”[5](P428)筆者有幸在當年便知曉此事,也知道僅僅兩三個月之后檔案管理便再次趨緊,甚至很多檔案封存不再示人,《書目傳承》作者所收集的寶貴檔案,構成了開展評彈書目研究的主體資料。當然,作者并沒有僅僅局限于收集檔案資料,而是在研究過程中綜合運用了檔案、報刊、口述資料等,這其中由作者親自訪談而得到的口述史的資料與檔案資料一樣,具有珍貴的價值。口述史在當前史學界受到高度關注,口述史料“可以了解許多復雜的人際關系,這在文獻檔案中自然是不可能出現的,而熟悉這些人際關系可以幫助你看懂許許多多文獻資料背后的運作”[15],《書目傳承》一書在介紹楊振雄編說《武松》的時候,就運用了楊振雄遺孀與弟子的口述,指出當時楊振雄“為了偏重‘起腳色’,曾向京昆劇藝人揣摩,可謂煞費苦心”[5](P48)。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金坡博士新著《評彈藝術的輕騎兵之路——十七年書目傳承研究(1949—1966)》突破了“十七年”研究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傳統文化研究的既有藩籬,也突破了戲曲、曲藝文化史研究中“就藝談藝”與社會脫節的弊端,既關注到領導人、政治運動對評彈的影響,也關注到書目內容細節與政治方針之間、書目與評彈其他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這本專著,不僅可以了解新舊變革背景下社會文化的變遷,也可以引發關心評彈人士對于當前評彈傳承危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