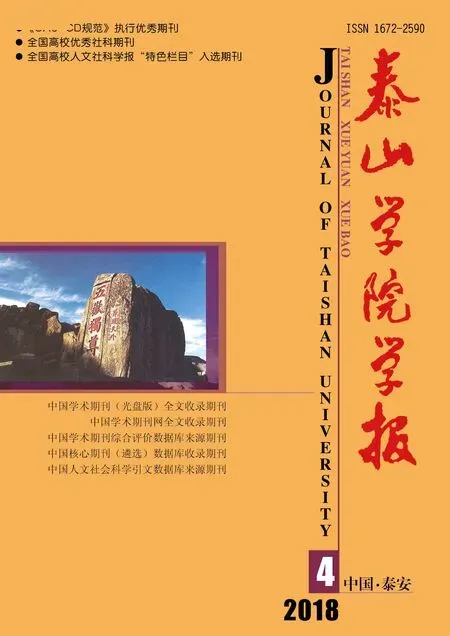吳伯簫年譜:人教社與《文學》課本(1954-1956)
子 張
(浙江工業大學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3)
1954年,48歲
1月18日,從沈陽東北教育學院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接洽工作調動事宜,與葉圣陶談話。
葉圣陶記述:“1、18星期一:下午兩點到社,與安亭、萃中談事。教部請調吳伯簫來我社編輯中學之文學課本,吳自東北來京先了解一下,再回東北師院交代,解副院長之職。余與吳雖相識而不太熟,話題不多,共談半時許而別。”“1、21星期四:致書安亭、萃中,談數學課本事。薰宇、蔡德祉等按計劃編三種數學課本,而教部調來之吳君謂不宜用,可用東北譯本。同人中亦以為吳言可據。余意則以為此是變更計劃,宜經詳商,何去何從,則最后當由教部決定之。”“1、30星期六:三點半董純才來訪,口頭答余上星期日致渠之書。謂將以吳伯簫、鞏邵英、戴白韜(將自上海調來)三人為副社長,本年度之計劃及五年計劃綱要俟三人來齊后共商,然后由教育部討論而決定之。”[1](P71,75)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了中央語文教學問題委員會的《關于改進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報告》,教育部據此責成人教社著手擬訂中學文學教材編輯計劃,編訂文學教學大綱,編寫文學課本和教學參考書。人教社在進行上述編訂、編寫工作的同時,相應地將中學語文編輯室分為文學、漢語兩個編輯室。
2月15日,在人教社與葉圣陶交談。
葉圣陶記述:“2、15星期一:下午到社中,與吳伯簫談。吳今后主持語文室編輯文學課本之工作,聆其所談似頗有辦法。余老實告以余之短處即在不會組織力量,不善作領導。”“2、22(星期一):吳伯簫領導中學語文室,似頗有辦法,亦復可慰。”[1](P79,81)
3月22日,將《文學》課本編輯要點交葉圣陶審閱。
葉圣陶記述:“3、22星期一:兩點半到社。吳伯簫以編輯文學課本之要點一稿交余。余即修改此稿,約花一點半鐘而畢。”[1](P90)
3月30日,在北京寫《理想與勞動》,收入《出發集》。
4月1日,就《文學》課本之編輯召集文藝界人士座談會。
葉圣陶記述:“4、1(星期四):午后三點至和平賓館,教育部與我社邀請文藝界同人開座談會,討論編輯中學文學課本之問題。此是吳伯簫所主張。邀請五十余人,而到者三十余人。董純才與余致辭一時許,馀則大家發言,至六點半而畢。期以此會為始,以后在編輯過程中,請大家隨時相助。于是會餐,盡歡而散。” “4、8星期四:兩點到社。芷芬、安亭來談社事,吳伯簫亦來。”“4、19星期一:七點,辛安亭偕戴白韜來訪。戴久任上海市教育局長,今調來我社為骨干人員。吳伯簫、鞏邵英、戴白韜三人究負何種名義,尚未確定。”[1](P94,95)
4月24日,在人教社與葉圣陶等談社事。
葉圣陶記述:“4、24星期六:兩點半散,余至社中,與白韜、安亭、萃中、伯簫、芷芬、少甫諸人談社事。皆所謂交換意見而已。”[1](P99)
4月,正式調任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參加編《文學》課本,同時兼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所長(至1956年夏),任《文藝學習》編委。
自述:“一九五四年春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參加編《文學》課本,兼辦中國作家協會的文學講習所,任所長。參加《文藝學習》編委。一九五六年全國總工會組織作家參觀團,任南團團長。走了太原、洛陽、武漢、南京、無錫、蘇州、上海等七個城市。杭州未到。十月到民主德國參加‘海涅學術會議’,往返一月。國內之行,寫了《難老泉》、《鋼鐵長虹》;國外之行,寫了《記海涅學術會議》(《詩刊》創刊號、《論海涅》(《解放軍文藝》)、《謁列寧墓》(《人民日報》)、《記列寧博物館》。”[2](P231-232)
葉圣陶記述:“1954年伯簫同志調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我們倆幾乎天天見面,直到1966年。他為人誠懇樸實,表里如一,是全社同志共有的印象。我們倆經常討論語文教材的編撰,有時似乎談得極瑣屑,近于咬文嚼字。其實絕非咬文嚼字,準確的意思和準確的記載非由準確的語言來表達不可,所以一個詞也不能隨便,一處語法錯誤也不能容許。在這方面從嚴些,對學生的語言、認識、品德都有些好處:這是伯簫同志和我共同的信念。”[3]
劉征回憶:“文學、漢語分科教學,是建國以后,花的時間長,規模最大,集中優秀力量最多,中央領導最重視,力度也最大的一次語文教學改革。中央指定胡喬木領導,教育部由副部長也是人教社社長葉圣陶直接領導,伯簫是第一線總指揮。”[4]
張中行回憶:“一分為二上課,先要有教材。編教科書是大事,要請專家主持其事。文學選定吳伯簫,社內的副總編輯,由延安來的文學家兼作家。漢語選定呂叔湘……”[5](P385)
徐剛回憶:“1953年夏季,胡喬木同志提出壓縮編制的問題。1954年初,‘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牌子就改成了‘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新任的領導班子,是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調配的。吳伯簫任所長(還兼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社長),從鞍鋼教育處調來公木任副所長,從《文藝報》調來蕭殷任第二副所長,蕭殷只在所內過渡了幾個月,就調到廣東省,只有公木在所內主管。”[6](P103,105)
5月1日,在北京寫《出發集·后記》。
5月3日,在社中與葉圣陶交談。
葉圣陶記述:“5、3星期一:下午到社,知黎明以昨日去世。今日十數人往視其殯,即付火化。……與文叔、安亭、白韜、伯簫共談,至六點半而后出。”[1](P101)
5月8日,教育部董純才約見葉圣陶,與談人教社人事安排事宜。
葉圣陶記述:“5、8星期六:飯罷到署已兩點。教育部來電話,董純才欲來看余,余乃往訪董。渠所談為人事安排。謂我社以戴白韜、辛安亭、吳伯簫三人為副社長,萃中不復為副社長。至于副總編輯,則戴、辛、吳三人而外,又有萃中、薰宇、文叔及鞏邵英四人。余謂悉可同意,無他意見。”[1]
5月18日,人教社召開社務會擴大會議,葉圣陶社長宣布調整后的領導班子:戴伯韜、辛安亭、吳伯簫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張萃中、劉薰宇、朱文叔、鞏紹英任副總編輯,戴伯韜主持日常工作。
葉圣陶記述:“5、18星期二:驅車到社中,已十日未到矣。三點三刻開擴大社務會議,由余宣布副社長、副總編輯之人選與分工。至此副社長有三人,副總編輯有七人,陣容較前為強,而主要倚靠戴白韜。白韜、安亭俱發表談話。”[1](P105)
本月致信公木,談自己正式調任人教社,邀請公木到文學講習所工作,公木于當年初秋以副所長調入。
《公木傳》記載:“1954年5月,時任文講所所長的吳伯簫曾專門致信公木,告訴他自己已去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編輯中學語文編輯工作,邀請公木來文講所工作。”“文講所在行政上歸文化部,教職工的工資和所內開支的一切費用都由文化部發。業務和黨務上卻又歸中國作協。而按照公木的想法,是要將文講所完全脫離中國作協的領導,辦成像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那樣直屬于文化部的正規大學。他的想法得到吳伯簫的贊同和支持,于是一起到文化部教育司去聯系——經過交涉,教育司同意吳伯簫和公木的意見,而且還給了一個出國留學的名額,讓文講所派人到蘇聯高爾基文學院學習。”[7](P81)
6月1日,在社中與葉圣陶談《文學》課本編輯提綱。此為本月工作重點,6月23日葉圣陶建議將編輯提綱送交胡喬木審閱。
葉圣陶記述:“6、1星期二:兩點半至社中,吳伯簫來談,中學文學課本編輯提綱又經修改,將據以開座談會,謂余必當參加。”“6、9星期三:晨間安亭、伯簫二位來談社事。俟其去,續看伯祥之注釋稿。”“6、23星期三:到署,看雜件。致吳伯簫一書,答以中學文學教材編輯計劃可送于喬木看后再說。”“6、28星期一:(下午)至社中,安亭患腹瀉在寓,未值。與文叔、伯簫、芷芬、曉先、劉御五位談話。”[1](P105)
7月20日,在社中參加小學語文教學問題討論會議,此后又多次討論此問題。
葉圣陶記述:“7、20星期二:午后到社,與白韜、伯簫、文叔、仲仁、超塵、王微諸君為會,討論仲仁所提小學語文教學之諸問題。三小時有半,僅及目的任務與識字教學兩問題耳,后一問題且未曾終結,后日將續為討論。”“7、22星期四:午后至社中,繼續討論小學語文方面之問題。”“7、24(星期六):晨至社中,八點繼續討論小學語文教學之問題。”[1](P129,130)
7月,散文集《出發集》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收入雜文、散文14篇,分“第一集”、“第二集”,“第一集”為散文,收入《出發點》《范明樞先生》《向海洋》《書》《十日記》《回憶延安文藝座談會》《頌〈燈塔〉》;“第二集”為論文,收入《愛祖國》《真理的發揚》《重讀〈亂彈及其他〉》《從教育看武訓》《理想與勞動》《文學——教育的有力武器》《談業余寫作》,另有本年5月1日寫的《后記》一篇,交代此集所收14篇作品之由來:“將一九四六年以來零星寫的文章,選了十二篇,將一九四一年寫的文章檢出兩篇,集攏起來,印成這本小書。篇數不多,但也分兩集:一集屬散文,二集屬論文。//這些文章曾先后在延安《解放日報》、張家口《晉察冀日報》、東北《知識》雜志、《東北日報》《東北文學》及北京《文藝報》《中國青年》發表過;現在重行選印,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簡單總結一下八年的業余寫作,借以自我激勵,期于寫作生活的路上往前再邁一步。//書名《出發集》,意思是說:自己寫文章,依然還只能算是開始學習;而寫作的目的,則想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從人民的利益出發’。”[8](P121)
8月6 ,參加人教社所召集中學《文學》《歷史》課本編輯座談會,此次參加座談者為高校教師。
葉圣陶記述:“8、6(星期五):三點到社中,召開座談會,討論中學文學及歷史課本之編輯問題。參加者為各大學來高教部開會之文學、歷史教師……余略致辭,即分兩組座談,余參加文學之一組。諸人皆甚熱心,各抒其見,不待催促。至七點半畢。實則如此題目,談一天兩天亦難談完也。于教育部食堂宴與會者,談飲甚歡。”[1](P135)
9月22日,在社中與葉圣陶等討論《文學》課本之選材問題。
葉圣陶記述:“9月22星期三:(上午)至文叔之室,與安亭、伯簫、仲仁共談中小學語文編輯事。最困難者仍為選材。得可誦之文篇供學生閱讀,為語文編輯首要之事,而其難得實非局外人所能意料。”[1](P151)
10月,《憲法照耀著我們前進》刊載于《語文學習》10月號。
11月6日,上午到北京站迎接離京修養旅行歸來的葉圣陶。
葉圣陶記述:“11、6星期六:醒來時車將到天津。九點三十六分到京,在站相候者有洛峰、戈矛、吳伯簫、白文彬、黃嘯曾(教部辦公室主任)五位。”[1](P161)
1955年,49歲
5月1日,寫《煙塵集·后記》。
5月,初級中學課本《文學》第一冊(供1955年秋季試教用)出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北京新華印刷廠,至1956年2月第六次印刷,僅北京一地印數即達到106001-213000冊。0.38元,171頁。
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遷址,由教育部(西單北二龍路鄭王府內小紅樓)遷至景山東街原北大第二院(理學院及校辦公處)工字樓。
7月,散文集《煙塵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繁體字豎排,印數14000冊,定價0.59元。
8月,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開始對“丁、陳反黨小集團”的連續批判。
邢小群記述:“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期間,1955年8月3日至9月6日,中國作家協會召開黨組擴大會議,宗旨是批判作協內部的‘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會議共舉行了16次。開始范圍不大,只限于作協各部門13級以上黨員干部。后來擴大到中宣部、文化部、全國文聯及其他協會的負責人。”[5](P82)
徐剛回憶:“這次批判從頭到尾我都參加了。第一次開會是1955年的8月初(8月3日),地點是在東總布胡同22號東邊的辦公室。”“當時參加黨組擴大會的文講所正、副所長吳伯簫、張松如(公木),只在會上作了表態式的批判發言。他們與丁玲接觸很少,都是作協黨組調派來的第三屆領導人。”[5](p116,122)
作協黨組擴大會后,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領導班子再改組,不再擔任所長。
徐剛回憶:“1955年9月6日的黨組擴大會后,黨組就指示文學講習所總結檢查過去的工作,把文學講習所改為短期訓練班。”“黨組擴大會后,文學講習所經歷第三次大改組。吳伯簫不再來所了,辭去了文學講習所所長的職務。公木調任中國作家協會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瑪金、丁力、沙鷗、王谷林等由作協分別調派至《人民文學》編輯部、《詩刊》編輯部、青委會辦公室、《文藝報》辦公室負責。潘之汀、葉楓等同志調至北京電影制片廠等單位。接著中國作協下達了一個通知,任命我為文學講習班主任。”[5](P123)
郭小川記述:“上午……因作協的機構問題,不斷地與默涵商量,與嚴文井打電話,最后還是決定吳伯簫參加工作委員會。”[9](P345)
11月15日,寫《齒輪和螺絲釘》,收入《北極星》。
1956年,50歲
1月24日,到中國作家協會與郭小川談丁玲作品是否編入教材事。
郭小川記述:“下午,吳伯簫來,談課本中的丁玲文章選不選問題。”[9](P383)
2月17日,紀念、介紹德國詩人海涅的長文《革命詩人海涅》刊載于《人民日報》。
2月27日-3月6日,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在北京召開。
3月2日,上午,在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發言專門談“文學教科書”編寫問題,首先向與會者介紹國家關于編寫文學教科書的計劃:“現在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經有了一個文學教科書的編輯室,試編一套二十四本(包括教學參考書十二本)文學教科書,明年年底可以編完。從今年暑假以后,幾千萬的中學生就要用新編的文學教科書進行文學教育。”其次在三個方面“請求作家同志幫助”:“第一、推薦優秀作品選入教科書。第二、請文學理論家、文學史家、傳記作家,在我們經過反復考慮,請求您寫一篇課文的時候,能夠慨然地答應我們……第三、同志們看到或者聽到我們編的文學教科書有什么錯誤和缺點的時候,希望能及時地給我們指出來,如果能夠改好就更歡迎。”發言全文被收入中國作家協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年6月出版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10](P202,203)
3月,教育部頒發《1956-1957學年度中學授課時數表》及《關于1956-1957學年度中學授課時數表的說明》,其中第四條為:“原語文科改為漢語、文學兩門學科進行教學。”[11](P688)
3-4月間,中央語文教學問題委員會負責人胡喬木約見中學語文編輯室負責人張畢來、吳伯簫二人,提出要解決“漢語”、“文學”分科后的作文教學問題。[12]
4月,教育部正式發出《關于中學、中等師范教育的語文科分漢語、文學兩科教學并使用新課本的通知》。
4月,擔任“校訂”的高級中學課本《文學》第一冊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版。
同時,初級中學課本《文學》第一冊分別由上海、遼寧、陜西、湖北、重慶等省市出版社“重印”,發行量驚人。如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本,1955年5月第一版,1956年4月上海第一次印刷印數為1-120000冊,1956年6月上海第四次印刷印數便達到185000-206000冊;至1956年5月第二版,1956年6月第二版上海第一次印刷印數為1-480000冊。到1957年1月第二版上海第八次印刷印數則為1036001-1151000冊。第二版增加了內容,頁碼由第一版的171頁增加到第二版的326頁,定價由0.38元調整為0.65元。
8月11日,散文《監督崗》刊載于《人民日報》,此文收入中國作協編《1956年散文小品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6月版。
8月14日,在張家口中學教師文學講習會發言,后根據發言整理為論文《試談文學教學的目的和任務》。
8-9月,參加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的中國作家協會參觀團,任南團團長,走訪太原、洛陽、武漢、南京、無錫、蘇州、上海等七個城市,9月4日,參觀武漢長江大橋,寫新詩《鋼鐵的長虹》。
自述:“1956年初秋,我們一天經歷了30個世紀,欣賞了晉祠那樣豐富的文物古跡。”[13](P70)
9月4日,在武漢隨中國作家協會參觀團參觀武漢長江大橋,后據此寫新詩《鋼鐵的長虹》,發表于1956年11月1日《工人日報》、1957年10月號《長江文藝》。
9月7日,在漢口寫散文《火車,前進!》。
9月9日,寫雜文《“因陋就簡”》。
自述:“解放后的第十年,我整五十歲,隨二十四人的學習訪問團第一次到上海,那是我半生中的大事。上海市文聯和總工會接待了我們,住上海大廈第十四層樓。我們瞻仰了紀念館,參觀了展覽館、機械廠、造船廠、棉紡廠和幾個大百貨公司,放大了眼界,開擴了心胸,也感到了充實。我們的收獲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上海是一座高山,那么我們只爬了一段盤山的公路;如果上海是一部百萬言的雄文巨著,那么我們只披讀了序言和目錄。這次旅行,離探深谷,窺堂奧,距離還很遠。”[14](P117)
《公木傳》記述:“那是1956年八九月間的一次盛會。全國總工會組織北方作家到南方去參觀旅游,由吳伯簫帶隊,公木和蔣錫金還有穆木天、彭慧等一些在東北辦大學的老朋友都有幸參加了這一行列,前后約20余天中,他們參觀了太原、洛陽、武漢、南京、無錫、蘇州、上海、杭州共八九個城市。這些地方的工業建設和祖國山川、名勝古跡都大開了他們的眼界,好一片郁郁蔥蔥,欣欣向榮的景象!太原晉祠,吳伯簫寫了一篇散文《難老泉》,后被選進語文課本。公木寫了一首同題詩,也多次選入各種版本的新詩選集。”“在從武漢到上海的旅程上,想起天藍來,公木就寫了《懷友二首》,還與同行的作家朋友穆木天、吳伯簫、彭慧等談起天藍所受的委屈,感慨萬千。”[7](P160-161)
10月8日-13日,海涅學術會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魏瑪舉行,往返一個月,返程順訪蘇聯莫斯科,拜謁列寧、斯大林墓,參觀列寧博物館。后寫作《記海涅學術會議》,刊載于1957年《詩刊》1月號(創刊號),一年后寫作散文《記列寧博物館》。
10月24日,在莫斯科寫新詩《謁列寧——斯大林墓》,刊載于本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11月初回到北京。
自述:“海涅學術會議的名稱,直譯應當是學術性的海涅會議。會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魏瑪舉行。魏瑪是世界的文化名城,是詩的城市。那里有偉大的詩人歌德和偉大的戲劇家席勒的故居。今年是詩人海涅逝世100周年,在魏瑪舉行會議討論他的作品和思想是很有意義的。”“會議從1 956年1 0月8日到1 3日,一共開了5天。”[15]
趙瑞蕻記述:“拙作中提到leipzig(萊比錫)和萊比錫大學教授招待所主任朗太太(Frem Maria Lang)等,也許多少會引起你那年到德國訪問、在萊比錫度過的日子的回憶。我記得你看見過那位瑪麗亞·朗夫人(我為你介紹過的),是一位很好的典型的德國知識婦女,她的丈夫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她自己也已于一九六〇年冬逝世了。”[16]
郭小川記述:“早八時許到大樓。九時多,白羽來,得知匈牙利卡達爾成立工農政府,蘇軍出動援助政府平息叛亂的消息,至為欣喜。吳伯簫從德國回來,略談幾句。”[8](P515))
12月10日,致信外甥亓舉安,提及本年下半年一些活動:“今年下半年,我曾于九月間去武漢、上海等地參觀一月,十月間又去民主德國一個月,在家的時候比較少,所以沒有常寫信給你。本月十二日我又要去湖南了,主要了解教科書使用情況,估計明年一月初回京。”
12月12日,隨教育部官員到湖南長沙、湘潭一些學校做調查、聽課,了解文學、漢語教科書使用情況,參觀湖南一師,又見徐特立先生。
自述:“記得1 956年冬天,在長沙交際處大樓,他在走廊一看見我就大談語文分科的問題。當時我很驚訝,因為我參加編輯語文教材以后還沒見過他老人家。可是老人對語文教學從理論到實踐談得條分縷析,頭頭是道。仿佛語文分科這件事他早已經過深思熟慮。分科有什么優點缺點,實行起來會遇到什么問題,他都了如指掌。”[17](P667)
自述:“一晃二十年,一次我去長沙,在一所他(指當年抗大戰友‘韋’,子張注)當頭頭的大學里我們再見。寄東西的事一字不提,他首先拉著我去看號稱‘三絕’(文字,書法,石刻)的李邕碑,瞻仰愛晚亭,暢談毛主席早年進行革命活動的勝跡,他雖然也已經是度過中年的人了,但步履矯鍵,精神抖擻,不減當年。登岳麓山像在游擊隊的時候爬太行山,直到云麓峰都看不出疲累。”[18](P35)
曾仲珊回憶:“大約是1956年,我在湖南省教育廳教研室工作。吳老那時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長,到湖南來作調查,我陪同他在長沙市中學聽了一些語文課,又去湘潭市參加一次語文教師的會議。在長沙市學校聽課的時候,他來回總是步行,從不乘車。在回來的路上談到聽課的印象,他對教師教學的點滴成績,都予以肯定,在湘潭參加會議,他和教師在一個組里討論問題,在一個桌上吃飯,絲毫也不特殊。”[19]
劉征回憶:“單說吳伯簫同志。當時的幾位領導,受到批評,都唯唯稱是,不敢有異詞,獨有伯簫不服。教育部組織了兩個調查組深入學校調查研究,實質上是為那些批評意見搜集事實依據,證明其符合實際,完全是正確的。那年月非常重視調查研究,‘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但是有些調查,實為帶著領導確定的框框去搜集證據,此即一例。調查組分兵兩路,一路按領導的調子跳舞,對分科作出否定的結論;另一路由伯簫領隊,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調查,得出了肯定的結論。兩個報告針鋒相對。吳的調查成了他的一項罪證。教育部組織對伯簫的批判,調子是‘以專家自居,同黨分庭抗禮’。批判進行中,伯簫忽然挺身站起,一手高舉中央文件(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的胡喬木的報告),理直氣壯地說:‘你們說陸部長代表中央,這也是中央,到底哪個是中央,我們應該執行哪個中央的指示?!’伯簫在延安就嘗過挨整的苦頭,并非缺乏黨內斗爭的教訓,在那種眾口一詞的形勢下,敢于如此以大無畏的精神據理力爭,令人感佩。”[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