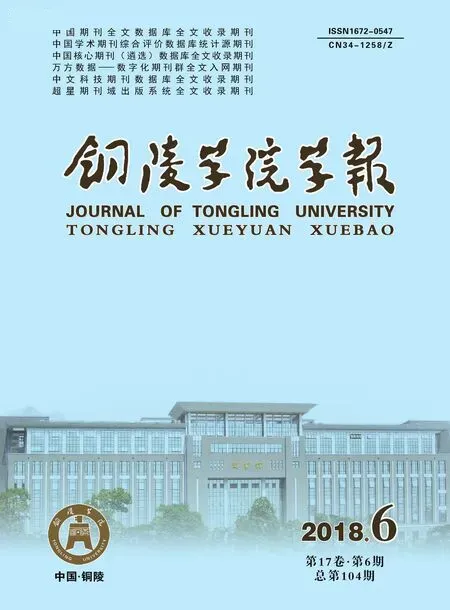優選論視角下的漢語連讀變調二語習得研究綜述
丁 涵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香港 999077)
優選論認為不同的制約條件組成語言,制約條件的普遍性和可違反性可解釋第二語言習得領域中的遷移及發展的相互過程,有效論證中介語發展,找出語言間普遍特征。連讀變調既是對外漢語語音教學與習得的難點,又是語音習得領域的焦點之一。本文在優選論框架下,梳理連讀變調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情況,希望對對外漢語語音習得發展有所啟發。
一、連讀變調研究概況
(一)連讀變調的界定及基本情況概述
連讀變調是音節在語音鏈后產生的現象,是聲調的動態組合。現代漢語中的連讀變調分為單純受語音規則制約的以及受詞法制約的變調,前者包括陽平、上聲和去聲的連讀變調,后者包括“一、不”的連讀變調和重疊詞的連讀變調(Lin,2007)[1]。
古代對連讀變調的記錄追溯至明代。裴銀漢(2000)[2]指出,明代崔世珍《翻譯老乞大》及《翻譯樸事通》注意到了上聲連讀變調的情況,這在漢語研究史上可能是明確記載漢語普通話的變調規律上上相連前上變陽平這一音變規律的首著。
現代較早注意到漢語方言連讀變調是趙元任(1956),發現詞句中單字調變化及語言變異現象的普遍性。較早研究連讀變調的專篇是1947年呂叔湘的《丹陽話里聯詞變調》,討論一般的兩字變調(劉俐李,2004)[3]。
(二)連讀變調的描寫性研究
描寫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漢語方言研究。從變調類型來看,余靄芹(Yue-Hashimoto,1987)[4]將漢語方言中的變調類型分為首音節型變調、尾音節型變調及鄰近音節型變調,將漢語方言分為左變調及右變調。錢乃榮(1992)[5]將吳語的變調分為四種,分別是簡單式、延伸式、初連式及復雜式。方松熹(2000)[6]將義烏方言的兩字組連讀變調歸類為前變型、后變型、不變型和全變型。袁家驊(1989)[7]全面介紹并歸類了北方方言、吳方言、閩方言等七個方言區的連讀變調現象。
從連讀變調與語法的關系來看,學界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了相關研究,主要是語法性變調和語法變調。前者如呂叔湘(1980)[8]列舉采取變調和不變調字組,體現了字組語法結構對變調的重要性。王福堂(1959)得出紹興話變調格式區分詞和詞組的結論。語法變調研究如鄭張尚芳(2014)提出溫州話中用變讀入聲表示近指的語法形態變調。
綜上,筆者發現對于描寫性研究,各方言區不平衡,吳語最多,北方地區方言研究較少,且方言點的描寫較為孤立,比較研究及語言共性研究較少,解釋力不強。并且,研究多注重連讀變調的單線研究,對與之相關的音節、重音、音步和語調等音系現象研究較少,與語義、語法的關系研究缺少深入思考。
(三)連讀變調的解釋性研究
國內外學者尤其是境外學者在生成音系學的理論指導下,對聲調及連讀變調進行研究討論。
王士元(Wang,1967)開創了生成音系學的聲調研究先河,提出一套聲調的區別性特征,更好地解釋漢語方言連讀變調現象。Woo(1972)[9]創造性地改革了王士元的理論,提出聲調的三個區別性特征,分別是[±高]、[±低]和[±修飾]。 Yip(1980)[10]使用自主音段音系學理論建構聲調特征系統理論,并運用浮游聲調和聲調調型等現象解釋了漢語方言的連讀變調情況。Wright(1985)[11]運用節律音系學的重音音步理論解釋上海話和福州話聲調丟失現象,使用載調單位莫拉進一步分析。根據刪除莫拉規則,推出福州話連讀變調模式。徐云揚(1988)[12]應用Pullyblank的普遍化法則,設定及應用個別語言連接法則,將不同音韻層次的上海話中聲調和音段相聯系,解釋上海話連讀變調的原因。林華(1998)[13]在非線性自主音系學框架下提出“調素”概念,運用調素論和調素脫落論解釋雙音節詞和三音節詞。
以上可見,已有研究成果對研究對象是有效的,生成音系學中尤其是非線性自主音系學所包含的浮游聲調、調素等理論對連讀變調現象有一定的解釋力,然而普遍性不夠,應用范圍有限。此外,相較于國外理論探索,國內處于初始階段。
(四)連讀變調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對外漢語聲調研究尤其是連讀變調集中于描寫聲調偏誤,對所獲得的數據進行偏誤分析,提出偏誤原因并預測聲調習得難度。郭錦桴(1993)[14]通過聲學和聽測實驗,發現留學生二字組詞中,連讀變調的偏誤以降調和平調代替其他調型,掌握情況與漢語水平成正比;而對三字組及四字組詞的考察中,他們易將三字組中間字調發成降調,掌握情況較二字組詞困難更大。由于現代漢語中的連讀變調以二字連讀變調為主(吳宗濟,1992)[15],朱川(1997)[16]從難易程度對外國學生在二字調中易偏誤的類型歸類,只有陰平和去聲的二字調容易掌握,包括陽平和上聲的二字調是學習難點,陽平和上聲的搭配最難習得,并從母語負遷移和協同發音兩方面分析偏誤原因。
在對外漢語教學的聲調研究中,主要存在聲調的國別化研究,得出外國學生習得漢語的聲調偏誤共性。在前人研究中,聲調偏誤主要為調型錯誤和調域錯誤。王韞佳(1995)[17]運用實驗語音學方法,發現美國學生習得陰平和去聲是調型錯誤,陽平和上聲是調型及調域錯誤,與他們對聲調感知的敏感度有關。相似的是沈曉楠(1989)[18]、劉藝(1998)[19]。李紅印(1995)[20]發現泰國學生在發陰平和去聲的動態聲調時,主要為調域偏誤,其原因是泰語詞重音后置的影響。得出相似結果的是蔡整瑩、曹文(2002)[21],并總結了教學對策。王功平(2004)[22]使用對比實驗,從調型、音高和音節三方面分析印尼留學生普通話上連讀的偏誤。吳門吉、胡明光(2004)[23]運用聽辨方法,發現全降調的調域較窄,去聲在四個聲調中情況最差。楊娜(2005)[24]從歷時角度,對越南學生連讀變調中的偏誤總結為去聲聲調。因此,越南零基礎學生聲調難易習得順序為去聲、上聲和陰平、陽平。其偏誤原因主要是受到越南語本身及羨余特征的影響。
以上研究中,聲調偏誤大致方向為從調型錯誤過渡到調域錯誤,較多研究單字調聲調,較少研究連讀變調習得。研究涉及的語種不平衡,偏誤原因主要是母語負遷移,研究方法不夠科學,被試容量較少(沈曉楠,1989;李紅印,1995;劉藝,1998;吳門吉、胡明光,2004)。二語習得過程中普遍性分析不多,較少從生成音系學或優選論探討。
二、優選論研究概況
(一)優選論的發展
優選論,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由Prince與Smolensky(1993)提出,研究重點為制約規則,重新定義制約規則的作用,明確制約條件在語言中具有普遍性,即研究語言的共性(Archangeli&Langendoen,1997)[25]。它建立于現有音系描寫與解釋所存在不足的基礎上,是目前主流音系學取得的最大突破,也是生成音系學發展的必然結果。
優選論經歷兩大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經典理論階段,研究語言中意義和詞庫形式的對應關系,涉及音系和句法領域;第二階段涉及語義、語用等其他語言領域,研究語言形式和意義的對應關系。在優選論中,有限和諧序列論(McCarthy,2000)[26]的制約條件體系能夠多次評估輸入式,從而獲得中間層次的表達方式,啟發二語習得中介語研究。目前,優選論最新進展為嘗試解決音系不透明現象的優選論候選項鏈理論(McCarthy,2007)[27],及從語言的產出和理解角度出發的雙向優選理論(Blutner,2000)[28]等。
對于優選論的理論研究和引介工作,國內最早的是王嘉齡(1995),介紹優選論框架體系及以制約條件交互作用的基本內容。李兵(1998)[29]回顧并總結優選論的產生、原理及應用,闡述一語習得、普遍現象和標記性問題及語言歷史演變的優選論觀點。王馥芳(2003)[30]評論優選論的理論框架及優勢,解釋優選論存在的原則不透明、絕對不合格現象和自由變體問題。
(二)優選論的應用概況
1.優選論的音系領域應用研究
在漢語方言鼻化韻方面,Yip(2001)[31]運用了同界制約條件和音長理論研究潮陽話音節結構和閩南語中鼻化現象。鐘榮富(1995)分析臺灣閩南語的鼻化現象,運用優選論的制約條件,從分布、音節合并和音節分開方面做出解釋。
在普通話音節組構方面,鐘榮富(1995)分析普通話二合元音的結構,說明同化制約和異化制約的重要性。 馬秋武(2004a[32],2004b[33])以和諧性制約條件為基礎,指出韻母組構制約條件的排列順序。另外,馬秋武(2004a)指出鐘榮富(1995)提出的制約條件違反優選論有關基礎豐富性的原則且未就音段組構的類型變化進行詳細說明。張吉生(2003)[34]分析漢語外來語音節的可接受性并重新制定針對漢語及外來語音節結構的制約條件。
在元音和諧研究方面,李兵(2004)[35]支持Myers(1997)和 Yip(2002)的觀點,證實了強制性非等值原則屬于標志性制約條件,分析優選論視角下的寄生型和諧現象。
在兒化韻研究方面,林燕惠(Lin,2001)[36]概括義烏方言兩類兒尾音變的有等級限制制約條件,突出優選論優勢。馬秋武(2003)[37]指出北京話兒化的不透明性,并應用共感理論解釋。周晉英(1999)[38]提出兒化韻的制約條件,通過層級篩選,解釋不同韻母兒化的異同點。
在漢語聲調研究方面,主要是漢語聲調分布規律及方言輕聲和連讀變調的優選論分析。在漢語聲調分布規律方面,蔣平(1999)[39]運用優選論闡述了漢語方言聲調分布概況,對聲調跨方言分布的不對稱性及各漢語方言中聲調分布的差異性提供有力渠道。
在漢語方言輕聲研究方面,路繼倫、王嘉齡(2012)[40]、孔慧芳(2006)[41]和魏玉清(2008)[42]對漢語不同方言輕聲作了詳細闡述。路繼倫、王嘉齡(2012)對六種方言輕聲進行分析,制定“輕聲”的制約條件,并針對不同方言制定“延長”、“莫拉”等制約條件,體現各方言間的聲調音系特點。
在漢語連讀變調研究方面,陳淵泉(Chen,2000)和閆小斌(2010)[43]對漢語方言連讀變調域的建構進行闡述,為不同漢語方言的連讀變調現象提供統一解釋。Chen(2000)、王曉梅(2009)[44]、馬秋武、吳力菡(2012)[45]研究天津話連讀變調的雙向性變調,且Chen(2000)引入涉及推導的制約條件解釋音系不透明現象。 Chen(2000)、林蕙珊(Lin,2004)[46]和閆小斌(2010)研究了博山話連讀變調。Chen(2000)提出制約條件,林蕙珊(2004)指出 Chen(2000)的時序性制約條件無法說明方向性連讀變調,因此可以在經典優選論框架下闡釋博山話的連讀變調。李文欣(2012)[47]指出天津話連讀變調可以在反復評估中推導,彌補了經典優選論的缺陷。從連讀變調類型來看,翟紅華(2014)[48]提出調域和調型制約條件,進而分析山東方言連讀變調模式,避免了以往相關研究中解釋過少的理論不足。
2.優選論的語言音系習得領域應用研究
(1)優選論的兒童語言音系習得領域應用研究
優選論不僅捕捉語言共性,而且嘗試解釋許多音系習得現象。在兒童語言音系習得領域中,Tesar與Smolensky(1995)[49]、Dekkers,Leeuw 與 Weijer(2000)[50]認為在母語習得初始階段,兒童所接觸到的優選輸出形式,都會使得違反它的制約條件降級,因此,制約條件就變成了一種層次分明的等級體系。Kager(1999)[51]對荷蘭語的實例分析,證實了Tesar(1996)的觀點,即兒童可以通過反復學習建立制約條件的等級體系。Goad(1997)、Barlow 與 Gierut(1999)、Bonilha(2000)[52]、Chin(2008)[53]、Stemberger,Bernhardt與 Johnson(1999)[54]研究不同國家兒童(包括聾童)的輔音和諧、音節結構、法語音系、輔音叢及U形習得。
(2)優選論的漢語連讀變調二語習得領域應用相關研究
在優選論的框架下研究第二語言的語音系統可以更好地了解該語言的地位 (Hacin-Bhatt&Bhatt,1997)。在第二語言音系習得領域中,Swanson(2007)[55]在送氣性制約條件和忠實性制約條件下分別對母語不同的兩組實驗對象進行二語音系過程的習得研究,發現個體差異需要在優選論的框架下解釋。Broselow,Chen 與 Wang(1998)[56]研究中國人習得英語時存在的輔音音尾缺失現象,在習得過程中,學習者會重新排列他們腦海中的制約條件,降級標志性制約條件。相似的還有Bunta與Major(2004)[57]對匈牙利的英語學習者的英語元音習得做的調查。
國內使用優選論研究學習者的音系習得較少。閻麗莉與蔡金亭(2004)[58]在優選論理論下調查了中國的英語學習者習得英語輔音群,發現學習者的偏誤違反了優選論的忠實性制約條件,因此學習者的英語輔音群習得經過了標記性制約條件的降級。曹瑞斕(2010)[59]對中國英語學習者習得英語英語音節輔音叢sC/sCC后發現,學習者的習得歷經優選論的制約條件相互調整及序列等級排列的過渡,因此中介語音系存在非標記性隱現。
筆者在知網搜索關鍵詞“優選論”及“連讀變調習得”,迄今只有儲丹丹(2006)[60]一篇碩士論文。其采用命名任務,運用實驗考察不同水平與背景的漢語留學生連讀變調習得及偏誤情況,并在優選論框架下解釋分析。結果表明,優選論中介語制約條件等級體系的不完備性可以解釋留學生的強勢偏誤。
回顧優選論的發展與應用研究,可以發現其已成為音系學研究的主要理論,并在理論的實際運用中不斷發展和完善,國外理論及應用方面較為完善,國內對優選論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引介與框架構建工作,在音系領域研究中主要運用該理論解決漢語方言中存在的一些音系現象,二語習得包括音系習得方面運用該理論討論的論著較少,尤其是將優選論和漢語連讀變調二語習得兩者結合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挖掘空間依然很大。
三、結論
造成外國學生學習漢語 “洋腔洋調”的原因主要是聲調和比聲調更高的語音結構層次。漢語四個單獨聲調容易習得,但聲調組合形成的連讀變調是對外漢語教學中一大難點。前人研究主要集中于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探尋中介語的語音系統及偏誤特征,研究對外漢語語音習得的個性較多,共性較少。而優選論的制約等級可以闡釋語言習得領域中的遷移與發展相互作用的問題。前人對漢語連讀變調的優選論研究主要集中于方言的解釋上,并運用制約條件建立了連讀變調模型,那么在優選論闡述的基礎上,如何運用二語習得者在學習漢語中的中介語所起的作用及優選論框架下的評估器和輸出式的模式,建立一套中介語的制約條件等級體系,及如何運用優選論解釋漢語連讀變調二語習得情況等,都是值得思索探究之處。本文希望拋磚引玉,為對外漢語語音習得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