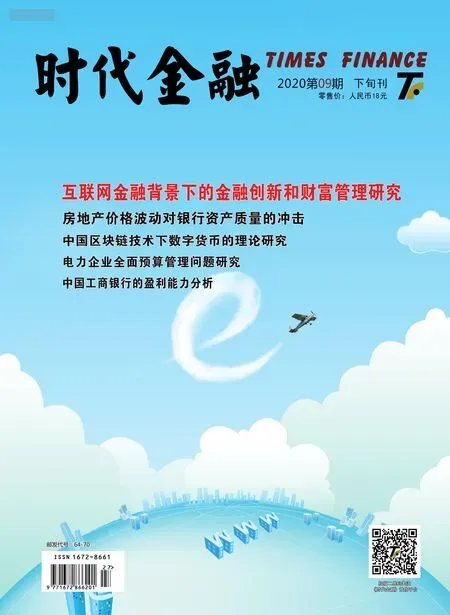產業轉移與經濟增長研究綜述
武惠惠 朱 兵
(安徽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3)
自20世紀30年代起產業轉移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90年代后期國內學者也競相開展有關研究,而今產業轉移各層面的研究則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一、國外產業轉移研究
(一)產業轉移的理論研究
基于產業視角的研究,形成了以下幾種理論代表,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的理論基礎。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了雁型發展理論,認為次發達國家的行業生產要經歷進口階段-國內生產階段-出口階段的過程[1]。美國經濟學家索德·弗農提出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產品的市場壽命分為創新-發展-成熟-衰退四個階段,并認為產品與產業的周期性發展促成了產業的區際轉移[2]。隨后,梯度轉移理論應運而生,該理論認為通過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要素和產業能夠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日本學者小島清提出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認為投資國將相對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至該產業處于相對優勢地位的國家,是對兩國福利最大化的選擇[3]。發展經濟學開拓者劉易斯從發達國家缺乏足夠的低成本勞動力角度出發,提出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理論,認為追求大量勞動力資源使得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4]。
基于企業視角的研究,英國學者卡森和巴克利提出了內部化理論,發現在市場交易中企業成本升高由壟斷和市場機制不健全造成,若將外部市場以公司內部市場代替就能發揮內部轉移價格的優勢作用[5]。內部化優勢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得到運用,通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方式降低要素和運輸成本。英國普雷丁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鄧寧在70年代末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提出國際市場投資必須具備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和企業所有權優勢[6]。
基于國家視角的研究,被廣為認可的“中心—外圍”理論由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維什提出,他認為外圍國家在發展中對中心國家技術和資本的依賴使得外圍國家處于不利地位,造成利益分配不均衡,而實行工業化則是外圍國家擺脫這種困局的捷徑[7]。在此基礎之上,其他學者也提出了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例如阿明的“依附論”、漢斯·辛格的“貿易條件全面惡化論”。他們認可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不利地位,低附加值的產業結構使得發展中國家無法獲得高技術產業壟斷下發達國家的發展優勢。事實上,發達國家在獲得產業結構升級契機的同時也為發展中國家的建設提供了發展路徑。
(二)產業轉移的影響因素研究
針對產業轉移影響因素的研究,綜合相關學者的觀點,列舉了以下廣泛適用的幾個要素,但產業轉移的影響因素不僅限于此。第一,比較優勢,小島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當立足于比較成本原理,通過產業的空間移動回避劣勢產業以及擴張優勢產業。圖梅和泰勒實證發現產業轉移的主要因素取決于區域間距離、原有區域和目標區域的規模、各區域的相對經濟優勢[8]。第二,要素稟賦,赫爾普曼從國際貿易角度強調產業國際轉移與關稅、運輸成本、投資壁壘有較大的相關性[9]。威廉姆遜認為產業早期的擴張是試圖達到對供應和市場的控制[10]。第三,規模經濟,惠勒和莫迪發現美國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主要是尋求集聚經濟和市場規模[11]。迪肯在對美國汽車行業的研究中發現產業轉移的動因在于追求規模效益或規模經濟[12]。第四,國家政策,普雷維什認為正是發展中國家加快國內工業化的策略促使了產業的轉移,從貿易保護主義理論出發解釋了國際產業轉移受國家行為的影響[13]。阿什克羅夫特和泰勒建立模型將產業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產業轉移首先發生于國家層面,然后在區域間依據區位優勢重新分配[8]。
(三)產業轉移的效應研究
產業轉移的目的在于實現效益提升與經濟增長,因此對產業轉移經濟成果的衡量成為研究重點之一。哈達德和哈里森對摩洛哥公司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更高水平的國際產業轉移并不一定會帶來國內企業生產率的增長[14]。克萊爾通過模型指出在跨國公司與本地企業聯系微弱的情況下,產業轉移與本國經濟增長呈負相關[15]。潘德認為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生產率也不同,這種差異造成的結構紅利使得生產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門流動,從而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一過程揭示了產業結構變遷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原因[16]。在對產業轉移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之外出現了污染避難所假說、污染暈輪假說、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等,研究的視野從片面的經濟產出上升為從經濟、社會、環境等多角度衡量產業轉移帶來的全面影響,對之后的研究有啟發意義。
二、國內產業轉移研究
(一)產業轉移動因研究
關于產業轉移動因的解釋眾多,本文列舉了以下代表性觀點。李穎基于比較優勢動因發現我國紡織業區位轉移的動力是全要素生產率的相對優勢[17]。張鑫基于產業集聚動因認為規模經濟效應是產業發生區位轉移的推動力,集聚區的不經濟狀態促使產業向具有良好競爭力的地區靠攏[18]。戴宏偉基于經濟發展階段提出各地區要素稟賦的差異造成各地區產業結構分工不同,正是這種差異帶動了要素的跨區域流動與產業的區際轉移[19]。借鑒國際相關學者研究觀點并立足我國現狀,國內學者發現基于區位經濟效應的集聚動因與尋求區位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動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產業為降低成本進行轉移的活動。
(二)產業轉移模式研究
石東平和夏華龍從梯形產業轉移論出發認為產業升級的發展路徑為勞動密集產業-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由此從低層級往高階梯方向發展[20]。汪斌則將產業以工序型轉移模式劃分為垂直順梯度轉移、垂直逆梯度轉移、水平轉移等[21]。馬子紅和胡洪斌從影響因素角度出發將中國產業區際間轉移歸納為以下七種模式:成本導向型轉移、供應鏈銜接型轉移、競爭跟進型轉移、追求規模經濟型轉移、市場開拓型轉移、政策導向型轉移和多元化經營型轉移[22]。不同研究視角下學者的劃分方式豐富了對產業轉移模式的認知。
(三)產業轉移對策研究
魏后凱分別就轉出區與轉入區的戰略選擇提出了對策,對轉出區而言,為避免傳統產業轉出弱化地區經濟發展,應適時調整產業結構并加快產業升級改造,積極培育先進加工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對轉入區而言,需要有選擇的承接相關轉移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同時加強軟環境建設,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建設環境友好型發展模式[23]。戴宏偉從國際產業轉移的現狀出發,就我國參與國際市場產業轉移提出的對策是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同時考慮承接地的可持續發展,不能盲目追求經濟發展而以破壞環境為代價[24]。參與國際產業轉移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產業轉移優勢加快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促進自主創新;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同時有利于內資轉移出去,積極參與到亞太地區經濟技術合作與一帶一路建設中。
三、產業轉移與經濟增長研究
目前,學術界對產業轉移與區域經濟增長的研究并沒有得出一致的觀點。一方面,學者認為產業轉移有利于轉入地經濟增長水平提高、資源配置優化、就業潛力提升等,而且還會促進轉出地產業轉型升級、帶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部分學者認為產業轉移對經濟可持續發展也會造成不利影響。對轉出地,產業轉移可能會使大量生產要素流失而導致“產業空心化”;對轉入地,引入資源密集型產業后,本地區資源利用強度加大將加重區域內的承載壓力,對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挑戰。因此,諸多學者研究認為產業轉移對轉入地和轉出地的經濟增長有利有弊。
在產業轉移促進經濟增長方面,鄒璇認為要素流動和產業轉移有利于消除區際發展壁壘,促進區域經濟穩步增長[25]。周世軍等研究發現產業轉移通過加強產業集聚程度推動了區域經濟增長,也促進了區域間的協調發展[26]。張遼以我國各省區面板數據為對象研究發現產業轉移通過資本、技術和勞動力三要素的加總效應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27]。王龍等對中西部地區的研究表明區際間產業轉移對承接地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并對省際間經濟增長的正溢出效應顯著[28]。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對僅從經濟增長數量考量提出質疑。郭麗認為對后發區域而言,產業轉移可能帶來生態環境惡化而造成產業結構失衡,也可能沖擊本土企業[29]。肖挺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調整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同時會帶來環境污染,產業結構優化除東部地區以外基本上加劇了總體發展局面的嚴重性[30]。郭子琪等提出產業轉移造成污染轉移的同時并未帶來經濟的同步轉移,發達地區仍然控制著大部分的經濟利益,使得欠發達地區可能落入“經濟欠發達-開發-資源耗竭、環境惡化-資源環境約束經濟發展-經濟落后”的惡性循環中[31]。進一步地,張秀生等運用DEA模型從產業的轉出與承接角度對國內主要地級市進行了分析,提出產業轉移對整體全要素生產率出現初顯著負效應,對承接地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出顯著負效應,對轉出地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出正效應[32]。吳傳清以長江經濟帶的中上游區域為對象采用DEA模型測度了包括經濟產出與環境產出在內的生態效率,認為產業轉移對中上游區域的整體生態效率未造成損害,但對中游區域生態效率呈顯著負效應[33]。總體來說,產業轉移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不明顯,主要在于產業轉移通過產業集聚、技術溢出、要素流動和結構調整等作用于區域經濟增長的機制尚無具體范式,對經濟增長效率的衡量基于單純經濟數量角度存在不合理之處,而基于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卻未形成統一的衡量標準。
四、結語
縱覽國內外大量文獻可知,產業轉移研究至今已形成諸多理論與實踐成果,但不可避免仍存在以下問題有待研究。首先,相關研究大多從宏觀和微觀角度研究了產業轉移的理論發展、影響因素、轉移績效等。從定量角度的研究也多集中于經濟增長數量而忽視了經濟增長質量,已有的考慮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的研究也未形成完整的指標體系。從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出發,單純的數量式經濟增長忽略了地區資源環境承載力以及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污染的負外部性。因此將環境的負外部性產出納入到經濟增長效率的測算框架,以全面反映其影響方式具有現實價值。其次,目前對經濟增長效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對具體區域的實證分析,而從產業轉移角度研究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作用路徑,揭示產業轉移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機理的研究尤顯不足。相關實證研究大多止步于對策建議,而對產業轉移與經濟增長機理的解釋缺乏深入研究。因此理論角度的探討也尤為必要。最后,針對產業轉移影響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提出的對策建議大多不具現實操作性,提升經濟增長效率的舉措本身復雜而多樣,因此探究產業轉移如何更好地提升經濟發展水平,需要從區際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綜合考慮和完善。立足于相關學者的研究貢獻,發現不足正是未來可以研究與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