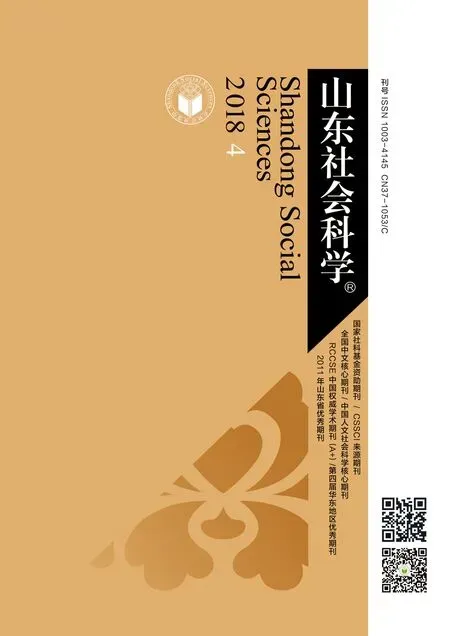馬克思人類學思想的再闡釋
——《人類學筆記》與作為人類學家的馬克思
卯 丹
(貴州民族大學 社會建設與反貧困研究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作為人類思想史上最燦爛群星中的一員,馬克思在生命歷程中呈現給世人的思想肖像卻是不同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許是馬克思一生中思想的轉變與身后大量手稿的出版。特別是身后出版的大量手稿,都是馬克思的未定稿,亦是他思想的未定型版本,故而引發了后世學者對他思想解讀的各種分歧。特別是馬克思晚年間(1879—1882年)對摩爾根等人的人類學著作所做的筆記,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又稱《民族學筆記》《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本書匯集了馬克思所有的人類學筆記摘錄內容,而本文所探討的《人類學筆記》,即是以該書的內容展開的。參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簡稱《筆記》),是晚年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最早對馬克思《筆記》做解讀的是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他于1972年編輯出版了《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TheEthnologicaiNotebookofKarlMarx)一書,收錄了馬克思對摩爾根、菲爾、梅恩和拉伯克等人四部著作的讀書筆記*Krader,L: The Ethnologicai Notebook of Karl Marx .Assen: Van Gorcum,1972.。克拉德對馬克思及其《筆記》的評價尤其值得重視,他十分認同馬克思對人類學的研究方式,認為馬克思不僅經歷了所處19世紀人類學學科的轉變歷程,即從一門哲學的學科變成了一門經驗的學科,還親身參與其中,他的著作亦經歷了從哲學的人類學到經驗的人類學的轉變*克拉德:《作為民族學家的卡爾·馬克思》,載《馬列主義研究資料》1985 年第1 輯,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作為對克拉德的響應,國內人類學家黃淑娉也旗幟鮮明地認為《筆記》是人類學理論學派中的進化學派著作*黃淑娉:《進化學派的人類學與馬克思:讀〈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社會科學輯刊》1990年第6期。。克拉德之后的許多國外學者,特別是人類學家與哲學家都對馬克思的《筆記》給予了很大關注*葉林、張顯揚:《國外關于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的研究》, 載《馬克思主義研究》1986年第3期。。中國學界對《筆記》的熱烈探討出現在1980至1990年代,當時的《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以兩期探討《人類學筆記》的特輯形式,分別在1988年*高崧、駱靜蘭、胡企林編:《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第11輯(特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筆記研究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以下簡稱“《1988年〈特輯〉》”)和1993年*胡企林、李宗正、陳勝華編:《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第15輯(特輯)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譯文集》,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以下簡稱“《1993年〈特輯〉》”),編輯(譯)了兩期國內外關于《筆記》的討論文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的《1988年〈特輯〉》,收錄了18位中國學人關于《筆記》的討論文章,以人類學角度觀之最為重要的討論文章是楊堃與周星合著的《關于馬克思晚年民族學筆記的思考》,該文主要是對克拉德編輯的《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一書的評介與對話,主要從內容的翻譯問題及馬克思生命中思想的轉變特征來認識《筆記》一書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認為其晚年對民族學理論的興趣、動機與對人類社會的思考是分不開的,都是其試圖完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嘗試*楊堃、周星:《關于馬克思民族學筆記的思考》,載高崧、駱靜蘭、胡企林編:《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第11輯(特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筆記研究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67-284頁。。《1993年〈特輯〉》翻譯并收錄了國外19篇蘇(聯)、美、德、英4國學者關于《筆記》的分析論文,其中較為重要的文章有列文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人類學》、萊維特的《馬克思的人類學和進化論問題》,以及克拉德的《西歐著作中的東方社會史》《東方社會觀探源》《進化論、革命和國家:馬克思與他的同時代人達爾文、卡萊爾、摩爾根、梅恩和科瓦列夫斯基的批判關系》*這些文章參見胡企林、李宗正、陳勝華編:《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第15輯(特輯)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譯文集》,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47-192頁。等,分別從各自角度探討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人類學觀念。總的來說,國內外學術界對《筆記》的研究現狀,聚焦點集中在人類學(民族學)與哲學領域。國外人類學(民族學)界對《筆記》的研究,主要是關于結構馬克思主義與“辯證人類學”的爭論,前者以“多元決定論”取代“經濟決定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來建立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理論,后者繼承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理論,主要目的是展開現代文明的批判;哲學界對《筆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社會制度及歷史和馬克思對社會發展模式的探索這兩大方面*⑨曹典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57-71、72-85頁。。國內人類學(民族學)界對《筆記》的研究,主要是從古代社會的研究探討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而哲學界對《筆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社會主體、原始公社和國家發展理論諸方面⑨。本文不想涉及并陷入關于《筆記》討論的所有學術爭論里,只集中探討《筆記》的人類學學術價值和作為人類學家的馬克思這一話題。以下便從《筆記》產生的背景、主要內容及《筆記》與作為人類學家的馬克思三個方面,詳細論述之。
一、《人類學筆記》產生的背景
戴維·麥克萊倫(David McLellan)在他權威的《馬克思傳》書中,簡略敘述了馬克思晚年摘錄《人類學筆記》的情況。他寫道:“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對剛出現的人類學很感興趣,并熱心路易斯·摩爾根的著作……摩爾根著作中特別引起馬克思興趣的是原始部落的民主政治組織以及他們的財產共有。”*[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王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0-421、421頁。
馬克思的最后10年,也被稱為“慢性死亡的10年”*[德]弗·梅林:《馬克思傳》,樊集譯,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19、621-624頁。,這時他的身體健康狀況很糟糕,只要“重新回到理論工作…舊病就會復發:大腦的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失眠,即使大劑量的安眠藥也不能使之緩解。每一次突然發作都讓人提心吊膽”。這樣的狀況使得馬克思無法繼續完成《資本論》的第2、3卷及其他理論著作,只能在文學與數學的世界里尋求精神放松,而《筆記》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中寫下的。那馬克思為何會在健康狀態十分不佳的最后10年,還熱心關注新生的人類學的著作,并很細心地閱讀摘錄呢?這恐怕要追溯到《筆記》寫作的大時代背景和馬克思的學術背景上,方能夠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筆記》的相關內容。
《筆記》的寫作時間是19世紀70至80年代,此時的大時代背景之一,無疑是資本主義的重要發展階段,即正走向資本主義壟斷階段,也是大衰退時期*曹典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頁;[法]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吳艾美等譯,東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54頁。。對資本主義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7、275頁。,“資本主義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7、275頁。,資產階級“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7、275頁。。無疑地,馬克思的敘述也透露了那個時代資本主義重要的特征。《資本主義史1500—1980》一書曾對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危機有過深刻的敘述和刻畫,如銀行倒閉、失業、資本衰退等*[法]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吳艾美等譯,東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50頁。。概言之,《筆記》摘錄和寫作的這個時期,正是資本主義的劇烈動蕩時期,前景不容樂觀。《筆記》的寫作的大時代背景之二,是當時無產階級的革命形勢風起云涌,復雜多變。值其時,巴黎公社革命剛剛失敗,這首個無產階級政權僅僅存在了72天(1871.3.18—5.28),便被資產階級瘋狂鎮壓而以失敗告終,無產階級或被捕、或被流放、或被殺害,達10余萬之眾*車有道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湖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55頁。。不僅如此,當時無產階級諸代表的觀念也存在著分歧*車有道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湖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55頁。,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也出現瓶頸,停滯不前,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尚待實踐及探索*曹典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4-28、28-33頁。。
無疑,馬克思的學術背景上更多植根于德國的哲學體系與西方思想脈絡,特別是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哲學理論,但馬克思此外也特別重視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經驗和歷史社會事實,如《筆記》的產生就是這種關懷的產物。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理想狀態,主要是對黑格爾《歷史哲學》*[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中理想社會狀態的揚棄。曹典順將馬克思這種理想社會狀態的西方思想背景歸納為四類,即以國家倫理為主題的社會權力、以宗教神學為主題的社會宗教、以個人主體性為主題的社會現代性和以絕對精神為主題的黑格爾社會思辨思想*曹典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4-28、28-33頁。。同樣地,理解《筆記》就必須理解馬克思本身,而傳統的馬克思理論認為其主要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領域。馬克思哲學最重要的特征是辯證法,其次是時代精華,再次是源于實踐、檢驗于實踐,最后是其批判性與革命性;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特征,一是闡明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規律,二是指出剩余價值理論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所在,三是認為資本主義永遠處于危機之中;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也有三個特征,即以私有制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必會終結,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和科學社會主義是宏大敘事而非微觀確證*曹典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4-28、28-33頁。。
顯然,馬克思的《筆記》產生的背景,無論時代背景或學術背景,都較為復雜,這為后世解讀作為手稿的《筆記》在整個馬克思理論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制造了種種困難與謎團,這也是造成后世解讀《筆記》有各種分歧的直接原因。但換言之,此種情況于馬克思及其總體學說一樣,充滿爭議與可能性,這又何嘗不是馬克思理論遺產解釋并改造世界的方式呢?就是如此,由果造因,因亦造果。
二、《人類學筆記》的主要內容
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是馬克思人類學思想最明顯的表達,中文版幾經努力,最后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為《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一書,于199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內容繁復,篇幅巨大,達58.5萬余字,544頁。《筆記》一書的內容主要包括五個部分:一是《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第1冊,1879年莫斯科版)一書摘要》,中文版共121頁;二是《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文版共244頁;三是《約翰·菲爾爵士〈印度和錫蘭人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書摘要》,中文版共66頁;四是《亨利·薩梅納·梅恩〈古代法制史講演錄〉(1875年倫敦版)一書摘要》,中文版共88頁;五是《約·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1870年倫敦版)一書摘要》,中文版共21頁。
《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第1冊,1879年莫斯科版)一書摘要》,是馬克思對俄國學者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一書所作的摘要。該書描述了北美洲印第安人、南美洲印第安人、印度土著和穆斯林、阿爾及利亞土著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以及殖民主義者對這些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瓦解的過程。馬克思在摘要中考察了原始公社土地制, 肯定農村公社是土地的主人,否定國君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同時,馬克思揭露了殖民地當局對當地的土地所有制性質的歪曲,批判了他們以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為依據, 打著“經濟進步”幌子強制瓦解公社所有制,并扶植大土地私有制的做法。馬克思認為,殖民當局的這些做法,不會給當地社會帶來任何進步,而只會給他們帶來深重的災難。此外,馬克思不同意馬·柯瓦列夫斯基將亞、非、美洲諸古老民族的社會歷史演變與西歐的社會歷史做簡單機械的類比,故而將這些對比在摘要時刪除或修改。另馬克思對印度在德里蘇丹統治時期和莫臥兒帝國統治時期土地關系的變化及性質作大段摘錄與評注,認為與其說此時期的土地關系是“封建化”,還不如說是“農奴制”的因素;且印度集權君主制的存在,其實妨礙了印度社會如同西歐那樣轉化為封建制度,也沒有使農村公社的社會職能轉變為國家職能。馬克思在這篇摘要中關于農村公社及其古代社會經濟形態發展規律性的觀點,對了解晚年馬克思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說明)第2-3頁、第1-121頁、第4-5頁、第122-366頁、第5頁、第367-433頁。。
《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是馬克思對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所作的摘錄,亦是馬克思用力最深最勤的部分。在《古代社會》*[美]摩爾根:《古代社會》,楊東莼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版。一書中,摩爾根通過自己長期廣泛的調查研究,發現了原始社會的社會結構,認為母系氏族(之后轉變為父系氏族)是原始社會的基本單位,并闡明了家庭形式的演變規律, 認為家庭與婚姻形式在原始社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且是私有制的產生導致了專偶制家庭的產生和文明社會的建立。摩爾根的這一觀點與馬克思對原始社會的發展規律及唯物史觀極為契合。因此,馬克思對摩爾根的這本書十分用心, 不僅從表征家庭、私有制、階級和國家起源諸方面作了詳細的內容摘錄,還對原書的結構進行了重新改造,剔除了他認為的錯誤觀點與不完善的說法。如摩爾根的著作認為從生產技術的發展到政治觀念的發展,再發展到家庭形式的變化與私有制的產生,這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但在馬克思的摘要中,這個演變結構被改為從生產技術的發展和家庭形式的變化到私有制和國家的產生。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即原始社會建立在兩種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人本身的生產)的基礎之上;私有制產生了階級和國家,導致了氏族制度的滅亡。此外,馬克思對摩爾根著作的摘要,不僅僅寫下了許多觀點性陳述的評論,還糾正了摩爾根一些不完整的論點,如摩爾根認為火是人類社會早期的次要發明,而馬克思認為是主要的,等等。摩爾根書中對人類親屬制度的研究是人類學界公認的最重要貢獻,馬克思對此進行了升華,認為不僅親屬制度,還有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學的體系,都是同樣的道理。另馬克思對專偶制家庭的起源和性質,還有從母系氏族過渡到父系氏族的原因和意義,也作了相關闡述。在摘要中,馬克思從古代作家的著作中引用了大量段落來補充希臘羅馬社會的分析,敘述了希臘羅馬社會中私有制的產生、氏族的瓦解及階級和國家的形成、階級之間的關系,等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說明)第2-3頁、第1-121頁、第4-5頁、第122-366頁、第5頁、第367-433頁。。總之,馬克思試圖用摩爾根的古代研究來驗證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適用性,這是他對此書摘要的最重要目標。
《約翰·菲爾爵士〈印度和錫蘭人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書摘要》,是馬克思針對英國官員約翰·菲爾作的《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所作的筆記。約翰·菲爾的這本書,主要寫的是他工作多年的孟加拉和錫蘭的當地農村狀況。馬克思對該書摘錄了孟加拉現時的農村生活、錫蘭的農業經濟和印度雅利安人社會土地制度的演化三大方面的資料, 但對整個著作持否定態度。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該書實質內容上甚為簡略,二是此書深受梅恩的影響,對個體家庭和社會之關系作了錯誤的歸納*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說明)第2-3頁、第1-121頁、第4-5頁、第122-366頁、第5頁、第367-433頁。。該筆記還從東方社會的經濟、文化、宗教與社會特征四個方面探討了東方社會模式的構成問題*曹典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95-97頁。。
《亨利·薩梅納·梅恩〈古代法制史講演錄〉(1875年倫敦版)一書摘要》,是馬克思對英國法學家亨利·薩梅納·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講演錄》一書所作的摘要。梅恩在學術界以古代法律闡述古代歷史的“權威”學者,《古代法制史講演錄》一書以“法律和社會的發展起源于‘各種關系的契約’”這一著名觀點為原則, 考察了古典法和印度早期法的演變,認為早期社會中, 人們之間的關系受性別、年齡、家庭關系等的制約, 隨著社會的發展, 人們逐漸轉而受各種契約的制約, 契約關系不注重人的身份, 而是把各個分散的、獨立的個人組成社會。梅恩的觀點間接認為社會的原始形式不是氏族,而其所研究的印度的父權制大家庭。由于馬克思摘要和評論該書的目的是為了深刻的理解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中的相關理論,而不是認同梅恩的觀點*曹典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98、97、100頁。。所以,馬克思對梅恩書中的觀點進行了批判,認為梅恩是從法律觀點對英國殖民主義罪惡的辯護。此外,馬克思還認為梅恩的觀點是一種資產階級抽象的、超階級的國家觀,于是他在摘要中論述了國家的起源、其階級性質和必然消亡*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說明)第6頁,第434-522頁、第6頁、第523-544頁。,其要旨在于關注古代法律與社會體制之間的關系*曹典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98、97、100頁。。
《約·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1870年倫敦版)一書摘要》,是馬克思對英國古史學家約·拉伯克所著《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一書的簡短摘要,從文本結構來說分為三大部分,即婚姻與親屬、宗教與政治、家庭與法律,旨在通過社會形態的研究闡明社會形態更替的必然性*曹典順:《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98、97、100頁。。約·拉伯克的著作研究的是原始婚姻與家庭制度。馬克思對該書作了作了尖銳的批判,認為約·拉伯克不了解氏族的本質,同時批判了他在原始的家庭形式和婚姻關系演變及宗教起源等問題上表現了許多資產階級的偏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說明)第6頁,第434-522頁、第6頁、第523-544頁。。
三、《人類學筆記》與作為人類學家的馬克思
著名人類學家雪莉·奧特納(Sherry B. Ortner)在最近一篇人類學理論史文章中寫道,盡管“馬克思-涂爾干-韋伯”三大家仍是當下社會理論核心訓練的授課基礎,但從對人類社會的現實解釋力而言,馬克思的影響較之涂爾干與韋伯,在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增長*Ortner, Sherry B.: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016,6(1): 50.。盡管奧特納是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所謂“黑暗面”(Dark)的有力闡釋來論述其影響力的,卻也在告訴人們一個重要的事實,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認,馬克思“就在那里”,就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里,闡釋和改造著我們生活的世界。
而作為人類學家的馬克思*對馬克思是一位人類學家,帕特森這位美國人類學家亦從馬克思的哲學人類學與經驗人類學的層面給出了自己獨到的解答。參見[美]托馬斯·C·帕特森:《卡爾·馬克思,人類學家》,何國強譯,云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也通過作為經驗人類學的《筆記》和作為哲學人類學的其他著作,深深地影響著人類學這個學科。第一個編輯出版《筆記》的克拉德言道:“在這里可以看到,馬克思在他的晚年重新撿起了青年時代所關懷的問題:對自然狀態的人和文明條件下的人的批判。可是他早期的方案是從哲學人類學(人本學)的抽象概念出發的,而后期的著作則是從有關人的現代意義的科學觀點來考察問題”。克拉德繼續論述說,早期的馬克思闡發了一系列哲學人類學的觀點,且從19世紀的50年代開始,他對人類學的研究,就逐漸從哲學課題轉到經驗課題方面來了。故而馬克思對哲學人類學和經驗人類學的態度, 成為他的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爭論焦點,即其思想是否具有一貫性。在克拉德看來, 這是一個“表面看來不連貫而實際上可能連貫”的問題,他的例證是馬克思在1841-1846年間探討的問題,與他1857-1867年間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 》和《資本論》各卷探討的問題實質上是一致的,且在1879-1893年間,馬克思對人類學的研究更加系統。馬克思在《大綱》中探討了原始民族的經濟和社會狀況, 后來又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又重新扼要地提到這個主題。在《資本論》講社會分工的章節里, 他又把原始社會的生產同資本主義生產進行對比分析。此外,在馬克思青年時代所闡發的哲學人類學觀點中,與晚年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筆記關系特別密切的是:關于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的相互關系問題(即《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人在社會里和在自然界里的異化問題(“經濟學-哲學手稿”文章)、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并通過他在社會中的各種關系生產和體現他本身(《德意志意識形態》和《神圣家族》),以及把人的具體化和抽象化對立起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克拉德進一步指出,馬克思對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是和農村公社、土地問題及農民問題的研究分不開的, 這些研究既是歷史問題的研究, 也是當時爭論問題的研究, 同時還涉及到在農業中科學技術的應用問題。馬克思還提到了多瑙河流域各公國和東方問題, 特別是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印度和中國的狀況。故馬克思的這些觀點是和歷史宿命論針鋒相對的,且也是直接反對一般歷史主義特別是歷史決定論觀點的。馬克思的《筆記》可以說正是一部涉及到古代國家以及古代和現代公社和部落問題的專門著作。由此,克拉德得出結論說:“可見,馬克思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筆記手稿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和《資本論》中的有關論點的補充,同時又是對他在1843-1845年期間所持觀點的發展”*轉引自葉林、張顯揚:《國外關于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研究》1986年第3期;亦請參見Krader,L: The Ethnologicai Notebook of Karl Marx .Assen: Van Gorcum,1972.。。因此,馬克思作為人類學家的觀點是前后一致的。
英國人類學家莫里斯· 布洛克(Maurice Bloch) 在其《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Marxism and Anthropology)一書中,敘述了馬克思接觸人類學的經過。他說馬克思是逐漸深入人類學領域的,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的興趣還主要集中于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相連接的歐洲封建社會時期,還未注意到氏族社會。至1873 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案)》中,其就以很大篇幅來討論古代社會、東方國家和氏族社會。之后,馬克思的著作中越來越多地引用人類學資料,直至后來他集中時間精力,摘錄了摩爾根等五人的人類學著作*[英]莫里斯·布洛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馮利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16-17、17、105、105頁。。布洛克繼續言道:“事實上,他們(馬克思和恩格斯)倆人所依據和重新解釋的人類學僅是其廣泛研究工作中的一個部分。他們的研究早已超出學科之間嚴格的分界線, 他們的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不存在障礙, 他們的歷史學、人類學與政治學之間也不存在任何障礙”*[英]莫里斯·布洛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馮利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16-17、17、105、105頁。。
馬克思的《筆記》對摩爾根等人著作中人類學資料的關注,特別體現在宗教、親屬關系、政治、經濟等等社會的不同方面。關注這些資料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他對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及規律性之探討,這種探討讓他假設其他非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所以馬克思埋首于人類學的文獻之中,致力于尋找與資本主義相對應的案例。具體而言,馬克思求助于人類學兩件事:“第一,到人類學中尋找一些證據,以證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起作用的某些原則是永遠存在的,是貫穿歷史的一般原則;第二,指望人類學向他們提供一些與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略有不同,甚至相對立的制度作為例證*[英]莫里斯·布洛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馮利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16-17、17、105、105頁。”,并通過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否與已知的人類早期文明相一致來進行驗證”*[英]莫里斯·布洛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馮利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16-17、17、105、105頁。,這種關于人類歷史具有一定發展順序的思想,被稱為早期“進化論”,但這不是人類學一家之言,而是當時時代的一種思潮與局限。盡管如此,馬克思還是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看待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式。此外,馬克思仍然從概念的層面證明了“宗教、親屬關系、政治、經濟等等社會的不同方面構成了一個彼此相連的整體,這一結論一直是當代人類學的試金石之一”*[英]莫里斯·布洛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馮利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16-17、17、105、105頁。,這永久地改變了人類學對自身的定義,“當這個整體中的某一方面發生變化之時,其他的方面也將隨之變化”*[英]莫里斯·布洛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馮利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16-17、17、105、105頁。。故從建構人類學學術大廈的理論基底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就是一個人類學家。
以人類學理論史觀之作為人類學家的馬克思,他的《筆記》宛若魔盒“潘朵拉”,打開了人們對馬克思與人類學之間無盡的話題與爭論。諸學者也充分利用馬克思的人類學遺產,在人類學的理論體系中形成“馬克思人類學”的各種派系。馬克思人類學發軔于馬克思的理論,尤以其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研究著作《資本論》第1卷和后期的《筆記》影響力最大。盡管《筆記》發展出的“進化觀”對早期人類學理論有一定的影響,但后來馬克思人類學的重要概念中,如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生產關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與生產力(forces of production),基底(base)、下層基礎(infrastructure)與上層建筑(superstructure),核心(centre)與邊陲(peripery)等等,更強調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權力,發展成為馬克思人類學之“結構馬克思人類學”、“文化唯物論”、“女性馬克思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派”*[美]艾倫·巴納德:《人類學的歷史與理論》,徐雨村譯,巨流圖書公司2012年版,第134-142頁。等等,這些理論學派都深刻地形塑和改變著人們對世界的看法。
四、結語
通過上文論述可知,《人類學筆記》產生于馬克思生命的最后10年,此時的馬克思健康狀況不佳,迫使他不能從事較為吃力的理論工作,而把精力放在文學與數學的世界里,同時他為思考資本主義制度的適用性,轉向摩爾根等人的人類學著作并作了大量摘要。由于時值資本主義的衰退期,馬克思在人類古代社會的人類學資料里,檢驗他在研究資本主義制度時形成的觀點之普遍性,從而發展出一種社會發展的進化論,這個進化論是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性進行一般化的理論企圖。遺憾的是,這種理論企圖被推翻了。但有意思的是,馬克思對社會是由“宗教、親屬關系、政治、經濟等等不同方面構成了一個彼此相連的整體”的看法,成為人類學這個學科理論大廈的基礎。而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在深入研究馬克思各時期的著作和思想脈絡時發現,馬克思的前后思想是一脈相連的,且是一種從哲學人類學向經驗人類學的轉變。而他的人類學思想遺產也深刻形塑了人類學理論的發展,特別是“馬克思人類學”諸流派的理論都與之相關,這些影響反過來改變著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故從思想脈絡觀之,馬克思就是一位真正的人類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