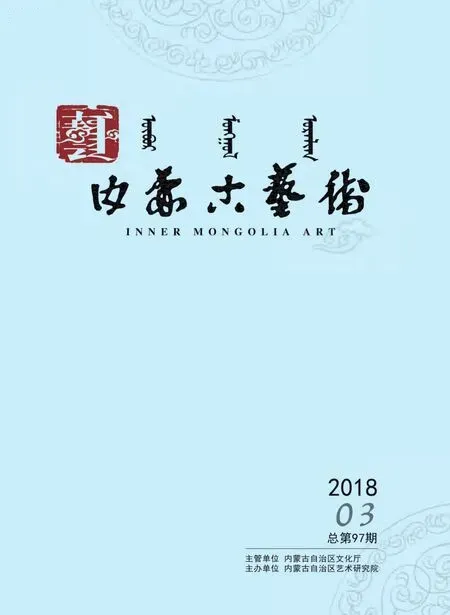寶雞西山新民村圣母廟壁畫(huà)與信仰的再調(diào)查
(寶雞文理學(xué)院美術(shù)學(xué)院 陜西寶雞 721013)
寶雞地區(qū)西部屬于黃土臺(tái)塬山區(qū),這樣的山嶺臺(tái)塬地區(qū)距離城市相對(duì)偏遠(yuǎn),交通不便,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也相對(duì)落后。這樣的情況才使山區(qū)的村落還基本保持原有的地域風(fēng)貌,其中包括一些老的廟宇建筑。西山地區(qū)鄉(xiāng)間寺廟遺存較多,它們多是鄉(xiāng)野小廟,供奉著民間信仰的俗神,這些神的形象與傳說(shuō)故事通過(guò)廟宇內(nèi)的壁畫(huà)與彩塑得以顯現(xiàn),但這些“老畫(huà)”也在漸漸消失,將它們記錄下來(lái),對(duì)地域歷史文化的研究或許有益。
一、圣母廟建筑與壁畫(huà)的空間情況調(diào)查
西山坪頭鎮(zhèn)新民村過(guò)去叫做城隍廟村,據(jù)老人講,村中原有一座城隍廟,廟里的城隍爺是唐代的一位將軍,所以村子因此而得名。如今城隍廟已不見(jiàn)蹤影,村中僅保留著一座古廟建筑,這座廟宇坐落在村頭,坐北朝南,靠著一座小山。古廟的建筑樣式古樸,屋頂為硬山雙坡頂結(jié)構(gòu),房脊采用了小青瓦直接堆砌出高脊身,屋面由小青瓦層層仰式排列,形成很強(qiáng)的韻律感。磚包土坯的山墻厚重高大,墀頭原有磚雕的裝飾,前廊地面鋪花崗巖石基,廟宇面闊三間進(jìn)深兩間。廟宇正面設(shè)木雕六扇門(mén),上部門(mén)芯為鳳眼齒圖案(中間兩扇的門(mén)芯已經(jīng)遺失),門(mén)扇腰板上的浮雕已經(jīng)被鏟除,上檻裝板為花卉透雕圖案,多數(shù)已經(jīng)殘破遺失,門(mén)的兩側(cè)是裝板套花立齒木窗。廟宇內(nèi)的采光主要依靠門(mén)窗透進(jìn)的光線,建筑前檐下的檐檁和拱眼上原本華麗的彩繪裝飾,經(jīng)歷歲月的風(fēng)吹雨打已經(jīng)非常模糊,由斗拱演變而來(lái)“九龍壓七象”的“闊”①也被破壞,但總體建筑的樣貌還基本保留,顯示出莊重與威嚴(yán)。廟前還留有一座麻石質(zhì)花崗巖雕刻蓮瓣紋的香臺(tái),廟宇基本處于無(wú)人照管的狀態(tài),周?chē)逊胖s物,地面雜草叢生,昔日的香火鼎盛的景象早已消失,一些后來(lái)建造的民房已將它擋在了不顯眼的角落,原有的建筑環(huán)境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但與民居建筑相比,可以想象當(dāng)年這個(gè)比較貧困的山區(qū),廟宇一定是村中豪華、高大和有威望的公共建筑,顯示出信仰崇拜在民眾生活中重要的地位。
廟宇內(nèi)部空間高大,從地面到房頂大梁的距離大約高5米,因?yàn)闆](méi)有頂部隔板,建筑頂部的梁架結(jié)構(gòu)能夠看得很清楚。內(nèi)部梁架屬于抬梁式結(jié)構(gòu),廟宇的進(jìn)深寬闊,殿內(nèi)兩根立柱通在梁架的桴子上,大桴子用料粗壯,桴子上的背板外形像一對(duì)鳥(niǎo)的翅膀,內(nèi)部陰刻一些裝飾花紋,主梁與桴子上彩繪有“龍紋”和“帶狀綰不斷”,因常年殿內(nèi)香火的熏烤,屋頂蒙著一層煙灰,彩繪圖案已經(jīng)不太清晰。
大殿的正墻前砌有供臺(tái),供臺(tái)所占面積不大,供臺(tái)之上是一位女神的塑像,正襟端坐,鳳冠霞帔,手執(zhí)笏板,兩側(cè)塑有侍女立像,女神塑像略大于真人,彩繪塑像與塑像后正壁上的彩繪屏風(fēng)裝飾都為新作,屏風(fēng)的左側(cè)有“隴縣東風(fēng)鎮(zhèn)普樂(lè)塬村余鴻科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五日塑像”的題記。借著室內(nèi)較暗的光線,可以看到山墻壁上人物、山水的生動(dòng)圖像。除正壁女神塑像背后較小面積的墻面重新裝飾外,其余地方還保留著老壁畫(huà)。正壁兩側(cè)殘余的屏風(fēng)畫(huà)加起來(lái)有六扇屏,屏風(fēng)占據(jù)了整個(gè)正壁,可能供臺(tái)之上曾經(jīng)供奉著多位神仙。每扇屏風(fēng)上都繪制花鳥(niǎo)或人物故事,筆法精細(xì)、色彩和諧。而山墻的壁面整個(gè)都被壁畫(huà)裝飾,是建筑中最重要的壁畫(huà)分布區(qū)域。
山墻上的壁畫(huà)基本保存完整,壁畫(huà)的下部因受潮而剝落、起甲,畫(huà)面漫漶嚴(yán)重,一些圖像已很難辨識(shí),壁畫(huà)的表面感覺(jué)像蒙了一層薄紗。后期調(diào)查了解到在“文革”時(shí)期殿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建筑上的木雕、磚雕等都被毀壞,壁畫(huà)也被泥和白灰覆蓋。“文革”結(jié)束后,廟宇恢復(fù)香火,于是又將覆蓋的泥灰清洗掉,所以逃過(guò)了劫難壁畫(huà)才能夠重見(jiàn)天日。左右山墻中心的位置安排著兩幅最大的壁畫(huà)。在主壁畫(huà)前方靠近大門(mén)的方向還有一個(gè)獨(dú)立的畫(huà)方(高200cm,寬100cm),繪制兩位天將,天將身姿挺拔各持金瓜與戟站立,“罡風(fēng)帶”飛動(dòng)飄揚(yáng)威風(fēng)八面。
二、壁畫(huà)圖像分析研究
山墻上的壁畫(huà)高300cm,寬400cm,整體看場(chǎng)景繁復(fù)人物眾多,整幅壁畫(huà)畫(huà)工采用了“通景”式構(gòu)圖,描繪了多個(gè)不同的故事畫(huà)面。不同的故事場(chǎng)景沒(méi)有劃分界欄,而是用樹(shù)石云水圖像巧妙分隔。這種構(gòu)圖形式早在北魏時(shí)期敦煌壁畫(huà)“薩埵那王子舍身飼虎”“鹿王本生”等故事中就有出現(xiàn),東晉顧愷之卷軸畫(huà)作品《洛神賦圖》也采用了相似的構(gòu)圖形式,反映出古人獨(dú)特的空間認(rèn)知與想象力。左右山墻上的兩幅壁畫(huà)構(gòu)圖相似,在畫(huà)面中部上方都繪制了宏大的殿宇,左壁的殿宇上端坐一位頭戴帝王冕冠的男性神仙,兩側(cè)排列男性文武官員,而右邊壁畫(huà)中宮殿內(nèi)的主尊為女神,兩側(cè)列女官,兩位主神都在接受殿階之下一位身著紅衣的女性的叩拜。
這些故事畫(huà)面講述了什么內(nèi)容?只依靠圖像來(lái)解讀故事內(nèi)容會(huì)非常困難,而這組壁畫(huà)都加了文字的榜題,壁畫(huà)中的榜題大都能夠認(rèn)讀,左壁右下角文字榜題為“其初生圣母”,描繪了一位產(chǎn)婦躺在房間的床榻上,庭院中三位侍者正準(zhǔn)備為新誕生的嬰兒洗浴,此時(shí)神人天降,其中一條神龍口中吐水而下為嬰兒沐浴,院外大門(mén)口還站著兩人,似乎是要告訴村人“瑞兆”的降臨。這個(gè)畫(huà)面會(huì)不會(huì)就是整個(gè)壁畫(huà)講述故事的開(kāi)始?
左壁還可以辨認(rèn)的榜題有:圣母吉日勝身;鳳嶺腳戶(hù)起意;判官盤(pán)問(wèn)腳戶(hù);夜過(guò)閻王峪;胡家村問(wèn)境;石佛寺降廟;龍王接駕。右壁可以辨認(rèn)的有:圣母過(guò)渭河;玉帝送衣;圣母進(jìn)善;白猿獻(xiàn)果;修蓋寶玉山。榜題文字中多次出現(xiàn)“圣母”這個(gè)名詞,在多個(gè)故事畫(huà)面中一位披云肩、著紅衣的年輕女子形象多次出現(xiàn),她的形象和壁畫(huà)中殿宇下跪拜的女子相似。寺廟壁畫(huà)的內(nèi)容與廟內(nèi)供奉的神祗有著聯(lián)系,供臺(tái)上只端坐著一位女神,形象也是身穿紅衣的年輕女子,壁畫(huà)與塑像在特征上相似,能證明壁畫(huà)上的紅衣女子就是這座廟宇的主神嗎?這名女子就是榜題中出現(xiàn)的“圣母”,整個(gè)的壁畫(huà)故事也是圍繞著“圣母”這個(gè)主要的人物展開(kāi)。
“圣母”一般出現(xiàn)在道教或民間的信仰之中,西府民間也把供奉的女性神祗稱(chēng)呼為“娘娘”,民間供奉的有祈子娘娘、送子娘娘、厚土娘娘、火星娘娘、姜嫄圣母、九天圣母、驪山老母、無(wú)生老母等[1]。這座廟的神像前沒(méi)有供牌位,廟宇內(nèi)也沒(méi)有匾額題記,供奉的“圣母”身份還有待進(jìn)一步考證。但我們把故事畫(huà)面和榜題聯(lián)系起來(lái)分析可以大概推測(cè)出,壁畫(huà)講述了“圣母”從出生開(kāi)始,經(jīng)過(guò)苦修和行善的積累最終得道成仙的故事。
廟宇還繼續(xù)著香火,村中應(yīng)該有人知道這座廟宇的事,在請(qǐng)教了村中年長(zhǎng)者這個(gè)問(wèn)題后,他們給出的回答是“九天娘娘”即“九天圣母”,但對(duì)于壁畫(huà)上故事的內(nèi)容,由于年代的久遠(yuǎn)已經(jīng)無(wú)法說(shuō)清楚。九天圣母,即九天玄女[2],“她是我國(guó)古代傳說(shuō)中的一位著名女仙,定名于漢。它來(lái)源于黃帝戰(zhàn)蚩尤的神話傳說(shuō),后以黃帝之師的身份兼任多種職能,唐末道士杜光庭在《墉城集仙錄》中為其單獨(dú)立傳,成為西王母駕下女仙——為道教納入其女仙系統(tǒng),以后廣泛地出現(xiàn)在道教典籍中”。文獻(xiàn)典籍中的九天玄女是傳授兵法術(shù)數(shù)、除邪滅煞、護(hù)國(guó)佑民的女神,明代之后她的形象進(jìn)入小說(shuō),除了傳授天數(shù)還多了很多扶危濟(jì)困的故事,她的形象多以端莊、正義、神通出現(xiàn)。九天圣母信仰過(guò)去也很普遍,全國(guó)各地都有九天圣母廟分布。然而這座“圣母”廟中的壁畫(huà)故事卻演繹得與文獻(xiàn)典籍的記述有所不同,并且?guī)в袧夂竦赜蛱厣v了些什么?這個(gè)傳說(shuō)的形成反映出哪些民間信仰的習(xí)俗與特征?
從內(nèi)容我們推測(cè)壁畫(huà)講述的就是九天圣母求道成仙的歷程,壁畫(huà)是關(guān)于九天圣母行跡故事的一個(gè)圖像表達(dá)。這個(gè)故事的獨(dú)特性在于描繪了一個(gè)帶有地域性特色的傳說(shuō)故事,主角是道教信仰中的女神。現(xiàn)在知道的十三個(gè)榜題中,出現(xiàn)了四次“圣母”,還出現(xiàn)了“玉帝”“龍王”的尊號(hào),這些都與道教信仰有關(guān)。出現(xiàn)的地理名詞有鳳嶺、閻王峪、胡家村、石佛寺、渭河、寶玉山,這些地名漸漸勾勒出一個(gè)地域范圍。渭河,發(fā)源于今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的鳥(niǎo)鼠山,主要流經(jīng)甘肅東部的天水和陜西關(guān)中地區(qū),寶雞位于渭河流域的中上游;寶玉山位于千山北麓鳳翔縣與麟游縣交界處的羊引關(guān),山上建有廟宇,風(fēng)景秀麗,是本地一處風(fēng)景名勝;石佛寺同樣是位于鳳翔境內(nèi)的一座古寺,據(jù)傳始建于北魏時(shí)期,廟內(nèi)有大小石佛千余尊也叫千佛寺,曾經(jīng)重建四次,是關(guān)中一帶有名的佛剎;鳳嶺就是古鳳州(現(xiàn)在的鳳縣)境內(nèi)的秦嶺,“縣南有鳳凰山,因?yàn)橹菝保ā对涂たh圖志》),鳳縣是由陜?nèi)氪ǖ囊獩_;而胡家村就是現(xiàn)在寶雞市以北蟠龍塬上的曉光村,在“文革”前這個(gè)村子因?yàn)楹杖思揖佣啵恢苯凶龊掖濉槭裁磿?huì)描繪這樣的傳說(shuō)故事?這個(gè)故事沒(méi)有記錄在關(guān)于九天玄女的道教文獻(xiàn)[3]中,那么它只是新民村圣母廟所講述的故事嗎?同樣的故事還在哪里流傳?應(yīng)該沿著故事發(fā)生地去尋找。
第一個(gè)調(diào)查的地點(diǎn)是胡家村,現(xiàn)在叫做曉光村,在離市區(qū)不遠(yuǎn)的蟠龍塬上,在村中廣場(chǎng)一側(cè)有一處廟宇,廟內(nèi)保存一座清乾隆年間九天圣母廟碑記,但字跡漫漶識(shí)讀困難。廟院內(nèi)只有一座大殿,殿門(mén)上方的匾額題寫(xiě)著“圣玄殿”,殿內(nèi)主尊就是“九天圣母”。據(jù)了解殿宇在“文革”時(shí)期遭到破壞,之后重新修葺。塑像與壁畫(huà)都為新作,壁畫(huà)所描繪的內(nèi)容與新民村圣母廟壁畫(huà)故事相近,兩處壁畫(huà)似乎能夠相互印證補(bǔ)充,從而使這個(gè)“圣母”故事逐漸清晰。曉光村圣玄殿壁畫(huà)每個(gè)故事也都留有文字題記,并且標(biāo)出了數(shù)字順序。故事以畫(huà)方的形式表現(xiàn),按照連環(huán)畫(huà)的順序共分24幅(每壁12幅)。故事文字內(nèi)容為:1.仙女降世、圣靈入竅。2.天資聰慧、習(xí)務(wù)針工。3.遇仙指引、指點(diǎn)迷津。4.花園坐禪、點(diǎn)點(diǎn)修真。5.為母療疾、親奉湯藥。6.為母祈禱、媒婆偷窺。7.媒婆提親、芳齡若周。8.仙女隱蹤、夜離綿竹。9.州官起意、盤(pán)問(wèn)腳戶(hù)。10.上蒼施靈、火焚州衙。11.留鳳關(guān)住宿、庵主接駕。12.留鳳庵夜宿、劉尼進(jìn)善。13.酒奠溝問(wèn)路、店主指途。14.酒奠梁露宿、山王護(hù)駕。15.途經(jīng)陳倉(cāng)、瞻望金臺(tái)。16.員外置宅、他人拆居。17.拆墓修居、仙女顯靈。18.大成殿飲茶、賊匪猖獗。19.仙女顯靈、賊匪窮追。20.兇心不改、自食其果。21.雍河求渡、渡工勒索。22.仙女施法、糜稈搭橋。23.金星指引、寶玉參真。24.功圓果滿、寶玉山坐化。故事內(nèi)容與新民村圣母廟相似,甚至在細(xì)節(jié)上更為豐富。
寶玉山在“圣母”故事的講述中是結(jié)尾,是“圣母”修道功德圓滿的地方,在寶玉山的調(diào)查使這個(gè)傳說(shuō)故事有了更詳細(xì)的資料。寶玉山風(fēng)光秀麗,山上修建九天圣母廟,每年“會(huì)期”,四方信眾前來(lái)祈愿,香火鼎盛,在民間有較大影響。傳說(shuō)“圣母”在這兒的“肉身洞”修行坐化,在“肉身洞”前兩塊民國(guó)時(shí)期的石碑清晰地記述了這個(gè)故事。
重修寶玉山圣母宮肉身洞碑記
寶玉山舊有肉身洞,為九天圣母羽化之洞府也。歷代久遠(yuǎn)不知其始而相傳至今,神恩浩蕩誠(chéng)無(wú)不靈,嘗(當(dāng))仙姑自蜀來(lái)鳳,每路遺跡不可盡述,始大槐社腳夫樊氏從川返鳳,遇仙于路要馬以乘,樊氏不允突馬臥地不行證明仙基,即將奉騎,路至廣元,縣官盤(pán)問(wèn)稽證以拐騙方刑樊翁,縣官之女神神差教言,聲明來(lái)歷,教父即設(shè)香案祈神釋罪,速備鼓樂(lè)發(fā)票送行,臺(tái)后沿途接送,安歸樊氏之家,適樊氏有女聰明穎慧仙體可征,相見(jiàn)歡迎甚如姊妹,由此同居同食異殊常人,苦用功果數(shù)年道成,秉行寶玉山,路過(guò)糜桿橋黑灘等籍,采之寶玉山地勢(shì)環(huán)秀,九龍五虎八景赫然,仙洞羽化。蓋樊姑舅于邱村,故認(rèn)邱村為舅家也,大槐社為娘家也,又創(chuàng)修祈子宮、藥王殿、文昌殿。歲饉以來(lái)?xiàng)潝潘徽扒f觀。會(huì)末等不忍坐視竭力修葺,但山土松散不易修建,工程浩大,各方善男信女共勷資助,現(xiàn)在功程告竣以勒石,石示萬(wàn)年不朽云。
香巖頌曰:
圣母家鄉(xiāng)在四川,肉身脫化寶玉山。秦中祈禱屢感應(yīng),香煙燭光萬(wàn)萬(wàn)年。
平川頌曰:
有蜀至鳳又歸樊,賜卦賜鞭在昔年。二仙相伴脫肉身,功圓結(jié)果寶玉山。
民國(guó)二十七年歲次戊寅年清和月中沅。
重修寶玉山圣母宮肉身洞碑記
夫?qū)氂裆秸吣司盘焓ツ竿雄櫜匦沃烧鏃硇薜乐畡倬撑c也。此山有茂林仙洞及甘霖泉與東北之九成宮之醴泉先后并口口代,貞觀之世考之仙鑑九天圣母成真于三代之前,后察凡世人民多陷迷途少成正果,因之?dāng)?shù)歷朝代圖托生顯化渡世拔真八十一變化身也,至唐宋之世轉(zhuǎn)化于四川青城,生而好道不染凡情,專(zhuān)持齋素苦心修真,聞鳳翔大槐社樊仙姑者生不為好道修行意欲結(jié)為道侶拔出凡塵,適遇余運(yùn)販腳夫樊姓者由川解貨回籍道中,付以腳資,乘便抵鳳,即旅于樊仙姑之口口道侶姐妹趁機(jī)隱此山,不久同協(xié)登仙。以故認(rèn)大槐社娘家,蓋樊仙姑舅于邱村,因認(rèn)邱村為舅家,所留有瑪瑙卦馬口口鞭鞍鐙諸物至今作為紀(jì)念,溯之宋元之世北胡溝亂擾我疆土兵災(zāi)頻仍水深火熱,寶玉山原狀蹤跡化為烏有迄于明重修此山之原狀仍見(jiàn)恢復(fù),由明及今則寶玉山之功程大備神像口修齊全而靈泉愈見(jiàn)靈應(yīng)矣,自今已往名山仙洞恐致湮進(jìn)考故敘其大概以志不朽不忘,云是為序。 民國(guó)三十年
兩塊石碑將“圣母”的身世、行跡以及寶玉山廟宇的分布、自然風(fēng)光都記述得十分清楚。隨后在傳說(shuō)“圣母”經(jīng)過(guò)的大槐社村、槐原村等地調(diào)研,這些地點(diǎn)都建有九天圣母廟以及有相似的故事流傳。清乾隆三十一年鳳翔知府達(dá)靈阿主持修撰的《重修鳳翔府志》記載,鳳翔城內(nèi)九天圣母廟在“城西街”,從文獻(xiàn)[4]和實(shí)地調(diào)查看說(shuō)明在一個(gè)時(shí)期九天圣母信仰比較普及。
將新民村圣母廟、寶玉山、曉光村寺廟中的壁畫(huà)故事聯(lián)系在一起,可以看出故事的相似性和連貫性,通過(guò)調(diào)查資料的相互補(bǔ)充、相互印證,這個(gè)故事也漸漸豐滿起來(lái)。新民村圣母廟壁畫(huà)的內(nèi)容就可以這樣解讀:九天圣母就是《封神榜》中“三霄”中的云霄,在唐代時(shí)下凡投胎到了四川綿竹(或青城山)的一個(gè)官宦人家,從小就抱有求道的信念,在家時(shí)她孝敬父母、也參禪悟道。待到成人后從老家出走,求得大槐社腳戶(hù)的幫助,經(jīng)蜀道入陜,從鳳縣越秦嶺來(lái)到寶雞,一路經(jīng)過(guò)艱難困苦的考驗(yàn),憑借她修道的法力懲惡揚(yáng)善(傳說(shuō)經(jīng)歷八十一難,認(rèn)七十二家干親),最后在鳳翔的寶玉山坐化成仙。在故事中我們還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圣母”的行程路線:四川綿竹——鳳嶺——留鳳關(guān)——酒奠梁——陳倉(cāng)金臺(tái)觀——胡家村——大槐社——鳳翔文廟——糜桿橋——石佛寺——寶玉山。這個(gè)故事不僅是保留在廟宇壁畫(huà)上的傳說(shuō),并且已經(jīng)根深蒂固影響到了當(dāng)?shù)氐拿袼孜幕睢1热绗F(xiàn)在的鳳翔縣糜桿橋鎮(zhèn)[5],這個(gè)地名的由來(lái)就是圣母用糜桿搭橋渡雍水的故事,就來(lái)自于九天圣母的傳說(shuō)。
新民村圣母廟壁畫(huà)的繪制,運(yùn)用了傳統(tǒng)工筆的壁畫(huà)繪制手法勾線、填色、渲染,造型工致謹(jǐn)細(xì),用色重彩與淡彩結(jié)合色調(diào)清麗,尤其是作為襯景的山水樹(shù)石,工寫(xiě)相兼筆法生動(dòng)頗具功力。人物形象塑造豐富,文臣武將、老者少年,都各具情態(tài),尤其是主角“九天圣母”形象出現(xiàn)在多個(gè)畫(huà)面之中,畫(huà)工結(jié)合每個(gè)故事的情節(jié)進(jìn)行了變化處理。作為故事壁畫(huà),畫(huà)工采用了傳統(tǒng)壁畫(huà)中的通景式的章法布局,故事帶有敘事性,畫(huà)工設(shè)計(jì)構(gòu)思時(shí)按照一定敘事方式安排,整個(gè)畫(huà)面主題突出。壁畫(huà)正中上方的位置繪制出高大的天宮,從布局位置顯示出天界的至高無(wú)上。玉帝與王母敕封九天圣母的畫(huà)面成為壁畫(huà)的視域中心,清楚地將道教神祗的等級(jí)關(guān)系交代清晰,充分表現(xiàn)了壁畫(huà)宗教服務(wù)的主題。壁畫(huà)中的人物形象和服飾借鑒了繡像小說(shuō)插圖與傳統(tǒng)戲曲人物的造型,甚至在服飾發(fā)型上反映了時(shí)代的特點(diǎn),人物形象中出現(xiàn)了清代特有的男性發(fā)辮,也從一方面說(shuō)明壁畫(huà)繪制的大致時(shí)間在清代。壁畫(huà)由畫(huà)工繪制但“畫(huà)什么”卻體現(xiàn)贊助人的意志,鄉(xiāng)間廟宇的集資修建主要來(lái)自于鄉(xiāng)民的捐助,這里的組織者就是民間以宗教信仰而組織的“會(huì)”。在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在大門(mén)上腰板的背面有墨書(shū)的題記“城隍廟合大二郎堡三村人等仝修”,說(shuō)明廟宇是附近幾個(gè)村共同的民間“廟會(huì)”組織修建的。新民村圣母廟保留的壁畫(huà)也反映出寶雞民間壁畫(huà)較高的藝術(shù)水準(zhǔn),也是本地域留存不多的有價(jià)值的“老畫(huà)”。
三、壁畫(huà)表達(dá)背后的社會(huì)文化信仰
新民村圣母廟壁畫(huà)生動(dòng)地描述了一位仁慈、善良、扶弱懲惡的女神形象。在傳統(tǒng)的女性神祗信仰中九天圣母信仰較為普遍,各地都有供奉九天圣母的寺廟[6],而新民村圣母廟和寶雞地域流傳的“圣母”故事卻有著明顯的地域性特點(diǎn),這個(gè)傳說(shuō)是怎樣形成的呢?從田野調(diào)查所匯總的信息分析,圣母故事傳說(shuō)在寶雞地區(qū)曾經(jīng)傳播很廣,但如今這樣的民間信仰在漸漸消失,調(diào)查中也發(fā)現(xiàn)一些九天圣母廟在毀壞以后再也沒(méi)有復(fù)建。當(dāng)?shù)匕傩找呀?jīng)不太了解這個(gè)傳說(shuō)。九天圣母?jìng)髡f(shuō)之前的興盛與現(xiàn)在的沉寂形成了明顯的對(duì)比。
這個(gè)故事流傳在什么時(shí)間,先從新民村圣母廟的修建時(shí)間查找信息。因?yàn)闆](méi)有碑記等文字記錄,調(diào)查中當(dāng)?shù)卮迕褚灿洃浤:越◤R的具體時(shí)間也存在疑問(wèn)。近年在調(diào)查民間壁畫(huà)時(shí)發(fā)現(xiàn)寶雞地區(qū)許多寺廟在清代光緒年間修建或修葺,原因大致是同治元年爆發(fā)的陜西回民起義致使許多廟宇因?yàn)閼?zhàn)亂毀壞嚴(yán)重,到了光緒年民眾經(jīng)過(guò)一定時(shí)間的休養(yǎng)生息,為了祈求平安與神的護(hù)佑,對(duì)于毀壞的廟宇又修葺重建。壁畫(huà)中一些人物的造型風(fēng)格與服飾特征也顯示出清朝中后期的特點(diǎn)。從這些信息也可推測(cè)九天圣母的故事在清代就已經(jīng)流傳。
從寶雞地區(qū)流傳的九天圣母故事可以看到這樣幾個(gè)特點(diǎn),九天圣母壁畫(huà)故事反映了女神崇拜的基本特征。信仰習(xí)俗的形成源于原始社會(huì)時(shí)期對(duì)自然和祖先的祭祀與崇拜,原始信仰中的生殖崇拜作為人類(lèi)生生不息發(fā)展的動(dòng)力,是一種重要的活動(dòng)也是女神崇拜的最早起源。從紅山文化時(shí)期女神像到歐洲的維洛特芙的維納斯,古今中外考古發(fā)現(xiàn)都證明了女神崇拜的起源。在宗教形成后,這種信仰需求同樣進(jìn)入到宗教信仰的體系之中,佛道系統(tǒng)中都出現(xiàn)了專(zhuān)司護(hù)生、求子的神祗(佛教中的送子觀音,道教中的送子娘娘、三霄娘娘等),并且都是女性形象。民間的道教信仰中以“三霄”專(zhuān)司祈子、護(hù)生系統(tǒng)的神祗[7],九天圣母故事中的“圣母”同樣被同化成了“云霄”的投胎轉(zhuǎn)世。
從壁畫(huà)以及民間傳說(shuō)中反映出在民間信仰中神祗身份的重合性,這個(gè)故事中將九天圣母與“三霄娘娘”中的云霄重合成為一個(gè)形象,然而在嚴(yán)格的宗教系統(tǒng)中神、仙、佛、道都有著各自嚴(yán)格的身份等級(jí),是不會(huì)混在一起的,文獻(xiàn)考證九天圣母(玄女)就是“傳授天數(shù)的掌劫女神”。從歷史發(fā)展來(lái)看,九天圣母(玄女)作為道教系統(tǒng)中的高階女神,并且是以“戰(zhàn)神”的身份顯現(xiàn)的,而新民村的壁畫(huà)故事并非道教典籍的經(jīng)變畫(huà),這或許與宗教的歷史發(fā)展有一定關(guān)系。宋代以后隨著宗教世俗化傾向的興起,原本煙火不食的神仙更多出現(xiàn)在普通百姓帶有功利性的信仰需求中,越發(fā)與百姓衣食住行的民俗生活相關(guān)聯(lián),并且在明清時(shí)期愈演愈烈。在民間傳說(shuō)與小說(shuō)故事中宗教神祗演繹出越來(lái)越多的身份與故事,九天圣母的故事演變也就是這樣的過(guò)程。在民間信仰與百姓祈愿的功利性目標(biāo)相適應(yīng),老百姓拜佛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某種物質(zhì)或精神上功利性的愿望。在調(diào)查中也曾問(wèn)到村民所拜的“圣母”是誰(shuí),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但相信“圣母”能夠保佑他們。民間信仰的實(shí)用性、功利性與民間信仰中神仙身份的模糊性、重合性形成了對(duì)比,使得民間的信仰傳說(shuō)糅雜著豐富又混沌不清的各種信息。
同時(shí)傳說(shuō)中還闡述了“神仙下凡”這樣的故事。“神仙下凡”與“靈魂出竅”都帶有強(qiáng)烈的迷信色彩,究其原因這些也和原始思維時(shí)期人們所建立起來(lái)的“靈魂”觀念有關(guān)。“人類(lèi)最初的信仰是從自身開(kāi)始的,如對(duì)夢(mèng)境和死亡的不解,導(dǎo)致人們相信人是由肉體和靈魂組成的,肉體是具體的、摸得著的,靈魂是虛幻的、摸不著的”[8]。九天圣母?jìng)髡f(shuō)一開(kāi)始就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神仙下凡的故事,最后這個(gè)肉身的“圣母”又坐化靈魂出竅而成仙,其實(shí)也反映出民間信仰最本質(zhì)的特點(diǎn)和民眾心理,對(duì)于上天與神靈的敬畏,就是“萬(wàn)物有靈”觀念的根深蒂固。如果民眾心中沒(méi)有這樣一個(gè)深刻的觀念,這一則故事也很難廣泛傳播。甚至民間一些從事迷信活動(dòng)的人也都以“神仙附體”這一行為來(lái)蠱惑人心。或者我們換一種思路,這個(gè)傳說(shuō)故事的興起可能就是民間迷信傳播者自稱(chēng)自己是“九天圣母”下凡而逐漸演繹發(fā)展而來(lái)。
新民村圣母廟是一座保留比較完整的古建筑,九天圣母廟壁畫(huà)極具地域特征,但整體又反映出宗教信仰的共同特點(diǎn)。壁畫(huà)從一個(gè)方面反映了民間能工巧匠豐富的創(chuàng)造力與想象力,也反映了民間信仰風(fēng)俗的地域性特征,值得進(jìn)一步保護(hù)與研究。
注釋?zhuān)?/p>
①闊:即外檐斗拱中的柱間斗拱。清工部《工部做法》將斗拱也稱(chēng)為斗科,柱間斗拱也稱(chēng)為平身科。在明清時(shí)期民間工匠在斗拱裝飾上將耍頭雕刻成龍頭,下昂雕刻成象頭,最多時(shí)上九下七,故民間有“九龍壓七象”之說(shuō)。陜西方言將“科”讀音為“闊”,當(dāng)然在民間又包含著“闊氣”(豪華)的寓意。
- 內(nèi)蒙古藝術(shù)的其它文章
-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藝術(shù)研究院開(kāi)展烏蘭牧騎調(diào)研活動(dòng)
- 基于有效決策模型的社區(qū)文化治理公眾參與研究
- 游牧文化影響下的蒙古文字造形藝術(shù)研究
——挖掘蒙古文字體設(shè)計(jì)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規(guī)律 - 民間放映和線下觀影活動(dòng)中的文化消費(fèi)場(chǎng)景
—— 成都“叢林文化”案例分析 - 民族舞蹈與社會(huì)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關(guān)系
—— 以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蒙古族舞蹈作品為例 - 海南盅盤(pán)舞與內(nèi)蒙古盅子舞的形態(tài)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