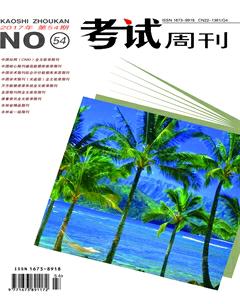創新與繼承
李林洋??
摘 要:近年來,我國對于外國文學著作的關注度逐漸增加,作為西班牙當代女作家卡門·拉夫雷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一無所獲》中的巧妙懸念設置為整部作品增色不少,使情節扣人心弦、撲朔迷離,給讀者帶來了一種別樣的審美體驗。小說的懸念敘事是對哥特小說懸念敘事的繼承,同時也為當時“玫瑰小說”風行的西班牙文壇,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
關鍵詞:一無所獲;卡門·拉夫雷特;懸念;哥特小說
《一無所獲》是西班牙當代女作家卡門·拉夫雷特的代表作。這部小說講述了在戰后時期的西班牙,一個名叫安德烈婭的孤女從鄉下來到西班牙大都市巴塞羅那的生活經歷。原本想要到巴塞羅那求學的她,見證了巴塞羅那外祖母家的衰落,家族成員古怪的個性,以及他們之間混亂又丑惡的矛盾關系,這一切讓她感到壓抑和痛苦,然而在學校里的同學關系也并沒有為她的生活帶來多大的快樂,最終她決定放棄巴塞羅那,到馬德里去尋求新的生活。1944年,《一無所獲》獲得了首屆“納達爾小說獎”,標志著描寫女性的文學作品在西班牙開始占有一席之地,開創了西班牙文學的一個新階段。在這部作品中,層層懸念的安排設置,吊足了讀者的胃口。本文試圖從懸念敘事的角度梳理《一無所獲》中的種種懸念,解讀它的審美意義,以及繼承和創新。
一、 《一無所獲》的懸念敘事
來自鄉下的安德烈婭對巴塞羅那這座夢想中的城市充滿了興趣,同時成長在鄉下的她,也有著和典型西班牙標準乖女孩完全不同的氣質。在舅舅胡安和阿姨安古斯蒂阿絲的眼里,安德烈婭并不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好姑娘,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壞女孩。她完全不符合當時社會背景下“好女孩”的標準,她愛出門閑逛,她不安分守己,她總是有自己的主張,她對這個城市、對她不了解的一切充滿了好奇,在好奇心的促使之下,安德烈婭觀察著這個奇怪的家庭,這個奇怪的世界。隨著她的視角,我們也看到了很多“怪現象”:動不動就大打出手的兄弟,無緣無故被罵的舅媽格洛麗亞,看上去和藹可親卻咄咄逼人的舅舅羅曼,突然就躲開安德烈婭的“閨蜜”埃娜……這些離奇的種種都不斷牽引著安德烈婭乃至讀者的好奇,讓她帶著我們一起去發現去觀察,去一層一層揭開這些疑惑,去解答這些謎團。
(一) 層出不窮的懸念設置
在故事的講述過程中,作者設置了大量的懸念引起讀者興趣,各種懸念敘事層層疊疊,相互嵌套,使小說的情節曲折化、復雜化。
首先,按照懸念設置的位置,《一無所獲》中出現了局部性懸念和全篇性懸念。前者指的是問題出現和提供回答之間的文本跨度不大的懸念。比如,在埃娜的母親意外地出現在安德烈婭家門前時,安德烈婭的疑惑就產生了:她來是做什么的?接著,埃娜的母親領她去喝咖啡、聊自己、聊埃娜,把安德烈婭繞的云里霧里,讓她愈發覺得埃娜的母親別有動機。而后,當埃娜的母親跟她講述自己被她舅舅羅曼傷害的故事,她才明白埃娜母親此行的目的。此情節從懸念出現,到懸念解答,篇幅不長,大概在一章左右。
后者,全篇性懸念,指的是在小說一開始就出現,在小說即將結尾才得到解答的懸念。比如,羅曼與格洛麗亞之間的人物關系。從安德烈婭在外祖母家吃的第一頓飯上,我們就看到羅曼與格洛麗亞之間的口舌之爭,接下來又聽見雙方彼此之間的描述,又撞見晚上在羅曼房間前的走廊不斷踱步的格洛麗亞,又在安古斯蒂阿絲的房間窺到兩人的爭執,作者一步一步的進行描寫,將人物之間的矛盾逐漸推向高潮,讓我們對這兩個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疑惑,直到在小說將近結尾,在羅曼死后,格洛麗亞對安德烈婭的傾訴,才揭開兩個人的關系,原來羅曼之前勾引過格洛麗亞并羞辱過她。
在整部小說之中,格洛麗亞和羅曼的關系時而劍拔弩張、時而忽明忽暗,難以分辨,原來事情的根本在于曾經羅曼對格洛麗亞的羞辱。事情的原委實際上是在兩人追憶往事的時候,才解開的,按照懸念講述的順序,這種只有追憶往事才能獲取解答的懸念,可定義為逆時性懸念。與之相對,隨著時間的發展,順其自然得到解答的懸念,即為順時性懸念。
小說中有一段篇幅不長但是非常精彩的順時性懸念。胡安和格洛麗亞的孩子發燒了,病情非常嚴重。當天晚上胡安因為擔心孩子,提前回到家里,卻發現太太格洛麗亞不見了。他詢問安德烈婭的外祖母,外祖母很忐忑地說她去買藥了,還暗示安德烈婭跟她統一口徑。前文雖然提及了格洛麗亞在丈夫離開家之后匆忙地出了門,但是并沒有說明她具體是去了哪里,結合之前的情節,她常常在夜里外出,家庭成員對她的評價是“一個不三不四的女人”,再加上她出門之前涂脂抹粉,打扮一番,而且又不告訴胡安她究竟是去做什么了,這樣的鋪墊難免要讓讀者想入非非:莫非格洛麗亞真的就是一個拋下病重的孩子不管,只顧玩樂的不負責任的母親?格洛麗亞到底去了哪里,安德烈婭想知道,焦急的讀者們也一樣非常想知道,然而作者在這里并沒有立即把答案告訴給讀者,而是一再延緩提供答案,跟著胡安的腳步,讀者走到了一個又一個廣場,一條又一條街巷,臟亂的街,人聲鼎沸的街,繁華的街,散發臭味的街,讀者的好奇被一次次放大一次次加強,直到最后,我們才跟著胡安走到格洛麗亞姐姐的家里,才知道格洛麗亞其實是去了她姐姐家。
同時小說中還安插了開放性懸念,即作者沒有為之提供解答的懸念,比如羅曼之死。從文中看羅曼的死是有些蹊蹺的,他先打給女仆說第二天要出遠門,還要女仆幫他準備咖啡,仿佛告訴讀者他原本是有固定的日程安排的,自殺并不在他的計劃之內,連糊涂的外祖母也說他在自殺之前后悔了,這讓我們懷疑他是否是自殺。同時,在發現尸體之前,格洛麗亞一個人在黑暗的房間哭,她對安德烈婭說她在害怕,那么她究竟在怕些什么?她和羅曼的死到底有什么樣的關系?羅曼因何而死?是他殺?是自殺?如果是自殺,那原因是什么?是因為埃娜的復仇讓他受傷讓他挫敗?還是因為格洛麗亞的舉報讓他畏罪自盡?這些作者都沒有透露出來,但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來猜測。這樣的懸念設置又使得整部小說更像一個待人來揭開的謎團,讓讀者忍不住去回味思考,更為小說的情節賦予了更多的曲折性和離奇性。endprint
(二) 逆變性懸念的解讀
在小說眾多的懸念中,逆變性懸念的設置非常精彩。作者在問題拋出之后,通過接下來的情節發展不斷向讀者呈現與答案有關的情境,把答案縮小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使答案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明確,但是問題最后的答案與之前的猜測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逆變性懸念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添了情節的曲折性和復雜性,為小說的懸念敘事增色不少。最為典型的就是埃娜和羅曼的關系。埃娜原本是安德烈婭最好的朋友,但是對安德烈婭卻突然冷淡了下來,安德烈婭正在費解的時候,突然從舅媽格洛麗亞的口中獲知,原來埃娜最近竟與她的舅舅羅曼關系熱絡起來,她成了羅曼閣樓的常客,兩人經常見面。羅曼在埃娜走后,孤單一人悵然若失,與以往驕傲的模樣完全不同。接下來,她發現埃娜竟與之前的戀人海梅斷了聯系。當安德烈婭開始相信埃娜與羅曼相戀之后,埃娜的母親找到了安德烈婭,告訴她自己年輕時候與羅曼之間的事,羅曼是個喜歡捉弄女人感情的花花公子,她希望安德烈婭能阻止埃娜和羅曼的來往。跟著情節的不斷推進,讀者也開始逐漸相信,埃娜和羅曼是不是已經產生了愛情。然而,事情的真相卻完全相反,埃娜接近羅曼是為了引誘他并且報復他。埃娜在母親的夢囈中獲知了過去羅曼對母親的傷害,了解到羅曼卑劣的手段,她深深地同情著母親,并且憎恨著羅曼。天生美貌的埃娜決定憑借自己的魅力來吸引羅曼,然后將他狠狠拋棄,讓他也感受一下被人捉弄的滋味。
安德烈婭與龐斯之間的交往也帶有著一定逆變性的色彩。初入大學的安德烈婭獨來獨往沒有朋友,這時候同學龐斯主動上前與她搭訕,希望和這個有點特別的安德烈婭成為朋友。接下來他帶著安德烈婭走進了他“藝術家”朋友們的小圈子,帶她認識新朋友。終于有一天,龐斯向安德烈婭提出邀請,邀請她去家里,要跟她跳舞,要介紹安德烈婭和他的母親認識,最后還握住了安德烈婭的手吞吞吐吐地跟她說,在那一天會出其不意地跟她“提出一件事”。他的一舉一動都讓安德烈婭想入非非,她覺得自己終于可以脫離這個壓抑的家了,終于可以像童話故事里的灰姑娘一樣了,終于不用再自卑,終于可以擁有愛情,盡管她不是多么愛著龐斯。當讀者抱著滿滿的期待以為龐斯會和安德烈婭求婚的時候,事情變了。安德烈婭來到龐斯豪華的家,看到他高傲的母親和那些美麗高貴的小姐,自己顯得那么格格不入,而龐斯不僅沒有向她表達愛意表示承諾,還嫌棄她的衣服和鞋子,這讓她無比的失落和沮喪,也是出乎讀者的意料。
二、 繼承與創新
《一無所獲》中的懸念設置并非空穴來風,從其神秘、恐怖、撲朔迷離的特點,不難發現它身上有哥特式小說的影子。18世紀90年代開始,哥特小說被正式確立為一種文學體裁,以陰森、恐怖、神秘、扣人心弦、懸念重重為特色,以古堡、荒野為背景,講述為滿足個人情欲或財產爭奪而引起的謀殺和報復。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哥特小說的發展達到了一個巔峰的時期,不少著名的浪漫主義作家都樂于使用哥特故事或者哥特手法進行創作,例如布萊克、柯爾律治、拜倫、雪萊、簡·奧斯汀、勃朗特姐妹等等,他們都為哥特文學的發展做出貢獻,使得哥特小說可以以通俗小說為入口,進入英美小說的主流世界。
在哥特小說中,設置懸念吸引讀者是非常常見的寫作手法。比如《簡·愛》中神秘的紅樓,午夜時分閣樓上傳來的尖叫,婚禮之前被撕成兩半的婚紗,讓簡·愛恐懼又好奇;《尤道弗的秘密》里,黑夜中的陰影、忙托尼夫人的尸體也成為了縈繞在艾米麗心頭的陰影,讓她猜測疑惑;《呼嘯山莊》中希刺克里夫極度的暴虐,又通過絕食靜靜死在了凱瑟琳原來居住的房間里,他的人生經歷和他謎一樣的結局不禁讓人產生種種聯想。哥特小說中懸念的設置,賦予了讀者和主人公一樣的緊張和恐慌的體驗,同時增加了小說情節的離奇性和傳奇色彩,為小說增添了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
《一無所獲》這部小說在繼承了哥特小說懸念敘事的基礎上,也在西班牙文壇特定的時代背景下有著自己的突破之舉。這本小說出現在戰后的西班牙,由于弗朗哥政府的獨裁統治和嚴格的新聞審查,作家的自由創作受到了限制。弗朗哥在內戰中的勝利直接使得西班牙倒退成了一個保守的父權國家,女性的權利再次被限制起來。在長槍黨的指引下,婦女事務所被創立起來。這一組織的主要工作內容就是引導女性成為一個溫柔賢惠、逆來順受的好太太。與此相應,為了迎合當時的政策管理,“玫瑰小說”成為了市面上流行的最主要的女性讀物。這種“玫瑰小說”力圖宣揚女性美德,不僅試圖給當時的西班牙女性樹立“賢妻良母”的觀念,還以“美好的愛情”為誘餌,為女性讀者們編織一個甜美溫柔的愛情幻想,讓她們成為單純愚昧,不具有任何危害性的社會角色。
同樣是出自女性之手,講述女性自己的故事,《一無所獲》卻與它之前的“玫瑰小說”大相徑庭——它不僅不強調女性應具備的美德,還打破了“玫瑰小說”里以美滿婚姻和愛情為結局的模式。《一無所獲》里的愛情往往是以逆變性懸念的形式呈現的——揭曉的答案與情景的引導完全相反。小說里安德烈婭和男同學龐斯相處愉快、互生好感,從此開始了有關安德烈婭的愛情懸念,她的愛情是怎么樣的?接下來會發生美好的愛情故事嗎?在龐斯的邀請下,安德烈婭來到龐斯的家里參加舞會,她一路上在心里默默期待了許多,感覺這一次龐斯可能會表白會求婚。然而,結局與小說情景一再做的鋪墊完全相反,沒有表白、愛情落空,安德烈婭更像是一只受傷的丑小鴨,離開了自己構想的愛情花園。小說情節這樣的設計,對于老套的“愛情美滿”的結局無疑是一種突破。
另外,埃娜和羅曼的逆變性懸念也是小說的愛情“反轉”,原本層層鋪墊出的愛情只是迷惑人的假象,這場假的愛情不僅沒有通向美滿婚姻,沒有帶來對花花公子羅曼的救贖,而是激烈的復仇。故事到這里,埃娜從一個甜美可人的少女轉身化作了一個堅決勇敢的復仇女神,這一人物的轉變,更是突破了當時“玫瑰小說”為西班牙女性搭建的乖巧溫婉的“美好天使”形象。盡管這種帶著狠勁兒的復仇女形象并非是傳統觀念里安守本分的“好女人”,但埃娜的形象里有著另外一個毋庸置疑的優點,就是她的正義感。這個角色的塑造,一方面是對西班牙文學作品里女性形象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對女性勇敢、富有正義感的品格做出了肯定。endprint
而小說對格洛麗亞的形象塑造也具有一定的逆變性,前文為她鋪墊的是看上去是不務正業的女人,而實際上她是希望通過打牌贏錢掙一點“外快”。她每天游蕩的行為確實與傳統的賢妻良母形象不符,但是她所作所為是為了填補她一貧如洗的家庭——一個連最基本的溫飽都無法達到的家庭,賣掉舊家具、賣胡安的畫、去姐姐那里想著辦法贏錢,羅曼偶爾會拿食物回來,但是這些食物卻沒有搬上家人的餐桌,胡安又舍不得低價出售自己的“寶貝”畫作。從照顧家用這一點來看,她對整個家庭的付出也是不可忽視的,在此,她看上去本不光彩的形象,一下反轉成了她這個人物獨特的正面色彩。由于小說采用的第一視角,讓我們和安德烈婭一起觀察,讓我們借由安德烈婭的眼睛逐步去發現格洛麗亞這個人物的完整的、全面的形象。一開始在作者的重重設計里,格洛麗亞是一個愚蠢的、神經質的女人,被羅曼和安古斯迪亞斯唾罵,作者似乎是在透露給我們她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讓我們對她有了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然而跟隨安德烈婭的目光觀察的過程,就是一個對格洛麗亞人物形象不斷挖掘和探索的過程,我們看到她優點缺點全面的凸顯,使得這個人立體了起來,不是教科書里一成不變的壞女人,也是不宣傳單上的好女人。作者通過她循循善誘的筆,打破了傳統好女人的形象,讓小說中女性的形象有了更加真實,更為深刻的轉變。
從關于愛情的情節逆變和關于女性形象的情節逆變上看,我們可以發現在創作過程中,作者實際上在引導讀者去觀察去發現,什么是真實的愛情,什么是真實的美好的女性形象,去領悟到那些每天在對女性進行的教育其實是把女性規劃到條條框框里的限制。《一無所獲》的出現為當時頗受“玫瑰小說”荼毒的西班牙女性遞上了一瓶解藥。
結語
小說《一無所獲》情節的懸念設置是這部小說的一大亮點,一方面為讀者增添了引人入勝的閱讀體驗和閱讀樂趣,另一方面也通過逆變性的懸念設置,打破了讀者的閱讀期待,一改當以美好愛情為結局的“玫瑰小說”故事模型,為當時西班牙沉悶文壇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另外,通過主人公安德烈婭好奇的眼睛,我們看到了人物形象的一系列反轉,在這反轉的情節中,作者通過環環相扣的懸念疊加,循循善誘地引領著讀者看清了人物的本來面目。尤其是一些女性形象的反轉,原本看似不光彩的行為背后,實際上表現出來的是她們美好的品格,在人物的塑造上面,也是突破了“玫瑰小說”中慣有的賢妻良母形象,這樣的描寫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完整、真實。
參考文獻:
[1] (西班牙)卡門·拉福雷特著,顧文波等譯.一無所獲[M].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2] 黃曉紅.敘事中的懸念[D].湖南師范大學,2013.
[3] 趙炎秋.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的女性哥特小說[D].湖南師范大學,2008.
[4] 張寧寧.阿里巴烏街上的怪女孩——《一無所獲》對傳統女性形象的顛覆[J].文藝爭鳴,2013,08.
[5] 肖明翰.英美文學中的哥特傳統[J].外國文學評論,2001,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