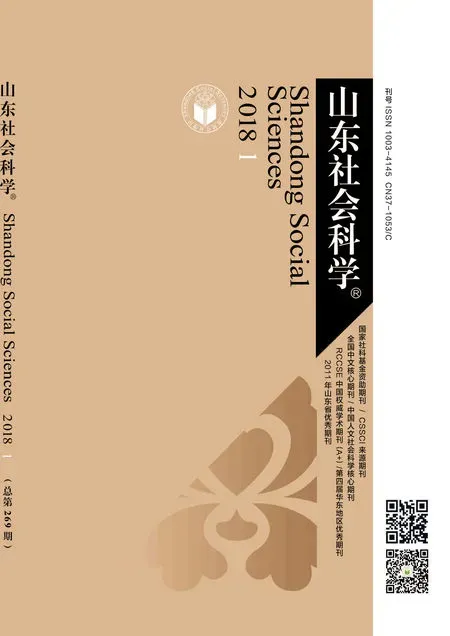習近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新認知新境界
左亞文
(武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2)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傳承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發表了許多重要講話。綜觀這些講話的精神,可以說它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不僅為我們正確地評價和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論原則,而且為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建設文化強國指明了方向。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我們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經歷了一個不斷提升、不斷進步最終臻于理性的過程。對于這個過程,我們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78至2001年,即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六大之前。在這一階段,雖然我們進行了文化領域的撥亂反正工作,文化教育事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從總體來看,我們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所堅持的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明的基本觀點。
1940年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從“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斷定當時中國占統治地位文化的根本性質是“封建文化”,屬于“中華民族舊文化”的范疇。他說:“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頁。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毛澤東盡管認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盡管其為我們黨確立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的基本原則;但是,對于這種“精華”和“糟粕”的辨別和判斷,在當時的條件下還不可能得出具體的結論。
新中國成立之后一直到改革開放的前20年,我們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在根本上并未超出毛澤東為我們確立的基本原則。因此,在2001年前我們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有兩個特點:
一是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的報告中,并沒有專門論述文化建設的部分。這一方面說明了當時我們黨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以改變國家極端貧窮落后的面貌,因而文化建設還沒有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們黨對文化建設特別是傳統文化建設的認知未能提升到應有的高度。
二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一般只是抽象提到“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良的思想文化傳統”(黨的十四大報告)或“批判繼承歷史傳統”(1986年《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或“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199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第二個階段,從2002至2012年,即從十六大到十八大。在這一階段,伴隨著我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深化,推進文化體制的改革,實現中華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的任務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與此相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實現了重大突破。
這一階段我們黨舉行了三次黨的代表大會,每一次大會不僅把文化建設擺在相當突出 的位置,而且在對傳統文化的認知上都有新的進展。
2002年黨的十六大在文化建設上有兩個明顯的變化。一是黨的政治報告中專門有一部分論述“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而且自此之后形成一個慣例,即每一屆黨的代表大會其政治報告都要專辟文化建設的部分,對其重要性及其基本方針作出具體闡述。
二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開始作出了嶄新的評價。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并且強調:“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在當代中國人民的偉大奮斗中,必將迎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高潮,創造出更加燦爛的先進文化。”*《十六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7頁。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對我國的傳統文化作出如此高度的評判,其創新意義是非同尋常的。
首先,對民族精神進行了集中的提煉。根據黑格爾論述,民族精神是貫穿于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過程中起支配和指導作用的一種精神源泉和力量。在其《歷史哲學》中,黑格爾明確指出:“每一個階段都和任何其他階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則。在歷史當中,這種原則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種特別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這種特性的限度內,具體地現出來,表示它的意識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個的現實。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這些特殊的特質要從那個共同的特質——即一個民族特殊的原則來了解,就像反過來要從歷史上記載的事實細節來找出那種特殊性共同的東西一樣。”*[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04-105頁。在黑格爾看來,民族精神并不是一種僵死的化石,而是一股不斷膨脹著的洪流。因此,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這種民族精神又具體化為特定的時代精神。無論是民族精神還是時代精神,盡管在其發展中存在著傳承和變革的關系,但其基本的核心精神卻是一以貫之的。黨的十六大報告第一次對我國的民族精神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將其凝練為“一個核心”和“十六個字”,這本身就是一個創舉。
其次,明確提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雖然文化有其歷史性的特征,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文化呈現出不同的社會屬性,但是,其文化中存在著的基本精神即民族精神卻能穿越古今而一脈相傳。我們中華民族正是有了這種民族精神,才能世代延續而不墜于地。黨的十六大報告充分肯定我國民族精神的傳承性及其“精神支撐”作用,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具有突破意義的命題。
繼黨的十六大之后,2004年我們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所作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第一次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這個《決定》要求全黨要“堅持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提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隨后,2006年黨十六屆六中全會又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不僅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行了具體的部署,而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建設和諧文化”的概念。《決定》指出:“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為此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
自此之后,“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和諧精神”“和諧理論”“和諧思維”成為時代的流行語,并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觀念之中。在思想觀念上的這種轉變,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長期以來,由于受“斗爭哲學”的影響,我們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和諧文化”視為調和主義和折衷主義的封建流毒,成為理論研究的禁區,甚至到了談和色變的程度。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起,我國學術界部分有識之士開始沖破這一理論禁區,對 “中華和合文化傳統”展開熱烈地研究,產生了一批學術成果。這種研究得到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江澤民、李瑞環、錢其琛、李鐵映等的認可和支持。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和十六屆六中全會,以黨的決定的形式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和諧文化”的思想,大力宣傳和倡導和諧理念、和諧精神與和諧思維,這在黨的歷史上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思想文化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反映了中華民族在思想上的新覺醒以及思維方式的一次大轉變。
2007年黨的十七大在文化建設上也有兩個重大變化。第一個重大變化是在其政治報告的文化建設“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部分,明確地提出了“中華文化”的概念。報告指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頁。正是這里,我們黨不僅首次提出了“中華文化”的概念,而且作出了充分的肯定性評價。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持肯定評價的是其中“優良的思想文化”或“優秀文化傳統”,在整體上因其屬于封建性質的文化,因而是持基本批判的態度的。黨的十七大報告突破了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勢,第一次從正面的意義上提出了“中華文化”這個普遍性的概念,并肯定其在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中的動力作用。這在一定的意義上表明我們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評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第二個重大變化是向全世界公開宣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伴隨著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頁。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講到,現代化所帶來的非西方社會經濟社會的發展,會導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復興。他指出,一般來說,“經濟和軍事權力的下降會導致自我懷疑、認同危機,并導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尋求經濟、軍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訣。當非西方社會經濟、軍事和政治能力增長時,它們就會日益鼓吹自己的價值、體制和文化的優點。”*[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自近代以來,2007年可以說中華文化發展的一個轉折點,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迅猛發展,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開始凸顯出來,這是任何文明和文化發展的內在邏輯。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我們黨在2011年10月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要專門作出《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原因。
2012年黨的十八大在文化建設上主要是圍繞著“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個主題展開的。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上,提出了“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戰略任務,強調要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由此可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必須立足本國的民族文化,離開這個文化本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就失去了根基和載體。
第三個階段,從2012年10月之后至今,即從黨的十八大之后至現在。在這一階段,我們黨對中華文化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和提升。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表了許多重要講話,把對中華文化的認知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高度。
二、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新認知
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為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遺余力,不僅提出了許多新的論斷、實施了許多新的舉措,而且身體力行,利用一切機會在世界舞臺上積極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貢獻。
首先,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習近平總書記表現出了深沉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理性自覺。2014年3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德國柏林同德國漢學家、孔子學院師生代表座談時講到:“我作為國家主席,有一些老前輩就跟我講,作為中國的領導人要干什么呢,就是不要把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搞丟了,還應該在你們手里傳承下去。”這幾句話道出了習總書記的心聲,這就是決心擔當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歷史使命。這幾年來,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大量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講話,在幾乎每次出訪演講中,總不忘向全世界人民宣傳和介紹中華文化,人們親切地稱呼習近平總書記為“中華文化的使者”和“優秀傳統文化忠實的傳承者”。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種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理性自覺,源于其對中華文化的真摯熱愛和深刻體認。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習近平在總結和反思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沿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的邏輯進程“接著講”,因而大大深化了對傳統文化的認知。
為了更好地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他明確提出,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光榮歷史,要加大正面宣傳力度,通過學校教育、理論研究、歷史研究、影視作品、文學作品等多種方式,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我國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參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頁。他強調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以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博大精深的燦爛文化,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頁。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最終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這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所自覺承擔的文化建設的歷史使命。
其次,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上,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把對中華文化的總體評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集中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充分肯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自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特別是相對于西方我國在科技和經濟上的落后,在社會中逐漸滋長了一種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乃至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所謂“全盤西化論”就是這樣心態的典型表現。在我黨的歷史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也經歷了一個反復曲折的過程,在很長的時期內片面夸大文化的階級性和歷史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重新評價中國傳統文化,對其的認知日益趨于深刻。正是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的論斷,并且指出這一論斷的理據在于中華文化不僅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而且它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由于有了這種文化,中華民族才能生生不息、薪火相傳;才能延綿至今、不墜于地。*《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8頁。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氣勢恢宏,有理有據,使過去存在于部分人心中的那種文化自卑心態為之一掃,大大提升了人們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
要想改善水利工程管理,首先應加深對水利工程重要性的認識,全面提升工程隊伍素質,同時完善管理體制,并注意規范監管制度,全面提升監管質量,將管理工作落實到水利建設各環節之中,并注意增加竣工以后的資金投入,加強后期管理與維護。具體來說,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改進管理方法。
二是反復強調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基因(Gene)是從細胞生物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借用過來的一個概念。根據基因學說,基因支持著生命的基本構造和性能,儲存著生命的種族、血型、孕育、生長、凋亡等過程的全部信息,盡管基因在環境作用下會發生“突變”和變異的現象,但是,其生命的最基本的特征仍然保持不變。習近平總書記運用基因這個概念來表達中華文化的獨特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可謂深刻地揭示了中華文化在其生成和演化過程中變動性和連續性、多樣性和統一性的辯證關系,糾正了長期以來存在的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從而將二者割裂開來的錯誤。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頁。在任何一個文化體系中,思想觀念文化都是包含在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中最核心的東西,而在觀念文化中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又是最為穩定的要素,因而成為中華文化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
“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頁。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如果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背離了自己的“根”與“魂”。這些論述從文化本體的高度深刻地闡明了中華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它告訴我們,中華文化作為遺傳基因的DNA已經滲透到我們中華民族每一個成員的神經和細胞之中,在一定的意義上,人作為社會的存在物同時也就是這種文化的存在。
誠然,文化傳統并不是一塊僵死的化石,勿寧說它一個激情膨湃的鮮活的存在。誠如黑格爾所說:“這種傳統并不僅僅是一個管家婆,只是把她接受過來的忠實地保存著,然后毫不改變地保持著并傳給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過程那樣,在它的形態和形式的無限變化與活動里,仍然永遠保持其原始的規律,沒有進步。這種傳統并不是一尊不動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離開它的源頭愈遠,它就膨脹得愈大。”*[德]黑格爾:《哲學史演講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8頁。對中華文化傳統,我們也要作如斯觀。
三是強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頁。。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必須向人們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頁。。他還指出,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它“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頁。。他還多次強調:“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頁。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部分也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頁。這些論述和觀點都具有突破性的創新意義。因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堅持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包括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盡管可以從封建的舊的傳統文化中吸取某些積極的合理的因素,但決不可能成其為理論淵源、思想根基和精神支撐。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思想徹底打破了以往的思維定勢,把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知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在理論界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再次,在對中國傳統文化本質內涵的看法上,習近平總書記對其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具體的分析,把我們黨對中華文化的認知推進到一個新階段。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思想或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學術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張岱年先生認為,貫穿于中國幾千年來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其主要內涵主要表現為這樣幾種思想基本觀念:(1)剛健有為;(2)和與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協調。*張岱年:《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劉綱紀先生認為,中國的民族精神大致可以概括為四個相互聯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2)自由精神。(3)求實精神。(4)應變精神。*劉綱紀:《略論中國民族精神》,《武漢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司馬云杰先生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尊祖宗、重人倫、崇道德、尚禮儀。*司馬云杰:《文化社會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還有不少其他學者從不同維度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進行過提煉和概括。應該說,所有這些概述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習近平總書記正是在吸取這些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從其時代價值的維度切入,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進行了新的概括。他指出:“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頁。在這里,習近平總書記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時代價值的基本精神概括為講仁愛、重人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六個方面。筆者認為,這六個方面不僅高度凝練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和精神,而且彼此之間相互關聯而形成一個有著內在邏輯結構的有機系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仁愛”是其內核,“民本”是其基礎,“誠信”是其規范,“正義”是其尺度,“和合”是其價值,“大同”是其理想,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由內到外、從體至用的邏輯關系。可見,這樣的概括不僅具有新的視角,而且給予了新的詮釋,使之融入了新的時代內涵。
除此之外,習近平總書記還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些具體內容作了深入的分析。2014年5月4日,他在與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列舉了中華文化中許多流傳千古的名言,如“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喻于義”“君子坦蕩蕩”“君子義以為質”“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鄰”“仁者愛人”“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貧濟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他強調:“像這樣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這些思想和理念,既隨著時間推移和時代變遷而不斷與時俱進,又有其自身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我們生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頁。這些分析的深刻之處在于闡明了蘊含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那些具有普遍價值意義的思想觀念,并且強調這些思想觀念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度的永恒魅力,這就消除了過去以歷史性和民族性之名而否定其普遍性的偏見。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和發展
問題在于如何進行創造性發展?在上個世紀50年代,馮友蘭先生針對那種簡單化的“批判繼承法”,提出其“抽象繼承法”。在他看來,在中國哲學史中,有些哲學命題,如果作全面了解,應該注意到這些命題的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抽象的意義,一是具體的意義。對中國哲學史中的有些哲學命題,如果只注意它們的抽象意義,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還要注意到這些命題的具體意義。當然,注意具體意義是對的,但是只注意具體意義就不對了。在了解哲學史中的某些哲學命題時,我們應該把它的具體意義放在第一位,因為,這是跟這些命題的哲學家所處的具體社會情況有直接關系的。但是它的抽象意義也應該注意,忽略了這一方面,也是不夠全面。
那么,什么是命題的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呢?馮友蘭先生以《論語》中所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為例進行了說明。他認為,從這句話的具體意義看,孔子叫人學的是詩、書、禮、樂等傳統的東西。從這方面去了解,這句話對于現在就沒有多大用處,不需要繼承它,因為我們現在所學的不是這些東西。但是,如果從這句話的抽象意義看,這句話就是說:無論學什么東西,學了之后,都要及時地、經常地溫習和實習,這就是很快樂的事。這樣的理解,這句話到現在還是正確的,對我們現在還是有用的。據此,馮友蘭先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一個命題的抽象意義是可以跨越時代而能被我們所繼承的,但其具體意義因其與當時的時代相聯系而不能被我們所繼承。*馮友蘭:《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光明日報》1957年1月8日。
應該說,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即便在今天看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它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一般的價值原則、方法論原則、認識論原則、道德修養原則、治國理政原則等,這些一般的原則因其具有最大的普適性而能被我們所繼承和吸取。當然,即便這些原則也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改變,但這種改變不會完全否定其原有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實質,只是在其基礎上的進一步完善和深化。
但是,“抽象繼承法”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任何文化都是一個有機體,其抽象義和具體義是相互滲透而融為一體的,因而不能將其當作單個的命題進行拆分。實際上,在一個文化有機系統中,如果僅從命題來看,有些命題至今可以完全接受,例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5月4日與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所提到的諸多命題;但有些命題則已過時,如“男女授受不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一切都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而不是進行簡單的區分。
改革開放之后,學術界對于如何繼承中國文化傳統進行了熱烈地討論,提出了種種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創造性轉換”的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正是在吸取這些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雙創”方法。這一方法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方法論原則。
所謂“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達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謂“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內在聯系在一起的,并非截然不同的兩個環節,創造性轉化本身就意味著創新性發展,而創新性發展則蘊含著創造性轉化。
依筆者的理解,“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一基本的方法論原則包含了豐富和深刻的內涵,其主要之點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客體性原則。十九大報告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行“轉化”和“創新”,首先必須弄清楚其對象、客體或載體。無疑,這個對象、客體或載體就是中華文化本身,而不是別的什么文化。因此,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在不忘本來的基礎上開辟未來,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這是我們創新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前提性條件。
其二,堅持創造性和創新性的主體性原則。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參見《 人民日報 》 2014年09月25日 02 版。因此,在傳統文化面前,我們也不能采取不動腦筋的消極被動的接受態度,而是要充分發揮主體能動的創造精神,在主體和文本客體的對話中實現“視界融合”,在“視界融合”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其三,立足當今現實的時代性原則。無論是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客體性原則,還是堅持創造性和創新性的主體性原則,最終都要統一到立足當今現實的時代原則之上。立足當今現實的時代性原則,既是我們進行傳統文化創新和發展的出發點、切入點,也是我們進行文化建設的目的和歸宿。離開當今中國的現實和當今時代的條件,來談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和發展是沒有意義的,也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因此,“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才是推動中華文化實現其自身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鑄就新輝煌的唯一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