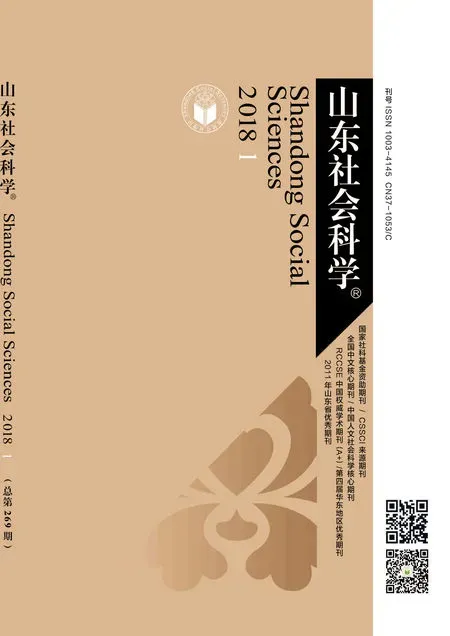西方“馬克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演替及其當代走向
張 亮
(南京大學 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江蘇 南京 210023)
19世紀90年代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獲得合法地位,進入資產階級政治體制,一舉成為影響日隆的主流議會黨。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馬克思的著作與思想開始超越社會主義政黨的宣傳教育以及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識形態攻訐,成為西方學院的研究、批評對象。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西方“馬克思學”由此發端。對于上一個世紀之交的西方學院來說,身在“西方”的馬克思創立了一種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異質性思想,以至于研究者不得不像對待“非西方”思想那樣去理解、“格義”他的著作與思想。經過半個世紀的摸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西方學院逐漸超越“格義”,掌握理解、闡釋馬克思的規范方法,推動“馬克思學”走向成熟和繁榮。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馬克思學”逐漸進入后成熟階段,除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生平、著作和思想的客觀闡釋,研究者們也開始關注自身學術主體性或個性的建構,“馬克思學”的“解釋學轉向”就此初露端倪。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后,隨著“馬克思學”過去曾具有的現實性的消退,這種“解釋學轉向”開始大行其道,成為當代西方馬克思研究引人注目的一個新特征。
一、馬克思: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
在上一個新舊世紀之交,致力于馬克思研究的西方學院派學者人數極少。不過,他們大多政治立場開明甚至傾向社會主義,具有極強的政治和學術敏感性,出身當時學院體系的中心而非邊緣地帶。例如,《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的作者尤金·馮·龐巴維克(1851-1914)是極有影響力的奧利地學派經濟學家,學而優則仕,1889年后成為奧地利財政部的高級公務員,并于1895年之后三度出任財政部部長。奧斯卡·斯科爾頓(1878-1941)是加拿大知名政治學家和社會活動家,長期擔任女王大學董事會主席,其代表作《社會主義的批判分析史》(1911)的基礎是其于1908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通過的博士學位論文。這或許是英語世界第一本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博士學位論文。至于德語世界,第一本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博士學位論文可能是埃米爾·漢馬赫(1885-1916)1908年通過口試、1909年擴充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濟體系》。《馬克思與黑格爾》(1911)的作者約翰·普倫吉(1874-1963)是德國有影響的政治學家,長期擔任明斯特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在出版《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1913)之前,弗拉基米爾·斯姆科維奇(1874-1959)已經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史教授,出版了多部有影響的俄國經濟史論著。
就代際而言,第一批西方馬克思研究者之于馬克思,類似于亞里士多德之于蘇格拉底、馬克思之于黑格爾,本應不存在什么理解困難。可實際情況是,他們在理解馬克思方面所表現出來的隔膜、困窘與穿鑿附會,與其說是在研究一個去世沒多久的西方人,倒不如說是在“想象”一種異質性的外來思想!我們知道,不管是在馬克思的自我意識里,還是在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的傳記敘述中,馬克思主義都是馬克思在繼承19世紀歐洲各種先進的思想文化成果基礎上創立的,毫無疑問是歐洲的、“西方”的。這一點現在已經得到人們的普遍接受。那么,在100多年前第一批研究馬克思的西方學者眼中,馬克思為什么會呈現出強烈的“非西方”性或異質性呢?
一方面,這與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傳播狀況密切相關。作為一名青年黑格爾派成員,青年馬克思曾是德國學院主流的寵兒。不過,1843年底,他在政治立場上實現從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主義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轉變,繼而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徹底走向資產階級社會的對立面。此后,他的著作和思想就不再能被資產階級社會和學院所容,主要在無產階級特別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政治團體中傳播。馬克思在倫敦生活了34年(1849-1883),但始終不為英國學院主流所知,這一點尤其能說明問題。1890年,德國《反社會黨人法》期滿失效,先是德國隨后是其他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陸續獲得合法地位,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也由此從地下轉到地上、從秘密流傳轉為公開傳播,成為學院派學者可以自由接觸的對象。但新問題也隨之出現:第一,當時馬克思的公開出版物極少,“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學院派學者缺乏理解馬克思的必要文獻基礎;第二,在長期隔絕發展中,馬克思主義形成了獨特的學術傳統,學院派學者需要足夠的時間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陌生的術語系統和論述方式;第三,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過程中,恩格斯以及第二國際理論家出版了相當數量面向無產階級的大眾化讀物,對于學院派學者而言,這種大眾化解釋系統既可以通向理解,也可以通向誤解,而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也就是說,在上一個新舊世紀之交,當馬克思像魯濱遜那樣結束漂流重回西方學院時,儼然成了一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中人”。
另一方面,這也與西方學院傳統的斷裂和更新密切相關。馬克思的思想來源包括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等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眾多先進思想文化。就此而言,他是法國啟蒙運動之后歐洲資產階級學院主流的繼承人,其思想充分體現了這種學院主流的基本特征:追求本質(規律)、社會總體性和人類未來。然而,19世紀60、70年代,也就是馬克思創作其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的那一階段,歐洲學術思想發生了一次大的斷裂和更新:人們不再追求甚至不再相信本質、總體性和未來,日益滿足于對現象、局部和當下的實證主義描述。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話說,就是物化意識取代辯證法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當然也包括學院——的主流。黑格爾從哲學王到“死狗”的變遷,直觀記錄和表征了這種斷裂與更新。也就是說,在馬克思和他的第一批學院派研究者之間,橫亙著一次迅速發生的范式轉換。這個轉換是如此劇烈、深刻,以至于前后相繼的兩種學院傳統或學院傳統的兩個階段,已經無法自然地相互理解,出現“兒童見面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式的尷尬局面。
總之,馬克思曾經不僅很“西方”,而且很“學院”,但當他在差不多半個世紀后再一次出現在西方學院面前時,已然顯得既不“學院”,也不“西方”。從某種意義上講,當時的馬克思確實成了一個在“西方”的“非西方”思想家。
二、20世紀早期“格義”馬克思的幾種流行路徑
20世紀30、40年代,陳寅恪、湯用彤等學者發現,“格義”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學者嘗試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國思想的第一種方法。*湯用彤:《論“格義”》,載《湯用彤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242頁。馮友蘭后來進而提出,“格義”是佛教和佛學在中國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他指出,就像人初學外國語時必須通過翻譯才能理解一樣,“一個國家的哲學,傳到別國的時候,也要經過類似的過程。佛教初到中國的時候,當時的中國人聽到佛教的哲學,首先把它翻成中國哲學原有的術語,然后才覺得可以理解。”*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冊,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頁。由是推而廣之,不難發現,當兩種異質性的文化思想初次相遇并力圖相互理解時,必然會運用“格義”方法,出現“格義”階段。當馬克思這個在“西方”的“非西方”思想家初次與西方學院相遇時,同樣遭遇“格義”方法、經歷“格義”階段。
在20世紀20年代盧卡奇、柯爾施等開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走上歷史舞臺前,用新康德主義“格義”馬克思是歐洲學院較為流行的一種路徑。19世紀60、70年代,新康德主義在德語世界悄然出現,到19世紀20世紀之交則已經成為德語學院哲學的主流,甚至流傳到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國,成為一種具有歐洲性的哲學潮流。新康德主義的流行是如此普遍,以至深受恩格斯信賴與器重、被賦予保管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重任的第二國際理論家伯恩斯坦都公開提出應當順應“回到康德去”這股時代潮流,用新康德主義修正、改造、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伯恩斯坦:《社會主義中的現實因素和空論因素(1898)》,載殷敘彝編《伯恩斯坦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96頁。伯恩斯坦的這種修正主義觀點遭到普列漢諾夫、梅林、盧森堡等其他第二國際理論家的批判,但我們必須看到的是,它卻被資產階級學院當做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用新康德主義“格義”馬克思就此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路徑。首先,大多數資產階級研究者都認為馬克思沒有或者已經拋棄了黑格爾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哲學,他的學說不過是一種已經被變化了的現實證明不再適用的“科學”。作為這段學術史的見證人,柯爾施有過非常深刻的評論:“資產階級的哲學教授們一再相互擔保,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學內容,并認為他們說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也一再相互擔保,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從其本性上來講與哲學沒有任何關系,并認為他們說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湜等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只有像漢馬赫這樣具有新黑格爾主義背景的資產階級研究者才能較為準確地認識到,馬克思的思想由“德國哲學的思辨形式和古典社會經濟學的唯物主義—經濟內容”這兩種異質性來源匯聚而成。*Emil Hammacher, Das philosophisch-?konomische System des Marxismu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9, s. 391.其次,資產階級研究者會在脫離現實過程、純思想性的認識論模型或者韋伯所說的“理想型”意義上來理解《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體系。1894年《資本論》第三卷出版,新新歷史學派的桑巴特(1863-1941)和奧地利學派的龐巴維克都出版了評論著作,認為馬克思提供的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無關的純粹概念和思維程序,基于它們不能有效說明新的經濟現象這點,或判定馬克思經濟學不再具有現實性,或判定其已經終結、破產。*參見張亮:《早期西方“馬克思學”視域中的〈資本論〉:批判的再評價》,《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雖然否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科學性,但有意思的是,資產階級研究者都不否定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為,最后,他們都像伯恩斯坦那樣,把社會主義理解為康德意義上絕對的道德律令的要求,從而把科學社會主義扭曲為了馬克思早就批判過的“真正社會主義”即倫理社會主義。
把科學社會主義“格義”為倫理社會主義,并不是新康德主義的專利,在英語世界占據主流哲學意識形態地位的功利主義也是如此。功利主義主張人性本善,把追求幸福的最大化作為判斷人的行為的根據。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家威廉·葛德文(1756-1836)更是認為人的最大幸福是來自社會的根本變革。他認為:“一個民族應該自行確定某種偉大的共同原則,而最高執政者則應該在聽到這種普遍意見之后放棄自己的要求。……一切個人考慮都必須服從于普遍的福利。”*威廉·葛德文:《政治正義論》(第一卷),何慕李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49頁。“根據一種博愛精神講出來的真理……不論其闡明的方式是如何毫無保留 但在它的發展上一定會是循序漸進的。真理,只能逐漸地為其最勤勉的信徒所充分理解;并且將以更加緩和的速度灌輸給社會上一大部分人,使他們成熟到能對他們共同的制度進行變革。”*威廉·葛德文:《政治正義論》(第一卷),何慕李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64頁。葛德文的學說有力影響了歐文空想社會主義觀念的形成。后世英語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大多不自覺地從功利主義哲學立場出發,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一種道德需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語世界研究者也是如此“格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在牛津大學哲學家H·W·B·約瑟夫(1867-1943)看來,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問題,因而可以通過道德的方式得到解決,完全不必要一定選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因為盡管蘇聯的社會主義解決了分配不公正問題,但卻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另一項罪惡,即“太多的人感到以自己無法掌握的方式虛度一生”*H. W. B. Joseph,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 Karl Marx,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p. 170.變得有過之而無不及。蘇格蘭哲學家斯科特也認為,剩余價值理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為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體系提供了一種“很多人都希望得到的”“道德判決”。*J. W. Scott, Karl Marx on Value, London: A & C Black, 1920, p. 15.澳大利亞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普特斯同樣認為,后世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會把勞動價值論作為馬克思主義核心來堅持,是因為他們在其中找到了可以激發千百萬勞動大眾的“道德本性”的“道德判決”。*G. V. Portus, Marx and Modern Thought, Sydney: 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N. S. W., 1921, p. 118.
用社會進化論“格義”唯物史觀是當時大西洋兩岸都非常流行的一種路徑。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1860年,在第一次閱讀《物種起源》后,馬克思致信恩格斯說:“盡管該書寫得有點兒英國式的粗糙,但它包含了支持我們的觀點的自然歷史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頁。不過,一年半后重讀《物種起源》時,馬克思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批評達爾文把自然選擇直接搬到了英國社會問題的分析上:“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如何在動植物中重新發現了英國社會的勞動分工、競爭、開拓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斗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2頁。也就是說,馬克思反對將進化論從自然界直接挪用到社會。然后,當時的英國社會卻出現了用達爾文、拉馬克的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理論解釋社會發展的熱潮,其代表人物是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斯賓塞認為:“……進步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必然。文明并不是人為的,而是天性的一部分;它和一個胎兒的成長或一朵鮮花的開放是完全一樣的。人類曾經經歷和仍在經歷的各種改變,都源起于作為整個有機的天地萬物之基礎的一項規律。”*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靜力學》,張雄武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7-28頁。由于對社會發展給出了符合進步論預期和資本主義野蠻擴張邏輯的“科學”解釋,社會進化論一經提出就在大西洋兩岸產生廣泛流行,甚至連部分第二國際理論家也受到影響。例如,天文學家出身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安東尼·潘涅庫克(1873-1960)1909年出版《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小冊子,*Anton Pannekoek, Marxism and Darwinism,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912.闡釋兩者的一致性。德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亨利希·庫諾(1862-1936)也說:“按照馬克思的發展理論,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也都屬于進化。這些也是進化的行動,然而是一種加速了的強有力的行動,是以大大加快的速度向前突進。”*亨利希·庫諾:《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學說》,袁志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65頁。在這種背景下,用社會進化論“格義”唯物史觀就顯得既“自然”又“合理”了。在1927年初版的重要論著《卡爾·馬克思對歷史的解釋》中,美國經濟學家曼德爾·鮑勃(1891-1957)認為,馬克思主張歷史具有類似于自然規律的特征,遵循進化論式的決定性道路,在其中生產起著支配性的作用。他開篇就說:“《物種起源》問世的十二年前出現了這樣一本書,它闡述了一種包羅萬象而又富有挑戰性的歷史進化論,宣稱自己既說明了過去又令人信服地預見了未來,而且沒有哪個階段的社會生活能逃出它的法眼。幾個月后,該作者與他的朋友合作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具體運用這一理論勾畫出了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指明了那種逐漸破壞現存秩序并為社會主義鋪平道路的力量。這本書就是卡爾·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而那本小冊子則是《共產黨宣言》。”*M. M. Bober, Karl Marx’s Interpret of History, 2nd, Cambridge: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3.美國文化史學家雅克·巴尊(1907-2012)1941年出版的《達爾文、馬克思、瓦格納的遺產批判》把馬克思和達爾文相提并論,此書多次再版,直到1981年還出版了平裝版。用社會進化論“格義”唯物史觀在美國的流行,由此可見一斑。
用基督教的術語、理念“格義”馬克思的生平與思想,也是當時比較流行的一種路徑。這種途徑大多存在于一些相當大眾化的讀物中,學術影響并不大。此外,不少傳記作者也嘗試用精神分析方法附會馬克思的思想發展過程,特別是解釋其絕不妥協的革命性。這種“格義”的遺跡在今天西方學者的傳記作品中仍然隱約可見。
三、西方“馬克思學”的規范化研究方法
20世紀30年代,西方“馬克思學”開始超越“格義”,逐漸達到西方學院一般思想史研究的規范化程度。這一過程緩慢且不均衡,直至20世紀50年代以后方才最終完成。那么,這種超越“格義”的過程何以能夠實現呢?首先,隨著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現實,進而作為一種世界性存在發揮越來越巨大的作用,西方學院不得不以更加嚴肅的方式對待馬克思恩格斯,越來越多的一流大學、一流學者進入該領域,實質性地改變了西方“馬克思學”的人員結構與水平。這一時期,英國的牛津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以及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已經成為西方“馬克思學”研究的中心,開始較大規模培養博士,顯著提升了西方“馬克思學”從業人員的專業研究能力與水平。其次,蘇聯積極致力于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的收集、編輯、出版和世界性傳播,在客觀上為西方“馬克思學”提供了越來越豐富可靠的文獻資料。文獻資料的匱乏是制約西方“馬克思學”早期發展的一個瓶頸。1921年,在列寧的支持和推動下,蘇俄成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舉國之力系統開展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的收集、編輯和出版。1924 年,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求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籌備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后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同年,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通過決議,委托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梁贊諾夫(1870—1938)進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訂版(MEGA1)的編輯出版。在此后10余年間,蘇聯編輯出版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并通過共產國際向全世界傳播。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方“馬克思學”過去主要依賴第二國際理論家二手闡述來理解、“想象”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窘境。最后,經過近30年的學術積累,西方“馬克思學”初步完成了量的積累,臨近質的提升的界限。總的說來,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西方“馬克思學”論著如今大多只剩下了文獻價值,30年代以后則出現了若干至今仍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論著,如悉尼·胡克(1902—1989)的《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1933)、《從黑格爾到馬克思》(1936)、以賽亞·伯林(1909—1997)的《卡爾·馬克思的生平與環境》(1939)等。它們的出現表明西方“馬克思學”最初的“格義”階段即將被整體超越了。
作為一門新興的思想史研究,西方“馬克思學”既繼承了西方學院思想史研究的一般規范化研究方法,也發展出了具有自身意識形態特征的特殊規范化研究方法。
首先是基于文本的思想闡釋方法。思想史研究的核心任務是揭示思想的形成、發展、本質及其效應。這就要求研究者應當根據第一手思想文本而非第二手研究文獻進行思想闡釋。隨著文本群的逐漸豐富完善,20世紀20年代以后,西方“馬克思學”明確地要求像其他思想史研究那樣基于第一手思想文本進行思想闡釋。在1930年出版的《馬克思的國家理論》中,華裔美國“馬克思學”學者張效敏就專門強調自己的思想史闡釋是“以實實在在的文獻作為支撐”的。*張效敏:《馬克思的國家理論》,田毅松譯,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頁。他既使用了具有第二國際背景的各種左派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原著英譯本,也使用了具有共產國際背景的紐約進步出版社的各種原著英譯本和研究論著英譯本。在MEGA1問世后,西方“馬克思學”學者則更多地標榜自己是以MEGA1為文獻基礎的,即便是力圖“妖魔化”馬克思的史華慈查爾德(1891—1950)也是如此。*Leopold Schwarzschild, The Red Prussian: The 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48, p. 8.基于文本的思想闡釋方法激勵西方“馬克思學”學者不斷走向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內在邏輯以及馬克思恩格斯文本賴以形成的社會史思想史語境,以更加準確地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發展及其本質。它使共識不斷得到積累,分歧日益得到縮小,是推動西方“馬克思學”規范化程度不斷提升的最重要方法力量。
其次是文獻考訂方法。文獻考訂是思想史研究中一種兼具基礎性和輔助性的方法:基礎性是指它承擔為思想闡釋提供準確、豐富文本對象的職能,沒有它的有效工作思想闡釋將有“無米之炊”之虞;輔助性是指它歸根結底是服從服務于思想闡釋的。在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文獻考訂方法起源于18世紀末19世紀上半葉。那時候,古希臘哲學研究方興未艾,歐洲學者們花費巨大精力投入古希臘哲學著作殘篇的發掘、輯錄、考訂和整理,取得巨大成就,從而使規范化的古希臘哲學研究成為可能。馬克思就是在這種學術史背景下選擇從事古希臘哲學研究,完成了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在古希臘哲學研究中大顯身手后,文獻考訂方法被德國學者運用到康德著作的編輯整理中,以期通過對康德大量手稿、筆記、書信等非公開出版文本的文字校勘、編年考訂、整理出版,為人們理解這位偉大哲學家提供更豐富、更準確的文本基礎。隨后,文獻考訂方法成為現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種規范化方法。西方“馬克思學”重視文獻考訂方法與梁贊諾夫編輯出版MEGA1直接相關。有感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本文基礎的薄弱現狀,梁贊諾夫主張“通過清晰的編排,準確地再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遺產”,認為MEGA1應當“提供的是……全部以手稿形式遺留下來的未發表的著作、全部發表過的文章和未完成稿”;“除了發表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全部書信外,還發表第三者寫給他們的全部書信”,“全部著作和書信都以原著文字發表”*《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第29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頁。。梁贊諾夫的這種構想得到西方“馬克思學”學者的積極響應。不過,西方“馬克思學”這種積極響應與梁贊諾夫的初衷一開始就存在差異:梁贊諾夫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展現蘇聯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出版方面的科學性和權威性,同時證明蘇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正統性和合法性;西方“馬克思學”則意在與蘇聯傳統的學術競爭,這點冷戰后變得越來越公開。以呂貝爾(1905-1996)為例,他雖然標榜自己繼承了梁贊諾夫的學術傳統,但卻從來不掩飾自己對蘇聯、共產國際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敵視:“前面的引文體現了我為自己稱為‘馬克思學’的研究領域的辯護。我把它理解為對各種蒙昧主義理論體系的傳播在理論上所做的自衛還擊。這些蒙昧主義理論體系通過乞靈于被斷言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將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用于政治壓迫和經濟奴役。”*Maximilien Rubel, “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 in Maximilien Rubel, Marx, Life and Works, trans. by Mary Bottomor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1979.為了支持他的恩格斯“發明”馬克思主義謬論,他認為必須要將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的準備手稿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一同出版,從而建構起馬克思的整個理論體系,并主張對恩格斯對《資本論》第二、三卷的編輯進行徹底的清理。*Maximilien Rubel, Rubel on Karl Marx: Five Essays, ed. by Joseph O’Malley and Keith Algozi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也就是說,文獻考訂方法原本追求文本的客觀性和準確性,但在西方“馬克思學”這里卻不可避免地與意識形態斗爭糾纏到了一起。冷戰結束前,西方“馬克思學”在思想闡釋過程中但凡祭出文獻考訂方法這個大旗,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要證明蘇聯學界的錯誤、扭曲或者別有用心。
再次是差異分析方法。差異分析方法是一種規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在西方“馬克思學”這里,差異分析方法主要用于解釋、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關系。1849年流亡英國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就在空間上和歐洲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界隔絕開來了。這導致他們主要通過文字與外界發生聯系,而外界也主要通過文字來了解他們。時間長了,人們就不自覺地形成一種印象,覺得他們是一體的。馬克思在1856年就已經察覺到這種傾向:“最奇怪的是,這家伙把我們倆人看成是單數:‘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等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日益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這種一體化思維不斷發展強化,以致于恩格斯逝世后,在很多國際共產主義者的眼中,恩格斯就是馬克思的第二個自我,也就是,他們已經從具有偉大友誼的兩個主體,變成了一個偉大友誼的兩個部分,即他們作為獨立主體的個性、客觀差別變得不存在了。無論這種一體化思維中包含的情感是多么真摯,但它的非批判性都是必須批判的。就此而言,差異分析方法具有不容否定的學術合理性和必要性。事實上,通過差異分析方法及其引發的學術爭論,我們對馬克思恩格斯關系的認識不斷走向深入和全面。不過,冷戰時期,差異分析方法往往和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批判結合在一起。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興起之后,當人們開始把恩格斯的思想指認為蘇聯社會主義、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源頭時,馬克思恩格斯差異就具有了鮮明的現實政治意味:人們拍的是口袋(恩格斯),要打的卻是驢(蘇聯社會主義)!
最后是原罪歸因方法。原罪歸因方法是冷戰時期西方“馬克思學”具有自身意識形態特征的一種特殊規范化研究方法。它的基本特點就是食果辨樹,根據結果來推斷原因,把現實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歸結到馬克思恩格斯那里。這種方法的學術性并不強,但在冷戰時期特別是初期卻頗為盛行。它之所以會有市場,就在于它符合當時人們的意識形態定式。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它的最大問題在于沒有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經歷了一個不斷本土化的過程,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并不能直接歸結到馬克思恩格斯那里。
四、西方“馬克思學”的“解釋學轉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馬克思學”在規范化道路上穩步前進,取得長足發展,最終在70年代以后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繁榮階段:越來越多的大學開設了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有關的課程和研究生項目,從事西方“馬克思學”相關研究與教學的學者數量與日俱增;西方“馬克思學”的成果也水漲船高,迅猛增長;同時,西方“馬克思學”研究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過去很可能只會作為一個章節來處理的內容如今則成為一本書的研究課題。在這種西方“馬克思學”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80年代以后,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悄然出現了:一些西方“馬克思學”學者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在誰的理解、解釋是關于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思想的唯一客觀解釋這種問題上爭執不下,而是肯定每一種解釋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進而力圖根據自己的狀況建構出自己的馬克思恩格斯。我把這種趨勢稱為西方“馬克思學”的“解釋學轉向”。
這種“解釋學轉向”何以會出現呢?
一方面,這和作為思想史研究的西方“馬克思學”進入后成熟階段有關。西方“馬克思學”在六七十年代的繁榮發展與大量馬克思恩格斯新手稿新文獻的發現、發表密切相關。新手稿、新文獻特別是那些能夠影響人們對馬克思恩格斯既有認識和定位的新手稿、新文獻的發現、發表,都會極大地推動西方“馬克思學”的發展,激勵新觀點的出現并引發激烈爭論。60年代《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新手稿的發現,70年代《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英譯本出版、《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的公開,都曾引發很大的學術轟動。進入80年代以后,馬克思恩格斯新手稿、新文獻的發現、發表的高峰期已經結束,雖然不時仍有新的發現、發表,但學術價值都相對次要,既激發不出新觀點,也改變不了既有觀點。西方“馬克思學”的發展由此失去了重要的推動力量。同時,經過前幾十年的不斷積累,西方“馬克思學”形成了大量學術共識,需要爭論的學術問題日益減少,而那些剩余下來可以繼續爭論的問題基本上都是些無解的難題,只能任其保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未定狀態。也就是說,隨著發動學術爭論的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的消退,西方“馬克思學”學者的注意力開始從客觀的對象轉向主觀的自我,從“我注六經”轉變為“六經注我”。
另一方面,這也與解釋學、后現代主義思潮等對西方“馬克思學”的方法論影響有關。伽達默爾和利科的解釋學與后現代主義思潮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哲學潮流,但兩者都強調個人主體的作用,具有相對主義傾向,更重要的是,都是從七八十年代開始流行的。因此,它們就以一種極其偶然的方式共同對西方“馬克思學”方法論變遷產生了影響。作為“解釋學轉向”的親歷者,卡弗曾做過如下評論:“伽達默爾和利科的解釋學、德里達的解構,以及劍橋的‘情境主義者’,都極大地改變了對文獻的理解方式,也同時改變了對作者意圖、語言本身的地位和重要性以及書寫者本人角色的看法等。對馬克思的闡釋工作有必要與這種后現代思想時代保持同步。”*卡弗:《政治性寫作:后現代視野中的馬克思形象》,張秀琴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冷戰結束。西方“馬克思學”在西方學院中急劇邊緣化,學術共同體內部出現了明顯的離心、渙散和解體趨勢。在這種情況下,80年代還如草蛇灰線一般的“解釋學轉向”就以一種清晰可辨的方式呈現出來了。在當代,西方“馬克思學”的“解釋學轉向”有四個重要表征:第一是疑古主義、挑戰定論。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他和恩格斯創作完成《德意志意識形態》“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破舊立新,“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見解的對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頁。。但是20世紀70年來以來,一直有西方“馬克思學”學者力圖證明《德意志意識形態》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創作的著作,而是他們編輯的論文集,其目的就是要通過改變《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性質地位否定唯物史觀的真實存在。前述英國學者卡弗幾十年來一直對此耿耿于懷,2014年,他與自己的學生合著《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編輯的政治史》和《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費爾巴哈章〉的呈現與分析》,*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euerbach chapt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再次挑戰定論。但有意思的是,其觀點連其學生也未能完全贊同。在2016年的《卡爾·馬克思:偉大與幻象》中,英國歷史學家瓊斯還是希望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的創造,而是恩格斯和蘇俄馬克思主義者的發明。*Gareth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Milton Keynes: Allen Lane, 2016.第二是文本編輯崇拜。文本編輯是服從服務于思想闡釋的。但始終有西方學者不愿或者不能擺正文本編輯與思想闡釋的關系,沉迷于文本編輯,期待能夠找到真實呈現馬克思恩格斯文本創作過程的奇技淫巧,一勞永逸地解決他們心目中的思想闡釋問題。第三是自我翻新。近年來,西方學界出現了不少新的研究流派,如“開放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閱讀”等。*參見孔智鍵:《價值形式批判、否定性革命主體與后共產主義研究——“開放馬克思主義”的起源與當代發展》,《天津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李乾坤:《“新馬克思閱讀”運動: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的一種新綱領的探索》,《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仔細觀察我們卻不難發現,學者還是原來的學者,觀點也還是過去的觀點,但他們卻借助新由頭實現了自我翻新,通過新瓶裝舊酒實現了再上市。第四是“自由”嫁接。所謂“自由”嫁接就是以主觀主義的方式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觀點與某種思想流派嫁接起來,“創造”新的思想“品種”。在這個方面,以過程神學嫁接馬克思思想“發明”出來的“有機馬克思主義”最能說明問題。
應當怎樣看待這種“解釋學轉向”呢?首先,它的出現表明經過100多年的曲折發展,西方“馬克思學”已經在充分成熟之后進入了相對停滯時期,在可見的未來難以再出現新的高潮、大的突破。其次,它的出現意味著中國學術界已經到了該打破西方“馬克思學”神話的時候了!關于西方“馬克思學”,國內學界一直存在兩種“神話”:一是認為西方“馬克思學”是真正的“科學”,二是認為西方“馬克思學”的研究水平高于蘇聯東歐以及我國。現在,這兩個“神話”都已然破滅了。最后,它的出現提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界應當勇于抓住歷史機遇、承擔歷史使命,為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新的典范轉移做好準備。馬克思恩格斯是西方的,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中心未必只能在西方。90多年前,蘇俄通過創辦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從第二國際手中奪取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中心地位和話語權。今天,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依舊處于低潮,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國際話語權正在等待新的典范轉移。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界必須做好準備,承擔自己的歷史使命,把中國建設成為21世紀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