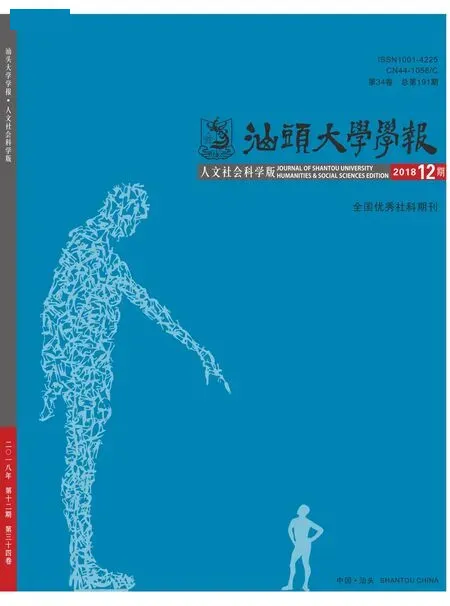歷史記憶的書寫與契約精神的重建
——評郭小東僑批題材小說《銅缽盂——僑批局演義》
曹亞明
(韓山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廣東 潮州 521041)
郭小東多年來以知青文學創作與評論活躍于當代文壇,集文學批評家、小說家、高等院校學科帶頭人多重身份于一身。他不僅以早期的《諸神合唱》與《中國知青部落》等著作奠定其生命記憶與激情體驗,還編著了《中國知青文學史稿》,被洪子誠先生稱為“國內第一部視野廣闊、資料詳實、論述系統的知青文學史著”。2015年1月18日,廣東省首家以當代作家命名的“郭小東文學館”在廣州揭幕,出版了22卷本的《郭小東文集》。但是,郭小東并沒有止步于已有的創作成就,而是借筆下文字重返生于斯長于斯的潮汕平原,創作完成了32萬字的長篇小說《銅缽盂——僑批局演義》。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文壇老炮”終于將隱藏多年的家族傳奇和僑批記憶鉤沉于近代歷史風云中,也使得2015年成為他創作道路和人生道路上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2016年1月13日,長篇小說《銅缽盂——僑批局演義》首發儀式在汕頭舉行。作為郭氏家族的傳人,郭小東有對故土的熾熱情感,又有作家的才情和評論家敏銳的洞察力。然而,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者,他也深諳潮汕文學在中國文學版圖中的邊緣處境,何以在沉潛多年之后,終于動筆寫這部以潮汕平原為背景的小說呢?自五四以來,鄉土寫作一直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題材。可是,《銅缽盂》這部小說與當代文壇其他鄉土題材小說寫作相比,其獨特性何在?這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汾陽世家的家族傳奇與歷史記憶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曹植《箜篌引》
首先,《銅缽盂》這部長篇小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作品不僅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礎之上,還是以郭氏家族傳人口述史的方式復現潮汕民間生活形態,記錄了潮汕地區一個與僑批業密切相關的大家族的興衰歷程。“僑批”是自清代以來在廣東、福建、海南、廣西沿海僑鄉出現的一種民間文書,它是由海外華僑華人通過民間渠道寄給家鄉親人的僑匯憑證和書信的結合體。①僑批涉及僑居地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緬甸、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國家。萌芽于明代的僑批銀信,在清末民初達至鼎盛,其勢頭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直至1976年納入銀行系統,僑批才退出歷史舞臺。由于年代久遠,大量僑批都沒能完好保存下來,此前多收藏于民間,直到21世紀之后,廣東和福建等僑鄉才開始大規模地征集僑批。饒宗頤先生認為,僑批可與徽州學的“契據”“契約”和晉商的“錢莊”“票號”媲美。其實,僑批遠比徽州契約更有研究價值,因為僑批除了金融屬性外,還具有很強的文化屬性。僑批不僅是僑匯憑證,還附有情真意切的家書,文字內容真實豐富,能夠“原汁原味”地反映出大至國家、海外,小至社會“細胞”——眾多家庭的具體狀況。通過對僑批文獻的整理和研讀,我們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清末民初中西移民文化的交融和發展歷程。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僑批所記錄的文字內容蘊藏著豐富的情感,尤其是在文化夾縫中生存的移民群體文化身份迷失的苦痛,僑民們面對中西方文化沖擊時內心深處的矛盾和沖突,這都是其他文獻所無法記錄的歷史細節和心靈曲線。多年來,僑批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2013年,“僑批檔案”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僑批文化才開始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尤其是郭小東這樣的知名作家開始涉獵僑批題材的創作,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對于僑批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相較于郭小東此前的知青文學創作,這部小說植根于潮汕平原豐厚肥沃的鄉土,具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濃郁的家族紀實色彩,展現出更為厚重的史學價值和更為深厚的人文內涵。既以史家筆法鉤沉歷史,又以虛構筆法書寫傳奇,是郭小東這部小說的重要特色之一。正如郭小東所說,虛構和想象,永遠是小說包括家族小說的題中之義。作者采取了傳記小說的通常方法,真人偽事,或偽人真事,打破了傳統家族小說、歷史小說的邊界,以戊戌變法、丁未起義、辛亥革命等歷史大事件為底色,讓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于右任、胡適、顧維鈞等清末民初的文化大家和政治人物躍然紙上。而作者則退隱到背后,依據史料記載的內容和口述記憶跳躍式地追溯歷史的真實。在老屋光德里的明式家具面條柜里,郭小東極為偶然地發現暗格中藏著一個精美絕倫的木匣。這個木匣是郭小東曾祖父郭信臣留下的唯一遺物,歷經65年的飄零與等待,承載著郭氏家族風云跌宕的歷史記憶,竟與其新作《銅缽盂———僑批局演義》同時面世,使得這部長篇小說不僅具有強烈的紀實特征,也增添了幾分飄逸靈動的傳奇色彩和神秘意味。《銅缽盂》這部小說以銅缽盂這個村莊為主背景,呈現了清末民初郭、馬、周、鄭四大家族在百年中國革命史中的嬗變史,通過潮汕地區銅缽盂這個小村莊的興衰史,描述了歷經百年滄桑的潮汕僑批文化及僑批演變史。潮汕歷來屬于族群式社會,銅缽盂就是一個同宗共姓的家族,它有傳承1,800多年的族譜。郭氏家族的始祖汾陽王郭子儀為唐代三朝元老,其嫡系的家居門匾均鑿有“汾陽世家”字樣,有著顯赫的家世和鐘鼎貴胄的文史淵源,這樣的村莊遍布潮汕大地。因此,郭氏家族所居住的銅缽盂,便是潮汕村莊的縮影。因此,以郭氏家族的歷史記憶為藍本,便可以想象出近代潮汕廣袤的鄉村世界圖景。
“文化記憶”理論的創立者揚·阿斯曼曾經說,20世紀是個苦難深重的世紀,太多的東西遭到了毀滅。觸及我們靈魂深處的是,那些曾經經歷人類歷史上最慘絕人寰的罪行和災難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來越少了。對于集體記憶而言,40年意味著一個時代的門檻,換句話說,活生生的記憶面臨消失的危險,原有的文化記憶形式受到了挑戰。這也就是為何近年來以“記憶”與“回憶”為題的研究風氣變得如此方興未艾。[1]《銅缽盂》這部作品中很多章節都是圍繞著關于銅缽盂的各種“記憶”展開的。作品中前半部分重點敘述的政治事件就是爆發于1907年5月的“黃岡起義”。“黃岡起義”是孫中山第一次派遣成批海外留學生回來發動的起義,也是中國同盟會成立后在廣東境內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顯然,黃岡起義在革命歷史上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也是潮汕近代史和中國華僑史上的光輝一頁。與其他歷史題材作品不同的是,郭小東主要通過銅缽盂郭氏家族僑批行的百年歷史展開敘述,通過批腳馬伯良的童年記憶從另一個視角重新審視這一歷史事件,渲染了黃岡起事遺留的惆悵與凄惶的情緒。關于十萬批銀和少年批腳的童年記憶,終生在馬伯心頭牽繞糾纏,成為了他一生的噩夢。馬伯良七歲時因親眼目睹校場上處決亂黨一幕,造成了他一生都無法釋懷的精神創傷。在光德里馬伯良居住的那間狹破的八尺里,進行口述訪談的郭同志如聽癡人說夢,完全被馬伯的夢囈帶進了一個又一個驚人的夢魘之中。“在汕頭開埠以來的幾百年間這樣的記憶現象舉不勝舉。不過,記憶的錯亂總是有深遠叵測的原因,歷史也因此變得詭異。”[2]65其實,作品中的“郭同志”實際上就是作者的分身,作為客觀的研究者,他本應有著更為深刻的洞察與理性的判斷,可是卻依然無法回避歷史的困擾。“馬伯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水客批腳的歷史。現在,郭同志就在這部活的歷史周邊,可他既走不進去,又難以轉身而去,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惶惑與迷惘。”[2]228-229這部小說的敘述者除了馬伯良之外,還有作者郭小東90多歲高齡的母親馬燕惠女士。通過母親和馬伯等人殘存的童年記憶,郭小東在小說中所要還原的就是潮汕這座城的歷史記憶。還原“那種嚴酷與溫情的人性融合,農耕與洋風共榮的日常生活”,追懷今日人們追之莫及的“風雅”,并力圖由此確定“潮汕族群文化生存”第一次出場的意義。
正如小說扉頁所寫的:“《銅缽盂》是一種與歷史見證和文化記憶共存的族群生存范式,它將中國從古典生存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程,呈現為一種讓人懷戀的潮汕文化風情,讓處于中國現代社會之初的潮汕文化風情,處于一種新的形式中,而這種形式的獨特,恰在于它的極端貢獻與它的衰亡過程同時進行,它所連帶的雙重生活方式,從中國古老生存觀念本身的復雜和現代需求中產生,于是《銅缽盂》生成了與這種文化風情相關聯、相映襯的主題和形式。”[2]扉頁作品中講述的故事時間跨度極大,從晚清一直寫到現代,作者對于這一區域文化的發掘與梳理,對于這片土地上生的堅強與死的掙扎的生命體驗,足以作為一部藝術化的潮汕近現代史,讓讀者融入到潮汕人的生活氛圍中,去了解嶺南文化發展過程的特殊性。因此,《銅缽盂》不僅代表著郭小東小說創作的自我超越,同時也預示著嶺南文學已開始具有了屬于自己的創作樣本,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標志性作品。時至今日,郭小東終于走出了熱帶雨林的“知青部落”,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潮汕文化母體,通過汾陽世家的家族傳奇,再現了銅缽盂這個村莊的歷史記憶,并以穿越歷史和連接現實的宏大氣魄,寫出了這部帶有史詩品質的長篇小說。
二、情緒記憶中復活的僑鄉
“打起包袱過暹羅,賺有錢銀多少寄,好返唐山娶老婆……”
——潮汕民謠
張志忠在《郭小東新作〈銅缽盂〉漫評》一文中指出,這部小說著力于潮汕人家及其生存環境的刻鏤,“以復調的方式,橫云斷嶺,把一個個風云變色的歷史場景切割開來,將凝重與飄逸交織在一起,保持了藝術的均衡和張力。”[3]也正是這種“凝重與飄逸交織”的寫法,才把潮汕民間風情與諸多重要歷史事件毫無違和感地銜接起來,用草蛇灰線的筆法來處理缺乏史料證實又無法明確的歷史細節,也更好地對應了作者回首故鄉時的憂傷而又不無焦慮的情緒記憶。因此,《銅缽盂》這部作品最能觸動人心的,其實是流蕩于作品中的各種情緒記憶。
情緒記憶又叫情感記憶,以體驗過的情緒、情感為內容的記憶。當某種情境或事件引起個人強烈或深刻的情緒、情感體驗時,對情境、事件的感知,同由此而引發的情緒、情感結合在一起,都可保持在人的頭腦中。有時經歷的事實已有所遺忘,但激動或沮喪的情緒依然留在記憶中。在這部小說中,“瞽師”和“老舵工”承擔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鏈接整部小說情節和結構的重要線索。潮州歌謠那凄絕的旋律和幽怨的歌詞,寄托了潮汕游子對故鄉的衷情思念和無處訴說的愁緒,作品中常常通過“瞽師”凄絕的彈唱來對映出情緒記憶的波動。翻開長篇小說《銅缽盂》的第一頁,瞽師憂傷的琴聲和穿越歷史的僑批歌謠,就把讀者帶入憂傷而又凄惶的情緒之中。瞽師的唱詞和命運穿插于各個章節之間,而在渡頭撐船的“老舵工”則是許多重要事件的目擊者,作者的很多情緒都是通過瞽師的唱詞和老舵工的心理變化表達出來,他們是歷史的敘述者,又是傳統精神失落的見證者。從第一章到第五章,都是以桃花渡頭瞽師的命運作為開場。而此后的章節中也都有瞽師的身影穿插出現,詩丐詹廷敬的靈魂化身瞽師從煙橋回來,游弋在仁記巷中。通過這樣一種奇特的方式,郭小東巧妙地把民間“無聲的記憶”復現于作品中,既融入作者對故鄉、歷史、國家和鄉土命運的深刻思考,又因燕子尾的傳說、《箜篌引》的傳奇和詹廷敬的絕命詩,而多了幾分古典小說的詩意和空靈。整部小說,便這樣通過不同的人的“情緒記憶”為線索草灰蛇線地貫串起來。作者通過這種特殊的方式與郭氏家族的祖先們對話,也是在為那些在黃岡起義中死去的義士們招魂。正如吳亮所說的,“《銅缽盂》如同一群難以驅逐的幽靈,從這個悲劇式的神奇故事去看,郭小東一個人完成了一種輪回向前的個人、家族以及地方志的重塑。”[4]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通過參與黃岡起義的革命黨人表達了對于這次起義的理性思考。
寫一個小村莊,是郭小東多年的夙愿。但是,祖居光德里的破敗與衰落則是促使郭小東最終把目光投向故鄉的最大動因。多年以后,重返光德里的馬燦漢行走在潮汕平原上,酒紅色馬行走在長長的古驛道,晚秋的風中有一種味道,稻草和干柴燃燒成炊煙的味道。這是一幅游子還鄉的典型圖景,故鄉熟悉的味道在天空中游走、飄飛,粘連起晚秋的村落。老宅光德里是五座“駟馬拖車”一字兒排開的庭院式建筑,又是少有的兼顧西洋古堡風格的潮州傳統民居,其建筑形制可追溯到唐代宋代的合院式格局。在外祖母去世之后日漸荒蕪,其中的馬氏家祠已經坍塌了屋頂,兩旁的駟馬拖車及后庫也已不堪風吹雨打。“荒疏衰草,殘垣斷壁,只是檐前畫梁,石上雕棟,在無奈地傾訴著曾經的繁華與奢靡。那種破敗與衰落,那些深鎖隱沒了的昔日聲氣,似乎連遙遠的回聲也難以捕捉。在遼闊的潮汕平原無數的城市繁華中,隨處可以尋覓到這些飄零于歲月時空中的舊日碎屑,它們像不死的魂靈,借風雨交加的陰晦天氣,以及從山間或海上吹拂而來,穿堂而過的霧靄,正在這些古舊敗落的墻垣中,無目的地游弋。”[2]158“碩士第”在百年間風云際遇,現在淪落為織造文胸的工廠。轟鳴的機器、紛飛的棉絮,和滿屋已然老去的畫梁雕棟纏結而成的氣氛,令人惆悵惶惑。也許,人們真的已經忘卻了這座隱匿在城市中的深宅大院。
光德里的頹敗和鄉村的解體,促使郭小東終于決定要記錄下母親和馬伯這一代人的童年記憶。雷蒙·威廉斯說,所謂文化,就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因此,郭小東想通過僑批史復活近代潮汕鄉村古典化的生存圖景,追憶那代人自然平樸的日常生活方式,以此來對抗歷史的遺忘。潮汕是一座沒有邊界沒有城墻的城,“無數的下山虎、四點金、大夫第、資政第、馬家祠堂、郭氏宗祠、周氏家廟、鄭家碼頭、仁記巷和大鼎元……古街古巷,還有田野、菜園,從山上流下來的清溪,有女孩在溪中洗衣……”[2]1-2當作者再度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仿佛嗅到老屋檐頭石雕的獅子和奔馬在古驛道上撕咬濺血的味道。那些鎦金飾銀的浮雕和梁上的故事,遮掩了多少難以言表、生離死別的衷情,以及道上慘酷的殺戮。作品中的語言既保留了潮汕方言中的語言特色,又有意識地運用馬伯追憶過去時那種半文不白的表述方式,切合那個年份人們的說話習慣和書面語言方式,引誘讀者穿越時空跟隨作者回到1907年的潮汕,并將記憶中的故鄉呈現給世界。“將潮汕第一次文學地敞現它全部的憂傷、焦慮和美麗的鄉愁,把銅缽盂這個郵票大的地方,把潮汕郵寄給世界……”[2]8
“在二十世紀以降的中國文學史上,鄉土與現代的狹路相逢衍生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立場:在魯迅那里我們看到現代精英對鄉土的俯瞰和悲涼,他悲哀的是無法盡快將鄉土帶入“現代”;在沈從文處我們則看到一種將鄉土審美化、浪漫化以對抗“現代”的立場。這兩種文化立場恐怕都無法被當代焦慮的精神主體所分享”[5]。在鄉土與現代相逢的狹路上,郭小東放棄了精英化的敘述姿態,選擇口述歷史的方式記錄民間生活的瑣碎記憶。其實,通過這種方式記錄下來的,不只是個體的記憶,而是由口述者的回憶交織而成的潮汕先民的集體記憶。“就中國社會而言,貫通個體記憶與社會記憶并由此重建社會記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任務之一。我們需要將中國社會獨特的文明歷史和文明的轉型與普通人民的生活經歷和常識常理建立起聯系。換言之,將文明落實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卑微瑣碎的經歷和記憶便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可以成為宏大敘事的有機部分。”[6]正是作家和學者的雙重身份,決定了這部作品感性與理性相融合的特色,超越了普通的家族小說,使個體的記憶轉化為宏大敘事成為可能。在回歸故土的旅程中,郭小東背負著中國傳統文人的沉重學統和憂患精神。所以,與純粹的作家相比,他的寫作更多指向中國文化傳統的重建,字里行間都滲透著焦慮與彷徨的情緒記憶。
郭小東這樣訴說自己面對故鄉的種種情緒:“我常去遙遠的地方,那些地方與潮汕全然不同。不僅僅是指風物,而是說人。人在另外的世界中,在別樣的文明中,在遠離潮汕的隔閡中,讓我更深刻地看到自己的內心,內心的惶惑及恐慌產生的對自我的排斥與憤恨,以至于無限的憂傷。因之對潮汕產生了一種切近的依戀,這種依戀隨著年輕時的疏忽、中年時的回眸、老年時的至切,而漸漸灌滿我的眼睛,成為我眼力所及的全部。”[2]7作為潮汕平原上成長起來的作家和學者,作為郭氏家族的傳人,郭小東通過口述史記錄下來的“憂傷”情緒,也夾雜著從原生家庭中傳承下來的精神創傷。陳劍暉說,《銅缽盂》“是一部家族小說,更是一次憂傷與美麗的精神之旅。它用美麗的文字傳達憂傷,既是指時代的憂傷,家族的憂傷,歷史記憶的憂傷,也指植根于作家內心深處的憂傷。”[4]這樣的情緒記憶,在潮州歌冊中代代流傳,在僑批泛黃的文字中隱約閃現,帶領讀者穿越時空,回到那個已然消逝的過去的村莊,看到了百年前的光德里,看到那些活在清朝的老人和孩子……
三、契約精神的堅守與文化記憶的重構
“我期待復活清末明初的生活圖景以及那時人們的精神向度,一種似乎與政治有關又無關的道德倫理。我在先輩先賢的人生細節中,一點一點地過濾這種精神。為了一件死批錯批,一件沒有地址的批封銀信,而終其一生地信守與尋找的精神,照亮了許多俗世幽暗的角落。”
——《銅缽盂·后記》
郭小東說,《銅缽盂》這部長篇小說最初的寫作緣起是僑批史。《銅缽盂》不僅僅局限于僑批局的歷史演變,而是以中國近現代史為背景,把僑批與宏大的歷史結合起來寫,通過一封封的僑批把小小的銅缽盂和遼闊的中國及遠在千里之外的南洋緊緊聯系在一起。因此,《銅缽盂》這部小說重點關注的不是財富的創造與流通,而在于潮汕人對財富的態度,是僑批從誕生之日到消失的幾百年中,所體現的一種有形或無形的契約精神。“在潮汕平原,村莊和僑批,似乎有一種天然的聯系。從什么時候開始,這種聯系便有著生死的至切。一封小小的銀信,有時便決定村莊和人的命運,幾個世紀的離亂故事……”[2]317可以說,每一封僑批,都是一部長篇小說,都承載著一個家庭的辛酸家史。水客是經常往來于國內外、專為僑胞代送僑批或物件的人,是一種以收攬和解付批款為主的特殊職業。批腳則相當于僑批投遞員的角色,在當時金融郵政機構尚未建立的時期,海外僑胞與家鄉親人的通訊、匯款(僑批)就全靠這些“批腳”來往傳遞。這種遙遠信托形成的依賴,雖無血緣,卻勝于血緣的承諾。“以鄉誼、誠信、口諾等精神性保約,化合而行的郵政交通,是僑批最豐富最任性最具人格魅力的信托結晶。它成為潮汕這座城邦之成為現代城市的精神保證。”2[5]
僑批背后承載的是契約精神與口諾,也就是說寄批人純粹通過口頭拜托水客以及批腳,全無憑證而承諾與囑托暢行天下,是傳統貴族精神的一種延續。作品中幾個重大事件都是圍繞著對“契約精神”的堅守而展開。“僑批是一種兌換憑證,一種契約精神,還有一種是口諾的,即純粹是口頭拜托,全無憑證而靠承諾與囑托暢行天下。這就是僑批從誕生之日到消失的幾百年中,所體現的一種有形或無形的契約精神。”[2]320但是這種契約精神背后,是一種牢固的文化支撐,這種支撐在何時崩潰?又在何時成為一種夢想?這實在是令人沉思的啟應。作者擔憂這部小說無法承擔這樣的啟應,但是他塑造的一系列復雜的人物形象,已經完整地表達了他的思考,現實與歷史的沖突,新舊文明與倫理道德的沖突,都在這些人物身上展現出來。他試圖去讀懂他們靈魂的每一條皺紋,每一次波動。
正如黃國欽所說的,郭小東筆下的郭仁卿、周季禮、林達、郭信臣、馬燦漢、馬文榮、馬伯良……他們的言談舉止和行為規范,他們的豁達、慷慨、大義、信諾,完完全全是源遠流長的潮汕文化和代代相傳的潮汕人文精神所塑造的潮汕民系的人格凸現。不管是高宅大戶,還是升斗小民,他們都表里如一,始終不渝地恪守著一種叫做誠信守信的人生準則。[7]作品中有幾個與僑批相關的情節被濃墨重彩地書寫,圍繞這些情節又成功地刻畫出郭仁卿、郭信臣、馬燦漢、周季禮等人物形象。作品中描寫的第一個重要事件便是1896年郭仁卿豪氣捐款十萬批銀一事。郭仁卿在惠如樓會晤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在俠肝義膽的譚嗣同救國言論的激發下,將“十萬批銀”一擲而出,從此以后便隱姓埋名遠走他鄉。郭仁卿不僅支持過戊戌變法,也支持過孫中山的丁未起義,還是中國同盟會最早的會員。他的兒子郭信臣也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潮商,在聽了馬燦漢的一席談話之后,就決然捐助50萬銀圓和15座別墅給國軍460師充作軍餉,保證退到潮汕地區的幾千士兵免遭劫持到臺灣的命運,也為下一步馬燦漢的策反行動給予了有力支持。潮汕平原無數的“下山虎”“駟馬拖車”“四點金”以及深刻的門樓,門樓上的名人匾額背后,沉淀著的是先人們的血淚,那些夕陽中的掮客和批腳們的身影。來自遙遠歲月皇親國戚的精神遺存,又有著天然的忤逆皇權管約的血性,兩者非常矛盾地交織著,成為郭氏性格中不羈的秉性。”[8]
《銅缽盂》不是單一性的家族敘事小說,我們會從閱讀中發現潮汕文化的某些神秘性——既傳統保守又包容開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為了能夠生存,無論是在貧瘠的土地上耕耘,還是漂洋過海去淘金,他們都相互扶持堅韌前進,始終都堅守著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一壺功夫茶,一口潮汕話,一種濃濃的家庭觀念,一腔剪不斷的鄉土眷戀,《銅缽盂》既寫出了潮汕人的堅強人格,也寫出了潮汕文化的獨特風韻。奧斯曼說:“文化記憶是一個集體概念,它指所有通過一個社會的互動框架指導行為和經驗的知識,都是在反復進行的社會實踐中一代代地獲得的知識。”[9]文化記憶并不是單一地附著在文本上,而是還可以附著在儀式、面具、圖像、韻律、樂曲、飲食、空間和地點、服飾裝扮等之上,這些形式以更密集的方式出現在了群體對自我認知進行現時化和確認時所舉行的儀式慶典中。
《銅缽盂》這部作品中記錄了不少潮汕當地最典型的儀式化的民間活動。如第二十五章郭信臣妻子連淑發的出殯儀式。據說買斷了銅缽盂附近十幾個鄉里“銀紙行”所有的香燭紙錢。送葬的隊伍排出十余里,沿路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紅色炮仗紙屑。繁復瑣碎的出殯大禮從凌晨5時持續到傍晚落山。接下來還有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300位僧人在大夫堂天井里日夜誦經。銅缽盂仁記巷的八座大厝里擺了100桌流水席,每日三餐請周圍四鄉八里的人來吃喝。這次出殯儀式是銅缽盂有歷史記載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除此之外,這部小說中還穿插了不少潮汕地區特有的出花園、祭祀、立牌坊等重要儀式。見過潮汕人營老爺時的熱鬧場面和日常的各種祭拜儀式的話,應該能夠感受到潮汕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其實,各種儀式的定期舉辦在時間和空間上保證了知識的傳達和群體的聚合性,并由此保證了文化意義上的認同的再生產。近年來,潮州復興青龍古廟的千香林堪稱一絕,受到廣泛關注。作為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青龍廟會,成為了凝聚全世界潮人潮心的重要紐帶,也是海外潮人尋根的重要依托。正是這些民間儀式保留了潮汕文化中最為久遠的文化記憶,甚至是日常生活中咸菜的腌制和潮汕生腌的制作,作者也都描述得極為細致,顯然來自于個人的生存體驗和童年記憶。細細品味這些文字,不僅能夠感受到作者作為潮汕人的無比自豪,同時更能令人感受到潮汕文化那份歷史的厚重感。
《銅缽盂》這部小說區別于其他地域文學的最大特色,也區別于其他潮汕鄉土題材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作者在作品中梳理與思考了有關僑批與家族的關系,不僅花了很多筆墨表現僑批所體現的契約精神和潮汕文化的傳承與積淀,還融入了作者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鄉村世界的深刻思考。這種思考是深刻的,同時又是傷感的,充滿著對上帝啟應的回眸。“這座完工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古宅老屋,如今淹沒在仁記巷僻靜荒涼的群樓之中,從天空鳥瞰,活像城市石屎森林中一直蟄伏已久的灰色老龜。它不死,伏在那里,想告訴人們一些老去的故事。它又似一封遺失多年的批封,抑或是只有姓名卻遺失了地址,無法發出的死封。它的名字,叫銅缽盂。”[2]316郭氏家族的痛史也不再只是關涉到個體的悲傷或是家族的衰敗,而是與現實中鄉土的撕裂密切相關的文化記憶的創傷,作者想要表達的其實是普遍的人文精神失落的悲傷。
總之,通過《銅缽盂》這部作品的寫作,潮汕之子郭小東完成了一次深情款款的精神返鄉之旅,也實現了對于鄉土歷史的記憶重構。而是否能通過《銅缽盂》的記憶書寫來對抗遺忘,在潮汕乃至整個中國復活“清末民初的生活圖景以及那時人們的精神向度”,復活那種“似乎與政治有關又無關的道德倫理”[2]320,從作品中彌漫的憂傷而惶惑的情緒記憶中,我們能感受到作者持著并不樂觀的態度。當代作家究竟是否能通過鄉土記憶的書寫來呼喚傳統文化精神的重建,尤其是當代社會最為缺乏的契約精神的重建,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筆者一直在想,《銅缽盂》這般震撼人心的記憶書寫,是祭奠,是招魂,還是絕望中的徒然掙扎?也許,“銅缽盂”這封遺失多年的僑批,終有一天,將穿越鄉村和都市,穿越海上絲綢之路,穿越歷史的迷霧和記憶的深淵,送達收批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