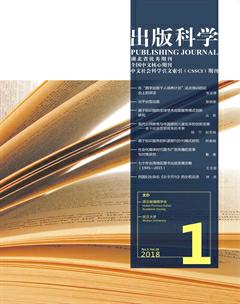網絡文學敘事圈的動因、過程與敘事制度
王一鳴
[摘 要] 當前網絡文學研究過分關注其外圍問題而忽視其內在發生機制問題,將數字敘事理論引入網絡文學研究領域,試圖彌補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基于圈內人視角從網絡文學敘事圈的動因、過程和制度三個層面剖析其生產、閱讀、互動等內在機制,以回答網絡文學“為何讀、為何寫”、“如何讀、如何寫”以及“因何能持續讀、持續寫”幾個基本問題。
[關鍵詞] 數字敘事 數字敘事圈 網絡文學 局內人知識
[中圖分類號] G2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8) 01-0090-06
[Abstract] Current researches on Internet literature pay more attentions to its external issues than its internal issue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digital storytelling theory to the Internet literature area, attempt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alyze the agent, process and infra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Internet literature storytelling circle from the insiders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answer the key questions such as “why they read and write”“how they read and write” and “why they sustain to read and write”.
[Key words] Digital storytelling Digital storytelling circle Internet literature Insider knowledge
網絡文學,這一新世紀文學的孽子,從誕生之日起就在產業界和學術界呈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觀。從1998年痞子蔡開啟中國網絡文學元年,到如今整體市場規模超過互聯網期刊、電子圖書、數字報紙的總和[1],網絡文學產業用輝煌的商業戰績無可辯駁地彰顯了其歷史在場性。反觀學術界,從世紀之初的不屑一顧到不愿正視,再到如今不得不正視,崇尚者將其捧上神壇,奉為“解放平民話語權”的文學救星,貶抑者斥之為商業文學、“快餐文學”、“三俗”文學。即便自詡客觀者,亦先入為主地站在道德高地妄圖“救贖”“引導”,殊不知諸如“文學性”“精神取向”“商業模式”等學術難題根本不在網絡文學原住民的思慮范圍之內。網絡文學生產和消費者們才不在乎他們寫的、看的是不是“文學”。在他們眼中,講好一個故事,并借助技術便利將它擴散到更多同好者的視野中,就是數字時代賦予他們的全部意義。然而從產業和國家的層面,網絡文學的意義顯然不止于此。習近平多次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其所指“中國故事”固然譬喻精當、旨意遙深,遠非通常意義上的文學性故事,而是涉及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傳播體系。但是,中國網絡文學近年來在全球各國讀者群體中引發的閱讀狂潮[2],卻以一種讓國人匪夷所思的方式確鑿地證明了自己的時代價值——僅就傳播力來看,網絡文學儼然已成為中國故事乃至中國文化海外輸出的旗幟和標桿。
因此,對待這樣一個復雜的研究對象,若是仍然沿襲一貫的研究范式,從理論到理論,基于“現狀、問題、對策”的邏輯研究什么網絡文學的概念、發展階段、文學性、商業模式、內容引導、版權保護等,終將只是隔靴搔癢不得要旨。惜乎現有的網絡文學研究大率如此,過分關注網絡文學的外圍問題,而對涉及其發生機理的內部問題不明就里——畢竟大多國內網絡文學研究者從未讀完一本貨真價實的網絡小說。由此,“兩個世界”出現了:作為網絡文學“圈內人”的讀者和寫手清楚真相而不具備“學術合法性”;作為網絡文學“圈外人”的研究者掌握學術工具,卻不具備“局內人知識”。筆者試圖在文中回應當前網絡文學研究的缺陷,溝通兩個世界的對話,從數字敘事圈的視角摒棄蕪雜的外圍問題不談,專注于網絡文學的內在發生機制。同時,堅持實踐原則,立足“局內人知識”,以寫手訪談問卷和讀者論壇發帖為一手數據來源,探明“為何讀、為何寫”“如何讀、如何寫”以及“因何能持續讀、持續寫”等一系列基本問題。
1 數字敘事圈與網絡文學敘事圈
數字敘事(digital storytelling)從詞源上講,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用數字化的方式講故事”,它的初衷是“讓人人借助數字技術便利地講故事”。丹納·阿奇利(Dana Atchley)在中東發起旨在保障言論自由的“數字敘事運動”,使得這一概念被世人知曉。1990年代,喬·蘭伯特(Joe Lambert)建立了全球數字敘事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Storytelling),數字敘事聲名漸起。新世紀之初,數字敘事引入國內,在教育領域大放異彩。如今,數字敘事已在電影、游戲、超文本小說等領域遍地開花。無論是美國電影還是日本動漫、韓國游戲,無不以故事“文本”為藍本,而網絡文學正是源源不斷制造這種文本的龐大機器。
數字敘事圈(digital storytelling circle)是在數字敘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概念,其概念首次出現在蘭伯特所著《數字敘事》(Digital Storytelling)一書中:在數字敘事運動中,個人故事的生產和交流發生在一個名為“故事圈”(story circle)的研討會中[3]。 2015年,英國學者威爾瑪·克拉克(Wilma Clark)撰文指出:我們將PCSF預科學校這樣復雜的機構環境中的數字敘事圈概化為敘事動因(agent)、敘事過程(process)、敘事制度(infrastructural conditions)等因素,它們使得敘事持續發生并通過交換和互動而得到認可[4] 。endprint
根據這一主張,網絡文學敘事圈就是基于對網絡文學的共同興趣,由以上3大組件構成的圈子或曰系統。其中,敘事動因是系統運作的直接推動力,包括網絡文學寫手的寫作動機和網絡文學讀者的閱讀動機,即“為何讀、為何寫”;敘事過程是系統運作的具體呈現形態和方式,包括讀者的閱讀(消費)方式、寫手的創作(連載)方式以及二者之間的互動方式,即“如何讀、如何寫”;敘事制度是系統運行的制度設計和基礎保障,包括各大文學網站的作者福利體系、作品生產和推送機制以及作者、讀者、編輯之間利益博弈的各種“明規則”和“潛規則”,即“因何能持續讀、持續寫”。網絡文學敘事圈的結構詳見圖1,從中可清晰地透視網絡文學的內在發生機制,探明不為圈外人所知的網絡文學真相。
2 網絡文學敘事動因
社會公眾和研究者早已對網絡文學產業的火爆景象習以為常,但是對于網絡文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即網絡文學的敘事動因或者說讀者的閱讀動機和寫手的寫作動機問題,研究者或是認為其不成為問題不屑回答,或是主觀臆斷想當然地將其簡單歸結為網絡文學是商業文學的代表,迎合了讀者口味,或是持批判態度歸咎于國民文學審美水平低下。而真正有發言權的網絡文學原住民——讀者和寫手的聲音卻很少被學術界聽到。為此,筆者通過電話、郵件方式對15位一線網絡文學寫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訪談,同時廣泛調研各大文學網站、龍的天空(國內最大的網文論壇)、知乎、豆瓣、百度貼吧等網絡文獻,力圖從圈內人視角將這些“民間理論家”的“局內人知識”[5]呈現出來(見表1)。
任何一個寫手本身必然也是資深的網絡小說讀者,其觀點毫無疑問要比甚少閱讀甚至從未閱讀網絡小說的學院派理論家更能貼近實際(盡管未必更加科學)。以表1中訪談對象的局內人知識為藍本,針對閱讀動機和寫作動機問題,筆者嘗試將這些民間的、口語化的表述用學術語言加以概括,賦予民間理論以“學術合法性”[8]。
先看網絡文學讀者的閱讀動機問題。從訪談結果來看,喜愛閱讀的原因五花八門,但基本可歸為以下三種。
(1)翻轉現實的強烈愿望是讀者閱讀動機之一。面對中國的階層固化問題,“努力工作不一定出人頭地”[9]、“知識不一定改變命運”[10],因此許多處在社會中下階層的年青一代面臨著“上升無門”和社會壓力日增的局面。他們亟需跳出生活的漩渦、沖破現實的牢籠。網絡文學恰逢其時,以其虛幻架空的故事設定和“扮豬吃老虎”“屌絲逆襲”的套路給予讀者超強的代入感。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滿足的欲望透過小說主角 “奧特曼打小怪獸”式的暢爽體驗得到實現。原先處在社會金字塔底層的人群在這個過程中一躍而成頂尖階層,不盡如人意的現實世界在《我欲封天》《完美世界》面前兜底翻轉。
(2)消費主義的娛樂需求是讀者閱讀動機之二。法蘭克福學派半個多世紀前對“文化工業”的批判套用到現代網絡文學頭上,絲毫沒有違和感。網絡文學本就是消費主義和泛娛樂化的產物,這一點毋庸諱言。然而這并不妨礙其成為廣受熱捧的文學新樣式,草根創作、草根消費。正如知乎網友說的:“看書(網絡小說)是種消遣性的娛樂活動,并不以學習提高為目的。所以能多娛樂感官,就怎么來。這就像一個超級大排檔,消費者只是想過來吃那種多放味精和香精的便宜小吃,你突然在里面開一個齋菜檔口,誰愿意吃你的?”[11]可見,網絡文學讀者對自己的娛樂化需求具有充分的自覺意識,反而對學院派理論家的精英主義批判態度嗤之以鼻。毋庸置疑,讀者基于消費主義的娛樂需求而選擇網絡文學確乎是其一大閱讀動機。
(3)反宏大敘事背景下的互動交流心理是讀者閱讀動機之三。眾所周知,對宏大敘事進行解構祛魅是后現代主義的貢獻之一。數字敘事運動發起的初衷便是以反宏大敘事的姿態,促進普羅大眾講述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故事。網絡文學作為數字敘事的一種,同樣如此。如果說傳統時代金庸的武俠作品還間或透露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宏大敘事情懷,那么網絡小說基本上只關注個體的自由表達和傳遞交流。正如一位自稱“憤怒的香蕉”的網文寫手所言:“寫網文很多年,雖然在去到魯院(魯迅文學院)的時候,我堅持文學并無傳統和網絡的區分,但事實上,確實是有的。我以前定義文學。習慣性這樣說:傳統文學側重的是對自我精神的挖掘和思辨,網絡文學側重的是傳遞和交流。”[12]確實如此,網絡小說敘事風格的平民性和敘事文本的開放性,讓讀者和作者的身份界限變得模糊。讀者通過書評、打賞、催更等一系列互動交流活動獲得了極大的存在感和參與感,因而是強調主旨宏闊的封閉式傳統文學所無法比擬的。
再看網絡文學寫手的寫作動機問題。從訪談結果來看,寫手們的觀點趨于一致,無外乎興趣和金錢兩方面。結合筆者從事網文寫作的經驗和圈內朋友的敘述,寫手們的寫作動機基本上經歷了一個“興趣—非貨幣認可—興趣—貨幣和非貨幣認可—職業”的演變過程。絕大多數寫手起初是出于對網文閱讀的興趣和愛好而嘗試寫作;當這種嘗試和連載作品得到書友們的喜愛和“非貨幣認可”(在網絡文學作品連載之初,即“上架”[13]前,寫手通常不可能獲得經濟收益),就會刺激寫手繼續“加更”進一步創作,直到作品更新到一定篇幅、積累了更多粉絲并得到網站簽約(貨幣認可),才會發展為持續穩定的創作行為(職業)。在這一過程中,興趣和金錢缺一不可:沒有興趣刺激根本不可能開始寫作行為;沒有金錢維系,興趣也不可能最終發展為職業。這一點與司馬遷“發憤著書”、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不求聞達的傳統創作有根本性區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文學是典型的商業文學。關于網絡文學的閱讀動機和寫作動機,尚有許多其他局內人知識可以借鑒,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3 網絡文學敘事過程
本部分主要圍繞讀者的閱讀(消費)方式、寫手的寫作(連載)方式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方式,探討網絡文學“如何讀、如何寫”的問題。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在敘事過程上的最大不同在于文本的開放性。傳統文學作品通常由作者進行封閉式創作,而網絡文學作品通常采用連載形式,寫手在寫作過程中會廣泛聽取讀者意見,經常調整故事情節和人物設定[14]。從某種程度上說,一部擁有廣泛受眾基礎的網絡文學作品就是寫手和讀者共同創作的結果。因此,網絡文學具有典型的互動敘事(Interactive digital narrative)特點。互動敘事與數字敘事是既相對獨立又不乏重合的概念,盡管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就其內涵達成一致看法,但一般認為互動敘事消弭了創作者和受眾之間的界限,關注創作者、動態敘事系統和由受眾轉化而來的參與者這三者之間的新型關系[15]。引申到網絡文學領域,也可認為網絡文學敘事過程關注的是寫手(創作者)、讀者(參與者)和網絡平臺(動態敘事系統)之間的新型關系。endprint
長期進行網絡文學閱讀或創作的圈內人會清楚地看到這一事實:任何一部成功的網絡小說從開始創作,到長年累月連載,到最終完結,在這一曠日持久的“催更、更新、再催更、再更新”過程中,讀者與作者之間建立起了牢固的情感紐帶。讀者通過書評、投票、收藏、推薦等互動活動極大地影響著寫手的創作行為,并深刻體現在以完本形式呈現的網絡小說作品中。關于互動活動如何具體影響作品本身的例證不勝枚舉,以筆者近期閱讀的“善良的蜜蜂”所寫之《修羅武神》為例,該書從2013年3月29日開始連載,至今仍未完結,總字數達650萬字。作者曾多次在小說中就主角楚楓的后續故事發展征詢讀者意見,并無一例外地按照讀者投票結果設計下一章節情節。這種建立在網絡平臺之上的互動活動共同創造的附加信息,已經成為網絡文學作品的一部分。甚至從更宏觀的視域來看,一部成功的網絡小說永遠不會完結。雖然作為文本的作品本身已經創作完成,但圍繞作品、寫手所構建的敘事空間仍然伴隨著讀者們的后續討論和關注獲得持久的生命力。這也是為什么大神級寫手的“現象級”IP能夠持續引爆受眾注意力的關竅所在。
由此可見,在網絡文學敘事過程中,讀者“讀”的絕不僅僅是作為文本的網絡小說本身,更包含由各種互動活動帶來的情感消費;寫手“寫”的也不僅僅是作品本身,更伴隨著對粉絲社群的維護和對作品、對自身的營銷。網絡文學的敘事過程,就是在上述敘事動因推動下,在下述敘事制度保障下,由寫手、讀者和網絡平臺共同形成的敘事方式和互動關系。
4 網絡文學敘事制度
敘事制度是網絡文學敘事圈賴以運行的制度設計和基礎保障。網絡文學產業常盛未衰、網絡文學作品之所以源源不斷產生,表明網絡文學的生產(創作)、流通(推廣)與消費(閱讀)絕不僅僅是偶發的個體行為,而是有著深刻的內生機制和保障機制。本部分即圍繞網絡文學的生產機制、閱讀機制以及網站推送和保障機制,探討網絡文學“因何能持續讀、持續寫”的問題。
首先,關于網絡文學讀者“因何能持續讀”,這涉及閱讀機制和網站推送機制。在網絡文學圈內,一個基本的業界共識是:當前的網絡文學山頭已經大半被“小白文”[16]和小白讀者攻占。盡管批判網絡文學內容低劣、讀者欣賞水平堪憂的聲音不絕于耳,但為何數量龐大的讀者仍然前仆后繼持續閱讀呢?知乎網友“蘭陵”以民間理論家的立場運用模型完美地回答了這一問題[17](見圖2)。
如圖2所示,網絡文學讀者群體中大部分位居金字塔底層,屬于“欣賞能力長期無法提升的”小白讀者。這部分讀者以不斷成長的學生為來源,一般是初次接觸網絡小說者,對小白文打怪升級的暢爽體驗感到新奇;當基礎層讀者被小白文不斷刺激,獲得快感的閾值提高到一定程度,就會不滿于大部分網絡小說的無腦套路,開始上升為“具有一定欣賞能力的讀者”甚至“高欣賞能力的讀者”或者干脆選擇“棄坑”[18]。然而根據“水池理論”,雖然欣賞能力提高會導致資深讀者不斷流失,但總會有新的小白讀者補充進來。因此從總量上看,網絡文學的讀者群體始終能維持在一個較高的規模水平,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讀者群體及其“持續閱讀”行為得以延續。以上是閱讀機制,再看網站推送機制。由于網絡小說每日更新數量驚人,但文學網站的有效版面有限,而且讀者的單次信息獲取能力亦十分有限,所以網站推送不得不依靠各類排行榜。而排行榜完全以數據說話,注定只有最受市場歡迎的作品(通常是小白文)才能出位。因此按照精英文學標準評定的網文精品被湮沒在這種機制中,廣大網文讀者亦在這一機制下終日被小白文反復轟炸,最終被無腦文“洗腦”,淪為長久的金字塔底層。
其次,關于網絡文學寫手“因何能持續寫”,這涉及生產機制和網站保障機制。先看生產機制,據網易云閱讀發布的《2016網絡文學原創作者生存報告》,網文作者的平均日更字數保持在5000—10000萬字的規模,超過半數的作者每天都會花數小時進行寫作,甚至有近一成作者每天寫作時間長達8小時以上[19]。長時間、高強度的持續寫作是網絡文學文本源源不斷產生的基礎,但比這種個體創作行為更能體現生產機制的是網文界內部的公開秘密:代筆和工作室。據局內人知識:“代筆一事就不用多說了,有名的大神許多都干過,還有不少繼續在找人帶筆,甚至有的還培養了專門的代筆團隊,自己只負責寫大綱和主干,水字數的事情就交給團隊……或者自己享受生活,但同時又能一天更好幾章近萬字”。至于工作室,則更具“組織性”:“但比代筆更毒瘤的是占據了市場中低端的、大量存在的工作室……如同工業流水線一般按照相對固定的套路去完成一部作品,還有分工合作的、多人前后接龍的,為了讓別人看不出這不是同一人寫的,便把各自的文筆壓低到基本雷同的程度,一個故事模板能套用幾十遍,然后由工作室負責外部工作的人員去找編輯、求推薦、求上架,簽約買斷忽悠到一批讀者訂閱。”需要聲明的是,上述代筆和工作室現象在網文界究竟普遍到何種程度,未經查證,筆者不作任何判斷。但不容否認的是,在這種遵循商業邏輯的生產機制背后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自由創作行為,而更像是一個源源不斷制造標準產品的巨大的文學工廠和生產機器。與這種生產機制配套實施的是為寫手提供各類福利體系的網站保障機制。以起點中文網為例,自2015年起推出作家體系“星計劃”,對每日更新達4000字以上者發放1500元“創作保障獎”和600元“全勤獎”;對每月累計更新10萬字以上者發放訂閱費20%分成的“勤奮寫作獎”;對點擊量和讀者推薦票數上榜者發放高額的“月票獎”等。此外,每逢重大節日或寫手生日、新婚、生子,網站還會送上“作家禮包”。正是在文學網站種種扶持和激勵機制下,網絡文學寫手兼具創作者和“碼字工人”雙重身份,投身到持續的文本輸出活動和世界級文化奇觀的締造進程當中。
綜上所述,將數字敘事理論與網絡文學研究相結合,一方面讓舶來已久的數字敘事理論落到實處,另一方面使得亟須破局的網絡文學研究另辟蹊徑,未嘗不是西方理論結合中國實踐的有益嘗試。盡管這種嘗試尚存在“隔與不隔”(王國維語)的風險,但從理論發揚與現實觀照的視角,研究界將樂于見到此類嘗試。endprint
注 釋
[1] 中國出版網.2015—2016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EB/OL].[2016-08-26].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8/26/
t20160826_15275477.shtml
[2]關于中國網絡小說受外國讀者追捧的報道不勝枚舉,茲舉一例:一個由美籍華人外交官創辦的專門翻譯中國網絡小說的網站“武俠世界”(wuxiashijie.com),在兩年不到的時間里總訪問量超過10億次,每月訪問用戶達200萬,《盤龍》《斗破蒼穹》《我欲封天》等國內熱門小說皆有收羅,其火爆程度可見一斑。
[3] Joe Lambert. Digital Storytelling[M].2006, Berkeley, CA: Digital Diner Press,70
[4] Wilma Clark, Nick Couldry, Richard MacDonald, Hilde C Stephansen. Digital platforms and narrative exchange: Hidden constraints, emerging agency[J]. New media & society,2015(6):924
[5]“局內人知識(insider knowledge)”是美國民俗學家托馬斯·麥克勞克林(Thomas McLaughlin)提出的概念,被韓國籍北京大學崔宰溶博士引用到網絡文學領域,他認為“長期活動在一個或一些文學網站的網蟲們一一他們往往是網絡文學的土著理論家,網絡文學的精英粉絲一一對網絡文學的理解的深刻是難以相信的”,“土著理論家會給我們學術研究者提供更加貼實的洞察力和我們經常缺乏的局內人知識”。
[6]訪談對象基本信息包括其網名、開始創作年份、主要創作類型和代表作。
[7] YY,網絡用語,指不切實際的幻想。
[8]此處所指“學術合法性”是一個與民間理論的草根性、隨意性相對的概念,指用學術的語言、學術的邏輯、學術的論證方式對某一社會問題進行闡述。
[9]為何你努力工作卻不能出人頭地?《人民日報》批中國階層固化[EB/OL].[2017-03-14].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255124.html
[10]中國青年報.寒門子弟為何離一流高校越來越遠[EB/N].[2017-03-14]. http://zqb.cyol.com/html/2012-04/16/nw.D110000zgqnb_20120416_2-07.htm
[11]知乎:為什么現在火的網絡小說大部分都是小白文?[EB/OL].[2017-03-15].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606019
[12]百度貼吧:一個三十歲網文作者的精神之旅[EB/OL].[2017-03-15]. https://tieba.baidu.com/p/3767339741
[13]上架,網文名詞,即“上架銷售”,指一本小說開始向讀者收費,令作者獲得報酬。
[14]這一事實已得到實踐證明,筆者的訪談資料中大部分訪談對象也表示會根據讀者意見改變小說發展情節,甚至讓個別忠實粉絲成為小說人物,限于篇幅,不再列舉訪談原文。
[15]徐麗芳,曾李. 數字敘事與互動數字敘事[J].出版科學,2016(3):96-101
[16]小白文,網文名詞,一般是指內容淺白、情節簡單,極度套路化又廣受讀者歡迎的小說,網絡小說是典型之一。
[17]知乎:普通流行的網絡小說作家(如方想)和非常流行的小說作家(如唐家三少)的差距是什么?[EB/OL].[2017-03-24].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176498/answer/23822381
[18]棄坑,網絡用語,即不會再堅持繼續做某件事的行為,尤指網絡小說讀者放棄繼續閱讀的行為。
[19]2016網絡文學原創作者生存報告(完整版)[EB/OL].[2017-03-24]. http://www.sfw.cn/xinwen/482467.html
(收稿日期:2017-04-2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