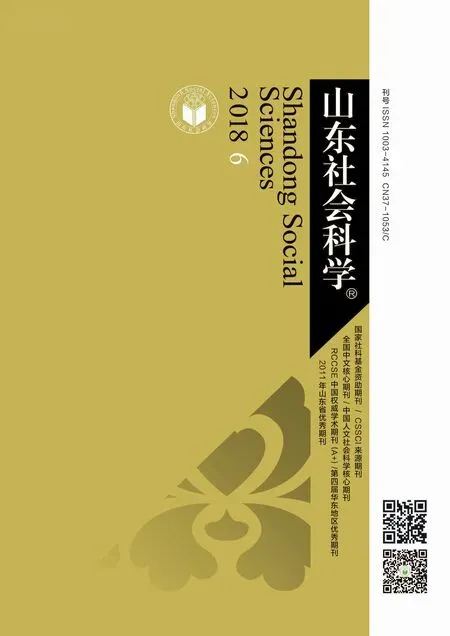極端民族主義之后的民族主義
——以戰后初期的丸山真男、竹內好與石母田正為例
譚仁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廣東 廣州 510420)
民族主義(nationalism)包含了太多令人困惑的龐雜內容,以至于很難對它作出一個明確的界定。*按照英國理論家蓋爾納的說法,民族主義的定義建立在迄今尚未得到界定的兩個術語之上:國家與民族,但這兩個術語本身同樣充滿爭議。([英]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韓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指出了民族主義本身的“空洞性”:“各種民族主義在‘政治上’的力量相對于它們在哲學上的貧困與不統一。換言之,和大多數其他的主義不同的是,民族主義從未產生它自己的偉大思想家:沒有它的霍布斯、托克維爾、馬克思或韋伯。這種‘空洞性’很容易讓具有世界主義精神和能夠使用多種語言的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產生某種輕視的態度。”([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但是,安東尼·史密斯又指出了另一個事實:大量人文知識分子,亦即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文學家、畫家、作曲家、導演等都扮演過民族主義代言人的角色。([英]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葉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就一般情況而言,在今天的知識界,至少在政治思想范疇內,構成民族主義的浪漫、狹隘、排他、暴力的極端側面已經受到了較多批判。然而,民族主義又是富有多面性的,它也能夠加強共同體凝聚力、喚起同胞之間的互助友愛之情、形成穩定的尊嚴感和自我認同意識、抗擊外國強權的不公統治。更加棘手的是,它似乎永遠不會因為受到了深刻批判便從此在現實之中銷聲匿跡,以至于有學者認為“民族主義在‘人民’之中的鼓動和共振作用,只有過去的宗教能與其媲美”*[英]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葉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史密斯還指出:“民族主義在某個層面上表現為政治意識形態,而在另一些層面上,則表現為一種公共文化和一種代理的政治宗教形式。”(同書第36頁)。1945年8月15日之后的日本社會,在所有的社會文化思想領域都經歷了一個激烈的價值顛倒。被法西斯利用為戰爭動員工具的國家主義、天皇神話、國體意識形態等,皆隨著戰敗喪失了支配性的話語力量。由此,日本進入了摒棄極端民族主義(ultra-nationalism)的新啟蒙時期。不過,若進入歷史現場,即可發現具體情況并非玫瑰色彩的一片美好。戰后日本從征服者淪為被征服者,政治、經濟、宗教、教育等體制都經受了占領軍強硬的民主化改革,整體呈現出一種復雜的民族狀態:欣喜與虛脫、解放與壓抑同時并存。*約翰·W·道爾在《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里詳盡展示了占領軍的民主改革過程,但也揭露了存在于美國占領軍之中的“新殖民主義”表現,包括對日本人的種族蔑視、美國人享受的諸種特權和強奸女性的罪行,并指出了民主革命的矛盾:“雖然征服者鼓吹民主,事實上他們卻依仗律令行事;雖然他們擁護平等,自己卻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權階級。”([美]約翰·W·道爾:《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胡博譯,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84頁)如果不了解這些細節,便無法理解日本人那種解放與壓抑共存的民族情緒。在此期間,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0年代初慘烈的朝鮮戰爭進入膠著狀態、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在日本的占領政策逐漸轉為紅色整肅(red purge)、警察預備隊創建、日本國內的民主主義進程遭遇寒潮。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日本主權全面恢復,實現了表面的“獨立”,但是在政治、社會、經濟上依然受制于美國(沖繩也劃歸美國管理)。美國解體舊日本帝國主義的同時,又把日本重新組織成了冷戰帝國主義的要塞。針對日本,它實施改造的第一任務是民主化,第二任務則是反共、反“極權主義”。由此,日本國內產生了“精神革命”尚未完成、民主改革被美國的冷戰政策打斷、日本將被美國長期控制的不安和抵觸情緒。這一峻急的歷史局勢喚醒了許多日本人渴望真正的民族獨立的欲求。*正如史密斯所介紹的那樣,“民族主義只有在短暫的時段內會變得極為重要,即在民族建構、征服、外部威脅、領土爭議、或內部受到敵對族群或文化群體的主宰等危機時,民族主義才顯得極其重要。”([英]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葉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頁)于是,1950年代初期,剛剛從戰敗之中站穩腳跟的日本,關于民族主義的討論又重新浮出水面。但是經歷過極端民族主義的噩夢之后,應該如何區分極端民族主義與健全的民族主義?日本部分知識分子對此作了深入的反思和探索,顯示出一種獨特的理論勇氣和火中取栗的靈活性。在此過程中,他們首先繼承了之前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批判性分析,并且試圖從民族主義這個概念之中抽取對政治性思考和歷史實踐具有參考價值的意義。本文重點不在于討論民族主義的定義,而是關注民族主義在日本知識分子的歷史實踐之中的功能。亦即為何日本知識分子會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時刻覺得有必要喚起民族主義力量?他們又是如何闡釋和行動的?通過考察該時期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1914—1996)、文學批評家竹內好(1908—1977)、歷史學家石母田正(1912—1986)的相關發言,本文將努力呈現一種關于日本民族主義——也是亞洲民族主義之一種——在一度破滅之后如何尋求發展的獨特思想經驗。
一、丸山真男:極端民族主義的病理
關于日本民族主義,丸山真男曾經為其賦予了一個精辟的比喻:“在亞洲各國之中,日本是唯一一個在民族主義上喪失了處女性的國家。”*[日]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思想的背景と展望」(初出:『中央公論』1951年第1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54頁。本文所有日文文獻,若無特別注明,均為筆者翻譯。原因是,與其他遠東地區那些生機勃勃的、包含著青春期之偉大混沌的民族主義相比,唯有日本的民族主義已經走過了“勃興—爛熟—沒落”的循環。今后的日本民族主義,無論是舊的復興還是新的修正,都無法擺脫這一歷史烙印。這一歷史烙印,當然是指上面提及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興盛與破滅。而最早從政治思想、社會心理學角度解剖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也是丸山真男。他在那篇后來廣為人知的論文《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中,以“超國家主義”指稱“ultra-nationalism=極端民族主義”。既然傾向于武力擴張的民族主義或曰國家主義乃現代民族國家的本質屬性,那么,“這種一般在現代國家中共通具有的民族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是如何區別的?”*[日]丸山真男:「超國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初出:『世界』1946年第5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2、13頁。丸山沒有停留于一般認為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特征,而是追究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背后的邏輯線索和心理動因。關于丸山的具體分析,可以擇其要點概述如下:
(1)國家邊界的擴張。吸取了宗教戰爭的教訓之后,歐洲現代國家試圖成為“中性國家”,在真理、審美、道德等“內容價值”上保持中立,僅將國家主權的基礎置于作為“形式價值”的法機構上。因此,形式與內容、外部與內部、公域與私域都是盡量分離的。與此相對,“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在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卻沒有試圖表明這種國家主權的技術和中立性質”*[日]丸山真男:「超國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初出:『世界』1946年第5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2、13頁。。隨著中央集權的強化,精神權威與政治權力開始合一,“第一次帝國議會召開之前頒布的《教育敕語》,可以說意味著日本國家公然宣布自己作為倫理實體,乃是內容價值的壟斷性決定者。”*[日]丸山真男:「超國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初出:『世界』1946年第5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5、18、25、26、27頁。既然國家本身可以規定正當性標準,其對內或對外政策便自然不會服從于任何超越國家的道義標準。這一邏輯結果便是:正義與國家活動同在,日本帝國體現了真善美的極致——丸山將此稱為“倫理與權力的相互代入”*[日]丸山真男:「超國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初出:『世界』1946年第5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5、18、25、26、27頁。。換言之,倫理只被權力代表,而沒有真正扎根在個體國民心中。
(2)主體性的缺失。倫理的權力化,也吊詭地導致了權力的倫理化。權力的惡魔性格、本質上的非道德屬性反而被忽略了。故丸山根據日本戰犯在審判庭上的軟弱表現指出,他們的權力一旦被剝奪,回到一個單純個體的時候,便迅速沉淪為不知所措的可憐蟲。與德國戰犯冷酷客觀的主體性或曰自由意志不同,日本戰犯主要是受到與天皇的距離意識的支配。距離作為終極價值的天皇越近,其地位便越高。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價值基準,主要由這種距離意識來決定。在這種缺乏“自由主體”之處,具有責任意識的“獨裁”反而難以成立,故無人自覺到是“自己”發動了戰爭。填補這種獨裁缺失之空白、維系國家精神之平衡的,乃是丸山稱為“壓抑轉移”*[日]丸山真男:「超國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初出:『世界』1946年第5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5、18、25、26、27頁。的體系。壓抑或壓迫的轉移,不僅表現在日本國內,同樣也延續到國際關系上,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日本士兵在中國或東南亞的暴行。“即使在國內僅是‘卑賤’民眾,在軍營里僅是二等兵,但他們一旦奔赴海外,便可以作為皇軍與終極價值相連,由此而占有無限的優越地位。無論是在市民生活還是軍隊生活里都無法擁有轉移壓抑之處的大眾,一旦獲得優越地位,便會受到試圖從全部重壓之下一舉解放出來的爆發式沖動所支配,這是不足為怪的。”*[日]丸山真男:「超國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初出:『世界』1946年第5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5、18、25、26、27頁。丸山進一步指出,即使是被視為終極價值源泉而高高在上的天皇,也并不是這個極端民族主義體系之中唯一的自由主體。因為天皇并非從“無”中創造價值者,而是萬世一系之皇統的繼承者,不得不根據祖宗遺訓進行統治而已。“如果用一個同心圓來表現以天皇為中心、萬民在與其的各種距離之中予以輔佐的狀態,那么這個中心并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垂直貫通的縱軸。”*[日]丸山真男:「超國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初出:『世界』1946年第5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5、18、25、26、27頁。這個縱軸就是所謂“天壤無窮的皇運”。
以上這篇論文偏重于歐洲與日本的國家形式或軍隊和官僚系統的比較分析,而在1951年的重要文章《日本的民族主義:其思想背景與展望》里,丸山真男一方面延續了以上關于日本民族主義內部缺乏主體性的思考,以及對無責任體系、非理性邏輯的批判,一方面又將視野延伸到了對新的民族主義的“展望”上。
丸山首先梳理了作為“攘夷思想”的“前期”民族主義的兩個特質:(1)它與統治階級試圖維護身份特權的欲求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與國民聯合的意識比較稀薄,反而伴隨著疏離、敵視民眾的特點;(2)在國際關系上缺乏平等意識,往往從國內的等級習慣出發,將國際關系理解為征服與被征服的二元對立結構,服膺于你死我活的叢林原則。在傲慢與恐懼這種特殊心理的支配下,消極防衛的姿態可能在一夜之間即可轉化為毫無限制的擴張主義。然而,舊統治階級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導入更加先進的西方技術文明,但是技術文明在本質上與西方精神文化是相互滲透的,所以又必然引發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
在這點上,中日兩國的舊統治者不約而同采取了“中體西用”“東洋道德、西方藝術(技術)”的策略。不過,中國的舊統治者因為內部的改革失敗,遭受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侵略,加上舊統治階級為了茍延殘喘而與帝國主義勾結,這便客觀上給中國的民族主義帶來了“反帝”同時又要“反封建”、亦即與社會革命相結合的歷史任務。與此相對,日本維新政權依然由過去的舊統治階級構成,成功實現了自上而下的“富國強兵”之現代化,一躍成為世界列強之一。日本民族主義的思想或運動盡管對這種全方位的西化進行了若干抵抗,但如玄洋社、黑龍會等所示,總體上是在正當化日本帝國軌跡的意義上展開的。因此,它不僅沒有與社會革命進行內在結合的契機,而且也對西歐古典民族主義的人民主權、資產階級民主原則置若罔聞,在上述“前期”民族主義的濃厚殘余之中,最終與作為現代民族主義之末期畸變的帝國主義同流合污。
更重要的是,這種民族主義邏輯還深刻地規制了日本國民的精神結構。在丸山看來,其表現主要有兩點:(1)國家被表現為第一集團(家庭或部落)的直接延長,統治階層通過鼓動第一集團的非理性情感,將“忠君愛國”捆綁為一體,把原本缺乏“國家觀念”的大眾培養成了帝國的臣民。帝國的擴張同時被視為自我的膨脹,個人的失意亦可通過國家的對外擴張獲得心理補償。(2)但是同時,以這種動員方式自上而下灌注的民族國家意識,沒有培養出具備政治責任意識的市民主體,而是量產了大批服從權威、“萬事由上面做主”的奴隸型人格。結果,像對征兵制的逃避一樣,有些家族鄉黨的利己主義反而固化起來,沒有提升為國家意識,有時候甚至還抵抗國策的執行。正因為具有這種兩面性,戰后的日本民族才會在民族神話崩潰之后陷入巨大的虛無感和精神真空之中。
那么,今后應該如何改造民族主義呢?對此丸山并沒有給出詳細系統的回答,但是從該文的某些片段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他的主張是:(1)民族主義本應該貫徹人民主權的原理。*[日]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思想的背景と展望」(初出:『中央公論』1951年第1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61-162、165-166、168、168-169頁を參照。(2)應該為新的民族主義找到足可以匹敵舊帝國日本之使命感的新鮮使命感。*[日]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思想的背景と展望」(初出:『中央公論』1951年第1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61-162、165-166、168、168-169頁を參照。(3)新的民族主義必須與民主革命有機結合在一起。民主化如果僅僅停留于高頭講章的理論或說教,而不是滲透到社會結構或國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沒有抵達國民精神結構的內在變革,便依然只是舶來品。因此,民主的非理性化與民族主義的理性化,應為正比例關系。*[日]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思想的背景と展望」(初出:『中央公論』1951年第1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61-162、165-166、168、168-169頁を參照。(4)警惕極端民族主義要素的復活。盡管天皇、“日之丸”旗、“君之代”歌的象征價值已經無法恢復到戰前那種地步,但不應該忘記這些要素被政治利用的危險性。因為,“日本舊民族主義最為顯著的作用,就在于遮蔽或壓抑一切社會對立,阻礙民眾自主組織的成長,將民眾不滿轉換為針對國內外贖罪羊的憎恨。”*[日]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思想的背景と展望」(初出:『中央公論』1951年第1號),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より,未來社1964年版,第161-162、165-166、168、168-169頁を參照。
在丸山的以上分析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認為日本民族主義一開始就離開了解放國民的根本原理,倒過來以國家名義壓抑國民。這使得日本的民主運動或勞工運動迅速馳向了世界主義,但長期以來卻放松了對“民族意識”或“愛國心”等問題的認真討論,反而讓統治階級或者反動分子獨占了民族主義的各種象征符號。*例如二戰期間唯一被以叛國罪名判刑并處死的日本記者、共產國際特工尾崎秀實,在戰后卻被視為“一位真正的愛國者,一位比自以為是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狂熱的愛國主義分子更加深沉、更加真實地熱愛自己祖國的人”。在1944年判處尾崎死刑的法官高田正,私底下也評價他為:“有理想、有道德的人,而且是一位愛國者的榜樣。”([美]約翰·W·道爾:《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胡博譯,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65頁)可見關于何謂愛國、愛國的價值評判,會因歷史條件的變化而出現轉折,而如果放棄了對這些歷史條件的注意和省察,便可能導致民族主義話語的僵硬和一元化。這點與下文將要討論的竹內好、石母田正的危機意識緊密相連,深刻提示了在現實政治局勢的客觀制約之下如何爭奪民族主義解釋權或話語權的必要性。
二、竹內好的民族論:表達完整人性的民族主義
作為著名的魯迅研究者以及丸山真男的好友,竹內好也是比較早從現代性批判和日本意識形態批判的角度探討民族問題的思想家。1951年9月發表在《文學》雜志上的《現代主義與民族問題》*原文為:「近代主義と民族問題」,收錄于『竹內好全集』(第7巻),筑摩書房1981年版。關于竹內好在魯迅論之外的文本翻譯,國內僅有孫歌編選的文集《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但不知為何沒有收錄此文。,相對集中地反映了竹內好在這方面的深刻洞察。他首先指出,至今為止,民族問題被左右兩翼意識形態所利用的傾向比較強,而作為學術對象卻被有意回避了。原因在于人們對右翼鼓吹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戰時苦難依然記憶猶新,自然難以簡單信任和響應戰后左翼意識形態關于民族問題的呼吁。戰敗之后,民族主義等于邪惡、擺脫民族主義才是拯救日本之正道的觀念占據了主流地位。尤其是那些在戰時抵抗過極端民族主義的人,在戰后以同樣的抵抗姿態繼續發言,更讓民族主義問題成為一種禁忌,以至于有人建議廢除日語,甚至還有人主張廢除作為人種的日本人。民族存在本身都被視為宿命般的罪惡,反過來也證明了民族主義確實剝奪過人類自由的歷史事實。
然而,承認極端民族主義之暴行的竹內好,又注意到人們無法理性看待文化民族主義在精神和情感領域的正面作用。他隨后將問題縮小到文學領域來討論的理由,也正在于此。竹內好指出,戰后的現代主義者主要以西方文學為準繩來衡量日本現代文學的“歪曲”或“落后”,忽略了日本文學的自我主張;左翼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雖然提出了“民族獨立”的口號,但其“民族”只不過是一種先驗概念,依然屬于現代主義的范疇,而非出自自然的生活情感,缺乏與現實的聯系。總之,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都沒有將民族問題納入自己的思考路徑。這些現代主義者們為了忘卻“民族主義”的噩夢,連“民族”本身都拋棄了,從而導致文化創造力的孱弱。下面這段話是竹內好關于日本民族主義表象之高峰的“日本浪漫派”*指1930年代后半期出現的批判現代文明、提倡“回歸日本古典傳統”的右傾知識分子,他們主要以保田與重郎(1910—1981,與竹內好是大阪高中同學)為中心,同時創辦了機關雜志《日本浪漫派》(1935—1938)。的著名論斷:
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現代主義者們,至今為止都回避了鮮血淋漓的民族主義。他們把自己定義為受害者,認為民族主義的極端(ultra)化不是自己的責任,認為將“日本浪漫派”悄然抹殺掉是正確的。但是,打倒“日本浪漫派”的,不是他們而是外部的力量。他們過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好像被外力打倒的東西都是他們自己打倒了似的。這樣的話,我們也許可以忘記噩夢,但卻無法清洗鮮血。*[日]竹內好:「近代主義と民族問題」,『竹內好全集』(第7巻)より,筑摩書房1981年版,第31、32頁。
戰后的文學評論,幾乎都對日本浪漫派置之不理,即使有少數人提及,也沒有深入到他們的發生根據進行內在的批評。這樣的話,其實談不上真正的否定。竹內好說:“我承認戰后現代主義的復活就是日本浪漫派的反命題,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本來日本浪漫派就是作為現代主義的反命題而出現的。什么反命題?那就是呼吁大家認可民族這一要素。”換言之,在急于批判日本浪漫派的國粹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虛妄之前,理性的態度應該是,先深入分析為何日本浪漫派會作為現代主義的反動而“認可民族這一要素”。竹內好洞察到戰后民主主義者視若無睹的重要問題:戰前日本民族主義的銷聲匿跡,并不全是因為現代主義或民主主義從內部徹底瓦解了其邏輯與信仰,而是由于戰敗以及美國占領的強行封殺所造成的。之前的日本浪漫派為何會橫空出世的問題——同時也是日本現代主義的弱點問題——尚未得到解答就被遮蔽了。然而,某種思想觀念或意識形態,包括其外圍所包裹的存在式情緒,如果不是經過細致的解剖、正當的辯論、理性的剝離,便會帶來某種危險。正如丸山真男所言,那些散落在社會底層的民族主義情感,可能會朝著舊帝國主義的象征方向再次被動員起來。
那么,竹內好反對何種民族主義?首先是天皇制的民族主義。在1930年代的共產主義者那里,已游蕩著欲將民眾與天皇制捆綁的民族主義幽靈。例如日共干部佐野學、鍋山貞親的轉向聲明《致共同被告同志書》里便如此宣稱:“真正的革命家必須明白:日本民族強國的統一性正是日本社會主義最優越的條件之一。民族就是多數人,也就是廣大的勞動大眾。我們對此勞動階級的創造能力充滿自信。”“我們要忠實于大眾本能顯示出來的民族意識。”*這份著名的轉向聲明發表于1933年6月10日,影響重大。不到一個月,許多共產黨干部紛紛隨之發表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聲明。但是,如果僅僅這樣是稱不上“轉向”的,因此佐野與鍋山必須將絕對主義的皇室視為日本民族的代言人:“日本皇室連綿不斷的歷史存續,是世界上罕見的、日本民族獨立的順當發展的表現。在勞動大眾心中存在著以皇室為民族統一中心的社會感情。”由此,民族主義便被天經地義地回收至統治階級的傘下了。與此相對,竹內好對天皇制的批判態度則非常明確。在《關于天皇制》(1953年4月《T·U·P通信》第11期)一文中,他把日本人對天皇制的接受方式分為三種:愛慕型、恐懼型、漠不關心型,并認為自己屬于恐懼型。
竹內好在反對日本皇國意識形態的同時,也反對教條現代主義者的“自由人”設定與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人”設定。自由主義傾向于視民族主義為應該消除的虛假意識或幻想,正統馬克思主義則將民族問題完全消解到階級問題之中。他認為這些設定作為某種階段性的操作雖有必要,但都錯誤地隔離和分裂了具體而完整的人性。日本現代主義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都忘記了文學本來的任務是拯救一切,而不是以偏概全,以部分來偷換整體。“從那些被拋棄的黑暗角落里,重新出現要求恢復完整人性的呼喊,乃是一種必然。”“民族問題就扎根在這些黑暗的角落里,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權力統治,喚醒了這一力量,而且把它拔高到極端民族主義來加以利用,我們有必要批判權力統治的機構,但卻不應該連樸素的民族主義也一并壓制了。”“如果沒有仔細考察樸素的民族情感被權力利用、同化的全部悲慘過程,只是避開與其的對決,那么今天是無法討論民族的。”*此段引用均出自[日]竹內好:「近代主義と民族問題」,『竹內好全集』(第7巻)より,筑摩書房1981年版,第34-35頁。
1951年,歷史學家遠山茂樹同樣給出了類似的警告:“不管其形態如何,民族主義傾向當然都會帶有保守的、排他主義的色彩,以及非合理的、沖動的側面。正因為如此,如果我們以厭惡的心情抽身而出,僅在外部表示擔心的話,便無法阻止反革命勢力再次掌控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且將其引向極端民族主義。”*[日]遠山茂樹:「二つ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対抗——その歴史的考察」,『中央公論』1951年第6號,第34頁。換言之,竹內好和遠山茂樹提倡的態度不是袖手旁觀,而是積極介入其中,奪回對民族主義的理論解釋權,引導民族主義往正確的方向發展。
在竹內好看來,那些不應該被排斥的健康民族情感,蘊藏在日本浪漫派的“正確部分”——竹內好同意使用作家高見順所說的“健全的倫理意識”來替換民族意識*[日]竹內好:「近代主義と民族問題」,『竹內好全集』(第7巻)より,筑摩書房1981年版,第31、32頁。——之中,也可以一直追溯到石川啄木(詩人,1886—1912)、岡倉天心(美術家,1863—1913)、正岡子規(俳句詩人,1867—1902)、北村透谷(詩人,1868—1894),甚至福澤諭吉(思想家,1835—1901)那里。這些人物——盡管竹內好有意不提他們同樣顯著的差異——構成了斷斷續續但確切存在的日本民族主義傳統。倘若忘記這一傳統,或者繞開了這一傳統,僅從現代主義的角度來合理解釋日本戰敗、日本社會文化之扭曲落后的話,其實無法阻擋這一傳統力量再次從黑暗的角落里噴涌而出。“如果僅停留在反命題的提出而不追求合命題,是不能完全否定對手的。……(恢復完整人性的要求——筆者補充)一旦開始萌芽,而由于整個社會結構基盤依然沒有改變,它肯定會發展為超國家主義的自我毀滅。”*[日]竹內好:「近代主義と民族問題」,『竹內好全集』(第7巻)より,筑摩書房1981年版,第36頁。據此,竹內好提出了“國民文學”的要求:即使這個詞匯已經被污染,但我們不能使用“階級文學”或“殖民地文學”(以及相反的“世界文學”)來代替它,國民文學必須實現整體人性的恢復。不扎根于民族傳統的革命不可能存在,而與民族情感無緣的文學也不可能得到認可。
在此我們無暇展開具體應該如何寫作才能稱得上國民文學的追問,只能通過竹內好屢次提到的一個隱喻,亦即“黑暗的角落”來思考他的民族主義概念意味著什么。從竹內好舉出的幾位詩人、批評家、思想家來看,貫穿在他們之中的是對民眾、鄉土、傳統、文藝的共同熱愛。這顯然與前面提到過的文化民族主義有關。這個概念主要指向歷史記憶、身份歸屬感、語言和象征、傳統習俗、自然的民族信仰等,不可否認帶著神秘主義色彩。我們既可以將竹內好使用的隱喻視為一切語言均無力完全反映的人性深淵,亦可理解為實際的民眾生活和歷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在時空方面的無限延伸,它遠遠大于所有“主義”的表象范圍,總是像海底冰山一樣,隱秘地影響著那些浮在表面的意識形態的此起彼伏。當某種意識形態試圖脫離民族或者欺瞞民族的時候,它的無聲抗議便會從某種民意的本能需求之中冒出來。盡管竹內好沒有點明,但我們可以推測,例如被“階級人”所排斥的個人欲望、被“現代主義者”忽略的作為結構性問題的勞工疾苦等,都會在“民族情感”這個范疇之中得到有機的安置。
以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也可以說竹內好這樣的民族主義論,恰好契合1990年代之后在民族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族群-象征主義”流派*亦被稱為“歷史主義”民族理論。載[日]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現代日本人自我認同意識的走向》,劉克申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7-30頁。作者吉野耕作是蓋爾納、安東尼·史密斯等人的民族主義研討班成員。,其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及的安東尼·史密斯。根據葉江的梳理,該理論的核心觀點為,民族的基礎是族群(ethnic community),亦即共同的族群起源神話、文化象征、歷史傳統,因此民族和民族主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歷史作用。知識分子從中吸取營養,不斷激發本民族的內在活力,而民族認同也在神話、記憶、象征和傳統中不斷持續。總之,該理論強調民族的族群基礎和民族主義的主觀因素(文化、象征、記憶等)而非政治和經濟因素。它與另外一種占據主流的“現代主義”民族理論(其代表人物是史密斯的老師蓋爾納)的不同在于,后者認為民族不過是法國大革命、英國工業革命之后才開始形成的現代現象,并不具有久遠的歷史性,同時強調民族主義的政治性、市民性及其發源的西歐性。而“族群-象征主義”民族理論主張古代便有民族,它同意民族主義是現代產物,但反對民族是由民族主義造就的觀點,重視民族觀念的歷史文化層面,不認為民族只是現代史發展過程中的暫時現象。*參照葉江:《當代西方的兩種民族理論:兼評安東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由此可見,如果說丸山真男的民族論大致可以套入“現代主義”民族理論,側重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批判;那么竹內好的民族論則偏向于“族群-象征主義”民族理論,并且試圖通過文學來喚醒日本民眾在現代性之幕下沉睡的價值意識和精神意涵。
如果再進一步思考竹內好對民族之持久性的重視,我們還可以用柄谷行人的民族論提供一個側面的佐證。在2000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訪日期間,與其同臺演講的柄谷行人對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說作出了自己的闡發。他借由康德指出:“我很重視康德所區分的單純假象和無法簡單去除的假象(超越論假象)。譬如我有翅膀這種想法只是單純的假象,但認為存在統一自我的想法——比如認為今日之我即昨日之我——則是超越論假象。對于后者,即使認識到它是假象也去除不了的。若是硬要去除,人就會患上分裂病(綜合失調癥)。”*[日]柄谷行人:『日本精神分析』,講談社2007年版,第44-45、49、59頁。原文為2000年的演講稿。“超越論假象”亦譯為“先驗幻相”。換言之,超越論假象是人類理性自身的固有原則和結構必然導致的,它不是實體,但人類社會需要它的引導和整合功能。例如,宗教與貨幣雖然是一種想象之物,但人類卻無法輕易消除它們,民族也同樣如此:“‘想象的共同體’不可能僅是想象之物(假象),而是所謂的超越論假象。”*[日]柄谷行人:『日本精神分析』,講談社2007年版,第44-45、49、59頁。原文為2000年的演講稿。“超越論假象”亦譯為“先驗幻相”。“民族主義不會因為啟蒙而消失,只要需要它的‘現實’沒有改變。”*[日]柄谷行人:『日本精神分析』,講談社2007年版,第44-45、49、59頁。原文為2000年的演講稿。“超越論假象”亦譯為“先驗幻相”。當然,竹內好不可能像柄谷行人那樣深入探討民族與國家、資本的三位一體關系以及三者的相互制約,當時的他,僅僅指出了民族這一維度在批判現代主義、安慰國民情感、回應歷史危機上的積極意義。
三、石母田正:發現民族的歷史學
因此,接下來我們可以討論竹內好與歷史學家石母田正如何看待與民族主義緊密相關的歷史研究。在重大的政治波動期間,由于統治的合法性和國民的身份認同往往會發生動搖,歷史學作為建構民族主義的重要學科,就會受到高度的關注。盡管歷史學與民眾的關系如何,可能平素無人在意,但在這個時期則會變成一個重要的“思想課題”。
1952年,竹內好在《給年輕朋友的信——對歷史學家的要求》*該文也收錄在國內編譯出版的竹內好文集《近代的超克》(孫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68-271頁)之中,以下對該文引用皆出自該文集,不再一一標注。這篇短文里介紹了一件學界軼事:日本某個學術機構把關于中國的研究著作寄給了中國學者,希望得到批評指正。中國學者表示肯定與贊賞,認為不加修改直接譯成中文,當作中國人的著作出版也行得通,但也提出了疑問:今天的日本人為何要寫這樣的書呢?竹內好據此指出,一味依附于對象國學界之“問題意識”或直接用對象國語言寫作的歷史研究喪失了作為日本人的主體意識和現實感覺,“沒有汲取日本民眾的喜怒哀樂,因為研究是在與民眾毫不相干的層面上進行的”。盡管學問必須超越生活,但是“從終極結果來說,與生活不相聯系的學問根本不存在,任何學問都是從我們應該如何生存這一追問出發的”,“如果終極意義上的聯系被忽略了的話,學問就會變成經院派的學術,那么學問也會墮落”。這種與研究者的同胞、所屬的國族社會或現實無關的歷史研究,被竹內好斥為“寄生性的、被殖民地化的、奴隸性的”人文學問,是一種“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奴隸的奴隸式思考”。*當然也必須注意,竹內好對這種學問的批判,并不意味著他在主張拋棄學術理性基本原則的煽動式寫作。
如果暫時脫離當時日本的歷史狀況考慮竹內好的以上觀點,我們也許會馬上陷入“為人生而學術”與“為學術而學術”的兩種傳統為學之道(或“思想”與“學術”、“現實”與“學問”等二元對立)延續至今的紛紜訴訟。就歷史研究而言,堅持為往圣繼絕學者,認為現實關懷會扭曲歷史研究之豐富性和科學性者,堅持同行評價、不受外部權力(包括民眾)干擾的自律性者,恐怕不會同意竹內好的意見;而另一方面,歷史研究如果走向高度的專業化、制度化甚至宅人趣味化,那么雖然貌似接近了“與國際學界接軌”的普遍主義,但缺乏來自研究者所處的生存處境的直接或間接刺激,不僅其自身生命力會因后繼無人逐漸枯竭,而且也的確意味著放棄了在民眾之間傳播文化、啟蒙思想、改革現實的另一重使命。用竹內好文中的話說,即是“學問的國際性并非意味著學問沒有國籍”,反而越是民族的,才越是國際的。也就是在這篇短文的末尾,竹內好推介了歷史學家石母田正不久前出版的《發現歷史與民族》(1952,前篇),將其理解為一種試圖“擺脫奴隸狀態”、重視聯系歷史與民眾的成果。在該書中,石母田正表達了他對歷史研究忽略當代民眾的誠摯反思:
我對待過去的歷史,并沒有現在的人們即使對待彈珠游戲愛好者也持有的那種親近感——而這種親近感,才是現在的危機贈予我的東西。在學問這種傳統世界里長大的我,轉向面對過去的日本歷史、過去的日本人時,總會忘記對現在那些為了生存而拼命掙扎的每一個日本人的同情與共鳴。每一個平凡人所擁有的廣闊世界、由成千上萬的個體世界匯聚而成的日本這一世界,其深度和可能性都無窮無盡,但是我卻沒有采用這種感覺或眼光來審視過歷史。我曾為自己通過理論或方法從陳舊的歷史學里解放出來而沾沾自喜,但是如今漸漸明白過來,在這一點上,只要我還沒有擺脫學問這種難以消除的強烈影響,便依然找不到出路。*[日]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上原専祿先生に」,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歴史學の課題と方法』(初版: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年),平凡社2003年版,第29-30頁。
這里所說的“每一個平凡人所擁有的廣闊世界”,正是竹內好念茲在茲的民族內涵。在竹內好與石母田正的文字里,都流露出對知識分子脫離民眾、人文歷史學術喪失現實根基的批評與自省。我們在討論他們所擔憂的民族意識危機時,顯然可以發現他們與丸山真男一樣,是緊扣民族主義本來應有的國民解放(盡管解放的方式不同)原則的,而并非站在統治者立場上把民族視為實現其特殊利益的工具。從該書中石母田正對勞工的同情共鳴、對統治者搜刮民膏壯大警察軍隊的憤慨來看,我們也可以辨認出,在作為反抗資源的民族意識與作為統治工具的民族意識之間,他努力的目標無疑是前者。例如,石母田正提倡“健全的民族意識”,而非排外的民族主義:
如果明治以來的統治者沒有利用業已形成的基礎,從外部注入民族意識,進行組織化教育的話,這種強烈排外的民族意識是絕不會產生的。排外思想其本身就與大眾健全的民族意識不同。傳統民族觀念在戰后大范圍崩潰,統治者也有意識地加速它的消亡(而這次為了反蘇反共,又打算重新使其組織化起來)。但是只要存在民族這個集團與其生活,民族意識就不可能消失。*[日]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上原専祿先生に」,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歴史學の課題と方法』(初版: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年),平凡社2003年版,第33、35頁。
這段話比較費解,石母田正認為既有從外部灌注的不良民族意識,也有民眾本來就具有的健全民族意識。受馬克思主義階級意識論的影響,石母田正認為民眾的民族意識無法自然生長,需要知識分子去努力喚醒,但是又不能重蹈明治時代以來那種排外的自上而下的灌輸方式,因為那樣反而糟蹋了近代以前健全的民族根基。在1948年3月所寫的批判日本漠視朝鮮之苦難的《擊碎堅冰》里,他早已指出,明治以后日本的擴張主義反而導致自己的民族意識變得虛無:“我們過去的一切頹廢,與朝鮮民族的被壓迫有著深切關聯。在戰時無比強烈的日本民族意識,一旦戰敗,卻完全轉化為奴隸性格、乞丐性格。顯現在這種典型變化之中的特殊民族意識結構,也與明治以后對其他民族的壓迫有關。”*[日]石母田正:「堅氷をわるもの」,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歴史學の課題と方法』(初版: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年),平凡社2003年版,第331頁。
很明顯,這種無節操的“特殊民族意識結構”,也就是竹內好同時激烈批判的缺乏抵抗精神的“優等生意識”和“奴隸式的進步觀念”。也只有奴隸,才可能毫無反省地把強勢民族虐待自己的方式同樣施加于比自己弱勢的民族身上。“當奴才成了主人的時候,將發揮出徹底的奴性。”(竹內好,《何謂近代》,1948)這樣的奴隸表現,便是竹內好、石母田正所強調的缺乏健康而平等的“民族意識”的反映。換言之,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隨意屈服,意味著民族的自尊、獨立和主體性的喪失。如何重新打撈民族遺產、重建一種更加健全的民族意識,便成為他們的當前課題。在石母田正看來,扎根在現實日常生活之中的民族意識雖然不會消失,但必須被自己客觀化之后才有意義。因此歷史學的緊迫課題便是“通過自己民族的經驗=歷史引發自覺意識”。“只有深刻理解祖國的歷史、熟知自己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風俗,才能產生真正的愛國之心。”金日成這句話表達了石母田正對歷史學任務的認識,他進一步宣稱:“唯有讓更多日本人自覺到民族的驕傲和傳統、自覺到日本人所具有根基的實踐,才能帶來學術上的創造。”*[日]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上原専祿先生に」,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歴史學の課題と方法』(初版: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年),平凡社2003年版,第33、35頁。于是,在具體的行動路徑上,竹內好選擇了發起在文學中重建民族意識的國民文學論,石母田正則選擇了構建“村莊歷史學”和“工廠歷史學”的國民歷史學運動。
國民歷史學運動,是日本戰后成立的“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簡稱“民科”)歷史分部從1952年到1955年左右牽頭推行的一系列大眾歷史教育活動。1946年,180名對戰前科學持批判態度的研究者聯合組成了“民科”,他們主要批評戰前科學:第一,漠視權力或迎合權力;第二,科學者和科學組織的特權化、階層化;第三,不對民眾開放的封閉性等。1950年,“民科”達到發展的高峰期,擁有114個地方支部、1772名專業會員、8243名普通會員,成為一個除了研究者之外還有一般市民與學生參加的大規模學會。
村井淳志指出,在這個時候,該協會強調的依然是“民主主義”,而非“民族”。但是受前面所述“現實性”的影響,“民科”主旨逐漸改變。1952年1月,屬于“民科”書記局的石母田正在向“民科”總部提交的意見書里指出,《舊金山和約》下的日本深受美國壓制,為了把民族從這種狀態下解放出來,科學以及科學運動應該作出貢獻,而且這個目的也只有通過“國民科學的創造”才能達成。1952年5月的“民科”第七屆大會決定提出“國民科學的創造與普及”口號,轉向“國民科學”路線,從而把民族性全面推到了前臺。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上述石母田正的《發現歷史與民族》(正、續)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刊出,成為國民歷史學運動的指導手冊,在學生之間更是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在創造民族主體方面,“民科”歷史分部組織各種生活記錄運動,讓本地工農展開自發的調查活動,也鼓勵知識分子或學生進入農村協助研究,通過考證村莊史、工會史、母親的歷史等等,極大推進了學界與民間對民眾史、鄉土史、生活史、女性史的研究。
遺憾的是,國民歷史學運動不久便遭遇了挫折。其中原因之一是居高臨下的啟蒙姿態意識不到自己創造了新的權力關系而妨礙了運動的順利進展。*例如農村工作隊操之過急的改造意愿、對農村多樣性認識的不足等,都讓運動逐漸走樣。石母田正在1960年的自我批評中認為,本應帶來喜悅與快樂的運動,被過度的政治目的裹挾而去,反而變成了某種義務和強制。有論者指出,作為國民歷史學運動的理論指導者,石母田正的民族概念主要有兩個側面:第一是可以抵抗美帝國主義以及賣國權力者的政治性主體;第二是非政治的、日常的、充滿鄉愁的情感主體。*[日]村井淳志:「國民歴史學運動と歴史教育」(『教育科學研究』第4號,1985年7月)を參照。這里似乎將前者視為公共主體,后者視為私人主體,但不管哪一個,國民歷史學運動強調的“民族、歷史、愛國心”其實是進步陣營的一次話語權力斗爭。雖然有人會將它們與右翼的語言混為一談*教育學者小國喜弘認為,國民歷史學運動在讓歷史觀照邊緣群體方面與1996年的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具有絕對差異,也指出了它與后者的相似之處:1.混同學習歷史就是學習民族國家的歷史,低估學習無法被回收到國民歷史之中的個人史或文化史;2.重視在國民內部共享歷史,但沒有通過與國民外部的對話來建構本國史;3.不把在日本國內居住的非日本民族納入日本史的構建主體,不太考慮日本民族的多樣性。([日]小國喜弘:『戦後教育のなかの〈國民〉——亂反射するナショナリズム』,吉川弘文館2007年版,第209 -210頁を參照)第1點正是石母田正的夙愿,或許在實踐中并未做到;第2點和第3點雖然有點過度要求,但的確也是這場運動的弱點。,但是如果不仔細甄別其內涵便對這些概念不屑一顧,其實就等于放棄了附著在這些語詞之上的道德吸引力和精神感召力,也就意味著堵住了一種干預和重塑國家社會的政治可能性。盡管國民歷史學運動存在著諸種局限,但是“讓民眾自己書寫民眾史”的開創之舉,依然值得今天的歷史實踐參考和借鑒。
四、結語
在現代民族國家批判理論之中,正如丸山真男所說,民族主義極端化之后,常常伴隨著過于強烈的自我意識、排他性和攻擊性,而且將內部多元的個體收編到均質化的集團之中,反而壓抑國民生活,因此往往被視為有害的政治情感或意識形態。以至于在后來的理論之中,民族主義干脆被理解為一種晚近才建構的、虛幻的人工產品。然而,就民族主義本身而言,它“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在各種歷史時點,根據某些條件,例如具體包含何種階級政治主張、被何種階級政治勢力所領導而形成政治課題等,民族主義既能成為革命的巨大能量供給源,也能成為反革命的堅固堡壘。”*[日]遠山茂樹:「二つ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対抗——その歴史的考察」,『中央公論』1951年第6號,第33頁。丸山真男、竹內好、石母田正同樣認為,如果不積極介入,便等于將民族主義的各種象征符號拱手讓給了反革命勢力。經歷過民族主義“暴走”的歷史之后,丸山真男深刻剖析了日本天皇制度綁架民族主義變身為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倫理,竹內好發起了試圖矯正現代主義文學之偏頗、回應健全人性之呼喊的國民文學討論,石母田正則嘗試通過組織民眾書寫自己的生活史或地方史來消解官方灌注的民族意識。他們三者的區別僅僅在于,不同于竹內好與石母田正的強烈移情,丸山真男對底層民眾的視線更加冷峻一些,不是一味的美化,因為他經歷過和認識到日本農村共同體(尊皇意識、在鄉軍人)同樣可以成為法西斯的溫床。至于竹內好與石母田正,應該說他們的民族論也不會被回收到戰前那種自上而下的、試圖建構同質化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現代性疾患之中。他們所念念不忘的“日本民族”,如果像柄谷行人所說,是一個無法祛除的假象,那么他們在現實之中唯一能做到的,也就是要努力保證這個假象的倫理性和獨立性,讓它成為一個值得尊敬和認同的對象。既然孤獨無助、原子化的個人可以形成極端民族主義的基礎,那么我們或許可以考慮,健全的“民族”想象也不是不可以變成某種抵抗原子化的、共享情感和行動力量的政治性同盟。正是因為如此,為了重建與民主革命相結合的新民族主義,我們需要更加冷靜地鑒別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的差異,平等地參與民族意識(同時也關系到世界意識)的塑造,激活民族的健康活力,同時必須抵制那些如影隨形的暴力沖動的誘惑。*1969年,漢娜·阿倫特在《論暴力》一文中指出:“只要民族獨立(也就是不受外族統治)和國家主權(也就是在外交事務中的不受審核、不受限制的權力要求)仍然得到認同,就不會有什么能代替戰爭。”([美]漢娜·阿倫特:《共和的危機》,鄭辟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頁)這是對戰爭這一暴力形式本身的否定,而非界定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以本文的問題意識來說,恰恰是因為民族概念被忽視而導致極端反彈,國家概念被利用來謀取部分統治階級的特權(獨立建制會提高該民族精英的政治經濟地位),才會出現阿倫特所說的戰爭沖突。事實上,僅僅到了1960年代,日本便出現了一個具有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思想轉向。例如在1950年代末登上文壇的江藤淳等文藝批評家打起了“否定戰后”的旗號,把日本戰后的反戰和平、民主主義文學和思想的歷史貶低為“喪失的歷史”“自我破壞的歷史”,試圖建構另外一種解讀文學、民族與國家的新話語。由此可見,在民族主義這個場域之中的拉力角逐是如何持久和反復,對此的凝視與介入又是多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