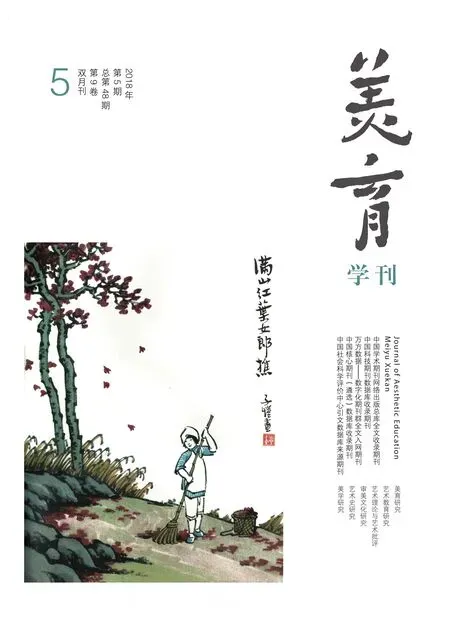覽物寄情 尋理暢思
——自然美育視野下的自然審美方法體系梳論
邱振國
(西南財經大學天府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美育同德育、智育、體育一樣,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我國對美育工作的重視不斷加強,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美育中存在重應試輕素養、重少數輕全體、重比賽輕普及的現象。[1]有的調查表明美育中存在著教育功利化、課程形式化、課程被擠占等突出問題。[2]不僅如此,美育內容的結構也存在著不均衡現象——藝術美育的發展如火如荼,自然美育卻相對冷清。自然美育具有難以被功利化、形式與內容多樣化、時間靈活等優勢,對優化美育內容結構、提升美育質量有積極的作用。自然審美方法是自然美育中的關鍵內容。構建自然美育視野下的審美方法體系,對于完善自然美育理論、開展自然審美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一、自然美育的獨特優勢
自然美育具有以下獨特優勢:
第一,自然美育難以被功利化。自然美育側重日常素養,與日常生活結合度高,與升學、考級的關系不明顯,不會像藝術類美育那樣容易淪為升學、考級的工具。
第二,自然美育能夠促進美育內容的結構平衡,使美育形式更加多樣化。在美育內容上,當下美育多以藝術美育為主,但美育不等于藝術教育[3]。自然美育可以大大拓展美育內容的空間,改變以往的藝術美育占比過大現象,使美育內容的結構趨向平衡合理。在美育形式上,由于自然美育活動多是在課外進行,可改變以往美育以課堂為主的模式,可使美育形式更加多樣化。
第三,自然美育具有時間安排上的靈活性。自然美育可在課外進行,不必占用太多課堂時間,周末、節假日都可以開展自然美育活動。因此,其時間安排不會與其他課程產生大的沖突,有效避免了美育課程被過度擠占。
第四,自然美育所需投入較少,實施門檻較低。自然美育通常是借助已存在的自然類美育資源,不用購買大量設備,不需要較大的教育投入。自然美育對審美者自身的早期積累要求不高,不會像藝術美育那樣對技能基礎、課程銜接上有過多要求。自然美育的這些優勢有利于審美教育的普及,非常適合經濟和教育欠發達地區廣泛開展,改變以往美育中“輕全體”的現象。
第五,自然美育有利于發揮家長、社會機構在美育工作中的積極性。自然美育需要走出校園,與旅游景區、自然保護區以及學生家長展開合作。這有助于發揮社會機構和家長們的積極性,凝聚更多力量和優勢,形成合力,促進美育不斷發展。
第六,自然美育有利于強化自然保護意識,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自然美育需要良好的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做基礎,重視和加強自然美育有利于反促自然保護工作的積極開展,對提高民眾的自然生態保護意識具有廣泛的積極影響。
二、自然審美方法體系的重要性
首先,對美育中的受教育者(審美者)而言,高品質的自然審美體驗需要有必要的方法體系做支撐。只有諳于自然審美方法的運用,才能獲得豐富體驗,邁向更高層次的審美。自然審美方法體系的運用,可使自然、歷史、藝術等多種養分交融,將審美者帶入一種綜合化審美活動中;可將情感與理性陶冶集結,使審美者得到多方面的發展。
其次,對美育工作者來說,只有重視和加強自然審美方法體系教育,才能使自然美育工作取得更顯著、更具實質意義的成果。自然審美方法體系的教育,不只是在進行審美教育,同時也可以幫助審美者學習文化、錘煉道德、開發智力、磨礪心理、接觸科技、蕩滌心靈、樹立理想。自然審美方法體系教育既是在實施美育,同時也會對德育、智育等產生積極影響。
三、自然美育視野下的自然審美方法體系
目前關于審美方法的研究已取得顯著成果,如在儒家、道家等傳統審美思想方法,美術、音樂等具體學科審美方法的研究上都已有突出成果。但是關于自然美育中的自然審美方法及其體系的研究還很缺乏。
自然美育視野下的自然審美方法體系的構建,應遵循一些特定原則。從“自然”本身的特殊性與“美育”的要求來看,應當秉持多樣性、基礎性、普適性、發展性(獲益性)的原則。基于這樣的原則和視角,本文對古今審美活動中的自然審美方法進行了析出和梳理總結。這些審美方法各具特點,在美育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一)空間變換法
空間變換法是自然審美中較為基礎和常用的審美方法。空間變換法又可細分為線性遞進、擴縮漸變、角度變換、空間出入四種常用方式。
1.線性遞進式
線性遞進式是在一條游覽線上依次觀賞審美對象的方式。這種審美方式能夠帶給審美者景隨目遷、步移景異的游賞體驗,使人就像在欣賞一幅風景長卷一般,具有很強的時間流動性和韻律感。
線性遞進式能夠使審美活動按照一定的空間規則進行,很好地保證審美活動的有序性和審美對象特征呈現的完整性。有助于塑造審美者良好的自然審美習慣,促進韻律感的發展,訓練審美中的注意力和發現力,感受大自然的秩序美。
2.擴縮漸變式
這種方式可細分為漸擴式和漸縮式兩種。漸擴式即視野由局部聚焦逐漸擴大范圍,直至對審美對象的整體進行觀照,是從關注對象的細節特征逐漸過渡到關注整體形象。漸縮式即由總體觀覽逐漸縮小至局部觀察,是從整體性審美對象漸漸過渡到細部對象。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寫道: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4]103
上文中審美者關注點的變化順序是:由“環滁皆山”,到“西南諸峰”,再到“蔚然而深秀”的“瑯琊”,又到山行六七里后“兩峰之間”的“釀泉”,最后止于“翼然臨于泉上”的“醉翁亭”。這是典型的漸縮式審美。
3.角度變換式
角度變換有助于審美者領略自然景物的多樣化風貌。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變換審美角度最直接的作用是改變審美對象的類型、規模和數量,調整審美距離。王羲之《蘭亭集序》云:“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仰觀”易成宏闊之景,“俯察”易顯精微之境。[5]明代薛瑄《游龍門記》中有角度變換式的典型運用:
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甓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峰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云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側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6]111
角度變換可使自然景物的特征得以立體化呈現。有助于培養審美者多方面觀察事物的習慣,使審美對象之特征得以全面展現。對文藝創作者而言,角度變換式有助于審美者更好地進行自然觀察的積累,這樣才能“搜盡奇峰打草稿”,創作出生動形象、肇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優秀作品。
4.空間出入式
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詩句,說明了審美者身居山中難以感受廬山整體美的道理。因此要適時采用空間出入式。王國維的“出入”說,在一個“側面”對空間出入式作了有力解說。他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間詞話·六十》)王國維在這里是談詩詞創作,但對于自然審美活動而言,這一理論同樣適用。自然審美中,“入乎其內”才能發現事物更多的細節特征,“出乎其外”才不會囿于一隅,而是能夠統覽整體,且在情感和認識上有所超拔。空間出入式中的“出”和“入”,既可以是自然界的物理空間,也可以是審美者的心理空間和思想空間,因為“出”和“入”都往往伴隨著豐富情感和思想。
空間出入式有助于培養審美者觀察事物、看待問題時的宏觀和微觀轉換能力。使審美者既能深入其中,窺其細節,又具宏闊視野,整體把握。既擺脫單純整體觀覽的空疏,又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限。使審美者自由穿行于審美對象的內與外,有即有離,即而能離,將自然界的細節美與整體美相統一、相平衡。
(二)時間變換法
自然事物總是隨時間變化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審美隨時間而動,才能領略到“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鐘嶸《詩品·序》)的四季風格。恰如北宋文學家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所言: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云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4]104
審美時間的不同,在觸動人的情感上也有很大差異。北宋文學家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道: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6]214
在自然美育中,注重審美時間的選擇,可提高審美視野的寬度。時間變換不僅是為了領略自然風景多姿多彩的風貌,更可以體會不同時間里物我互動的不同。
(三)物我互動法
物我互動法是審美者與審美對象發生交流互動的審美方法,可分成主動式和受動式兩種。主動式即審美者主動作用于審美對象,使其發生一定變化,呈現出不同于常態的美學特征。比如,鄉村的湖泊一般呈現出的是靜態美特征,但是當隨手將地上的一塊扁石橫向投于湖面后,就會產生一系列變化:扁石在湖面上的跳躍前行,繪成了優美曲線,泛起了圈圈水波,原有的倒影隨之粼粼而動,魚蟲驚走,鳥獸注目……這一系列的變化,都是審美者主動作用于審美對象的結果。
受動式即審美者未主動做出行為改變,而審美對象的某些特征或變化,引起了審美者體驗的變化。唐代詩人王維《山中》一詩寫道:
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7]
冬日天寒,水淺石清,山色空明,所以“空翠”。“山路元無雨”,“空翠”也本不會“濕衣”,但翠色濃郁,人行其間,仿佛全身都為之浸潤,因此會產生“濕人衣”之感。這是審美對象的特征作用于審美者而產生的一種奇妙感受。
在自然美育中,物我互動法可幫助審美者認識到自然景觀形態的無限豐富性,培養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使審美者敏感于自然的特征和變化,提升審美活動中人與自然的友好交互能力,塑造審美者對大自然的敬畏感,培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與情感。
(四)參照比較法
參照比較法,是審美者在自然審美中,將即時的審美體驗與審美理論、其他審美對象、他人審美經驗等相融合,在遷移、互驗、對比、融通中體味自然、探究蘊涵的審美方法。可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審美理論的參照遷移。自然景觀的欣賞可以從描繪自然景觀的藝術作品出發,將相應的藝術知識和藝術欣賞能力遷移到自然景觀的欣賞中去,使對自然景觀的欣賞有一個可借助的形式,便于對眼前的景色進行選擇處理和組織。[8]
第二種是審美對象的參照比較,也就是將即時的審美對象與其他審美對象作對照,以更準確地把握審美對象的特征。古人凝練出的“泰山天下雄”“華山天下險”“黃山天下奇”“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的經典美譽,就是在廣泛游覽,精心對比的基礎之上得出的。在進行審美對象的參照比較時,須有足夠量的自然審美經驗的積淀。有了這樣的基礎,才能夠貫通各個審美對象,在總體上準確把握各審美對象的核心特征。
第三種是審美經驗的參照比較。這可以借助經典的文藝作品進行。在描繪自然的文藝作品中,可體會到作者的審美方式和體驗,將其同審美者自身的直接體驗相對照、相融合,就容易提升認識,增進理解,產生更深層次的感想。比如,在登上東岳之巔時,可以參照杜甫的詩句,體會詩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宏闊氣度。在多態的瀑布前,融入對古曲《流水》的意象體驗。將創作者與審美者自身的審美體驗、人生經驗進行比較、融通之后,往往會產生新的更高層次的感受。
(五)心理機能法
1.心境調控式
心境是人的持續時間較長的情緒狀態。只有保持良好的心境,才有益于自然審美活動的進行,使審美者專注于自然,陶醉于自然,充分領略自然之美。那么怎樣保持良好的審美心境呢?中國古典美學的“虛靜”理論或有助于此。“虛靜”理論包括三個層面:一虛,虛廓心靈,滌蕩情懷,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在無我無物的雙重否定中創造一個自由寧定的審美主體。二靜,這是審美感知中最靜的一剎那,一個富于包孕的片刻和觀照永恒的瞬間。這個心靈的“空筐”是以專注的神情、曠遠的情懷、細微的體味能力和從容自適的藝術感知為經緯而編織成的。三動,“虛靜”不是虛無消極的等待,它以無載動有,以靜追求動,以平如大漠的情懷去擁抱勃郁奔騰的大千,去迎接騰挪不絕的美和噴涌而至的靈感。[9]自然審美正是要在虛空心靈,寧定專注的心境下,去尋求和包容無限的自然之美。
2.情感調動式
審美者的情感狀態對審美活動有直接影響,會給審美對象染上相應的情感色彩,給審美氛圍蒙上不同的情感基調。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言:“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確,在強烈的情感參與下,審美者往往容易進入“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審美狀態。這正是情感在自然審美中的擴散作用。情感調動式審美能夠擴大審美者的主觀感受,使審美者不僅是在“游物”,更是在“游心”,是心與物的融合,情與景的交糅,主體與自然的合一。
在自然美育中,情感因素具有多方面的作用:第一,情感因素能夠影響審美者的審美決策。審美者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喜好決定是否將某個或某類自然物納入審美視野。通過影響審美者審美意愿的強弱,情感因素起到了篩選審美對象的作用。第二,情感因素參與的深淺程度直接影響到審美動力的強弱,進而影響審美活動所能達到的層次。積極的情感促進審美活動的開展,幫助審美者進入更深層次的審美狀態,消極的情感則會阻礙甚至中斷審美活動。第三,情感因素的適當調動可使審美者的主觀感受擴大化。因為這樣有利于創造出情景交融的情境,這種情境又會反過來作用于審美者,擴大審美者的主觀感受。第四,情感的參與可以激發和促進審美者的聯想、想象等其他心理機能的發揮。總之,美育工作者應當重視情感的多方面作用,積極培養審美者優良的情感調動能力,使審美者既能以情入景,又能以情馭景,以理馭情,始終保持情感因素參與的適度狀態。
3.聯想、想象式
通過聯想和想象,審美者可以開辟出更加自由的心理空間。李白“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豪邁、王維“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的壯闊,都具有這樣的效果。充分運用聯想和想象,能夠使審美者“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神與物游”,將即時的自然審美經驗與過往的生活經驗建立起廣泛聯系,在多種事物的交融與相互作用下,獲得自然審美的高峰體驗。
具體地講,聯想和想象在自然美育中具有以下作用:第一,通過聯想和想象,能夠發現審美對象本身更豐富的美學內涵,增添更多的審美趣味。第二,聯想和想象可以擴大審美范圍,使參與到審美活動中來的審美對象不僅包括眼前的景物,還包含了聯想和想象所觸及的一切事物,不僅涉及所見的自然景物,還可容納進其他自然的、社會文化的事物。第三,聯想和想象具有心理上的超越性,這種心靈上的超越又能作用于審美者的情感,從而使人的情感得到更進一步的喚出,使審美者的體驗得到升華。“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詩句中都可見出這種效果。第四,聯想和想象能夠提升審美層次,使審美活動不止于景物的形式層面,而是會進入諸如宇宙審美、社會人生審美等高層次狀態之中。“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莊子·列御寇》)的宇宙感、“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王安石《登飛來峰》)的體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周敦頤《愛蓮說》)的境界、“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慨嘆中,都可見出這種功能。總之,聯想和想象能夠突破審美中的諸多局限,使審美者跨越時空,騁心于無限。
(六)思想感悟法
思想感悟法是審美者欣賞自然對象時,經過一段時間的復雜心理活動,最后獲得思想上感悟的審美方法。這樣的審美往往包含著深沉的宇宙感、歷史感或人生感。蘇軾的《前赤壁賦》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10]
人生遭遇的困苦沉積于胸,不得解脫,但經過自然審美時的心靈激蕩,作者最終參悟了宇宙人生的道理,使思想和情感得到了升華。
思想感悟法在自然美育中有著特殊意義。在這樣的審美過程中,思想的閃現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這往往是審美者苦苦尋求的某種答案。審美者的這種尋求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定向尋求,即審美者先產生了一些人生困惑等疑問,不得解脫后,付諸自然審美,主動尋求答案。另一種是非定向尋求,即審美者本身沒有特定尋求的答案,而是在自然審美中對某方面有了頓悟。但不管哪種類型,尋求的答案并非總是招之即來,它的出現需要審美者有深切的人生體察,有敏銳的自然觀察,對萬事萬物的相似性和規律性有足夠的敏感度。思想感悟法屬于較高層次的自然審美方法,因為這不僅是在審自然之美,更是在審宇宙和人生之美。
(七)科學探尋法
科學探尋法是審美者通過觀察自然界的科學現象,探索科學規律,以體察其中的科學美的審美方法。盧梭曾談及感官愉悅后的沉思:徜徉在自然中觀察它們,對其不同的特性進行比較,標出其相互間的聯系和差異,最后觀察其結構探索這些生命有機體的生長過程及其活動規律,探索它們的普遍規律和不同結構的原因和結果。[11]在這樣的過程中,能夠領略到事物發展的科學美。
自然美育中,應注意到科學探尋法的特點。首先,它有明顯的理性因素的參與,因為這種審美須建立在對自然事物科學理性認識的基礎之上。其次,科學探尋法運用的目的在于探求自然客觀規律的科學美。這與科學工作者純粹的自然科學研究活動不同,這種審美活動要在自然規律當中發現出科學美。自然景觀中包含著科學的秩序或法則,審美者須具有相應的自然科學知識基礎,才能夠按照自然界特點和規律來觀賞自然,發現和感受自然中的科學美。
(八)作品依托法
作品依托法是通過欣賞文藝作品以間接審美自然的方法。我國古代盛行的“臥游”之法就屬于此類。“臥游”是以欣賞山水畫代替親臨游賞的審美方式。“臥游”在魏晉時期就已十分盛行,當時的交通條件十分落后,難以進行經常性的遠游賞玩活動,同時,玄學思想極為盛行,許多文人雅士極力推崇之,于是漸漸興起了通過欣賞山水畫來感受山水風光的審美方式。宗炳在《畫山水序》中寫道:“于是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這是典型的“臥游”法的運用。
作品依托法雖然難以帶來親臨自然的真實感,但它也有一些顯著優點。首先,作品依托法不會像親臨式審美那樣有時間、空間、天氣、心境等方面的限制。審美者可任意擇時擇地而游,不用擔心天氣的變化,也不須等到心定氣閑、雜念空無之時。其次,作品依托法可以與其他審美活動同步進行。審美者可一面“拂觴鳴琴”,一面“披圖幽對”,兩不相擾。再者,作品依托法極富時空的跨越性,審美跳躍度很高。須臾之間便能“坐究四荒”,足不出戶即可縱覽四海。
作品依托法在美育中有著特殊意義,它可以彌補審美者在某些審美條件上的不足。比如,在交通條件欠佳、審美者身體條件受限的情況下,作品依托法卻可為審美者“暢游”自然提供可能,為審美者的情感抒發與精神寄托開辟通道。
(九)科技憑借法
科技憑借法是審美者憑借一定的科學技術條件間接審美自然的方法。基于虛擬現實技術的審美是當前科技審美法的一種重要形態。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VR)是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生成與一定范圍真實環境在視、聽、觸感等方面近似的數字化環境。它是人類在探索自然、認識自然過程中創造產生、逐步形成的一種用于認識自然、模擬自然,進而更好地適應和利用自然的科學方法和技術。[12]虛擬現實技術給審美者帶來了更逼真的、身臨其境般的審美體驗。VR的典型特征被概括為“3I”,即沉浸感(immersion)、交互性(interaction)和構想性(imagination)。其中沉浸感是指虛擬環境“欺騙”人體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多種感官,給參與者帶來臨場感;交互性是指在虛擬環境中提供參與者適人性化的人機操作界面和自然反饋;構想性是指通過沉浸感和交互性,使參與者隨著環境狀態和交互行為的變化而對未來產生構想,增強創想能力。[13]虛擬現實技術提供了一種高仿真、多視角、動態化、可交互的場景。虛擬技術的發展,還促成了“虛擬旅游”的出現。在業界,虛擬旅游是指利用計算機技術將現實中的旅游場景做成三維實景展示,使得游客能夠通過互聯網等多種媒體游覽虛擬的場景,獲得身臨其境的體驗。[14]可以憑借虛擬現實技術和網絡等手段,將旅游中的各個要素完全的進行展示,根據游客的意愿自由的選擇游玩線路、速度和視點。[15]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基于虛擬技術的自然審美定會得到更大發展。
科技憑借法在自然美育中有其獨特作用。首先,它使很多原本受某些因素限制的人能夠參與到自然審美活動中來。這部分人中有的是審美時間受限,工作繁忙,無暇遠途旅行;有的是資金條件受限,如學生群體、社會低收入群體等;還有的是身體條件受限,如殘障人士、行動不便的老年人等。其次,科技憑借法能使人進入很多現實中無法或難以到達的場景中。例如,在現實中我們很難近距離懸空觀察到峭壁懸崖,很難進入熱帶雨林深處目觸其內部景觀,但是憑借虛擬現實技術就可以輕松“實現”。科技的日新月異,不斷帶給人們新奇感和愉悅感,不斷拓展著人類的審美能力和審美空間,也使人們不斷產生新的審美期待,相信這種審美方法在自然美育中會發揮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十)回憶審美法
作品依托法和科技憑借法都借助了一些外在物質條件,回憶審美法則不必如此。回憶審美法是通過回憶來重拾先前審美經歷以“重游”自然的方法。唐代詩人白居易在《憶江南》中對江南自然美景的回憶,是回憶審美法的經典運用: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游!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復相逢![16]
審美者在回憶時,不但與審美對象有了時間的間隔,而且產生了人生經歷積累的變化。回憶中,審美者往往會得到高于原先直接經驗的審美體驗。當相隔較長時間,或是身體受到局限后,審美者難以重游故地,因此會對先前的審美經歷更加珍視。再者,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心理上,回憶都能夠于審美者和審美對象之間建立一種“距離”,這種距離會帶來一種純粹感,增強美的感受。此外,回憶中也往往會有更多情感的融入和更多記憶的參與,激發出審美者更高層次的思想和情感。由于時間上的間隔和主觀因素(如記憶)的變化,回憶中的審美經歷難免存在一些失真,但這樣的缺失性和模糊性,卻強化了審美者的主觀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