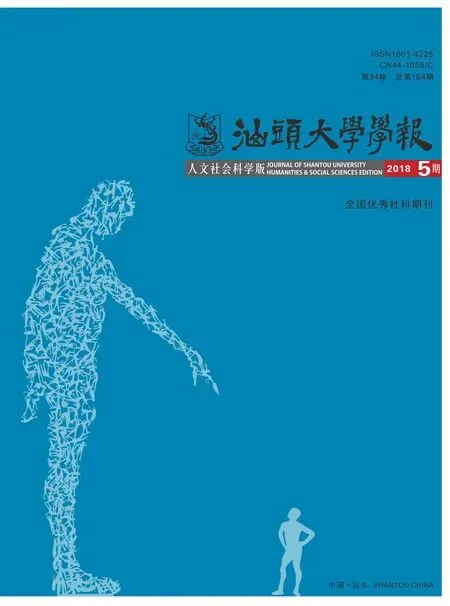論《創造月刊》之編輯思想
盧妙清
(肇慶學院學報編輯部,廣東 肇慶 526061)
創造社乃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與文學研究會并肩而立的兩大重要社團之一,其麾下辦有《創造》季刊《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創造周報》等十余種刊物。《創造月刊》以其關注社會民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作倡導及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介紹而在中國現代文壇眾多刊物中脫穎而出,獨樹一幟,引起了廣大文學青年的強烈共鳴,深受中國現代文學界的重視,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與其編輯思想是密切相關的。《創造月刊》的編輯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以刊濟世,促進社會變革
1926年3月,《創造月刊》創刊,由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出版發行;1929年1月,受國民黨政府查禁而被迫停刊,歷時近3年,共出版2卷18期。一開始由郁達夫、成仿吾、王獨清3位創造社主要老成員輪流擔任編輯,后來由于從日本留學歸來的馮乃超、李初梨、朱鏡我、彭康等新銳的加入并成立了文學部,其編輯工作便由文學部委員會負責。
在《創造月刊》中,郁達夫擔任第1卷的第1、2、5、6期的編輯,成仿吾擔任第 1卷的第3、4、11期的編輯,王獨清擔任第1卷7-10期的編輯,從第1卷第12期至第2卷第6期的具體編輯工作由文學部負責。雖然編輯者性情、風格迥異,但以刊濟世,關注社稷民生,促進社會變革的辦刊理念卻一以貫之。
首先,郁達夫率先提出借助刊物以鼓舞士氣,改革當時社會的不合理。他在創刊號中明確地闡述了《創造月刊》的辦刊宗旨:對那些正直而慘敗的人生戰士給予“安慰”和“同情”,但更重要的則在于呼吁廣大愛國文學青年來促進改革眼下的不合理社會[1]。由此可見,《創造月刊》并不是一份游離于社會之外的茶余飯后以資消遣的休閑雜志,其所負載的是辦刊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意識。自此,如何以同情和呼聲來促進改革當時的不合理社會,便成為《創造月刊》同人的一致追求。
其次,成仿吾從時代需求出發,主張通過《創造月刊》來傳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和創作革命文學,以更好地實現其變革社會的目的。他先是進一步指出《創造月刊》的二重使命:一是從事于以永恒的人性為基調的表現之創造,二是努力于同以永恒的人性為基調的生活之創造[2]。而后,隨著大革命結束,革命成為了知識分子所關心的主題,但在當時革命的現實需要與革命理論的匱乏卻形成了巨大反差。因此,革命理論的介紹及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創作有其獨特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成仿吾執編時,便逐步把《創造月刊》引入了傳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和革命文學創作的航道,刊發了大量在當時開革命文學理論風氣之先的重要文章和革命文學作品。
再次,王獨清接手《創造月刊》編輯工作時,進一步強調刊物命運與民眾、與時代緊密聯系的重要性。在王獨清看來,就像理論對實踐有指導作用一樣,文學對于時代也有一定的指引作用,所以,文學創作者應深入民眾,體驗民眾生活,重視文學創作的時代性、使命感;同時,他極力反對那些走向低級趣味的文藝刊物和作品,認為“這種病菌的低級趣味[3]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倒、清除。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他在《今后的本刊》中為《創造月刊》同人提出了三個努力方向:一是承受新時代將開展以前的朝氣;二是參加催促新時代早臨的戰線;三是準備好歡迎新時代的禮物。具體體現在《創造月刊》中便是,他一方面刊發了大量的國內外詩歌創作及理論介紹,包括段可情的《旅行列寧格勒》、許幸之的《牧歌》和馮乃超、沈起予等人的詩作及穆木天的《維尼及其詩歌》等論作介紹,以提高刊物品位和理論深度,這對促進中國現代早期詩歌創作繁榮和理論發展不無貢獻;另一方面積極響應成仿吾提出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變,刊發大量革命文學作品。
最后,以馮乃超為主導的文藝部負責編輯工作后,《創造月刊》更加貼近社會現實,更加旗幟鮮明地提出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主張。他們把《創造月刊》視為“戰斗的陣營”,而這陣營的設立目的一是襲擊敵人,二是互助同志,最終是為了“建設人類解放的藝術,建設無產階級的藝術”。其目標更明確,褒貶更分明,志向也更加遠大。因此,從文學部負責編輯工作以后,《創造月刊》的方向和風格都有了明顯的轉變,加強了對文藝界的批評,加強了對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理論的宣傳和譯介,創作上則多以普羅大眾及其生活為素材,更加貼近現實生活。
從上,我們可感受到《創造月刊》的某些發展演變軌跡,但以刊濟世,關注社稷民生,促進社會變革的宗旨貫穿始終,未曾改變。這也是該刊至今仍有其生命活力,仍為學界所重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動蕩不安,貧困閉塞。當時的人們不只物質生活貧瘠,精神上也是一片荒蕪,努力探索救國救民之路便成為擺在眾多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前的迫切問題。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成為《創造月刊》執編者的不二之選。
(一)翻譯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
創造社大多數成員如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早年都曾留學日本,而成為《創造月刊》文學部主要成員的馮乃超、朱鏡我等也曾就讀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社會學系,較早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創造月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方面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來實現。一是同人的譯介,這主要歸功于朱鏡我的努力。朱鏡我留日回國加入創造社后,致力于宣傳和介紹馬克思主義,曾翻譯恩格斯的著名經典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一譯著是中國最早出版的中文單行本,也是大革命失敗后中國最早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其意義不言而喻。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介紹主要來自重譯日文,所譯對象多為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倡導者和支持者,內容涉及藝術、文藝批評等方面。如先是重譯了《日俄藝術》第22輯所載的弗里契的《繪畫底馬克思主義的考察》一文,表達了對以線去傳達自己感觸的主理主義藝術家的認同。而其最重要的貢獻在于重譯了日本無產階級文藝批評家藏原惟人所翻譯的盧那察爾斯基的《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底任務之大綱》,刊發于《創造月刊》第2卷第6期,該文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觀,這一“很重要而富于示唆”的文章,對于關心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發展的文學家、評論家有很重要的參考和借鑒價值。同時,彭康、馮乃超、彭芮生等或以自著或以翻譯的方式,也通過《創造月刊》這一平臺從社會學、哲學等方面向國內文學界、理論界譯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大加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的力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的內容。
二是以連續摘登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主要觀點的方式來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創造月刊》連續摘錄了《哲學的貧困》、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與社會生活》等著作的主要觀點及盧那察爾斯基、柏林斯奇等人的經典論點,以饗讀者。這些論點在今天也許不足為奇,但在當時卻著實令讀者耳目一新,爭相購閱。
三是對即將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系列著作進行預告式的宣傳和介紹,對讀者的購買和選擇起到指導性作用。如對屈章所翻譯的《歷史的唯物主義》一書的出版預告既包括著者的學術背景、譯著的內容章節和特色,也指出了譯者的特點及譯著的適用范圍、意義所在,對研究者及感興趣之人的選擇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較之單篇論文,著作更具有系統性和完整性,因此,《創造月刊》還對林伯修所譯的《舊唯物論底克服》、彭康所著的《前奏曲》、彭芮生所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本原理》等著作進行出版預告,以給讀者提供更加豐富而多樣的選擇。
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時尚未為國人所熟知,對其譯介也尚處于探索階段,譯者多為現學現用,但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所做的努力不可抹煞。
(二)大力譯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創造月刊》在譯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上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宣傳、介紹革命文學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伴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世界上第一個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正式建立,為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從服務中國革命出發,介紹更多的為爭取民族解放而斗爭的、以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為題材的文學,成為當時的迫切需要。由于中俄兩國在社會背景、發展道路上的相似,以及俄國無產階級文學家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及其關愛弱小、關愛主權的文學主題,引起了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關注。因此,《創造月刊》上雖然也介紹了法國等一些國家的作家作品,如《維尼及其詩歌》《法國文學的特質》《巴比塞之思想及其文藝》等,但其編者卻主要把目光投向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如蔣光慈的《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這一長文分5期刊出,是國內讀者了解、把握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關系的一篇重要文章。而其中又著重介紹高爾基,嘉生譯自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倭羅夫斯奇所著的《高爾基論》及李初梨譯自塞拉菲莫維奇所著的《高爾基是同我們一道的嗎》,這些對尚不了解高爾基的中國社會是必不可少的介紹。譯介的目的很明顯,即在于給國內愛國青年以啟迪,創作出更多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品。對此,馮乃超也曾坦言自己所撰寫的《革命戲劇家梅葉荷特的足跡》介紹了戲劇巨匠梅葉荷特對于俄國戲劇界的偉大貢獻,其目的在于希望對今后的中國革命戲劇運動發展有所幫助。由此,也可明確地看出《創造月刊》編者們的態度: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歡迎和擁戴,對“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排斥和抨擊。
二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品的翻譯。這主要基于執編者認識到有必要向落后閉塞的現代中國介紹海外新興文學,因此,從第2卷第1期開始,《創造月刊》逐漸增加了對國外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品的譯介。其譯介表現出四個特點:(1)所譯作品多為無產階級作家所創;(2)體裁多樣化,包括小說、戲劇、詩歌、童話等;(3)范圍涉及日本、德國、美國、匈牙利等多個國家;(4)主題多為反映弱者、被壓迫者的反抗和不屈。如日本無產階級女作家松田解子的小說《礦坑姑娘》、無產者藝術聯盟成員之一的上野壯夫的詩歌《讀壁報的人們》、藤森成吉的小品文《不拍手的人》等都在譯介之列。而最重要的也是對《創造月刊》同人影響最大的則在于戲劇方面的翻譯,李鐵聲翻譯了德國劇作家恩斯特·托勒爾的七場劇——《群眾=人》這一反映20世紀的社會革命劇,李初梨翻譯了威特福格爾的劇本《逃亡者》,與前文的戲劇理論譯介相結合,目的在于促進中國革命戲劇運動的發展和繁榮。這些作品多數是第一次被譯成中文,對國內渴望了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發展狀況以及想要創作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優秀作品的進步青年來說,是非常難得的借鑒對象。
三、倡導與創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創造月刊》創刊于1926年3月,在其生存、發展、壯大的前后幾年間,國內形勢非常嚴峻,創造社部分主要成員意識到文化工作者跟上時代步伐的重要性,所以,有的從事實際革命工作去了,如郭沫若;而大部分人也開始傾向革命,如成仿吾、李初梨、馮乃超、朱鏡我、彭康等,表現在文藝工作上則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與創作。
(一)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建設
《創造月刊》同人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上的建設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明確創作內容為反映無產階級的生活。
其次,主張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以上兩點主要見于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和李初梨的《對于所謂“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底抬頭,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二文,前者倡導文學“是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后者指出無產階級文學不只是“為勞苦群眾而作”,也是為一切被壓迫層而作,強調無產階級革命作家應該用嚴正的寫實主義的態度去描寫觀察世界所得的結果。
第三,強調創作者獲得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重要性。成仿吾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中,號召創作者“努力要獲得階級意識”“努力把握唯物的辯證法的方法”。麥克昂在《桌子的跳舞》中也指出:“我們的文學家假如有無產階級的精神,那我們的文壇一定會有進步”。
第四,強調文學的時代性以及文藝對社會的變革作用。偉大的作品都是有時代精神的,成仿吾在《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全部的批評之必要——如何才能轉換方向的考察》等文中指出“文藝決不能與社會的關系分離,也決不應止于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應該積極地成為變革社會的手段”。
《創造月刊》同人認識到文學理論建設的重要性,“正確的理論絕不是空虛的,它是轟破敵軍的強有力的炮火”[4]。因此,圍繞革命文學產生的時代要求、文學與時代和社會生活結合的必要性、作家獲得階級意識的重要性以及提倡寫實主義手法等方面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理論建設問題展開了系統討論。在自覺與不自覺中,他們已把《創造月刊》的發展與普羅列塔利亞藝術運動的發展等同起來。
(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作
《創造月刊》共發文204篇(卷首語、編輯后記等除外),其中與“革命文學”有關的有137篇,占比67%,可見執編者對革命文學創作的重視。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除了理論上的建樹,創作上也收獲頗豐,主要表現在戲劇、小說、詩歌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創造月刊》同人認為“在革命期底武器底藝術中,演劇占有最重要底位置”,這是理論上及先進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了的[5]。所以,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戲劇創作方面進行了努力嘗試,主題多為反映無產階級在苦難中的掙扎及其覺醒。如鄭伯奇創作的《軌道》,工人們認識到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對警察說“你們完全和我們是利害一致的”,呼吁警察聯合起來抵抗日兵。值得一提的還有趙伯顏的《沙鍋》和李白英的《資本輪下的分娩》二部劇本,前者通過留學生、其妻、其友的對話記錄了在饑寒交迫的冬天里,連一碗填肚子的稀飯也沒有的窘況,喊出了“不情愿做弱者,我們要活!我們要吃飯”的呼聲;后者則通過青年、群眾與資本家進行斗爭的劇情,得出了“誰是世界上的創造者?只有我們勞苦的工農”的結論。
小說上,主要通過刻畫窮人和苦難者的饑寒交迫、前途茫然黑暗的生活,反映了他們對解放和光明的渴望。這方面首推龔冰廬的作品,題材多為礦工生活。由于當過礦工,他的《碳礦夫》系列小說真摯感人,其小說與伯顏的戲曲被同人譽為“有自信的力作”。從其作品中,讀者能感受到“無產者一代的希望是怎樣實現出來,他們的幸福從哪里可以奪回,他們的生活感情是怎么樣”[6]。得到了同人的好評:冰廬的創作愈加發揮其雄厚的勢力,他所描寫的是直接的感情,不是模擬的東西[7]。汪錫鵬的《窮人的妻》如實地描寫了窮人的生活,給讀者們以很難得的參考;趙伯顏的《牛》,敘述了一位洋車夫為了五塊大洋,在半個小時內跑完20里路,最后倒地而死的故事,生動地再現了窮苦百姓如牛馬般的生活。
《創造月刊》上還刊發了大量的無產階級革命詩作,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馮乃超的詩作。馮乃超早期詩歌創作受象征主義影響,帶有朦朧美和感傷色彩,但致力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建設后,其詩作明顯地表現出與現實接軌,觀照生活,憧憬未來的特點。此期他發表了《快走》《今日的歌》《憂愁的中國》等革命詩作。《快走》一詩以牛喻人,表達了只有加快腳下的步伐,才能早日迎接光明和自由的看法。《憂愁的中國》則表達了詩人放下包袱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光明和幸福的堅定信念,“忘掉吧,昨日的憂愁與悲哀,今日的頹唐/然而,明日的太陽,光明,自由,幸福再不是遠方的希望”。
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品充滿了革命情緒,多以社會底層民眾(工人、貧苦百姓)、青年知識分子等為描寫對象,以其生活為題材,刻畫了他們的苦難和屈辱,表達了他們的追求和向往,呼吁祖國強大起來,讓民眾早日擺脫苦難,過上幸福生活。
四、注重培養文學青年,擴大刊物影響
(一)注重培養進步文學青年
1926年《創造月刊》出版時,其編者中年紀最長的郁達夫30歲,成仿吾29歲,王獨清28歲,文學部主要成員的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都只有25歲,正處于血氣方剛的青年階段,所以,他們天然地把讀者定位為文學青年,其辦刊的宗旨便是向廣大好學上進的文學青年宣傳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激發廣大文學青年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共同促進社會的變革。
1.他們把與青年文藝家的直接聯絡作為解放《創造月刊》的根本方針,可見對青年讀者的重視。馮乃超在翻譯日本上野壯夫《讀壁報的人們》一詩時,坦言翻譯的動機是為年青詩人們提供參考。并應許多青年文藝家的要求而新辟“詩欄”以供青年詩人的試作,為登載者呈送雜志和書券。
2.不唯古是從,鼓勵青年新興勢力的增長。正由于這樣,《創造月刊》所刊作品受到青年作家誠摯而熱烈的歡迎。
3.大量刊發缺乏資產階級“文藝素養”的青年作家作品,表達其“革命的熱情”,鼓勵他們努力創作。
4.通過開展征文活動等方式來激發愛國青年的創作熱情,汪錫鵬《窮人的妻子》一文即為征文作品。通過讀者來稿選登、答疑等方式,了解讀者需求和意見,不斷完善刊物。
(二)多方努力,擴大刊物影響
《創造月刊》主要通過以下努力來擴大刊物的影響:
1.通過論爭的方式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既有創造社同人間的論爭,也有與其他社團間的論爭,如對新月社的徐志摩、梁實秋等的批評,對茅盾寫實文學論的質疑,與魯迅關于革命文學認識的交鋒等,使其成為20世紀20年代末革命文學論爭的重要陣地[8]。這些都是當時文壇關注的熱點和焦點所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促進理論的進步和刊物的發展。
2.增設欄目,不斷豐富刊物內容。集國內外理論譯介、文學評論、作品創作于一體,且不局限于文藝,美術、音樂、演戲都是其提倡的事業。
3.有明確的發展計劃,如紙面之擴張,部門之增加,討論會場之增設,致力于刊物從少數人的團體解放出來成為民眾的共有物。還計劃“增大本志地域的擴張及本志的部數,增加本志的內容,提高本志的水準”,呼吁廣大青年“對于本志之一萬部突破運動”加以積極的支持[9],其影響和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4.從細節上完善刊物。如封面的設置變化,一開始的封面較為寫意和浪漫,倡導革命文學之后,其封面主圖是一個青年正在打造武器,更契合刊物內容和風格。其他如卷首語、編輯后記的開設,封三、封四的宣傳廣告,前一期對下一期的預告,這些都對吸引讀者的關注起到了重要作用,足見執編者的細心和周全。
從《創造月刊》中我們可明顯地感受到,其同人對文藝進步和社會進步的迫切追求,對社會現實的直面和勇敢擔當。他們在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建設和創作實踐等方面的率先垂范,功不可沒;而曾經活躍在《創造月刊》上的眾多作者至今之所以仍為學界所關注,如郭沫若、郁達夫、穆木天、沈起予等人的作品至今仍為學界的重要研究對象,是與上述編輯思想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