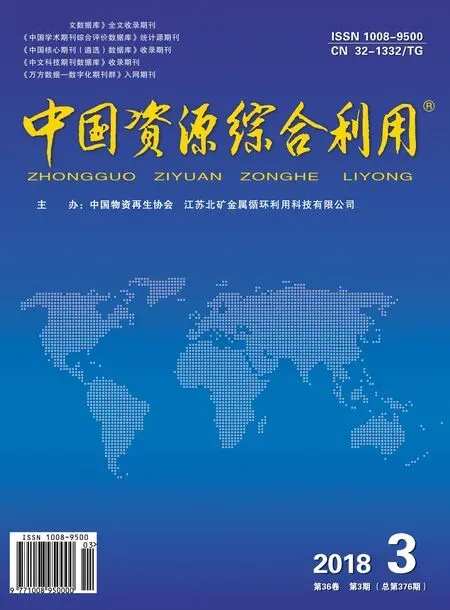我國礦產資源利用現狀及對策研究
吳 翟
(江西財經大學,南昌 330013)
1 礦產資源及其戰略價值簡析
1.1 礦產儲量有限,運用廣泛,潛在價值極大
礦產資源是埋藏于地下或裸露于地表的相關礦產的總稱,包括以石油為代表的動力資源、以稀土為代表的金屬資源、以石灰石為代表的非金屬礦產等。礦產資源屬不可再生能源,其儲量有限。世界上用途較為廣泛、大量開發利用的礦產資源大致有80種,其中,部分礦產資源相較稀缺,且廣泛應用于航天、軍事、動力等方面,具有較強的戰略意義,對國家經濟發展或社會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分布狀況、剩余儲量、開發利用現狀及資源的保護引發了政府及有關人士的關注和警惕。
1.2 以稀土為代表的稀有礦產資源戰略價值顯著
以稀土資源為例,稀土資源蘊含元素種類豐富,產地主要分布于我國江西、四川、內蒙古等地,儲藏量世界范圍而言極為稀少,其在石油、化工、冶金、紡織、陶瓷、玻璃、永磁材料等領域都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是相關催化劑、超導體、發光劑等的首選材料,被冠以“工業維生素”“工業味精”的美譽。稀土同樣被廣泛運用于核動力、巡航導彈等軍事領域,在軍事領域的運用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國家間的戰爭全局起著重要作用,有著極強的戰略價值。我國稀土資源全球儲量第一,但近年來人們無節制開采和大量出口,2005年我國稀土開采量占全球的96%,使得我國稀土資源受到極大侵害。
1.3 礦產資源枯竭日益突出,保護刻不容緩
戰略性礦產資源較為稀缺,在軍事、經濟建設等領域發揮著巨大作用,關乎國家生死存亡,其安全問題關乎國家生產發展。當今社會不斷發展變化,波譎云詭,機遇與危機并存,經濟制裁、顏色革命甚至武裝斗爭在世界的角落仍然時有發生。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實力日漸雄厚,逐步引發各方關注,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大量礦產資源不斷消耗,部分礦產資源開采水平不斷降低,有枯竭趨勢。在此大背景下,戰略性礦產資源的保護問題更應該為人們所重視、時刻警惕。
2 我國礦產資源利用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2.1 礦產行業中小型民營資本滲透嚴重,開采較不規范,利用率較低
我國礦產資源星羅棋布,分布較為廣泛,蘊藏水平較不集中,由此造成了礦產開發行業難以形成大規模壟斷格局,中小型民營資本滲透嚴重[1]。該行業多數企業為本土礦產開發企業,規模相對較小,多為民營資本注入,此類企業大多采用租賃等手段依托當地政府獲得礦產開采權限。此類礦產具有相對地域限制,且規模相對較小,獲利空間有限,不利于大型資本進入。該類企業限于規模和資金水平,管理水平不完善,礦產開采缺乏相關技術支持,且缺乏相應安全防護措施,為追求經濟性考慮,大多雇傭當地村民進行作業。作業人員素質水平較差,缺乏相關培訓,資源開發極不規范,開放缺乏科學指導,多采用土法爆破,對資源造成極大破壞,礦產資源利用遠低于世界標準水平,且安全風險十分顯著。
2.2 礦產資源開發缺乏可持續性,對當地生態造成較大破壞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礦產資源的海量缺口,大量資源開采企業為追求短期經濟效益,倉促上馬,對相關資源全力開發,對相關礦產資源不加保留地進行開發利用,缺乏可持續發展觀念,部分城市資源枯竭情況嚴重,當地生態環境受到較大破壞。以江西省萍鄉市為例,萍鄉是江南煤炭的重要生產基地,有100多年的礦產資源開發歷史,當地礦產資源開發由于缺乏可持續性,極大地破壞了其生態環境,礦產開采對當地植被和覆蓋土層造成了極大破壞,屬于典型的礦產資源枯竭城市[2]。地質結構疏松,地底遍布坑道,極易造成土地房屋塌方,土地退化情況嚴重,生物豐度指數、植被覆蓋指數等指標較低,當地生態環境受到了較大破壞[3]。
2.3 缺乏相應法律監管,亂采亂挖、非法開采情況嚴重
我國礦產資源開發亂采亂挖現象嚴重,且大多屬于無證經營、當地人非法開采,缺乏相應法律監管。該現狀形成的原因有:相關礦藏的地理位置較為偏僻,較難進行有效監管,同時監管措施不夠完善,缺乏統一領導,多頭監管部門較難形成合力進行集中治理。我國礦藏大多存在于山區等偏遠地帶或農村地區,村民較缺乏法律意識,宗族關鍵較重,村干部及鄉鎮干部行政水平較低,不具備執法權力,對亂采亂挖難以進行有效監管。部分黑礦開采采取檢查時停業,不查時開業等投機手段,較難真正監管。礦產資源開發整個流程受到多部門多頭管理,相關部門不具備行政或處罰權限,發現問題后較難進行有效整治。
2.4 大量礦產資源用于出口,資源流失情況較為嚴重
改革開放早期,我國曾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之一。改革開發初期,由于歷史局限性等因素,礦產資源所在政府及當地居民未能及時認識到礦產資源的巨大戰略價值,缺乏有效判斷,以較低價格大量出口礦產資源,給我國礦產資源造成極大損失。隨著相關政令的出臺以及群眾知識水平的日益提高,信息不對稱水平逐漸降低,部分商人出于短期經濟利益考慮,在發達國家大規模停止開采本國資源并著眼于國外市場的大背景下,大量開采礦產資源進行出口以換取經濟利益,甚至不惜對部分限制礦產進行走私,走上違法犯罪道路,極大加劇了我國礦產資源的消耗速率。
3 我國礦產資源利用問題的相關建議
3.1 健全監管機制,實行準入措施,打擊非法開采,加強動態監管
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在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方面仍較薄弱,相關法條較為陳舊,不能滿足現今的監督監管要求[4]。政府及相關立法部門應建立健全礦產資源開發監管機制,嚴厲打擊非法開采、亂開亂采行為,著力整頓礦產開發行業,建立長效機制,進行動態監管,保證礦產開發能夠合法合規,避免相關資源受到額外損耗。同時,相關監管部門應對該行業實行準入措施,通過注冊制等手段,使得開采企業能夠初步具備相應資質,促進后續監管活動的有效開展。
3.2 大力推廣一體化循環經濟模式,推動可持續發展
鑒于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對環境造成的較大破壞,政府應大力推廣一體化循環經濟模式進行開采作業,充分運用綠色理念,盡可能減少對環境帶來的破壞,邊開采邊治理,使環境影響降到最低。在宏觀方面,相關輿論應加強引導,積極宣傳環保理念,政府應通過對循環經濟模式企業進行政策傾斜等方式推動綠色礦業發展。地方政府部門應注重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理念,通過對礦產開發企業的數量及其規模的控制達到控制資源開發速率的目的,同時充分關注資源用途,做到精準利用,可持續發展。
3.3 著力改進資源開采工藝,提高資源利用水平
當前,我國礦產資源開發工藝和效率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由此造成的資源利用不充分令人痛心疾首。同時,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工藝等技術的進步已在環境保護方面產生了較為積極的成果[5]。著眼于長期效益,相關企業應加大研發支出,政府相關部門可通過調整稅收結構等手段對礦業企業改進資源利用工藝進行鼓勵,著力提高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工藝水平,尋找更為清潔有效的資源利用模式以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提升資源開發利用的管理效率,同時減少其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6]。
參考文獻
1 陳從喜,吳 琪,李 政,等.2016年中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形勢分析[J].礦產保護與利用,2017,(5):1-7.
2 《萍鄉年鑒》編纂委員會.萍鄉年鑒[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
3 劉 澍.萍鄉市生態環境質量狀況及變化研究[J].環境科學與管理,2016,41(10):142-147.
4 劉天科,靳利飛.中國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問題探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1):424-429.
5 陳 軍,成金華.中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環境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3):111-119.
6 畢獻武,董少花.我國礦產資源高效清潔利用進展與展望[J].礦物巖石地球化學通報,2014,33(1):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