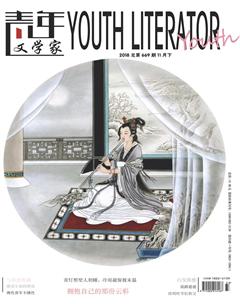盛唐遺風(fēng) 一座活著的古城
文明月
——我不曾見過草色侵官道,花枝出院墻的秀美城池;也未曾感受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驚心壯美。我只靜靜的走過,聽見鞋底摩擦青石板上細碎沙礫的低語,弱柳拂過肩頭青絲的喃呢,看見輕輕掉落在神社屋檐的樹葉,和你那雙流淌著風(fēng)情,望穿秋水道不盡離愁別緒的眼睛。
幼年時候,父親牽著我的手,走進大唐芙蓉園。我只依稀記得樹木蔥郁,亭臺樓閣被各式的彩燈包圍。一切都很新,椯木新刷的油漆還有微微的不平整的顆粒,灰色石板包裹著樓臺的外緣,連石間的細縫都很整齊。深紅色的木料整齊排列在烏青的穹頂下,正脊上的裝飾也嶄新的如水面掀起的浪花。別的,再沒有其他的印象。父親說,這個園子是盛唐的影子。我默然。因為園子只是園子,供人一觀便走了,沒有煙火氣,就像是印在書頁里的標(biāo)本,絢爛但沒有生命。
也是機緣,我與同伴踏上了東瀛的土地。或許是新的環(huán)境,也或許是無意闖入不一樣的生活,竟然莫名的平靜與安定,沒有工作生活中的焦慮與匆忙,就像回到了很久很久的過去。我們看到田間翠色欲滴的稻秧,看見黑胡桃色的建筑錯落在山間,那建筑不是標(biāo)本式的呆板凝滯,而是煥活的有生命力的蒼勁質(zhì)樸。像是年邁的但是卻精神矍鑠的老人,縱使是溝壑縱橫身形枯槁,但卻掩蓋不了眼神的明亮和思路的清晰。
京都是個值得去的地方。回想起來竟有一種時光空間交錯的錯覺。京都和洛陽竟然意外的相似。我不曾到過唐的洛陽,可是當(dāng)我看見一枝不起眼的樹枝穿過木質(zhì)的建筑,悄悄地伸開枝蔓,輕輕的吐翠的時候,看著細窄的街道旁一些有些模糊的粗糲石像,看見屋檐整齊排列的瓦片把流動的藍天裁剪出細致的花邊,聽見小橋下流水潺潺,不擾的唱著叮咚的小曲,白云流淌在水里,輕輕一瞥不知道那戶的男丁綁著毛巾在頭上,荷著重物,持著紙扇,在太陽的擁抱下噓噓氣喘,那紙扇上畫著神奈川海浪,在炎熱的夏天泛起一絲不易察覺的涼意。我覺得這就是了,就是洛陽了。盛唐時,倭國拜服,遣唐使一波又一波的來到洛陽,來一覽繁華洛陽的靜美。他們把所看到的一切視若珍寶,好生收藏,默默地帶回國去效仿。那時的唐像是個風(fēng)情萬種的女子,揮一揮輕紗,抿嘴不露齒的一笑就可以讓天下浮想聯(lián)翩。那時的東瀛像一個膽小的瘦削的侍女,小心翼翼地模仿著這一切。每一個腳步,每一個動作無比認(rèn)真,認(rèn)真到生硬。如此便帶回國家,仔細練習(xí)。
我們經(jīng)過祗園的時候,走過起起伏伏的小徑,街道周遭的門前都很干凈,還擺著一棵棵或大或小的植物。我想起《藝伎回憶錄》里那個濕濕的袛園,撐著油紙傘的花魁伸著長長的脖頸,費力卻優(yōu)雅的提著華麗的和服,生怕雨水弄污了衣裙。如今袛園晴朗,陽光是透明的。好像那透明里折射了過去那個濕濕的雨季。在去八坂神社的路上,偶遇一個正在出街的花魁。黛眉,白妝,點絳唇,還有那繁復(fù)的嵌滿裝飾的頭飾。似曾相識,似那舊書里泛黃宣紙上的仕女。只不過仕女們云淡風(fēng)輕的賞花戲耍,花魁們隆重嚴(yán)謹(jǐn)?shù)男凶弑硌荩雍裰睾蜐庥簟?jù)說遣唐使們參觀唐歌舞伎表演的時候,不巧天色變暗,又一時難尋合適的光,于是便讓舞女們化白臉,化濃妝好讓人看清。這一化,倒是被遣唐使們記了去,以為那是當(dāng)時盛行的妝容,至此東瀛的歌舞伎便以白妝入俗,嘴唇上的一點紅,正是盛唐的遺風(fēng)。我看不清花魁的目光,輾轉(zhuǎn)的、迷離的、堅定的、輕蔑的,像是同過去的過去在進行一場無聲對話。我們在路邊靜靜地瞧著這場莊嚴(yán)又華麗的儀式,不做聲,怕驚擾了那斑駁的未曾開啟的歲月。
走在京都曲曲折折的老巷子里,想起歐陽修說曾為洛陽花下客,芳野雖晚不須嗟。或者是劉禹錫口中的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jié)動京城。牡丹華貴絢麗奪目,碩大的花冠和艷麗飽滿的顏色驕傲地向世人展示它驚世駭俗的美麗。艷冠群芳是她的代名詞,那種由內(nèi)而外的自信與淡定好像就再說,世人見我要叩拜,我才是當(dāng)之無愧的花中之王。那時的洛陽也保有如此的自信。可是在京都,看不到驚艷奪目的牡丹,看到的都是細碎的探出城墻的花朵,或是路邊不經(jīng)意的各色小花,低調(diào)的恬淡的盛開或輕輕靜靜的凋謝。一切都是那么不經(jīng)意,但卻又那么自然。就像過去了很多年,東瀛毅然把櫻花作為國花,千朵萬朵壓枝頭,不單單突出哪一朵,是否也與性格有關(guān),恬靜淡然,又緊密團結(jié)。我們此行并沒有見到那云蒸霞蔚的櫻花。看到的都是寧靜舒爽的秀美。
最讓我驚奇的是,京都的街道上沒有垃圾桶,所產(chǎn)生的垃圾都要由自己隨身帶到住所再丟棄。可是縱使這樣,街道也干凈的如同剛剛打掃過。同樣在街上也鮮有吃東西的人。京都不大,偶有看到街道上在維修的建筑竟然也是用塑料板材包裹得嚴(yán)嚴(yán)實實的,不細看竟不知道這里在修繕,沒有粉塵沒有噪音,我也很好奇是怎么做到的。不打擾別人,不驚擾寧靜,小心翼翼地踩著自己不變的腳步,過著自己不擾人的生活,大概這也是他們的生活哲學(xué)。我不清楚盛唐的洛陽的生活是否也如此平靜安逸,但是從京都的生活中卻可看見人們的腳步慢了下來。我們在龍安寺檐廊下的平臺上席地而坐,中國建筑東渡過來以后結(jié)合季節(jié)和地理原因有了一些變化,不過大體上還是很類似的。石庭被菜籽油浸潤的土墻圍著,時間將油漬轉(zhuǎn)化成了土墻上變化莫測的圖案,院內(nèi)是枯山水景觀,有15塊組合擺放的石頭。可是不管從什么角度,都只能看到14塊。細砂在院內(nèi)被耙成了或同心圓或波浪線的整齊線條。枯山水便由此誕生。沒有翠植,沒有假山,甚至沒有真正的水。游客們在這里坐著靜靜地看著眼前的一切,所衍生的想法或者是思索都是個人自己的所得,也是這些景物給人們的不同禮物。大體上是受漢傳佛教禪宗文化的影響,修行已達到心靈的凈土。
唐朝是出了名的飄逸,不然也不會出那么多杰出的詩人和精美娟秀的藝術(shù)作品。在沒有電子產(chǎn)品的時代,人們只能通過吟詩作畫討論人生的情懷,只能縱身歌酒去體會人生苦憂。所以他們活得很認(rèn)真,活得很詩意。慢下來體會生活的種種,與人為善,詩意的棲居。在去清水寺的路上途經(jīng)茶鋪,看茶藝師繁瑣而精細的儀式,茶粉研磨的細膩,烹出綠色的茶湯。在這個過程中陶冶性情培養(yǎng)道德觀和審美觀。茶道起源于中國,具有東方文化的韻味,但也在逐漸均衡和發(fā)展中形成了特有的特色和敬清寂。昔年白居易坐在茅屋前,看茶葉在碗盞中浮沉,釀出一碗清淺的茶湯,品下一口,不知道是苦是甜,可能是香茗劃過舌尖流下喉頭,往事一飲而盡心之淡然,也可能是存留在舌面上的苦澀,久久不化,后又回甘。我端詳著案前的茶湯,像是白樂天手中的那一碗。
人事流轉(zhuǎn)光陰變遷,昔年的紅墻綠瓦今不在。內(nèi)有樂彩的宮殿也成了斷井頹垣。都在變化,京都也在變化,只是它變得很緩,我還可以感受到過去的種種,縱使也不斷被無限擴張的城市所擠壓,但是那根植于內(nèi)心的傳統(tǒng)文化卻還是生生不息,在一輩又一輩的的延續(xù)中不斷流傳。盛唐的遺風(fēng)猶在,坐落在東國的古都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