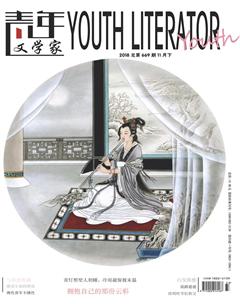文學作品中的故事講述:地方性知識的載體
高麗
摘? 要:《白馬部落》是作家陳霽所著的非虛構作品,作者用人類學田野方法——參與觀察、深入訪談——進行資料搜集,用文學方式還原白馬地區在近一個世紀之中的變化,呈現真實的生活狀態。從某種角度看,作家的文學創作與民族志相似,也起到文化摹寫的作用。《白馬部落》在故事中動態地塑造人物,有記錄變遷、以小見大、反映地方性知識的作用,在人物故事中展現了白馬與外界的橫向關聯與縱向變遷。
關鍵詞:《白馬部落》;人物;故事;地方性知識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3-0-02
白馬藏族是一個古老的少數民族支系,素有“語不與中國同,姓為中國姓”的特點,目前大約近2萬人,平武縣白馬藏族鄉和文縣鐵樓鄉是最大的聚居鄉。[1]作家陳霽的新書《白馬部落》是關于平武白馬藏族人故事的作品,本書與文學人類學關聯密切,在書中對地方性知識的描繪,還在于對人類學田野工作中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借鑒,其故事記錄呈現生命史的樣態。“既然是非虛構,我力求還原真相,尤其是追求本質的真實。所有的故事都來自第一手采訪。”[2]作者根據訪談內容還原近一個世紀白馬藏區的生活,通過十七個人物生命歷史的還原展現更宏闊的時代風云變幻。
民族志是人類學家寫文化的工具,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的闡釋人類學思想及“深描”概念的提出溝通了民族志與文學文本彌合的橋梁。民族志也可通過故事反映時代變遷,如林耀華先生所著民族志小說《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最突出的特色是用小說形式來反映社會學內容,系統全面地反映了一個社區的文化現象,還描述了社區的歷史變遷。[3]
閱讀民族志文本,可以獲得較為真實可信的族群資料。文學文本一定程度上記錄文化,將故事文本當作文化文本閱讀,可以得到關于其對象的描寫,這類描寫族群的文本與民族志有什么相似或相異的部分?筆者擬從兩者相關性入手,通過《白馬部落》分析,辨析故事創作中的文化呈現功能。
一、人物故事背后的歷史背景
民族志作為人類學家記錄文化的創作,反映地方性知識是題中之義,但作家創作也能有記錄文化的作用。本節以《白馬部落》中的人物故事描寫為對象,分析書中十七位人物故事,及如何在人物塑造中反映當地文化與變遷,通過不同人物的遭遇以及故事重組,可以畫出白馬地區在近一百年世紀中的更迭圖像。
(一)人物安排:時間線索
作者講述的故事發生是完整的時間線索,人物故事可以根據發生時間先后構成白馬變化路徑。白馬是放在整個中國環境之中的,其變化受中國整體環境變化的影響,在時代洪流中被動向前。
全書故事從一個世紀前講起,故事組成白馬與外界交往中的百年變化。大番官楊汝(1903-1958)經歷了平武由傳統的土司-番官-頭人三級管理系統,變為解放后政府設立平武藏族自治區管理。楊汝本來由于身份不能當土司,但在時代變化中,土司被廢,楊汝從番官變為區長,登上現代平武政治舞臺,楊汝還接受了主席的接見。而后隨著新政權的鞏固,禁煙運動開始,漢區土改,時局變化,被逼無奈的楊汝只得自殺。在民主革命的背景下,白馬人被卷入中國的現代化與改革潮流中,民兵隊長索尼成為帶頭人批斗山神,許多白馬人被批斗,如楊汝之女波拉,白馬好漢查拜等,白該活動被禁止,經書被毀。改革開放開始,白馬木材生意火爆,卷入木材生意中的人很多,格繞珠醫生的妻子因為木頭生意與其產生嫌隙才釀成悲劇。尼蘇只比波拉小幾歲,是曾被毛主席接見的白馬人,是與被批斗的波拉不同命運的美人。尼蘇既是遵從家長安排與表哥尼珠結婚的女人,同時也是在白馬很穩定的婚姻狀況下第一個離婚的女人。時局變化,白該再次活動主持嘎尼早的婚禮。入獄的格珠是因為新政策與當地傳統沖突:在當地認為倒賣熊貓皮不算什么,可是卻違反了國家規定。入獄七年,返鄉后的格珠依舊認真實干,相比下,在白馬伐木場被禁下長大的格朗養成偷盜的習慣,常年混跡在外。沒有學生的校長阿波珠是從白馬出來的知識分子,看見白馬的變遷,白馬學校2010年剛落成,現在卻沒有一個學生,大家都到外面念書了。在作者安排下,人物故事與社會變化路徑一致,格繞珠醫生依舊行醫,五保戶羽西兄弟的生活,格朗盜竊在外,阿波珠沒有學生,嘎尼早風生水起的旅游業,都是白馬正在發生并將寫下去的故事。
每個人物的遭遇都與社會變化關系緊密,通過對人物故事的講述作者還原白馬變化,展現隱藏其后的近百年來中國的變化。故事中每個人都經歷了變化極速的半個世紀,作者沒有把每個人的生活進行詳細羅列,而是選擇與時代變化息息相關的人物故事進行講述,突出個人在不同階段特殊遭遇,通過強調和刪除細節展現白馬及外部環境的改變,反映白馬近一個世紀的變化線索。
(二)人物故事:白馬網絡
作者聚焦于十七個章節的十七個人物身上,通過這些故事構成白馬。每個人物之間多多少少有聯系,所有故事組成一個網,涵蓋白馬的歷史縱深和橫向關聯。“這十七個不同的側面。組合在一本書里,就是一張原生態白馬社會的完整拼圖。”人物故事聯結成為白馬的全貌,縱向來看,通過家族變化傳承看歷史變化最為明顯;橫向來看,藏在故事后的線索緊密相連,組成綿密的白馬網絡,在不同人的經歷講述中串聯整個白馬。
通過人物故事講述,將白馬百年的變化刻畫出來,這成為觀看白馬變化、國家變化的窗口。通過對于白馬內部縱向和橫向線條的勾畫,白馬人的生活成為一個整體,展示了白馬在歷史中發生的改變。
二、故事中的地方性知識書寫
新時期以來許多小說書寫族群文化、具有民族志般的文化記憶功能。這些小說在對“地方”、“族群”的描寫中,對自然物候、地理風情、人文脈息進行追本溯源的、真實生動的描繪,呈現出鮮明的書寫“地方性知識”的特色。[4]文學文本開始自覺承擔記錄文化的功能,《白馬部落》中關于白馬的地方性知識書寫貫穿全書,都通過故事展現出來,故事中的人物行為展現其心理與文化。
白馬人對歷史的信仰不可忽視,從前的白馬人有超穩定的婚姻。書中三位女性在婚姻中的表現正反映白馬精神生活也在發生的改變:波拉的婚姻由父母決定;尼蘇被迫與表哥結婚后離婚;美人嘎尼早的婚姻自由。三位同樣美麗聞名白馬的女子,經歷不一樣的婚姻,是隨著白馬受外界影響改變的。
書中關于白馬人的信仰描寫不可忽視,關于儀式描寫很多。儀式、信仰的描寫也是人類學民族志的重要部分,民族志學通過自然場景的面向及其主要的活動特色,能夠針對研究現象的不同面之間的聯系,提供一個“脈絡性(語境化)的了解”,[5]通過儀式描寫反映族群性格。《白馬部落》沒有忽視儀式細節,文中關于祭祀山神的儀式描寫較為完整。
在對于歷史和山神兩方面交融的信仰中,故事不斷上演,構成白馬社會。外來的新事物也被納入當地的系統中,被當地信仰吸收。許多事情,當地人有自己的解釋體系,正是地方性知識所在。
三、故事:人物塑造過程性
以人物為中心的《白馬部落》在故事中塑造人物,人物在白馬的世界中活動。在動態中完成對人物外貌、語言的刻畫,人物其變化也在不同情境下展示出來,人物形象通過經歷展現出來,人物性格的描繪則直接依賴于故事的闡述。
塑造人物是動態過程性的,人物內心與事件的變化過程及作家塑造過程、外部環境變化的過程是一體的。動態中的人物讓讀者感受其性格與人生進程的發展脈絡,給人真實感,同時不刻板化任何一個人物,在同一個故事中每個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故事中還動態地展現了人物關系,通過事件串聯起來的人物不斷互動,整個世界被聯系起來。故事的發展變化也是外部世界和社會發展變化的脈絡,通過故事側面反映環境變化,不同故事反映不同變化角度,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段的不同遭遇會帶給讀者對于時代變化的思考以及對于人物命運的思考,讀者閱讀中能夠感受到時間歷史下小個人的無力感。正是在過程塑造的聯系使得作品更立體,事件發生在很多敘述的線條組合下復原了。
結語:人物故事的多元功能
《白馬部落》一書以人物為中心描寫白馬地區在近一百年中發生的變化,其人物描寫以故事為中心,在故事中或正面或側面塑造人物形象。全書十七個章節,以十六個人物故事為中心,涉及大大小小十多個家族,勾勒出動態的、與外界聯系中的白馬社會。故事賦予了敘述新的功能,從人物故事織成的網絡聯系整個地區,人物活動又將白馬和之外的世界相聯系,白馬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在故事中得到展現,如楊汝銜接了上世紀前半葉的白馬與中國政治,平武伐木場則聯系著新中國成立后的白馬內外,尼蘇的流動聯系著中央與白馬。作者在書中展現的白馬地方性知識,通過故事描述得以體現,故事發生細節透露白馬地方特點,其客觀文化描寫可作為文化文本閱讀。
彭兆榮教授指出:我們是不能漠視人類學與文學兩個學科之間的本質差別的。不論人類學家在寫作民族志時怎樣運用文學手段,它仍然在人類學本身的范圍內,原則上忠于并指向社會基本事實。而文學作品可從社會事實出發,但卻指向以虛構和想象進行文學世界的營造,目的在于審美。[6]從人類學角度看,可以將文學作品作為記錄某個族群的文化文本,看成是對民族志的有益補充。貝特森認為,藝術家描述文化的方式是,將很多預設和文化各部分之間的內在關系隱含在其作品里;他將文化的最基本的方面留給讀者去發掘,不是從他的字面詞句中,而是從他所強調之處。他選詞構句,使它們具有的超出字典釋義之外的言外之意凸顯出來;他謀篇布局,使讀者幾乎是無意識地接受了那些并沒有在句子中明確表達出來的信息。而如果使用分析性術語,這些信息是很難——幾乎是不可能——得以表達的。[7]相較于分析性術語,文學作品中的故事描寫的言外之意留給讀者廣大的閱讀思考空間。文學創作與民族志雖然有相關聯之處,其間的鴻溝終無法跨越,可以把其當成是文化文本來閱讀,但是文學終究不是民族志,文學創作的審美性要求并不要求科學性。
注釋:
[1]蒲向明:《論隴南白馬藏族儺舞戲的文化層累現象》,《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3月第31卷第2期。
[2]陳霽:《白馬部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291頁。
[3]王興周:《一部以小說形式寫成的社會學研究著作——<金翼>評介》,《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3年Z2期。
[4]葉淑媛:《民族志小說:新時期小說研究的新視域》,《文學史論》2013年第4期。
[5]李一松:《民族志及其實驗趣向》,《學術探索》2000年第1期。
[6]彭兆榮:《再尋“金枝”——文學人類學知識考古》,《文藝研究》1997年第5期。
[7](英)貝特森 著,李霞 譯:《納文:圍繞一個新幾內亞部落的一項儀式所展開的民族志實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