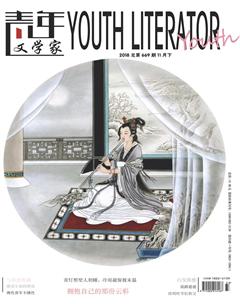底層能否發聲?——以魯迅作品為例
章穎
摘? 要:底層能否發出自己的聲音,底層應該怎樣發出聲音一直是文學評論界討論的焦點。在文學創作中,除了底層群體進行自我書寫以外,知識分子也在試圖書寫底層,然而知識分子采取什么樣的態度進行底層書寫至關重要。魯迅是自五四以降第一位專注對底層群體進行書寫的作家,他對底層群體的態度極其復雜,這也表現在了他的作品當中。
關鍵詞:底層;底層文學;魯迅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3-0-02
1997年5月《天涯》雜志重登汪暉發表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讓知識分子們開始激烈討論社會出現的諸多問題。在討論中,由于所持觀點立場的差異,使他們對此有不同的認識。在論爭當中對底層問題的討論尤為激烈。然而問題在于,底層寫作真的存在嗎?底層有自己的聲音嗎?假如底層真的有自己的聲音,那么所謂的底層發聲能否得以實現?如果將這個問題進一步的深入下去,由知識分子書寫的底層,就真的不是底層的聲音嗎?
著名的后殖民主義批評家斯皮瓦卡在《屬下能說話嗎?》一文中明確反對福柯和德魯茲提出的“被壓迫階級一旦有機會,并通過同盟政治而趨于團結之時,就能夠表達和了解他們的條件”[1]。在她看來,馬克思提出的關于小農的“代表”和“被代表”的問題也具有強烈的社會欺騙性。因此,對于屬下能說話嗎?她的回答是否定的。
斯皮瓦克所說的“屬下”,最早來源于20世紀初意大利共產主義者安東尼·葛蘭西《獄中札記》中的“subalterno”一詞,這個詞語可以被翻譯為“屬下”、“底層”等。斯皮瓦克更關注后殖民背景下的屬下階層及其特殊境遇,以及他們在構成上的各種內在差異,尤其是其中的性別差異。[2]
在斯皮瓦克看來,屬下不能說話。在對于屬下問題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兩種再現的方式。一種是作為“代言”的再現,如在政治領域,和作為“重新表現”的再現,如在藝術獲哲學領域。但是在“再現屬下的過程中,知識分子也清晰地再現了他們自己。”[3]
一、文學創作中的底層書寫
事實上,在文學創作中確實存在著大量的作品試圖“再現”底層,這樣的書寫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由底層群體進行自我書寫,時下流行的打工文學可以歸入其中,代表作家有鄭小瓊、王十月、周崇賢等人。他們的問題在于,在試圖以己之筆書寫與自己想同命運的底層人生的同時,往往沉浸于對自我生存狀況的訴說當中。在南帆看來“底層作者往往更為熟悉自己的生活,這是他們的優勢。但他們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會不會不知不覺地進入中產階層作家的行列——特別是在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4]以曾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小說家王十月為例,他的小說《少年行》、《國家訂單》、《白斑馬》等都曾刊登在文學界主流刊物上,獲得了主流文學界的認可。但就其作品內容而言,雖然他身為一名打工者,極其熟悉同為打工者的底層群體的生活和命運。但是他顯然缺乏超脫打工者身份,從更宏大的層面上駕馭文本的能力。他的小說描寫對象局限在有限的打工群體之間,表現的生活也大多大同小異,缺乏深度的人文關懷。
與王十月有相同境遇的還有女詩人鄭小瓊,她也憑借詩歌和散文創作將眾多文學大獎收入囊中。在文學批評界關于鄭小瓊的評論文章很多,但鄭小瓊好像成為了一個“符號”,成為了評論者眼中的“案例”。“在絕大多數關于鄭小瓊的評論文本中,評論家們感興趣的是她的打工者身份,女工身份,從她身上評論家們可以‘各取所需”[5]。但她詩歌本身的關注少之又少,評論者們對她身份的熱情遠遠大于她身為一個作家作品的文學性判斷。
另一種則是有一批具有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進行的底層書寫,如曹征路、陳應松、尤鳳偉等,在他們的寫作當中流露出對底層命運的同情。他們試圖表現人性、反思人性,但知識分子與底層之間無法忽視的身份隔膜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他們對底層問題的判斷。以曹征路的中篇小說《那兒》為例,《那兒》在2004年發表之后,曾經引發過轟轟烈烈的討論。《那兒》被視為新左翼文學的代表作之一,甚至曹征路本人,也被貼上“新左派作家”的標簽。然而事實的確如此嗎?《那兒》講述了“我”的小舅朱衛國,身為工廠的工會主席,在國企改革的浪潮之下,面臨工廠被變賣的危機。朱衛國試圖通過各種方式挽救工廠,最大程度的爭取工人階級的利益。然而這一努力最終付之東流,小舅也在一種無能為力的無奈感當中悲情自殺。這樣具有明確的階級主題指向的文章一經發表便備受爭議。事實上,《那兒》當中的工人階級已經“被底層化”。同時,當工人階級作為底層群體面目出現時,他們依然沒有逃脫新左派所批判的那種“中產階級寫作”中底層書寫的范式——即底層群體的命運是等待被拯救的。朱衛國作為工會主席盡心盡力,但他身為工會主席,本能的就會遭到普通工人們的懷疑。當小舅朱衛國自以為通過召開“全廠職工大會”,通過三千人的倡議書,能夠挽回工廠的時候。真正阻撓他的并不是政府或者房地產開發商,而是他的行為根本無人響應。小舅朱衛國作為領導者的天真和工人群體的愚昧無知被刻畫得活靈活現。在這樣的作品當中,工人階級當然是等待被啟蒙的,但這與百年前魯迅的呼喊并無二致。以曹征路為首的堅持底層寫作的作家和魯迅那個時代的作家所面臨的具體問題是不同的。對于魯迅而言,在清王朝大廈將傾,中國的命運掌握在幾大帝國手中的時候,魯迅想要做的,是以知識啟蒙底層,將底層視作待改造的對象。而對于處于“新啟蒙”時代的作家而言,所面臨的具體困境已經變成了在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當中,在消費社會和商品社會的聯手之下,金錢所帶來的人性異化。
再比如善于從平凡生活中進行取材的短篇小說家劉慶邦,他的小說致力于關注社會底層。在批評家們看來,“劉慶邦的底層敘事與一般的苦難敘述之不同,在于它不回避苦難,但也不渲染苦難,而是將苦難用輕松甚或溫馨的敘述筆調輕輕化解,從而達到從苦難中發掘出詩意的藝術目的。”[6]但劉慶邦的小說當中,缺乏對苦難問題的根源性追溯,底層問題的苦難并不是一種“原罪”,而是由現代社會中出現的階層分化施加的。因此,作者停留在了不加憐憫的書寫當中,缺乏對底層問題的探討。在這樣的底層寫作當中,勢必會掩蓋真正的底層問題。
從上述兩種情況來看,底層出身的作家進行的底層寫作或淪為訴苦或轉換為中產階級式寫作。而知識分子進行的底層寫作似乎又對真正的底層問題有所遮蔽。由此看來,底層真的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在這樣的思考當中,又會有新的問題出現,即當知識分子在一定的距離當中重新審視底層問題的時候,這種具有一定張力的寫作真的不能反映底層問題嗎?
二、以魯迅作品為例看知識分子如何書寫底層
五四以來,魯迅是第一個書寫底層群體的作家,魯迅的文學創作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對作家以何種態度敘述底層給予一種新的嘗試和回答。眾所周知,魯迅在雜文中最關注的就是“國民性”問題,特別是在早期雜文中,側重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魯迅雖然常常使用“奴隸”、“奴才”這樣的詞語表現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態,但魯迅個人對底層的情感是復雜的。在他的小說中,他對底層群體時而以同情的態度進行描寫,時而又是充滿不屑的。但更多的時候,難以以一個絕對的標準判斷魯迅的態度,他是中立的、復雜的。魯迅試圖用他的作品揭露社會的病痛,然后再尋求治療它的方法。
關于魯迅對底層群體的不屑心理,在《示眾》一文中表現的最為明顯。魯迅本人對國民性中的“看客”文化極其不滿。作品中一反常態的不去描寫被殺的人的罪行是什么,反將視線瞄準文學作品中沉默的大多數——看客。看客們對“犯人”的罪行并不感興趣,他們完全是出于看熱鬧的心而來,他們不關心罪行本身,而只是圖“有趣”。他們在相互擁擠中看犯人的同時,也在相互示眾。他們的冷漠與麻木讓魯迅極為憎惡。看客們的神態被魯迅描寫的活靈活現。同樣,他也唾棄那些生活中一些斤斤計較,受封建文化荼毒頗深的小人物。他稱呼楊二嫂為“圓規”、譏諷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四銘、嘲諷不倫不類的偽君子高老夫子等人。
同時,魯迅對那些鄉間單純可愛的孩子們飽含深情的愛意。在他的《社戲》一文中,寫到看完社戲回家的時候,孩子們想要烤豆子吃。這時候同行的小伙伴阿發說:“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7],這短短的一句話便表現了一個鄉間少年的無私與童真。而在迅哥兒闊別故鄉二十余年之后,他依然還記得童年時與閏土的情誼,這種少年的感情的真摯與美好,反而襯托了成年人之間充滿隔膜的交流的悲哀。因此當他離開家鄉的時候,他并沒有感到多少悲傷,在他看來“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并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墻,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8]
絕大多數時候,魯迅對底層群體的情感態度是復雜的。他憐憫他們的身世和遭遇,但又不忿于他們甘心忍受這樣的命運,甚至用“精神勝利法”進行自我寬慰。如《藥》中的華老栓,他選擇買下蘸上革命者夏榆鮮血的饅頭固然有其愚昧和麻木的一面,可是當這樣買下人血饅頭的行為是為了拯救他唯一的孩子——患肺癆的華小栓的時候,這樣的行為又變得似乎可以被同情了。在魯迅的筆下,麻木是值得被批判的,但是底層群體的愚昧本身是一種錯誤嗎?還有那位穿著長衫,但實際上生活在底層的孔乙己;接連失去丈夫和孩子,命運從不由自己決定,將微薄的希望寄托于來生的祥林嫂,這些底層人民的命運也只能讓人發出一聲悲嘆。
底層可以通過知識分子發出自己的聲音,知識分子也有責任和義務關注底層,盡己所能關懷底層。但重點在于,對于知識分子而言,特別是作為一名作家,應該選擇以何種態度和方式書寫底層。魯迅對底層書寫的偏愛,和對底層情感的復雜只能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知識分子的底層書寫應該如何展開。也許在未來的寫作和文學批評當中,底層能否發聲這個問題能夠以更好的方式得到解決。
注釋:
[1](印度)斯皮瓦克.《屬下能說話嗎》,羅鋼、劉象愚主編.《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118頁。
[2]劉輝.《論斯皮瓦克的屬下研究》[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9):第101頁。
[3]同[1].第106頁。
[4]石一寧.《“底層文學”引發思考》[N].《文藝報》,2006.1.21,第1版。
[5]夢亦非.《是誰制造了鄭小瓊》[J].《出版廣角》,2008(11):第69頁。
[6]劉建兵.《對底層的詩意書寫——論劉慶邦的小說創作》[J].《小說評論》,2009(3):第38頁。
[7]魯迅:《魯迅全集·編年版·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第255頁。
[8]同[7].第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