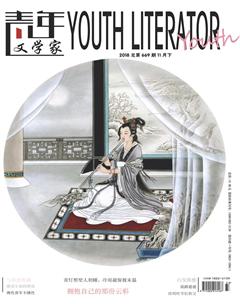先秦隱士中的漁父形象
吳雨霏
摘? 要:中國早期的知識分子主要以仕為職業(yè),當(dāng)他們決定歸隱的同時,也就意味著放棄了傳統(tǒng)的飯碗,這時,漁釣便很自然地成為其聊以維持生計(jì)的手段之一,如莊子釣于淮水即此。然而,漁釣與隱逸的關(guān)系,遠(yuǎn)非糊口這么簡單,其間深藏著極其豐富的隱逸人生哲學(xué)的象征意蘊(yùn)。
關(guān)鍵詞:先秦;隱士;漁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3-0-02
1.漁釣與隱逸之關(guān)系
捕魚是早期人類的一種主要謀生手段,《易傳.系辭下》:“古者包曦氏之王天下也……作結(jié)繩而為網(wǎng)署,以佃以漁。”在我國最早的文字史籍甲骨文中,已有有關(guān)漁獵的記載。而在《詩經(jīng)》中,其描述又漸趨細(xì)致,如《衛(wèi)風(fēng)·竹竿》:“鰲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yuǎn)莫致之。”《小雅·采綠》:“之子于狩,言振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魚生于水,漁亦必于水,而先秦道家向來對水懷有深情的愛戀和崇高的敬意,并賦予生命之源的水以道家隱士的特征。《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莊子·刻意》:“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郁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道和德是道家隱士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天(自然)則是道家隱士所效法的對象,老子稱水“幾于道”,莊子稱水為“天德之象”,其評價之高,可謂“無得而稱”了。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相對而言,儒家近于仁者,而道家則更近于智者。水的靈動而不拘執(zhí)的特性,也正是道家隱士為了在大道業(yè)已淪喪的時代追求個人適性而采取的處世態(tài)度。
除開水之德、舟之性的象征意味,現(xiàn)實(shí)中水域之風(fēng)景清佳、閑曠宜人,這也是“古來賢哲,多隱于漁”的一大原因。《莊子·刻意》中有一段話就道出了隱士的這一偏愛:“就數(shù)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呂氏春秋·觀世》亦云:“欲求有道之士,則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遠(yuǎn)幽閑之所。”南朝吳均乘舟經(jīng)過風(fēng)景秀美的富春江時感慨道:“鶯飛峽天者,望峰息心;經(jīng)綸世務(wù)者,窺谷忘返。”這也就難怪漢代的嚴(yán)子陵要選擇在這條江邊隱居垂釣了。
2.作為道家隱士的漁父形象
《漁父》在《莊子·雜篇》,陳鼓應(yīng)先生總結(jié)其大意云:“((漁父篇》,主旨闡揚(yáng)‘保真思想,并批評儒家禮樂人倫的觀念。孔子坐在林中杏壇,見一白眉被發(fā)漁父,漁父斥孔子‘擅飾禮樂,選人倫,指責(zé)他‘苦心勞形以危其真,教導(dǎo)孔子要‘謹(jǐn)慎修身,保持本真,使人與物各還歸自然。漁父,為一隱逸型的有道者。”《莊子》一書塑造出漁父這么一個道家隱士來對孔子進(jìn)行教導(dǎo),并非空穴來風(fēng)、毫無根據(jù),孔子在其一生游歷中,的確遇到過不少隱士,比如長沮、架溺、楚狂接輿、荷徐丈人、微生畝、石門晨門、荷贅者等等,而且他們大多數(shù)都對孔子進(jìn)行過善意的批評和勸導(dǎo)。我以為,《漁父》作者是個對孔子非常了解的人,《論語》中有關(guān)孔子的言行事跡對《漁父》故事情節(jié)的形成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其理由如次:其一,《漁父》篇中,漁父先是與子路交談,在了解孔子的為人及主張之后,對他作了一番否定的評價,然后即引船而去。而在《論語》記載中,孔子有三次與隱士發(fā)生關(guān)系也都是以子路為中介,隱士對孔子的評價和勸告都是通過與子路的交談來傳達(dá)的,他們之間并沒有真正見過面。大約深知孔子用世之心太重而無可救藥,《論語》中幾乎所有隱士都不愿直接與孔子辯論,或是“趨而辟之”,或是“至則行矣”,這與漁父同子路言畢即去完全一致;只不過出于作者要其主人公對孔子授以大道的安排,漁父才不得不在孔子恭敬備至的請求下又回過頭來對其進(jìn)行了一番訓(xùn)示。其二,《漁父》的部分情節(jié)和言論與《論語》中的一些描述極為相似,又《論語·憲問》:“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按乎?”《漁父》:“莫之顧而進(jìn)之,謂之餒。”都是在譏諷孔子雖遍歷諸侯不見重用卻仍就游說不休。
其三,在《論語·微子》中,子路曾對隱士荷葆丈人進(jìn)行過嚴(yán)厲的批評,謂其“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于是,《漁父》的作者便把他塑造成一個缺少悟性難體大道的人物,連其老師孔子都說他“甚矣由之難化也!湛于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這不能不說是因他對隱者出言不遜而給予的一個小小懲戒。
《漁父》的道家隱逸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三段話中,其一是漁父聽完子路對孔子的介紹后作出的一個評價:“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yuǎn)哉其分于道也!”道家隱士是以追求個人適性為人生第一要義的,而孔子高舉著仁義的大旗汲汲于救世,“苦心勞形以危其真”,此即道家所謂“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所以漁父批評他“遠(yuǎn)哉其分于道也”。
在孔子的虛心求教下,漁父開始啟發(fā)他:“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這無非是在暗諷孔子太多事,不能無為。然而孔子不悟,漁父便用了“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這個絕妙的比喻予以提示,然后非常直白地說出第二段重要的話來:“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jié),而幾于不免矣。謹(jǐn)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所謂“審仁義之間”等等,可以用道家的一句話來總結(jié),即“繕性于俗學(xué)”,這樣做當(dāng)然會“幾于不免”了。只有保持個人天性,使人與物各還歸自然,這樣才不會有什么累害。
第三段是漁父最后說的一段總結(jié)性的話,它是本篇思想的核心,也是漁父向孔子傳授的真正的“大道”:“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這里明確指出所謂“真”即是人的自然本性,亦即道家隱士所適之性。圣人效法自然珍貴本真,不為人為的世俗之學(xué)所拘;愚者卻正好相反,故顯得有所不足。
許多學(xué)者均認(rèn)為《漁父》篇混雜有儒道兩家的思想,比如陸欽說:“在‘法天貴真的議論中,也夾雜‘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的觀點(diǎn),可見文章道儒觀點(diǎn)混雜。”郭維森也說:“作為莊子后學(xué)所作的《漁父》篇,思想比較駁雜。作者一面批評孔子‘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另一面卻又在設(shè)計(jì)理想政治的藍(lán)圖。
他說:‘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然后分述庶人之憂、大夫之憂、天子諸侯之憂等等。這一套設(shè)想,豈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張。”對此我提出一點(diǎn)個人的不同看法:
首先,在漁父發(fā)表“天子諸侯大夫庶人云云”這段言論之前,已經(jīng)非常明白地說過這樣的話:“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jīng)子之所以。子之所以,人事也。”意謂漁父要用自己的大道來幫助孔子分析一下他的行為,可見后面說的都是“子之所以”,是孔子的所作所為。我以為這里漁父所使用的其實(shí)是辯論中常用的一種假設(shè)讓步法,意謂即便如你所說,但你的做法還是錯誤的。試看,他先退一步肯定儒家“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各有其職司的說法,然后順勢得出孔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亦泰多事”的結(jié)論。況且我們還要注意漁父所說的是:“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這已經(jīng)帶有了道家無為而治的色彩。
其次,漁父說:“真者,精誠之至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我在前面已經(jīng)說過,道家主張“絕仁棄義”并非反對仁義本身,“大道興隆,仁義行于其中”,在道家的“道德”中已經(jīng)包涵了仁義,但道家反對將其特地標(biāo)舉出來,認(rèn)為這是“散樸”。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真正理解漁父這段話的意思了:人只要保持其本真天性,自然而然就能做到慈孝忠貞;相反的,儒家過于看重外在形式,大肆標(biāo)榜慈孝忠貞,其結(jié)果反而會導(dǎo)致人心不純,競相作偽以盜取名爵。
第三,《漁父》篇中明明說過:“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禮者,世俗之所為也。”作者應(yīng)該不太可能在如此短小的一篇文章中又自相矛盾地肯定儒家觀點(diǎn)。常言道:看菜下飯,看人說話。漁父勸導(dǎo)的對象是儒家的祖師爺孔子,言談中自然不免要涉及到一些儒家的主張,如果因此就斷定篇中雜有儒家思想,恐怕有欠斟酌。
參考文獻(xiàn):
[1]隱士與中國古代文學(xué)[M]. 湖南教育出版社, 李生龍著,2003.
[2]試論先秦文學(xué)中的隱逸情結(jié)[D]. 孟慶茹.東北師范大學(xué),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