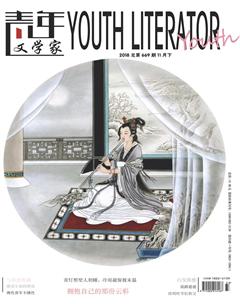李白古體詩中的“單句”及其結構功能簡析
王登婷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3-0-03
李白詩歌眾體兼備,數量上以樂府和古體取勝。”太白樂府五言,約六百十余篇,體勢多端。”[1]李白古體詩成就斐然,明人高棅的《唐詩品匯》就高舉李白為五言古詩的正宗。“李白是一味主張復古,而鄙視齊梁的,故其詩亦以古體為多,近體為少。”[2]可見,自由度高、寫作靈活的古體詩和樂府,一方面可以任憑詩人的才情發揮,用詩歌內容恢復古道;另一方面也是詩人有意為古體和樂府,“要在形式上給后人留下可以效仿的榜樣。”[3]
李白是擅長古體詩寫作的高手,游俠與求仙的經歷、桀驁不馴的性格成就了他飄逸不凡的古體詩風。他的古體詩就如他的個性一般,飄忽超逸、無跡可尋。他完全超越了古人談詩歌寫作所謂的字句章法之限,直接進入了一種自由空靈的境界,故王漁洋稱贊李白的詩歌是“飛仙語”,朱東潤則稱“李白是詩國的飛仙。”[4]然而盡管如此,看似飄逸無法的李詩也并不是真的毫無章法可尋,“李太白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盛于詩者也。”[5]完整把握李詩的創作特點,我們還是能從中發掘出李白寫作的慣用筆法和技巧。筆者在此擬從李白古體詩的“單句”使用情況入手,通過分析“單句”的結構功能從而從一個側面反映李白詩歌寫作的某些慣用手法。
何為“單句”?有必要對詩歌中的“單句”下一個定義。此處所講的“單句”,區別于語言學意義上與“復句”相對而存在的一個語法概念。這里的“單句”是從詩歌形式角度進行的定義,它不同于“兩句一聯”的標準模式,在詩歌中出現的不與上聯構成語義聯系而單獨存在的詩句,謂之“單句”。“單句”大體出現在古體和樂府之中,因為近體詩有嚴格而明確的律對關系存在,字數明確、句數明確,嚴格受到限制,是不大可能出現在近體詩之中的。縱觀古體詩的寫作,形式上極端自由,字數上、句數上、韻律關系上都憑借詩人的才力自由發揮,故容易出現“單句”這一特殊的詩歌形式。“古代詩歌以兩句為一聯,一聯常是一個意思單位,也是一個聲律單位。”[6]正因為“單句”不同于詩歌標準形式的“兩句一聯”,所以方顯示出其特殊性,才有對“單句”這一特殊形式進行討論的必要。
前人對“單句”問題還是比較關注的,楊倫和浦起龍便是其中的代表。杜詩《虎牙行》,“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沾臆。”楊倫在句下注為“用單句收縮黯然。”[7]浦起龍對《白馬》詩的末尾“嗚呼淚如霰”則注成:“末以單句總結四層。”[8]清代喬億在《劍谿說詩》言及“單句”問題:“七言中有單句,有長短句,五言亦兼有之。古辭《陌上桑》云:‘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余云‘單句也。”[9]此外,梁章鉅在《退庵隨筆·學詩一》言“單句”位置與結構關系,“若《甘棠》、《小星》章,俱單句結;后人作古體詩,亦常用之。”此外,近人王力先生則是從聲韻的角度對“單句”進行了定義,“畸零句必須入韻,”[10]且“不與別的句子成為一聯。”[11]王力先生把這種形式的詩句稱為“畸零句。”“畸零句”與“單句”從定義上而言是一致的。在《古體詩律學》談及李白的《長相思》,“‘美人是畸零句。”[12]《飛龍引》“‘鼎湖是畸零句。”[13] “由此可見獨立句和畸零句是和雜言詩很相宜的。”[14]從以上材料可見,從言數上看,“單句”多在七言古體、樂府中出現;從句數上而言,“單句”的出現多是三句一起出現;從情感表達上,多表現為一種黯然失落之感;從結構上看,多用于末尾結束文意;從位置而言,不是固定在開頭、中間、結尾的某一處,而是根據詩人的情感表達指向靈活安排位置。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情況。形式上為偶數、“單句”本身是雜言體式的兩句也是可能出現“單句”的,比如《短歌行,贈王郎司直》。“沈確士曰:上下各五句,俱用單句相間,此亦獨創之格。”[15]
一、李白古體詩“單句”的數量及其言數、位置特點
據中華書局版《全唐詩》的統計,李白古體詩出現“單句”的數量為五十首,出現“單句”的體裁多是歌、行、吟、曲、辭、引、歌行等古體樂府。其中,以“歌”命名的古體詩有九首,以“行”命名的古體詩數量是六首,以“歌行”命名的古體詩數量是三首。從李白“單句”出現的位置而言,出現在開頭的是二十六首,出現在中間的是十七首,出現在末尾的是二十八首,雖然“單句”出現的位置不是固定的,也沒有一定的規律可言,全憑詩人的才情而定,但是從李白詩歌出現“單句”的位置情況來看,“單句”更常出現在開頭和結尾的部分,“單句”出現在開頭多用“興”手法,引起下面情感的抒發,出現在末尾的“單句”則更多指向情感的戛然而止。此外,出現在開頭、中間、結尾的“單句”數量之和不是出現“單句”數量之和,這是可以解釋的。因為一首古體詩之中是可以多處出現“單句”的情況的,有的中間和末尾都出現“單句”,比如《將進酒》、《元丹丘歌》。有的則是開頭和末尾出現“單句”,比如《鳴雁行》。有的則是中間位置多處出現“單句”,比如《鞠歌行》。所以出現數據上的重合是可以理解的。
形式上而言,“單句”呈現雜言體的情況較多,“單句”呈現齊言體的形式少。句式整體上看,整齊的三言體“單句”是六首,整齊的七言體“單句”數量是八首,雜言體“單句”的數量則是三十六首,占到了出現“單句”數量的百分之七十二。可見,雜言入詩是李白詩歌的重要特征之一。雜言體的情況又有多種,有三、四、六、七雜言;四、四、七雜言;三、三、七、七雜言;三、五、七雜言;三、七、七雜言;三、三、五、五雜言;三、三、七雜言;七言、十一言等等多種情況。其中最常見的是三、三、七體,“單句”出現三、三、七體的數量是十五首。這些數據恰恰表明了,“七言中有單句”[16]的情況,無論是出現整齊十一言的《有所思》,還是七言中夾雜著其它三言、五言、九言、十言的情況,這其實都可以把其歸入為七言之中,這也說明了七言古體更容易出現“單句”。李白古體詩中的“單句”,形式上類似于一種騷體式的“散句”,自帶古典句式的美。“單句”本身而言,夾雜著古體詩特有的虛詞,如“之”、“乃”、“或”、“乎”、“于”、“其”、“而”、“亦”、“且”、“呼”、“何”、“哉”、“兮”。
為了直觀分析李白詩歌中的“單句”情況,特別制作一個表格如下。李白詩歌出現“單句”位置、“單句”本身的言數情況總表:
“單句”存在入韻的情況,這也是一個可以分析的問題。李白雜言古體“單句”數量占到了總體出現“單句”數量的百分之七十二,比例不低,討論的空間很大。“雜言,如果是以五言或七言(或更多)起首,也是以入韻為常。”[17]《公無渡河》“山”、“間”押的是上平十五刪韻,《飛龍引二首》(其二)開頭的“單句”中“閑”、“間”,押的也是上平十五刪韻,“顏”、“關”也是同押此韻。《飛龍引二首》(其二)中間位置“單句”中的“語”、“女”,押的是上聲六語韻;而結尾位置“單句”中的“方”、“光”押的是下平聲七陽韻。《天馬歌》中間位置“單句”中的“趨”、“鳧”押的是上平聲七虞韻。《前有一樽酒行二首》結尾位置的“單句”中 “衣”、“歸”,押的是上平聲五微韻。《白纻辭三首》(其一)開頭“單句”中的“齒”、“子”,押上聲四紙韻。其二中的開頭部分“單句”中“音”、“吟”、“心”則押下平聲十二侵韻;結尾位置的“單句”中的“微”、“違”則押上平聲五微韻。《鳴雁行》開頭位置“單句”中“山”、“關”,押上平聲十五刪韻。《東山吟》結尾位置“單句”中“時”、“奇”押上平聲四支韻。《贈裴十四》開頭“單句”中的“山”、“間”,押的是上平聲十五刪韻。《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中間位置“單句”中的“海”、“彩”,押的是上聲十賄韻。《送別》開頭“單句”中“水”、“里”,押上聲四紙韻。《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間位置“單句”中的“刀”、“袍”押的是下平聲四豪韻。《寄遠十一首》中間位置“單句”中的“枝”、“離”,押的是上平聲四支韻。《鞠歌行》中間位置“單句”中“狀”、“相”,押的是去聲二十三漾韻;“人”、“神”押的是上平聲十一真韻。《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間位置“單句”中的“張”、“光”,押下平聲七陽韻。
綜上,押上平聲韻的“單句”是十首,押下平聲韻的“單句”是四首,押上聲韻的“單句”是四首,押去聲韻的“單句”是一首,可見,李白“單句”多用上平聲韻來表達和緩暢達的感情世界。從位置關系上看“單句”押韻情況:“單句”開頭位置押韻的是六首;“單句”中間位置押韻的是七首;“單句”結尾位置押韻的是四首。可見,開頭、中間位置的“單句”更加容易入韻,這也是“單句”押韻較多的部位。
二、李白古體詩中 “單句”的結構功能及特點
李白詩歌“單句”呈現出總的特點是“形散”。句式上以七言雜言體為主,且“單句”形式更加長,字數更多,最長的“單句”字數達到十一言之長,比如《有所思》。詞語使用上,多用虛詞入詩,尤其是楚辭筆法入“單句”,形式活潑靈動,與呆板嚴整的格律詩自是不同。這自是和李白崇尚老莊的思想有關,更是與其偏愛古體詩相關。趙翼《甌北詩話》謂其:“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于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18]古體詩重要標志的“君不見”在李白古體詩“單句”中同樣出現,出現的次數為六次。“單句”伴隨著“君不見”出現在李白古體詩的開頭位置的是一首,在中間位置的是三首,在末尾位置或是臨近結尾位置的是兩首。
“單句”對李白古體詩結構功能的意義也值得關注。李白《荊州歌》看似是兩聯加上一個句子組合而成的,其實不然,末尾是一個“單句”,結構功能上而言是句意的結束,情感的戛然而止。李白的《遠別離》開頭出現的“單句”寫出了人物、地點的所在,句式包含有三言、七言、六言、四言,形式上呈現出一種雜言體,“形散”明顯,加之句中夾雜著三個“之”字,濃郁的古體詩氣息呼之欲出。開頭出現的“單句”,使用了一種“興”的筆法言“娥皇女英”起,而后接著敘寫遠別離的景象。下文似用了楚辭的筆法“兮”字,兩句“四言加兮字加二言”的詩體結構,且其中一句還用了疊詞;三句“三言兮加三言”的詩體結構;一句“二言兮加二言”的詩體結構散落在全文,只開頭的“單句”風格異于下文,形成了一層獨立的結構,表達了獨立的意思,交代了人物地點的所在。《西岳云臺歌,送丹丘子》開頭出現“單句”的功能也與此類似,也是運用了“興”的手法起,總起感嘆黃河之壯美,“開頭劈空而起,詩人仿佛站在半空。”[19]下文句子緊接著形成一個完整的起承轉合結構。
《蜀道難》中的“單句”出現在中段,結構上呈現出一種轉接的作用,句中的“夫”字呈現出同字的特點,然而卻不呈現出“對”的特點,本質上是使用了重疊的歌行字法。“單句”而上,描寫了蜀道之難、險峻的特點。“單句”而下,句意開始轉折,轉寫人事。“單句”成了結構和句意的中轉站、承接口。李白擬樂府《長相思》中的“單句”出現在詩的中間部分,“單句”而上以“長相思”起,用比興手法發端“長相思”,“單句”之中望月思人留下嘆息,美人更是不能相見。“單句”而下則思而不得。
“單句”入詩,對后來的詩歌形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式更加活潑自是毋庸置疑的,更是直接影響到詩人對詩體的創新,不拘于近體詩的格律形式,更容易表達詩人的情感指向。“東坡《歲日家宴戲示弟妹》首句云:‘弟妹妻孥子姪孫,實填名詞,無一虛字,蓋移‘柏梁體入律詩。”[20]
注釋:
[1]郭紹虞 編選.富壽蓀 校點.清詩話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1080.
[2]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217.
[3]喬象鐘.李白論[M].濟南:齊魯書社.1986.4.97.
[4]朱東潤.杜甫敘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3.176.
[5](宋)魏慶之 編.詩人玉屑(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311.
[6]王運熙.唐人的詩體分類[J].中國文化(第十二期),160.
[7](唐)杜甫,(清)楊倫 箋注.杜詩鏡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12. 874.
[8](唐)杜甫,(清)浦起龍.讀杜心解 [M].北京:中華書局,1961.10.216.
[9]郭紹虞 編選.富壽蓀 校點.清詩話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1091.
[10]王力.古體詩律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3.79.
[11]王力.古體詩律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3.79.
[12]王力.古體詩律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3.80.
[13]王力.古體詩律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3.81.
[14]王力.古體詩律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3.82.
[15](唐)杜甫,(清)楊倫 箋注.杜詩鏡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12.917.
[16]郭紹虞 編選.富壽蓀 校點.清詩話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1091.
[17]王力.古體詩律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3.75.
[18]四川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編.中國文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3.198.
[19]《文史知識》編輯部(編).名家講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2016.4.61.
[20]錢鐘書.談藝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