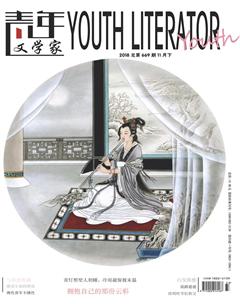昆德拉小說《身份》的主題變奏
韓依言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3--03
在音樂中,完全重復和變化性重復都是很重要的作曲手段,其中對主題有規律的變化性重復又稱為變奏。與傳統的小說在文章中緩緩鋪墊,逐漸在敘述中滲透出小說主題不同,現代西方小說中對于主題的處理方式,很多都與這種變奏音樂相類。即在小說甫一開始,就明確交代出小說主題,隨著情節的進展和內容的充實,通過多角度地充實主題,使主題不斷演變進化。
昆德拉是一名自覺在小說中加入音樂技法的小說實驗者,十分重視變奏在小說中發揮的功能,經常在小說中對其主題進行結構性和裝飾性的變奏。在他看來,變奏技法的應用既可以讓音樂和小說“只談及最根本的東西,做到一語中的。”無限指歸原始主題;也可以越來越遠離原始主題。于內部探索主題,于外部放逐主題。好像挖掘“每一件事物里的內在世界的無限多樣性”。又“好像在廣袤無際的外部世界中穿越的一場旅行,從一處到另一處,越來越遠。”[1]在遠與近之間往返穿梭,使音樂或小說在統一與變化之中達到最大程度的渾然一體。
一、《身份》的主題
于是為了弄清楚變奏在文章中的應用方法,我們需要首先提取出小說的主題。縱觀全文,小說始終圍繞著“身份”和“愛”這兩個關鍵詞進行敘事。小說的思考性正是由“身份”“愛”這兩個抽象詞組成的支架撐起來的[2]。我們首先來看一下昆德拉筆下的“身份”意指為何。如果單從譯文角度進行揣摩是難以實現的。事實上,《身份》一書原以法文寫成,原書名是Lidentité。Identité一詞來源于拉丁語,詞根identitas的本意是“le même”,即“一致”。詞意為 “Ensemble des données de fait et de droit qui permettent d'individualiser quelqu'un (date et lieu de naissance, nom, prénom, filiation, etc.”(確定某個體所需要的一系列數據和事實,包括出生日期、姓名、父母子女等)。由此,“identité”一詞在法文原意中存在著個體與他者的一致性、人存在于社會中的個體性兩個緯度上的沖突。與此同時,另一關鍵詞“愛情”中也同樣包含著個人與社會的矛盾。愛既是個體的,也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是個人受到社會熏陶形成自己判斷后鎖定的個人需求,是個體與群體雙重作用下的產物。
于是,我們也不難理解小說的主題:人應該怎樣面對個體獨特性與群體一致性之間的矛盾,以及如何在兩者當中協調人對個體特性的堅持和對社會共性的妥協。小說中描繪的對身份、對愛情的迷失與復得正是這樣緊緊銜扣著個體與群體的矛盾。這個主題“毫無例外地存在于作品的各個部分,不管這些部分占據什么樣的位置,涵蓋的范圍如何,類別如何,敘事功能如何,本體意義上或虛構意義上的地位如何,它們都只是這個共同主題的特別變奏。”[3]小說《身份》中兩個關鍵詞“身份”和“愛”共同指歸個體與群體必然存在、無法規避的矛盾。對“身份”和“愛”的甄別與選擇融入了對個體的堅持和對群體的妥協。而小說正是圍繞著這樣兩個主題詞進行敘述,從而實現主題的一系列變奏。
二、讓-馬克與尚塔爾對待愛與身份的原始態度
在讓-馬克這條旋律中,自從讓-馬克在沙灘上將別人“可笑地”錯認為尚塔爾,他開始在潛意識(夢)中發覺尚塔爾的社會性,乃至意識中發現自己的尚塔爾“變形”了,變成他認不出的愛人。他不能接受這樣擁有兩張面孔的尚塔爾,他不愛尚塔爾社會性的那張面孔。他只認識尚塔爾個體性的那一面,也只愛那一面,他并不完全了解他的愛人。與此同時,他對尚塔爾的愛是清晰可見、毋庸置疑。他真誠地愛著尚塔爾,唯恐失去她。至此,讓-馬克方面的主題清晰地呈現了出來。
與此同時,作為與讓-馬克的主題形成復調的尚塔爾的主題是這樣呈現的:為了生活中有足夠的物質保障,尚塔爾選擇了自己并不喜愛的工作,違背自己興趣和意愿融入到社會當中,自愿選擇同時擁有雙重身份。尚塔爾驕傲地看著自己成為一名“雙面的叛徒”,并把這當作是一種“戰績”。她似乎忘記了自己當初選擇社會性身份的原因:擺脫自己厭惡的婚姻身份(事實上,這也是社會身份的一個分支)。尚塔爾是對待個體與社會的兩難選擇中如此地矛盾,不斷搖擺。她真的在心理上需要社會身份嗎?答案并不是完全肯定的,她很愉快地享受著不被其他男人注意的生活,遠離“人類社會不成文法”,沉浸在對讓-馬克的純白的幸福的愛之中。
至此,呈示部結束,尚塔爾和讓-馬克兩條旋律共同奏響的關于身份的主題已清晰地展示出來。身份和被身份認知影響的愛情、個體性與群體性的矛盾已經陳述完畢。至此,作者畫好了小說的主題之樹,有待接下來的變奏為主題之樹填充枝椏。
三、對原始旋律的變奏
1、讓-馬克身份觀與愛情的變奏
小說來到發展部后,主題的結構發生改變,關于讓-馬克對尚塔爾愛情的變奏一共發生了四次。首先第一次變奏是讓-馬克方面,他對尚塔爾的愛的旋律中加入新的元素,對尚塔爾的愛愈發強烈。這個始終與世界保持距離的男人,只有通過尚塔爾才能產生對這個世界的熱情。這一時期,讓-馬克對自覺歸屬社會抱持著不屑的態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他拒絕登上社會的這輛他所厭惡的“火車”,拒絕擁有社會身份。(第28節)
大姑子的到來瓦解了他的愛與信任。讓-馬克恐懼而煩惱地意識到尚塔爾一直好像一個叛徒一樣生活在她自己討厭的世界里,還跟那個世界和睦相處時,他否認了對尚塔爾的愛情。他的愛情線索迎來了最徹底的顛覆性變奏。(第34節)。他的意識中她變成了“強者”,因為她更有錢。(第37節)
接下來,爭吵過后失去了尚塔爾經濟依靠的讓-馬克也在貧窮和孤獨中更加看清自己的社會地位。“他突然明白他以前經常對尚塔爾說的話,現在終于得到了確認:在他最深的內在召喚里,他是個邊緣人……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一個流浪漢”,一個沒有片瓦可以遮孤避寒的窮人。(第44節)
在強與弱的顛倒中我們隱約看得出讓-馬克潛意識里對待社會身份的態度。他真的那么不在乎社會身份嗎?不是的,尚塔爾的年紀正是她女性價值的體現,具有群體屬性,與她個體價值并無關聯。通過年紀大否定她的群體價值,正表現了他對主流社會對群體價值判斷的認可。他真的那么不在乎金錢所體現的社會地位嗎?也不是的,他雖然宣稱驕傲于自己忠實地做一個“社會邊緣人”,卻在矛盾爆發后終于承認貧窮令他成為了弱者。“兩個人都在自我與自我身份的不確定面前感到驚訝。”[4]
發散性的變奏使讓-馬克的真實想法在暗流中激烈涌動,讓-馬克對尚塔爾的感情的變奏從清晰呈現到補充闡釋(深刻)到懷疑模糊到暫時信任原諒再到想要“毀掉”兩個人的“小世界”和完全否定愛情。對自身與對方社會身份價值的態度從自傲于自己與社會的疏離不喜對方在社會中的融入逐漸變奏到客觀審視雙方在社會中的地位。變奏使兩人潛藏的矛盾經歷了壓抑和爆發,使小說充滿了傳統小說的戲劇張力。
3、尚塔爾身份觀與愛情的變奏
自從尚塔爾發覺了匿名信的真正作者,她對讓-馬克純白色的愛全部變成了懷疑和憤怒。(第29節)在憤怒中,她宣示房子的所有權,從房子中驅逐了讓-馬克。起初的“純白色的愛情”變成了“沒有廉恥”的、“放肆的、充滿敵意的謊言”(第36、37、38節)。這一情感的轉折伴隨的是對于自身社會屬性的追索。“她心里想,讓—馬克一直都在拉她脫離原本就應該屬于她的生活”[5](第40節)。
與此同時,小說終于為我們解開了一個疑惑。究竟尚塔爾如何看待她的社會身份,怎樣看待她所融入卻并不喜歡的集體呢?“她覺得非常惡心”,一種“沉默的、不會背叛的惡心”。與讓-馬克一樣,尚塔爾也不喜歡科技發達的人類社會。那么為什么還要違背本性,甘心做一名附敵分子呢?小說的第43節為我們揭開了她主動融入社會的動機。尚塔爾認為“人沒有能力改變世界,也永遠不可能改變它”。
小說的最后,尚塔爾對身份的態度和對于讓-馬克的愛情發生了最后一次變奏。無情的世界讓尚塔爾冷靜了下來,她意識到只有通過愛她的讓-馬克,她才能夠找到自己。只有愛人才在乎她的個體特征。在具有強烈的同化個體性的社會中,當她忘記自己獨特性的時候,她只有從愛情中獲得拯救,從愛人的珍視中獲得對自己獨特性的認可。(第49節)
追根究底,兩人對身份與愛情的矛盾來自于對自我的迷茫。與對讓-馬克的愛情一樣,尚塔爾對自己的身份定位也經歷了清晰認定到彷徨猶豫,然后回到更加堅定的清晰這樣一個過程。事實上,無論對身份的態度還是對愛情的態度,都是個體與社會的摩擦與平衡。他們所共同經歷的是尋找自我和擺脫迷茫。
四、變奏的意義
1、并置對比
以上我們分析了小說是怎樣逐一交錯地對尚塔爾和讓-馬克兩條線索進行變奏的,情節隨著變奏的展開而不斷推進。基本形成了這樣的發展次序:
尚的愛情/身份觀變奏1——讓的愛情/身份觀變奏1——尚的愛情/身份觀變奏2——讓的愛情/身份觀變奏2……
兩條旋律的情緒經過逐漸上升的變奏先后緊隨地驟然降落。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尚塔爾的愛情變奏2不僅挨著讓-馬克的愛情變奏2,也緊靠著讓-馬克的愛情變奏1。逐一變奏產生的滯后性使一方還處于高點時,另一方已經先行降落至低點。也就是說當讓-馬克的愛情還處于頂峰時,尚塔爾的愛情已經驟然降落至谷底。頂峰的愛與谷底的愛形成另一組更強烈的對比,牢牢抓住讀者的情緒。
第28節,我們看到讓-馬克沉浸在偷偷給尚塔爾寫信的快樂中。別人所經歷的痛苦只有想象為尚塔爾在經歷著,他才能有憐憫之心。關于讓-馬克的情感的變奏還處于較高的位置。然而,尚塔爾感情的顛覆性變奏卻先于讓-馬克的變奏來了,緊跟在讓-馬克還處于高點的前一個變奏之后。第29節,尚塔爾懷疑讓-馬克寫信的動機是“想要陷害她”。因為她老了,他想要離開她了,一旦她可能背叛,他就可以“輕易冷酷”地離開她。與29節形成復調的讓-馬克的復調在第34節來到。滯后的讓-馬克的變奏線索認為這個“附敵分子”不是“他所愛的那一個”,這個尚塔爾只是一個虛幻的幌子。他想要摧毀與這個幌子組建的愛情世界。
尚塔爾和讓-馬克這對膨脹的情緒經過雙重旋律和變奏的聯合應用實現了最大程度的對比并置。我們看到這對情侶之間已經“越來越遠,越來越失去對方,越來越不協調”。[6]作者帶領著我們來到了一處邊界。
2、不斷定義主題詞
在發展情節的同時,作者也不忘繼續對人的群體性、從眾性,即人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身份”,進行補充再定義。在尚塔爾眼中,人主動融入群體這種隨和流俗的行為能夠與別人“更貼近”,跟眾人共同參加一場大聚會。“無論出生在這個世界上是幸運還是不幸”,“任由自己被帶著走”都是“度過人生的最好方式”(40節)。與此同時,而緊接著在下一節(41節)中,讓-馬克看來,這些從眾的人群正在微笑地奔赴死亡隧道,“都準備好冒生命的危險進行這場大征戰。”[7]。“身份”的主題在兩條旋律中的變奏出現懸殊的差異。妥協于社會群體既可以是必須遵守的律令、與別人更貼近的大聚會,也可以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大征戰。到底應當如何看待個體與群體的沖突?小說并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它只是帶領我們持續探尋。
從內容上來說,是在探尋的過程中對主題詞“愛”與“身份”的“定義”、“再定義”[8],從意義上來說,變奏的過程就是一次對自我的永恒尋找。這樣一次變奏的旅行就“貫穿在這主題,內在思想,和獨一無二的內在情境”[9]之中了。并通過這種疏離與匯聚將小說整體聚焦于“個人身份究竟基于哪一點而存在”上面,而這,恰好正是“昆德拉所有小說都試圖解答的問題。”[10]
選擇遠離社會群體隨心所欲,意味著被邊緣化,衣食無著。選擇另一極端,被卷入生活的洪流,喪失對自我的堅持與追尋,則生命也無異于死亡。就這樣,小說《身份》賴以延展的是一直處于變動中的主題。
3、決定小說結構
小說主題的推手“愛”和“身份”兩個關鍵詞決定了小說的情節。最初兩人安于自己的位置,對待身份和愛情的態度都清晰明確,但這個位置是潛藏著危機的、不穩定的。于是對個體身份和對方身份的態度從清晰到模糊再回歸清晰,兩人的愛情也經歷了深愛到出現裂痕再到漸行漸遠最后回歸深愛的過程。情節隨自我在社會中的偏離、尋找和定位而發展。兩人在面對自我時的不確定逐漸找到了出口。能否在社會與個人的沖突中找到舒適的位置決定了對待自己身份和愛情的態度。就這樣,“主題——而不是情節、人物、背景或環境——決定了小說的結構”[11]。
到小說結尾,個人與群體的矛盾這一主題之樹已經畫成。身份到底是什么,愛到底什么,如何面對社會與個體之間的沖突矛盾,小說并沒有作出決斷,以至于沒有任何理論可以結束疑問。“直到最后,真理都是無法抓住的,或者更確切地說,真理無法脫離多元的闡釋與話語,而所有這些闡釋與話語也只能緊追真理不放,卻永遠無法抓住它。”[12]昆德拉只是不斷繪制著主題之樹,定義再定義個體與群體的沖突,通過人物和人物的行為帶領我們一次次地探索主題的變奏。
注釋:
[1]米蘭·昆德拉:《笑忘書》,王東亮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255頁。
[2]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157頁。
[3]弗朗索瓦·里卡爾:《阿涅斯的最后一個下午》,袁筱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73頁。
[4]弗朗索瓦·里卡爾:《阿涅斯的最后一個下午》,袁筱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25頁。
[5]米蘭·昆德拉:《身份》,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49頁。
[6]弗朗索瓦·里卡爾:《阿涅斯的最后一個下午》,袁筱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24頁。
[7]米蘭·昆德拉:《身份》,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53頁。
[8]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102頁。
[9]米蘭·昆德拉:《笑忘錄》,王東亮譯,2011年,第87頁。
[10]弗朗索瓦·里卡爾:《阿涅斯的最后一個下午》,袁筱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25頁。
[11]《阿涅斯的最后一個下午》,弗朗索瓦·里卡爾著,袁筱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75頁。
[12]同上,第122頁。
參考文獻:
[1]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
[2]米蘭·昆德拉:《笑忘錄》,王東亮譯,2011年。
[3]弗朗索瓦·里卡爾:《阿涅斯的最后一個下午》,袁筱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