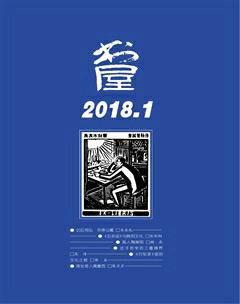莊子哲學的三重境界
吳靖
莊子是繼老子之后中國道家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留下的著作《莊子》一書展現了玄遠高妙的思想、汪洋恣意的想象以及生動瑰麗的文字,被稱為“文學的哲學,哲學的文學”,對中國哲學史和文學史均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中國哲學的主體部分主要是宇宙論和人生哲學,其中宇宙論部分由老子《道德經》起始,至漢代《淮南子》得到了更為完善的發展。而人生哲學部分,莊子的偉大成就是空前絕后的,其中創造性地融匯了“游世與游戲”的人生態度、“自然與自由”的人生價值和“審美與創造”的人生境界,可以將之視為莊子哲學的三重境界,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與人格理想,并極大地豐富和提升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境界。
一、游世與游戲
通常而言,儒家思想被認為偏于入世,佛家思想被認為偏于出世,道家思想處于入世與出世之間,仔細研究莊子哲學就會發現,正是莊子開創了不同于單純入世或出世的第三種處世哲學,我們可以稱之為“游世”或“間世”。要理解莊子所開創的這種對中國人的人生哲學影響深遠的思想,必須從《內篇·養生主》的一個著名故事講起: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這個“庖丁解牛”的著名典故的精華在于庖丁說的那段話:他說初學解牛時看見的是一頭整牛。三年以后,牛體已不再是渾然一體的龐然大物。而今,他無須用肉眼觀看,僅憑超越表象的高超直覺,刀鋒就能在牛體中輾轉回旋,暢行無阻。由于依循牛體的天然生理構造,行于寬廣的正道,一頭牛分解下來,庖丁的刀鋒連牛的筋腱都沒碰到,更不用說與牛骨頭硬碰硬了。優秀廚師一年換一把刀,因為他們用刀鋒割開牛的柔軟筋腱。普通廚師一月換一把刀,因為他們用刀刃猛砍牛的堅硬骨頭。他的刀軟硬不吃,用了十九年,解牛數千頭,刀刃還像剛在磨刀石上磨過一樣鋒利。牛體的每個關節都有空隙,刀的鋒刃卻沒有厚度——以無厚入有間,筋腱骨肉之間的狹小空隙,就是自由遨游的廣闊天地。
在上述這則寓言中,莊子將普通廚師隱喻為入世者,將優秀廚師隱喻為出世者,將至人庖丁隱喻為游世或間世者。他認為,入世或出世,游方于內或游方于外,就是計出入,辨小大,都是執于一偏,而非中道。因此,他在《內篇·養生主》的首段中就點出:“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督即中,緣督就是遵循中道,這樣才能保護生命,保全天性,養護新生,盡享天年。也只有“游刃有余”的庖丁式游世或間世,才是不分內外、出入自由的逍遙游,才是“緣督以為經”的中道。在《內篇·人間世》和《外篇·山木》中,莊子又以樹木作為隱喻,反復闡明自己的這一中道思想,他分別寫道: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不材之散木,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
莊子主張,游世或間世者的定位應該“處乎材與不材之間”。如果一棵樹長得筆直,成材以后就會被砍下來,造房作具,這便成了器,成器對用器者有益,對樹木卻有害。成器意味著樹木的喪生和天性的扭曲。反之也不好,如果一棵樹長得歪歪斜斜,那么不僅沒人給它施肥澆水,而且沒等長大,就會被砍下來當柴禾燒掉。如果把有智慧的人比做一棵樹,那么這棵樹就應該處在成材的“文木”(喻入世者)、不成材的“散木”(喻出世者)之間,一開始似乎能夠成材,人們澆水施肥,盼著樹趕快成材。但這棵樹長到老大,仍然不能令人完全稱心,砍下來派上大用場還不行;砍下來燒掉又舍不得,或許再長兩年就會成材,于是這棵樹就能不受干擾地自由生長,終其天年。因此,《人間世》之“間”,并非名詞,而是動詞,既是“間”于“世”,又是“間”于“人”。間于世,就是獨立于世界的不同力量之間;間于人,就是獨立于人的不同定型之間。莊子的一切思想和終身履踐,都以此為根本。
值得一提的是,莊子由游世思想又引申出游戲精神,這種游戲精神亦深刻地烙印上游世或間世思想。一方面,莊子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的逍遙游舍棄了目的性和功利性的追求,以一種自由的游戲精神超越世間的苦難,抵達了審美人生的彼岸。另一方面,莊子又強調獨立于世界不同力量和人的不同定型之間,不傾向和偏袒任何一方,這又為他的游戲精神注入了公平公正的思想。正如裁判不直接加入游戲,公正執法是他加入游戲的方式,然而裁判也是整個游戲的組成部分,而且是確保游戲正常進行下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莊子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批判者,既身處游戲之中,又在游戲之外,這正是“游”或“間”的真正奧義。
二、自然與自由
“自然”是老子哲學的核心思想,“道法自然”簡潔地概括了老子思想的精髓。這個“道”一方面是指天地萬物大化流行的“自然”之樣態,一方面也指具體事物存在的“自然”之樣態。莊子哲學的特點在于,他善用極為形象的語言闡發和延伸老子哲學的許多思想。對于“自然”概念的闡發,以《外篇·知北游》中“東郭子問道”的一段對話最為典型:
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可后?”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汝惟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endprint
東郭子就“道”之所在的問題被莊子答得啞口無言,且被莊子指出其所問根本就沒有觸及“道”的本質,原因在于:他將“道”看成一個“東西”(或曰“物”),既然是“物”,那它就應該有其“所在處”。如此,作為“生天生地”之本根的神圣的“造物者”之“道”就不應該存在于螻蟻、稊稗、瓦甓甚至屎溺之中,否則,“道”豈不是也如此卑下和不堪嗎?因此,在視“道”為“行”或“存在”這一點上,老、莊之間是相通的。同時,莊子以其由自然而自由的思想,對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進行了重要的發展,使道家哲學達到了一個嶄新的境界。
相對老子高度概括、辯證的語言風格,莊子的語言風格更加具體,更具穿透力。換言之,莊子哲學有一個始終不渝的原則,就是將抽象化為具體、將混雜化為純粹、將思辨化為直感。如果說莊子哲學的核心思想之一是“自由”,那么最能體現莊子自由思想的便是著名的《內篇·逍遙游》,在這篇氣勢磅礴的文章中,莊子以自身敏銳、深刻的主觀感受,寫了大鵬、蜩、學鳩、斥鴳的不同,以豐富的想象和靈動的語言暗指這種不同不僅是大小不同(物理意義上的),更是境界有別(精神意義上的)。莊子通過描寫蜩、學鳩、斥鴳對鵬的嘲笑,道出了背后的荒謬和不可理喻: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世界所有的人或物都有自由,換言之,自由是存在的基本形式。但是,不同的人或物的自由又是很不一樣的。無知無法蔑視有知,渺小難以傲視偉大,卑俗不容消解崇高,與蜩、學鳩、斥鴳這些小鳥相比,鯤鵬具有更加寬廣和雄大的自由,也就有著更加豪邁和宏偉的自由精神。然而,莊子同時清醒地指出,即使鯤鵬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也沒有進入他所說的“逍遙”的境界,因為鯤鵬的自由仍然是“有待”的,即須借助外在力量才能實現。由此,莊子引出了作為精神個體的人的“大自由”,亦即莊子所謂的“逍遙游”。從北冥到南冥,從三千里水域,到九萬里高空,莊子的神魂無所不至,無所不見。對于他,時間難隔,距離難阻,神到之處萬形畢現,心到之處眾意并出,整個宇宙都是他自由出入的地方。因此,在《逍遙游》中,真正自由的不是任何一個物質的實體,而是莊子的“精神”。這就是古語所謂的“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抑或今人所謂的“神游”。
顯然,莊子的這種出入宇宙的大自由,并不是通過任何現實的物質手段建構起來的,因為依賴物質的自由始終是“有待”的,而莊子則是依靠個人的想象力和如椽妙筆來實現心靈和精神的自由,讓人在無邊的時空中自由飛翔。正如清代著名學者劉熙載的感嘆:“文之神妙,莫過于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烏知非鵬之學為周耶?”基于這樣的價值取向,莊子認為對真理或正確觀點的探究往往是徒勞的,他在《外篇·秋水》中寫道:“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之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個體所知的領域往往小于未知的領域,存在的時間遠遠短于不存在的時間,以有限的心智去探究無限的宇宙,往往內心迷亂而難有所得。顯然,莊子認為人生的價值另在他方,而非知識的探求。莊子對于知識的態度有待商榷,但他對知識局限性的洞察卻是意義重大。兩千多年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論科學》一文中寫下了舉世皆知的格言:“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并且是知識進步的源泉。”西方世界在經歷了數百年對于知識的探究之后,憂傷地發現知識和理性的局限,如果莊子泉下有知,定將會心一笑。
三、審美與創造
莊子的人生哲學起于游世的人生態度,行于自由的人生價值,最終化于審美與創造的人生境界。換言之,莊子哲學的終極歸宿乃是一種基于審美觀照的創造境界。因此,有人稱莊子為古今第一藝術哲學家,他對中國后世美學思想和藝術創造的深遠影響無人能及。國學大師徐復觀在其代表作《中國藝術精神》中鮮明地指出:“他們(指莊子的修養功夫)所達到的人生境界,本無心于藝術,卻不期然而然地會歸于今日之所謂藝術精神上。”
的確,莊子將審美之境寓于自由游世的人生態度和價值,“游”本身是一種審美過程,過程就是一切,目的是無須預設與達到的。“游”是人之心靈的自由狀態,無拘無束,一種無偏執于“心”的自由。此“心”乃功利之心、認知之心、敬畏之心。破斥功利、認知與敬畏之“心”,便是審美。正如西方大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的名言:“美是一種無目的的快樂。”審美的本質在于精神自由,它可以超越時空的界限,做無窮無盡的想象,審美心理活動當然也有它的目的性與規律性,但它是無目的的合目的,無規律的合規律。有一次,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兩人展開了一場堪稱中國文化史上最精妙的辯論,精彩的論辯過程將莊子的美學思想展露無遺,之后他將這段對白記錄了在《外篇·秋水》中:
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面對同一對象——出游從容之魚,莊子能體會到“魚之樂”而惠子不能。前者的心靈是審美的,后者則是認知的、功利的。從審美角度看,物我渾一,主客同體,“魚之樂”即我之樂,此之謂“游”;從認知功利角度看,魚之游動無所謂樂與不樂。顯然,惠子是在談對魚的科學認識,莊子在談對魚的審美體驗。對此,著名美學家李澤厚先生有一句精辟的評論:“在這個著名的論辯中,惠子是邏輯的勝利者,莊子卻是美學的勝利者。”
莊子認為審美的極致乃是一種觀照,但這種“無為”與“不作”背后卻蘊含了創造的基因。他在《外篇·知北游》中寫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他認為天地的無言之美才是美的極致,這與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一脈相承的,圣哲之人探究天地之美并通曉萬物生長之理,對世間萬物采取一種觀照的態度,這是對老子“自然無為”思想的深化。與早期人類對自然或恐懼或崇拜的心理判然有別,莊子以審美關系觀照自然,深刻洞察到了人與自然的一種新的關系,我們可以在《內篇·應帝王》“混沌鑿竅”的著名故事中更深刻地加以體味: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以“混沌”隱喻自然原本的規則與秩序,在“倏”與“忽”鑿通“七竅”的干涉之下,失去本原而死。莊子認為,天地間的大美是在人為地進行審美判斷之前所“存在”的那一種美,是“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美之美”,亦即“混沌”之美。值得一提的,莊子所開啟的混沌之門直通兩千多年后當今科學前沿——混沌學。在這則寓言中,南與北可以視為事物對立的兩極,倏和忽都是形容事物運動非常快的形容詞,“中間地域”好比處在一張紙正反兩面之間的中間面。“混沌”既是一個形容詞,也是一種狀態,用于描述那個“中間地域”的不確定性和客觀存在,這相當于數學中的極限概念。莊子以這個精妙的故事,無意間直指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把非線性現象擺在了線性思維的面前,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第三次革命正是與此有關。
若論審美與創造,莊子哲學對于后世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藝術領域。他認為美的創造過程就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過程,他在《外篇·田子方》中寫道:“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檀檀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蠃。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在莊子看來,畫家“解衣般礴”,坦然自若,不為世俗陋習所拘囿,以奮振、自然和率真的態度進入藝術創作的自由境界,這樣才能藝與道相通,畫出符合大美要求的作品,這一思想對于中國藝術的創作和欣賞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