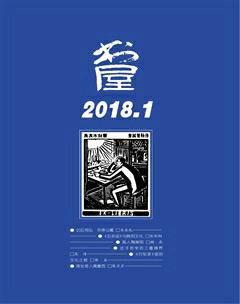北宋新、舊黨爭與理學
李勝壘
學術和政治之間有密切的關系,學術的發展往往會受到政治的影響。黨爭是北宋政治中的一個突出表現,其對學術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北宋的黨爭和漢、唐的黨爭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漢、唐的黨爭多與皇權、外戚和宦官存在關聯,北宋黨爭于此并無關聯,而更多是不同文人集團之間的斗爭。北宋黨爭始于仁宗、英宗兩朝,自王安石變法,形成了支持新法的新黨和反對新法的舊黨,使得黨爭在哲宗之后日益激烈。“宋室朋黨之禍,雖極于元祐、紹圣以后,而實濫觴于仁宗、英宗二朝。其開之者,則仁宗時范、呂之爭;其張之者,則英宗時之濮議。及神宗時,王安石創行新法,舊黨肆行攻擊,附和安石者,復逢迎新黨,反對舊黨,兩相排擠,而其禍成矣”。舊黨當中,又分為朔黨、蜀黨、洛黨,朔黨以司馬光為首,蜀黨以蘇軾為首,洛黨以程頤為首。蜀、朔、洛三黨雖屬于不同黨派,但在反對王安石新法的立場上是一致的。新、舊兩黨之間相互傾軋,斗爭甚是激烈,一直延續于北宋之末。新黨不僅在政治上施行王安石新法,更在學術上推崇王安石新學,是新學的推行者,例如,蔡京就曾把王安石納入孔廟配享,在《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中蔡京更被列為新學學者。在新、舊黨爭的歷程中,新黨除在哲宗元祐時期沒有得勢外,在其他時期,均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對舊黨予以打擊,舊黨的學術同時也會受到連帶打擊。程頤為首的洛黨作為舊黨之一,其所創的理學更不免受到其影響。
一、“帝王之學”的建構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元祐元年(1086),蔡確、章惇等新黨人士被罷,司馬光等舊黨人物上臺,“閏月庚寅,蔡確罷。以司馬光為尚書左仆射、門下侍郎。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壬辰,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丙午,守尚書右丞李清臣為尚書左丞,試禮部尚書呂大防為尚書右丞……辛亥,章惇罷”。同時,程頤得到司馬光等人的極力推薦,被任命為崇政殿說書,給年幼的哲宗講課。
司馬光極力推薦程頤是有淵源的。在神宗時期,由于王安石及新黨人士執政,司馬光等舊黨人士被排擠出中央,其中很多人集中于洛陽,他們在洛陽多次進行集會,討論時政、學術。在這些集會當中,就有程頤的父親程珦,正由于其父親的存在,程頤得以有廣大的交際范圍,與司馬光等人有往來。程頤的學術正是在此得到了司馬光等人的賞識。隨著哲宗即位,司馬光等人重返政壇,程頤便被舉薦為崇政殿說書,從一介布衣成為皇帝師傅。如何對哲宗進行教育,程頤圍繞這個問題建構了其“帝王之學”。程頤的“帝王之學”以“修德”、“進學”、“立志”展開。
程頤認為皇帝要“修德”,說:“將欲治人,必先治己。”皇帝必須從自身的道德做起,只有把道德修養完善,才能治理好國家。程頤還認為,皇帝鞏固自己的統治,不能憑自己的高位和權力,而是自己的道德,“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所以修德是君主當務之急,“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那怎么“修德”呢,程頤認為,首先是正人君之心,“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正人君之心,就是端正人君的思想,例如,“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有之。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其次要有良好的環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袛應宮人內臣,并選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皇帝身邊的侍臣要在四十五歲以上,而且都要是厚重小心的人。器具也要質樸,不能使奢侈華麗。總之,皇帝必須在良好環境之中成長,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
皇帝還要“進學”。程頤說:“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于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系于此。”皇帝要認真讀書學習,增長見識,否則將不能治理好國家,禍患無窮。程頤對哲宗“進學”的要求非常嚴格,例如,按照慣例,夏季天氣炎熱,皇帝是可以罷讀的,但在程頤這里卻不允許,即使天氣炎熱,依然要求哲宗讀書學習,“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
皇帝更要“立志”。程頤指出:“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于近規,不遷惑于眾口,必期治天下如三代之治。”皇帝必須“立志”,堅信圣人的教訓,不拘泥于陳規陋俗,這樣方可國家大治,進而達到三代之治。
總之,程頤正是通過“修德”、“進學”、“立志”這套“帝王之學”來教育哲宗,希望哲宗成為他理想中的帝王。對于程頤的教育工作,司馬光等舊黨人士是滿意的,“呂申公、范堯夫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而嘆曰:‘真侍講也。”
二、傳道的使命感
元祐八年(1093),哲宗親政,次年改元紹圣,章惇新黨人士再次上臺執政,司馬光等舊黨人士被罷,“甲寅,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蔡確追復右正議大夫。以資政殿學士章惇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秋七月丁巳,以御史黃履、周秩,諫官張商英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王嚴叟贈官,貶呂大防為秘書監……詔:‘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布告天下。除悉不問,議者亦復勿言”。隨著舊黨人士的被罷,程頤也受到牽連,于紹圣四年(1097)被流放涪州。被流放的程頤并沒有因困境而無所作為,相反卻激起了他傳道的使命感,潛心鉆研于學術之中。
程頤一直想定六禮,作《五經解》,但之前由于朝廷之事,使這項工作耽擱了,現在居于涪州,擺脫了朝廷政事,便可以潛心于這項任務。“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成七分,后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陜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定六禮的工作,之前完成了七分,現在程頤打算一二年內完成剩下的部分。關于作《五經解》的任務,《易》由程頤親自來完成,其他經書則交由關中的弟子分擔,《禮》經經過陜西諸公刪定,送到了呂大臨處。《禮》經等的解釋是以程頤的意思為本的,陜西諸公只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刪定。endprint
流放涪州期間,程頤付出了很大精力去研究的便是《易》。沒有了官職,擺脫了政事的煩惱,在這種環境之下,去鉆研蘊含天、地、人規律的《易》,是再合適不過了。此前,蘇軾在被貶黃州的時候,也是潛心于《易》的研究,“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于《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據記載,程頤在訪成都的時候,從造桶者那里聽到了關于《易》的解釋,這個解釋也被他所接納,“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可見,程頤被流放的失意,已變為其研究《易》的熱情。經過程頤的努力,《易傳序》在哲宗元符二年(1099)于涪州完成,另外,他的《程氏易傳》在此期間也得以完成。《程氏易傳》的完成,使程頤多年的夢想得以實現,因為自少年時,程頤跟隨周敦頤便學習《易》,“子謂門弟子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顏子之所樂。”程頤完成《程氏易傳》已七十多歲,這期間已過了五六十年,此書的完成,無疑是程頤學術上的一個里程碑。
雖然《程氏易傳》得以完成,但程頤卻不敢輕易拿出來示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黨爭,“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本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最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廷。于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察覺”。在新黨如此嚴厲的黨禁之下,程頤是不敢把《程氏易傳》示人的。徽宗崇寧五年(1106),蔡京被罷相,黨禁解除,程頤也疾病纏身,才把《程氏易傳》傳給弟子,以此來傳承圣人之學,“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后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三、后學的流變
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程頤被移往峽州,四月,獲大赦,回到洛陽,被授予權西京國子監。回到洛陽之后,程頤再度聚徒講學,這期間羅從彥、張繹、謝良佐等人前來問學。然而這種平靜的生活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兩年后,激烈的黨爭再度開始。
徽宗崇寧元年(1102),新黨人士蔡京執政。為了打擊舊黨,蔡京立了“元祐奸黨碑”,把舊黨人士統統列入此碑中,程頤也未幸免名列其中,“于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人,侍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余官秦官等四十八人,內臣張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等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崇寧二年(1103)四月,程頤的著作和學術活動也遭到了禁止,“詔:‘……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察覺……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诐行,惑亂眾聽,而尹淳、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程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程頤弟子們的安危和前途受到威脅,不得不離開程頤,“其后,黨論大興,門人弟子四散而四歸”。
程頤的弟子們離開程頤,去往其他不同地方進行講學,形成了許多地域性的學派。譙定、謝湜、馬涓在四川傳播,是謂涪陵學派;謝良佐、胡安國等在湖南傳播,是謂湖湘學派;楊時、游酢、羅從彥在福建傳播,后經朱熹集大成,是謂閩學派;周行己、許景衡、劉安節、鮑敬亭在浙江傳播,是謂洛學別派事功之學的永嘉學派;王蘋在江蘇傳播,是謂吳學派。
程頤于徽宗大觀元年(1107)去世,他經歷了黨爭激烈的哲宗和徽宗兩朝,后半生可謂就是在黨爭中度過的。哲宗元祐時,舊黨得勢,程頤得以任職崇政殿說書,給皇帝做師傅,自己的“帝王之學”進而得到構建。自哲宗紹圣以來,程頤就面臨著來自新黨的嚴厲打擊,然而這種困境并沒有使他屈服,重要著作《程氏易傳》反而寫成。盡管自己的弟子紛紛離去,卻形成了許多地域性的流派,使自己的理學發揚光大。這正如《老子》所云:“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