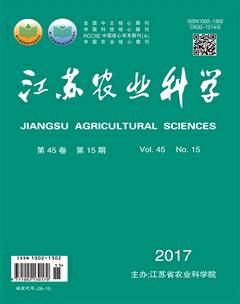喀斯特貧困山區土地利用結構優化
魏媛 李儒童
摘要:為了解決城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問題,采用計量模型對喀斯特貧困山區貴州省貴陽市土地利用動態度變化、生態可持續發展狀況進行定量分析和預測,運用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型對其土地利用結構進行優化。結果表明,2004—2013年貴陽市土地利用類型變化最大的是林地,呈正向變化,增加了2.816%,其次是水域;2004—2013年貴陽市生態足跡表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生態承載力表現出下降的態勢,生態足跡遠遠高于生態承載力,表現出生態赤字現象;2020年研究區土地利用結構總體呈現了耕地、林地、建設用地保持不變,草地、水域增加,其他用地減少的趨勢,人均生態足跡為1.080 3 hm2,比2020年的預測結果減少了 0.480 9 hm2;人均生態承載力為 0.480 9 hm2,與2020年預測結果相比增加了0.073 7 hm2,表明達到了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目的,提高了各類用地的生態經濟效益,有利于促進研究區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喀斯特貧困山區;生態足跡;灰色預測;土地可持續利用;多目標線性規劃;貴陽市;生態承載力;生態赤字
中圖分類號: F323.211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15-0228-05
十八大提出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國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載體,必須珍惜每一寸國土,調整空間結構,有序擴大城市的居住空間、公共設施和綠色空間,保持農業生產空間,逐步、適度地減少農村的生活空間。生態足跡法是評價研究對象可持續發展狀況的方法之一[1-2],目前對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研究主要是從理論和方法兩方面開展的,在理論方面主要有不確定理論、土地適宜性評價理論、景觀生態學理論,方法上主要有線性規劃法、灰色預測法等。李鑫等基于不確定理論,對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進行研究[3]。余光英等將碳平衡引入土地適宜性評價研究中,并選取多目標規劃在適宜性評價的基礎上對城市圈的碳排放權進行優化配置研究,得出各城市2020年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結果[4]。李曉丹等采用景觀生態學中“斑塊-廊道-基質”模式和景觀指數對甘肅省土地利用結構進行研究,得出相應結論并對研究區土地利用結構進行優化[5]。曲藝等引入生態優先的概念,用碳氧平衡法分析規劃目標年區域用地生態約束,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構建基于生態用地約束的土地利用數量結構優化模型,并以江蘇省南通市為例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優化后可保證區域生態安全[6]。魏媛等運用GIS與RS技術對貴陽喀斯特山地城市土地利用動態變化進行了研究[7]。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已運用不同方法對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進行研究,但對喀斯特貧困山區城市的研究較少,貴陽市是喀斯特地貌極為顯著的地區,近年來由于經濟快速發展帶來了城市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結構。因此,本研究對喀斯特貧困山區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進行研究,以期為喀斯特貧困山區土地優化配置以及集約高效利用提供參考。
1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研究區概況
貴陽市位于我國西南區域(24°37′~29°13′N、103°36′~109°35′E),該區地貌有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以山地和高原為主,全省的61.7%是山地,30.8%為丘陵,喀斯特地貌顯著,占全省土地面積的61.9%,2013年貴陽市總人口379.09萬人,土地總面積8 034 km2,人口基數大增長快,1 m2的土地上就有471人,根據貴陽市土地利用變更報告,總的土地面積(8 034 km2)中有耕地271 941 hm2,占土地總面積的33.8%;園地7 452 hm2,占0.93%;林地273 653 hm2,占3406%;牧草地26 670 hm2,占3.32%;建設用地(含居民點及工礦用地、交通用地和水利設施)63 017 hm2,占7.84%;未利用地113 163 hm2,占14.09%。
1.2研究方法
1.2.1生態足跡的計算
在土地面積量化的基礎上,在需求層面上計算生態足跡大小,在供給層面上計算生態承載力大小,然后將二者進行比較,最后對生態赤字/盈余進行判斷并對生態狀況進行評價[8],計算方法:
1.2.7線性規劃模型
把影響土地利用系統的有關因素用一定的參量表示出來,區分可控量(數值有待確定)和不可控量(數值已定)。把可控量當作未知變量,按問題給定的相互關系列出數學方程式或不等式或其他數學表達式,這就是土地利用系統的規劃模型。土地利用規劃系統的數學模型有很多種類,但有其共同點,即由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兩部分組成,規劃意味著尋求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達到最佳目標的途徑。用待定變量函數表示土地利用規劃系統的功能目標(即效益目標)稱為目標函數。設x1、x2、xn為待定變量(系統的土地利用類型),目標函數可表示為
[JZ]F=F(x1,x2,…,xn)。
目標函數反映系統的功能目標與結構、特性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其極大值或極小值代表系統功能的最優值。結構優化存在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和生態、經濟、社會、技術以及土地現狀、潛力、需求等多方面不可避免的限制,數量上表現為對待定變量作如下形式的約束條件:
3式一起構成土地利用規劃系統的結構優化模型。其中,非負性條件也作為約束條件的一部分。若用向量[WTHX]X=(x1,x2,…,xn)、[WTHX]B=(b1,b2,…,bn)分別表示待定變量和約束條件,則土地利用規劃系統的數學模型為
目標函數max(min)F(X),
約束條件g≤(=,≥)[WTHX]B,
非負條件[WTHX]X≥0。
根據實際情況建立模型,編制計算機程序或運用相應軟件進行調試計算。
1.3數據來源
用于生態足跡計算的數據來源于2005—2014年《貴陽市統計年鑒》,為統一數據口徑農產品均采用產量代替消費量,全球平均產量來自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數據庫,貴陽市各類土地利用面積參考各年貴陽市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的數據。生態足跡方法中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的取值見表1[8]。endprint
2結果與分析
2.1貴陽市土地利用動態度分析
土地利用動態度有2種表現形式,包括特定種類單一的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和綜合的土地利用動態度,前者是從局部進行研究,后者是從整體進行研究。而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描述的是某特定區域內、在某時間段內、某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變化。從表2可以看出,9年間土地利用類型變化最大的是林地,呈正向變化,增加了2.82%;其次是水域,也呈正向變化,增加1.89%。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4—2013年9年間各種類型土地面積一直處在變化過程中,同一時期不同類型土地動態度不同甚至方向相反。影響動態度變化的因數是多方面的,建設用地動態度最大年均增加1.81%,說明研究區大量耕地、草地轉化為了建設用地,經濟發展還是建立在資源損耗基礎上,再就是林地年均增加2.82%,說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仍是這一時期的工作重點。
2.2貴陽市生態足跡動態變化分析
根據國際通行標準,貴陽市生態足跡由三大賬戶組成,分別是生物資源賬戶、能源消耗賬戶和貿易調整賬戶,本研究不做貿易調整賬戶,僅從生物資源賬戶和能源消耗賬戶計算貴陽市2004—2013年生態足跡。
2.2.1生物生態足跡
貴陽市的生物資料消費包括農產品、動物產品、林產品和水產品等26項,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1993年有關生物資源的世界平均產量資料[9]將貴州省近10年的消費轉化為提供這類消費需要的生物生產面積,計算結果見表3。表3表明,2004—2013年人均生物生態足跡表現出波動下降趨勢,從2004年的1.023 3 hm2/人波動下降到2014年的0.917 7 hm2/人,揭示節約高效利用資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各類土地人均生物生態足跡的順序為草地>耕地>水域>林地,表明在貴州省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肉類、禽蛋類的消耗占比增大。
2.2.2能源生態足跡
貴陽市能源足跡計算選擇了煤炭、焦炭、燃料油、汽油、煤油、菜油、電力,計算時將能源消費轉化為化石燃料生產土地面積,數據參考前人文獻數據以世界上單位化石燃料生產土地面積平均發熱量[10]為標準。能源生態足跡的計算結果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2004—2013年人均能源生態足跡表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但下降幅度小。2004年為 1.090 hm2/人,2005年達到最高,隨后逐年下降,在2013年為1.047 hm2/人,說明研究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注重能源的節約高效利用,低碳經濟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2.3貴陽市生態承載力動態變化
通過測度和比較人類社會發展的物質需求與自然生態系統所能提供的生態承載力之間的虧狀況有助于對貴陽市資源與環境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有效評估。表4表明,2004—2013年貴州省人均生態承載力及其構成總體上均呈穩中略降的趨勢,在人均生態承載力中,耕地的人均生態承載力最高,占68.10%,其次為林地,約占16.2%,其他草地和水域僅共占0.33%左右,耕地和林地是生態承載力的主要構成部分,表明耕地和林地在生態平衡中的起著重要作用。這種現象與貴陽土地利用中耕地和林所占比有關。
2.4生態可持續性分析
根據表3和表4中的結果計算出2004—2013年研究區人均生態盈余或生態赤字及生態壓力指數,結果見表5。
從表5 可以看出,2004—2013年貴陽市耕地、林業、建設用地為人均生態盈余,草地、水域及化石能源用地為人均生態赤字,總體上表現出生態赤字的現象,人均總生態赤字表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在2005年最高,隨后總體上呈現出波動下降的態勢,從2005的1.792 1 hm2/人下降到2013年的 1.454 0 hm2/人,下降幅度為18.87%,研究明研究區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能源的開發利用及排放的廢棄物超過了生態環境的承載力,生態環境處于不可持續的狀態,但這種情況通過科技水平的提高在逐步緩解;生態壓力指數也在2005年達到最高,隨后表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由2005的5.006 9下降到2013年的4.371 8,下降幅度為12.68%,表明研究區的生態壓力得到一定的緩解,可持續發展能力在緩慢增強,但這與綠色低碳發展的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 貴陽市應進一
步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節約高效利用資源能源、減少碳源、增加碳匯,促進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
3貴陽市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預測
3.1人口預測
采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以2004為基準年,2020年為目標年,對2014—2020年人口進行預測并建立回歸模型:
[JZ]y=-6 367.459+3.352x。
模型擬合結果與樣本實際值誤差較小,擬合優度R2=0969,說明模型具有統計學意義,所以采用此模型對貴陽市人口進行預測,預測結果見圖1。
從圖1預測結果可以看出,2014—2020貴陽市將表現出不斷上升的態勢,2020年全市人口將會達到403.545萬人。
3.2生態足跡預測
通過灰色系統分析方法預測貴陽市生態足跡發展趨勢和狀態。通過建立灰色模型GM(1.1),得到貴陽市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預測公式如下:
生態足跡為x(k+1)=-51.425 993e(-0.091 2k)+51891 993;
生態承載力為x(k+1)=-108.982 924e(-0.193 28k)+111096 024。
其中:k=1,2,3,…,n。表6為模擬值與實際值對比結果。
表6表明,實際值與模擬值擬合效果較好,因此,可利用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公式對貴陽市2014—2020年生態足跡及生態承載力進行預測,結果見表7。endprint
表7表明,2014—2020年貴陽市人均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及生態赤字均表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分別下降了1095%、5.32%、12.77%,表明貴陽市在土地開發利用過程中仍然處于不可持續的狀況,人均生態足跡下降幅度生態承載力2.06倍,揭示研究區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資源環境保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果不是很明顯,因此研究區在未來的發展中須要對土地利用結構進行優化調整。
4貴陽市土地利用結構優化
4.1模型構建
該研究所采用的線性規劃為多目標線性規劃,為了保證貴陽市土地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模型在把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作為決策目標的前提下,同時將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作為約束條件。土地利用變量設置說明見表8。
對多目標線性規劃求解大致分為直接法和間接法,間接算法是指將多目標問題在某種意義下轉化成單目標問題進行求解;直接算法是對多目標規劃本身直接求解或尋求多目標優化問題整個(或部分)有效解集的算法,多目標線性規劃的直接算法主要有單純形法、目標規劃法和模糊規劃法等。這些方法的實現有一定困難,因此本研究采用間接算法對土地利用結構進行優化,優化結果圖2。
從圖2可以看出,2020年研究區土地利用結構優化大致呈現了耕地、林地、建設用地保持不變,草地、水域增加,其他用地減少的趨勢,同時根據2020年優化結果對貴陽市2020年生態足跡進行重新計算,得出的人均生態足跡為 1.080 3 hm2/人,較之于2020年的預測結果減少了 0.480 9 hm2/人;同時對生態承載力進行重新計算得出的結果為0.480 9 hm2/人,較之于2020年預測結果增加了 0.073 7 hm2/人,達到了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目的。
5結論與討論
5.1結論
從貴陽市土地利用動態度中可以看出10年間土地利用類型變化最大的是林地,呈正向變化,增加了2.816%,其次是水域,也呈正向變化,增加了1.894%。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4—2013年10年間各種類型土地面積一直處在變化過程中,同一時期不同類型土地動態度不同甚至方向相反。影響動態度變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建設用地動態度最大年均增加1.811%,說明在土地挖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量耕地、草地轉化為建設用地,經濟發展還是建立在資源損耗基礎上,再就是林地年均增加2.816%,說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仍是這一時期的工作重點。
貴陽市2004—2013年可持續發展評價分析結果表明,貴陽市人均生態足跡表現出波動下降趨勢,從2004年的 2.113 0 hm2/人波動下降到2014年的1.964 7 hm2/人,人均生態承載力也表現出波動下降的態勢,生態足跡遠遠高于生態承載力,經濟發展處于不可持續的狀態。研究區在城鎮化進程中,工業發展對生態造成了很大壓力,經濟發展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生態經濟系統的發展遠遠超出其本身擁有的潛力,最終導致生態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人均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生態赤字預測結果表明,2014—2020年貴陽市人均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生態赤字分別下降了10.95%、5.32%、12.77%,可以看出貴陽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因為貴陽市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區,特殊的地形地貌導致當地土地利用結構存在一定問題,目前貴陽市土地利用效率很低,處于不可持續發展態勢,急需對土地利用結構進行優化。
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結果表明,2020年研究區土地利用結構總體呈現了耕地、林地、建設用地保持不變,草地、水域增加,其他用地減少的趨勢,人均生態足跡為1.080 3 hm2/人,比2020年的預測結果減少了0.480 9 hm2/人;人均生態承載
力為0.480 9 hm2/人,與2020年預測結果相比增加了 0.073 7 hm2/人,表明達到了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目的。經過優化調整后,提高各類用地的生態經濟效益,有利于促進研究區經濟社會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5.2討論
本研究采用計量模型對喀斯特貧困山區貴陽市土地利用動態度變化、生態可持續發展狀況進行定量分析和預測,運用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型對其土地利用結構進行優化,優化調整結果基本上可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但本試驗還存在有待于深入研究之處,對于生態足跡的計算,雖然參照了前人較為有權威性的研究,不同地區生態狀況不同,其影響因子的界定也應當適合于該地區的情況,本研究在影響因子的確定方面由于受數據可獲得性等諸多原因限制,仍然參照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因此,根據研究區實際對影響因子進行調整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周濤,王云鵬,龔健周,等. 生態足跡的模型修正與方法改進[J]. 生態學報,2015,35(14):4592-4603.
[2]魏媛,吳長勇. 基于生態足跡模型的貴州省生態可持續性動態分析[J]. 生態環境學報,2011,20(1):102-108.[HJ1.7mm]
[3]李鑫,歐名豪,劉建生,等. 基于不確定性理論的區域土地利用結構優化[J]. 農業工程學報,2014,30(4):176-184.
[4]余光英,員開奇. 基于碳平衡適宜性評價的城市圈土地利用結構優化[J]. 水土保持研究,2014,21(5):179-184,192.
[5]李曉丹,劉學錄. 土地利用結構的景觀生態學分析——以甘肅省為例[J]. 中國沙漠,2009,29(4):723-727.
[6]曲藝,舒幫榮,歐名豪,等. 基于生態用地約束的土地利用數量結構優化[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1):157-163.
[7]魏媛,王陽,姚晨,等. 基于GIS與RS喀斯特山地土地利用動態變化研究——以貴陽市為例[J]. 江蘇農業科學,2016,44(11):435-439.
[8]楊屹,加濤. 21世紀以來陜西生態足跡和承載力變化[J]. 生態學報,2015,35(24):7987-7997.
[9]劉紅嬌,常勝. 基于生態足跡的土地利用可持續性評價[J]. 湖北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26(2):237-240.
[10]Wackernagel M,Onisto L,Bello P,et al. 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J]. Ecological Economics,1999,29(3):375-39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