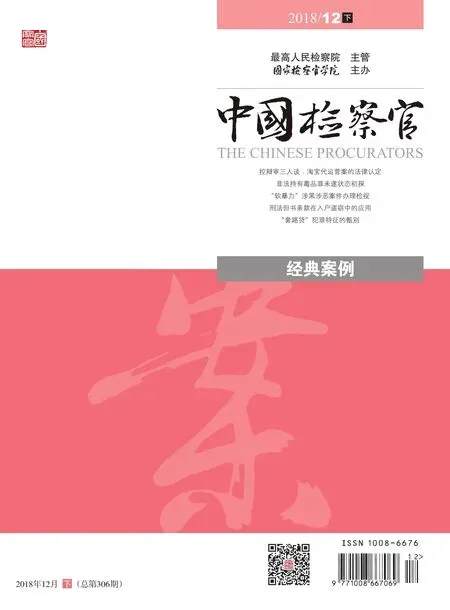承租人不救助出租屋內中毒人如何定性
文◎季文生 閆永磊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300101]
[案情]被告人程某某與孔某某系朋友,二人關系密切。2016年1月6日11時19分,程某某駕駛汽車將孔某某載至某小區(qū),二人共同進入程某某承租的7號樓某室,孔某某在室內誤食鼠藥中毒,程某某明知而未予救助。期間,程某某與他人進行通訊聯(lián)系,并出入案發(fā)小區(qū)。同日18時許,被告人程某某將孔某某轉移至汽車內,后將孔某某拋至某產業(yè)園綠化帶內。同月9日,孔某某尸體被發(fā)現(xiàn)。經鑒定,孔某某系有機氟類劇毒殺鼠藥中毒死亡。
關于本案被告人程某某明知孔某某中毒而不救助,后將尸體拋棄至偏僻處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程某某構成侮辱尸體罪;第二種意見認為程某某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
[速解]筆者認為程某某之不救助行為應以不作為故意殺人罪論處。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程某某具有救助孔某某的作為義務。本案的爭議在于程某某明知孔某某在其承租的房間內發(fā)生中毒后是否具有救助的義務,這也是上述意見罪名相異的根本原因。持第一種觀點者認為程某某與孔某某僅為朋友關系,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義務”“職務要求的義務”“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等法義務來源,據(jù)而認定程某某不具有作為義務。筆者認為,鑒于現(xiàn)實中個案的復雜程度導致理論上無法將義務來源類型確定化,判斷個案行為人是否具備作為義務不應完全依據(jù)形式的作為義務來源,因為這樣很難實現(xiàn)法益的全面保護。基于這一立場,對于需要處罰的不作為犯罪,應判斷被告人之行為是否符合實質的法義務產生根據(jù),即是否對危害結果發(fā)生的原因、進程或領域具有支配地位。具體到本案,被告人程某某系案發(fā)房屋的承租者,孔某某生命的保全與逝去處于被告人的支配之下,基于二人之間的密切關系及所處的封閉空間,孔某某生命法益的狀態(tài)變化完全、具體地依賴于特定人程某某,即程某某能夠對明知的、已經發(fā)生的危險(中毒結果)施加控制性影響,且具有排他性救助地位,由此可以確認孔某某死亡結果的發(fā)生進程及發(fā)生空間均處于程某某的支配之下,符合實質的法義務根據(jù),應產生作為義務。
第二,被告人程某某有能力履行救助義務且可能挽救孔某某生命。現(xiàn)有證據(jù)表明,孔某某發(fā)生中毒后,程某某能夠自主使用手機、自由出入案發(fā)小區(qū),具備施救的能力與條件,但其并未施救。被告人程某某與孔某某共處一室,知曉孔某某發(fā)生鼠藥中毒具有即時性。醫(yī)學資料表明,有機氟類殺鼠藥中毒行為發(fā)生至產生中毒癥狀時間間隔一般為半小時至兩小時(慢則4個小時以上),且有機氟類殺鼠藥存在特殊解毒劑乙酰胺,若程某某及時予以救助,孔某某死亡結果可以避免。綜合上述分析,程某某之不救助行為符合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犯罪構成。
第三,被告人程某某之拋尸行為符合侮辱尸體罪犯罪構成,因系事后行為而不具可罰性。筆者認同第一種意見對拋尸行為的定性,被告人程某某將孔某某尸體拋棄至偏僻處,損害了尸體的尊嚴,有違公序良俗,構成侮辱尸體罪。但由于其不救助行為與拋尸行為系對同一對象實施,故雖兩個行為侵害兩項法益,但基于事后不可罰理論,拋尸行為不應再獨立成罪。
結合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以不作為的故意殺人對被告人程某某之行為進行評價,符合不真正不作為犯的理論要義,也符合法益保護的現(xiàn)實需要。程某某的行為應定性為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