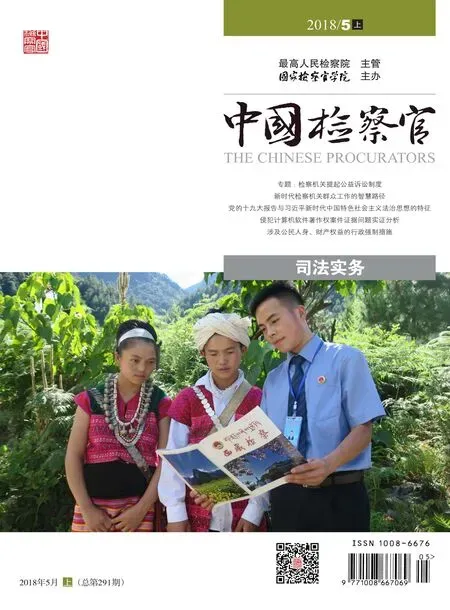刑事證據審查的基本制度結構
2018-02-07 00:17:50吳洪淇
中國檢察官 2018年9期
文◎吳洪淇
現代刑事證據審查體系是以“證據準入—證據評估相分離”為核心特征,由術語范疇、審查主體、審查標準與程序保障等多個維度構成的一個立體制度結構體系。多層次的立體制度結構體系有利于保障證據準入與證據評估的相對分離,從而確保刑事證據規則的有效實施。
我國最新的刑事證據立法已經通過“材料—證據—定案根據”這三個基本范疇確立起證據準入的兩道審查門檻。第一道門檻是從“材料”到“證據”,包含著對材料證明作用和材料形式分類的兩項審查要求。第二道門檻是從“證據”到“定案的根據”,包含著真實性、可采性(未被法律規則所明確排除)和證明力的三項審查要求。
我國證據審查的基本制度結構呈現出四個基本特征,在當下我國刑事司法環境當中存在一定的潛在危險。第一,我國的證據審查體系是二元審查結構,而對材料、證據和定案的根據的審查并未呈現訴訟階段上和訴訟主體上的分離。第二,證據審查的制度結構呈現扁平化的線性特征,從審查主體上看,職業法官承擔著證據準入與證據評估的雙重職責;從審查程序來看,證據準入活動與證據評價活動并未呈現明顯的分離。第三,證據的準入要求與證據證明力評估標準被混同在一起,這將大大提高證據準入的一般性標準,并可能鼓勵事實認定者為了獲得證據的相互印證而忽略了證據的準入這一前提條件。第四,證據審查的程序場域呈現多中心的彌散格局,證據審查流程既可以發生在審判階段,也可以發生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
因此,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推進,我國刑事證據審查的制度體系也需要出相應的調適。
猜你喜歡
哲學評論(2021年2期)2021-08-22 01:53:34
新世紀智能(數學備考)(2020年11期)2021-01-04 00:38:16
遼金歷史與考古(2019年0期)2020-01-06 07:44:44
中華詩詞(2019年7期)2019-11-25 01:43:04
影視與戲劇評論(2016年0期)2016-11-23 05:26:01
中國衛生(2016年7期)2016-11-13 01:06:26
中國衛生(2016年11期)2016-11-12 13:29:18
中國衛生(2016年9期)2016-11-12 13:27:58
現代企業(2015年9期)2015-02-28 18:56:50
新高考·高一物理(2014年1期)2014-09-18 01: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