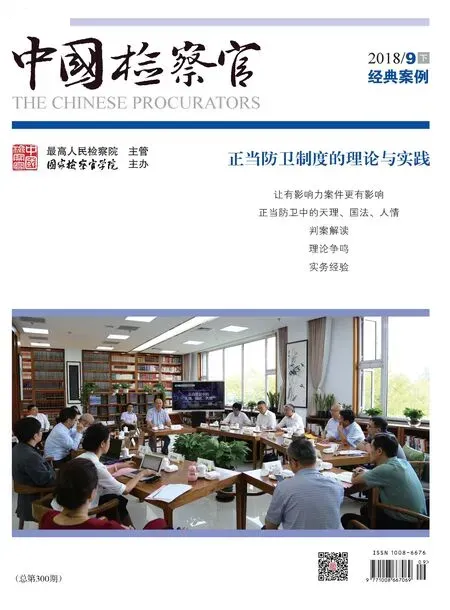不退讓和城堡規則在正當防衛制度中的運用
阮齊林(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案例是推動學術發展的火車頭,其實也是推動立法、司法的火車頭。在于歡防衛案、昆山防衛案發生之后,大家聚焦于正當防衛制度適用的時候,國家檢察官學院及時召集各位學者聚在一起,研討于歡案、昆山防衛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案件發生過、處理完,熱鬧一陣后就一哄而散過去了,錯失良機,十分可惜。今天,召集各位學者、司法實務人員,繼續從法理、學理上進行總結和升華,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我今天借昆山防衛案想講的話題是:一方面,天理、人情影響到從于歡案到昆山案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另一方面,通過《刑法》第20條正當防衛國法的適用于于歡案和昆山案,推動天理、國法降落人間。這個天理、國法降落人間,形成人們的交往準則、社會秩序,或者說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禁忌。
正當防衛有兩個要點:第一是“前提條件”,正在發生著不法侵害,這是“啟動”防衛的前提條件。具備這個前提,就能夠適用正當防衛制度,即使不能成立正當防衛至少可以成立防衛過當,即使因防衛過當造成損害構成犯罪,至少具有一個法定的應當減輕、免除處罰的情節。于歡案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之后二審改判為5年有期徒刑,一審與二審的事實證據相同,處罰卻天壤之別,根源是有沒有啟用正當防衛。二審認為于歡致人死傷的行為是針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適用正當防衛制度,屬于防衛過當,依法應當減輕處罰,故判處5年有期徒刑。由此可見,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關鍵是確認“發生了不法侵害”。發生正進行的不法侵害,就涉及到何時何種情況之下能夠啟動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這就想到人們常說的兩個正當防衛方面的規則:
其一是“不退讓規則”,面對不法侵害不退讓。如昆山防衛案,劉海龍持刀攻擊,顯而易見是不法侵害,于海明面對其不法侵害,可以啟動防衛權進行防衛。沒有人對于于海明的行為具備防衛前提有異議,因為不法侵害太明顯,所以昆山案的焦點在防衛限度上,防衛前提上的分歧。于歡案則不同,一審判決只是認為對方有“過錯”,不屬于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因而沒有啟動防衛制度,由此導致于歡失去了防衛過當的法定減輕處罰情節,導致于歡被重判無期徒刑。可見,需要考慮合理啟動防衛制度。換言之,公民遭遇不法侵害有權不退讓,針對什么樣的不法侵害可以不退讓、實施防衛,不退讓規則該如何掌握?這個應當以人們交往規則為依據。俗話說的“君子動口不動手”,人們發生爭執,動口不動手是“君子”,君子處事之道,就是人們解決糾紛的基本規則。人與人之間難免發生糾紛,最基本的解決方式是擺事實、講道理、守法律,不得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動輒訴諸武力或暴力,“動手”是違反規則和法律的,非君子之道。確定了這個規則后,再來考慮“不退讓”,是對什么“不退讓”?應當是對率先發起的暴力攻擊不退讓。發生了爭執,如果一方沖上來打人,另一方不必逃避,就站在那里,給予前來暴力攻擊者迎頭痛擊。這是防衛前提起點,技術性非常強。有一個指導案例:甲乙二人騎車時發生碰撞,繼而爭吵,之后甲沖向乙揮拳打乙。甲乙爭吵之時雙方尚有一定的距離,甲揮拳打乙之前有沖向乙的過程。乙被甲拳擊的同時反擊一拳。甲被拳擊中頭部摔倒,后腦勺磕地致顱下腔蛛網膜出血死亡。這個指導案例要旨認為乙拳擊行為不具有故意傷害性質,不成立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僅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案例指導要旨沒有提及防衛。我在課堂上講這個案例時,就有學生提出來,甲率先沖向乙揮拳打乙,屬于不法侵害,乙不退讓原地還擊一拳應該是防衛行為。只不過乙回擊一拳打得比較瓷實,致年已6旬的甲頭部遭拳擊摔倒、后腦磕磕地死亡。對這類偶發糾紛引起爭執,一方沖來率先揮拳襲擊,是否可以認為是不法侵害?另一方沒有躲避退讓,而是在遭到拳擊后揮拳反擊,是否可以認為針對不法侵害的反擊?從而啟動防衛前提。這值得討論,不退讓到底針對什么而言?如果能夠達成共識、通過發布系列案例示范認定規則,將有利于正當防衛制度的合理啟動。同時,也有利于促進社會文明禮貌規則。發生糾紛、爭執,人人需恪守“動口不動手”的君子規則,擺事實講道理;講不通,可以報警找警察尋求公權力救濟,依法解決糾紛。誰也不許率先動手打人,訴諸暴力。誰率先動手攻擊他人,就認為是不法侵害,被攻擊一方對其反擊,就可以認為是針對不法侵害的反擊,就可以啟動正當防衛,也即認為具備“防衛前提”。
人們發生糾紛,比如說走路、騎車相撞,汽車發生刮蹭,一般有三種可能:一是有理方率先攻擊,比如對方逆行,違反交通規則而且不留心觀察導致相撞。有理一方火冒三丈,動手打人。這種情形率先動手打人,是否應當認為是不法侵害?對其反擊是否認可具備防衛前提?最令人猶豫。我認為,未嘗不可認為是不法侵害,因為破壞了“君子動口不動手”的規則。交通中相撞或刮蹭畢竟是無意的,率先動手打人是故意的,性質不同。當然,個中是非曲直非常重要,有理方斥責無理方在情理之中,如果無理方蠻不講理,激怒有理方有推搡舉動,這類激憤中肢體動作不能認為是不法侵害,不得啟動防衛權。年輕力壯一方無理,在爭執中蠻不講理故意激怒對方率先動手之后予以痛擊,應當認為是防衛挑撥,不應認為具備防衛前提。二是雙方各有過錯,爭執起來,率先動手打人可以認為是不法侵害。三是無理方不知錯或不認錯,爭執起來還率先動手打人,就像昆山案中的劉海龍,應當認為是不法侵害。總之,堅持一個基本原則,發生糾紛爭議,誰也不許率先打破“君子動口不動手”的規則,正當防衛的“不退讓”,應當是針對破壞“動口不動手”規則的行為。久而久之,形成“禁忌”,爭執中誰也不許率先動手。這個一般規則之外,認定防衛前提時,還需重視個案中的是非曲直,嚴格防范惡意防衛挑撥行為。
此外,遭遇到無端或無緣無故的侵害,如遭遇搶劫、盜竊、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行為的不法侵害,當然可以啟動防衛權,認為具備防衛前提。
其二是“城堡規則”。“住宅”或“家”是人們生活起居場所,也是人們人身、財產安全的庇護所,身心安寧的港灣。因此,住宅遭遇非法侵入,就可認為是不法侵害,主人可啟動防衛權。非法侵入住宅行為,侵害到人的安全、安寧的最后寄托之地,往往會引起主人嚴重不安,也嚴重威脅到人對于自己住宅的主權感、支配感。法律也應當維護住宅庇護功能、主人的主權感。因此,應該賦予主人在自己住宅、維護住宅安全的優越地位,可啟動防衛權。比如,半夜突然有人出現在客廳里或院落中,好多人家是空巢老人手無縛雞之力,或家中有老有小。在家遭遇這樣突如其來情況,主人主動攻擊致不明侵入者死傷的,應當認為是防衛行為。如果事后發現是鄰居醉酒或夢游或其他不速之客走錯門,沒有違法犯罪意圖,對這種情況我們過去都認為不是不法侵害,對其防衛是“假想防衛”。這種見解有問題,因為未經主人許可進入他人住宅,即使沒有違法犯罪惡意,也應當認為是非法侵入住宅行為,可以認為是不法侵害,可以啟動防衛制度。即使造成不應有損害承擔刑事責任,至少具有防衛過當的法定減輕、免除處罰情節。再如,債權人、討債人未經同意也不得進入債務人住宅討債,也不得有侵犯住宅的行為。如果有非法侵入住宅行為,可以啟動防衛權或者報警求助。不能憑借存在經濟糾紛的理由就可以隨意侵犯住宅權。因為經營貸款業務,存在債務人無力償還甚至賴債的風險,不能把防范這種風險建立在滋擾、妨害債務人居所安寧的基礎上。
綜上,一方面通過確立不退讓規則和城堡規則,保護人身、住宅安全,另一方面,還要進一步深入探討對什么行為可“不退讓”,啟動防衛權;對什么樣侵犯住宅行為,可以按照“城堡規則”,啟動防衛權,從而合理適用正當防衛制度,保護個人人身、財產安全、人格尊嚴。由此促進“君子動口不動手”、尊重住宅安寧的觀念深入人心,維護社會生活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