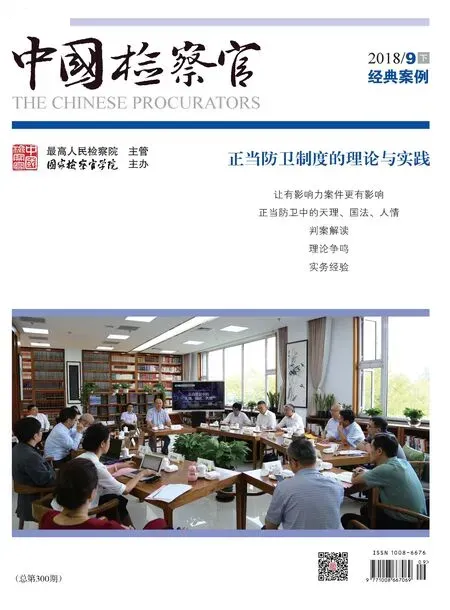正當防衛疑難問題的司法適用
文◎王 勇
9月1日,昆山市公安、檢察機關相繼通報了“8·27”于海明致劉海龍死亡案調查處理結果,認定于海明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公安機關依法撤銷案件。處理結果發布后,社會各界紛紛給公安、檢察機關點贊。本案從開始引爆輿情到最終實現民意和法治的高度共振,折射出一個現實問題:認定正當防衛案例稀缺,因此才值得高度關注。盡管我不同意正當防衛是僵尸條款這種過于絕對化的觀點,但確實無法否認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認定難的現狀。因此,個案的處理只有上升為類型化的經驗,對司法實踐才有真正的指導意義。
一、《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行兇”要從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兩個層面把握
(一)形式要件
“行兇”并非法律用語,在漢語中的含義基本上可統一為“殺人或傷人(打人)”。但將“打人”全部認定為《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的“行兇”,則明顯擴大了范圍,對保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不利。因此,刑法規范中的“行兇”應視為一種嚴重暴力侵害行為,在形式上具有暴力性、手段的不限定性、程度的嚴重性等特征。
本案中,劉海龍持管制刀具毆打他人,盡管未導致可鑒定的傷情后果,但形式上符合“行兇”的要求。管制刀具之所以被嚴格限制,攜帶即可被治安處罰,就是因為具有顯著危險性、暴力性、不可測性等特征。由我國司法解釋的一貫立場也可略見一斑:如《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都將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直接視為兇器。因此,持兇器隨意毆打他人,符合“行兇”的形式要件。
(二)實質要件
判斷一個行為是否為 《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行兇”,除形式要件外,關鍵要看是否為“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就是要看實質要件。但是,此處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不應也不可能要求確實發生,只要有較大可能性即可。“較大可能性”的判斷,應結合全案證據情況,進行綜合評判。
本案中,劉海龍在客觀上實施了三個行政違法行為(非法攜帶管制刀具、實線變道、結伙毆打他人)和兩個犯罪行為(危險駕駛罪、尋釁滋事罪)。從其短時間現場違法行為可看出,其不法行為數量多且逐步升級,從攜帶管制刀具到危險駕駛罪,從違反治安處罰法的毆打他人到尋釁滋事罪,沒有限制、約束自己的跡象。醉酒的劉海龍在毆打于海明已經占優的情況下,又取出砍刀攻擊,同行的劉某某都無法勸阻,難以預料其下一步攻擊是否會繼續升級。因此,如僅憑沒有發生危害后果認定沒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勢必要求防衛人等待劉海龍刀刃砍擊、刀尖捅刺時才能防衛,即使對擁有“空手入白刃”的能力者也過于苛責,何況對于社會一般人。
二、《刑法》第20條第3款“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要結合現場具體情景以社會一般人的認知水平進行判斷
防衛行為通常類似叢林狀況下的本能應激反應,要求防衛人在孤立無援、高度緊張的情形之下明確判斷對方實質的侵害意圖,進而仔細觀察對方的打擊方式和可能對自己造成的損害后果,不僅明顯違背立法精神,也有悖常理常情。所以,“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要結合現場具體情景以社會一般人的認知水平進行判斷。而不應當單純的客觀判斷或者主觀判斷——單純事后的客觀判斷,容易對防衛人過于苛責;單純基于防衛人立場的主觀判斷,容易限縮假想防衛的空間。
綜觀本案言辭證據就可以看出,案發現場的人員,在瞬間的驚嚇中,均不能完整陳述整個過程,而是只記得一個片段。央視播放的防衛人于海明的錄像中也提到“當時感覺就是要死了的那種感覺。就感覺頭‘嗡’了一下,什么都想不起來那種感覺。”在激烈的爭奪中,于海明搶先一步拿到刀的同時,順手捅刺對方屬于本能反擊。司法人員不能苛求防衛人在激烈的爭奪中,精準的遏制對方的不法侵害作為限度,更不能根據我們事后對視頻反復播放研究出的結論,認為對方不是行兇,否認適用無限防衛權。
從社會一般人的角度而言,本案中劉海龍先是徒手攻擊,繼而持刀連續擊打,其行為已經嚴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其不法侵害應認定為“行兇”。這種“行兇”是現實存在的,不屬于事實認識錯誤,不應認定假想防衛。
三、《刑法》第20條第1款中“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應進行整體判斷而不能進行簡單的攻守比較
司法實踐中對于如何把握 “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也是一個重大爭議問題。我們在論證本案時,就有觀點主張分段認定于海明的行為:前期對方進攻,于海明防守,有正當防衛權;于海明持刀捅刺對方腹部、臀部后,已經變成進攻者,對方喪失了不法侵害能力,成為防守者。于海明此后砍擊、追擊行為屬于事后防衛,可獨立評價為故意傷害行為。
這種論述方式本質是將正當防衛時空進行了人為分割,未考慮現場人員的感受和實際情況。一是就本案而言,于海明前五刀盡管可以再次細分為兩刀和三刀,但這五刀在七秒完成,捅刺屬于時間間隔較為緊密的連續過程,屬于一個整體。進而言之,于海明后面追擊未砍中的兩刀,與前面五刀盡管在時間上有間隔,空間上有距離,但時間沒有因為介入因素而中斷,空間也是現場的短距離延續,反擊行為一氣呵成,也應視為一個整體行為。易言之,除非時空有明顯距離,如對方已經逃走還長途窮追不舍等,否則不宜認定事后防衛。
二是對于海明而言,劉海龍的同行人員劉某某也對其實施過暴力毆打行為,其他同車人員盡管為女性,但都是劉海龍一方人員,應作為一個整體陣營看待。劉某某等人一直在現場,應視為共同對于海明人身安全構成威脅,不能認為劉海龍倒地危險就已經消除。
三是劉海龍砍刀甩落在地后,其立即上前爭奪,沒有放棄跡象;其受傷起身后,立即跑向原放置砍刀的汽車——于海明無法排除其從車內取出其他“兇器”的可能性。砍刀雖然易手,危險并未消除。盡管表面上看,短時間內攻守易勢,但于海明的“攻”仍然是防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延續,不是獨立的“攻擊”傷害行為。
四、從法律規定正當防衛的價值看,要適當作有利于防衛者的選擇,樹立防衛者優先保護的觀念
“合法沒有必要向不法讓步”。正當防衛的實質在于“以正對不正”,是正義行為對不法侵害的反擊。故應承認防衛者在刑法中的優先保護地位。在刑事政策上,在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之間難以明確清晰界定的時候,實際上存在著防衛者和不法侵害者的人權保障沖突問題——認定為正當防衛,有可能使不法侵害者的人權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視;而認定為防衛過當,又可能打擊了無辜,挫傷了公民與不法侵害行為作斗爭的積極性。在二者產生矛盾時,利益保護的天平傾向于防衛者合乎天理國法人情。
實踐中,許多不法侵害是突然、急促的,防衛者在倉促、緊張狀態下往往難以準確地判斷侵害行為的性質和強度,進而選擇相應的防衛手段。在事實認定和價值判斷上,司法者都應作出對防衛者有利的選擇,從而樹立良好的社會價值導向。本案是劉海龍交通違章、尋釁滋事、持刀攻擊在先,于海明面對這樣的不法侵害有正當防衛的權利。如果在事實和價值上不作出對于海明有利的選擇,不僅難以起到警示那些惡意滋事者,更會在未來,讓公民不敢行使法律規定的正當防衛權利。
現實中,對于發生緊迫性的不法侵害,應當如何處理,社會公眾缺乏重大影響案例的指引。本案認定為正當防衛,理清了正當防衛的界限,具有破除錯誤認識、倡導社會良好風尚、弘揚正氣的現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