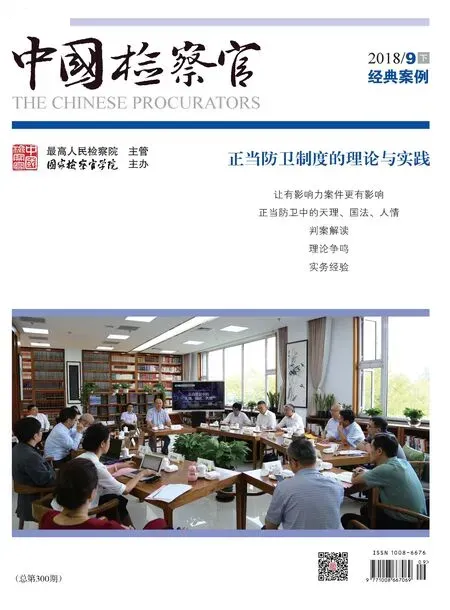防衛過當的認定:思維誤區與方案選擇
梁根林(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長期以來,我國刑法規定的正當防衛制度沒有被真正激活,立法者的良苦用心沒有被真正的體認。盡管《刑法》第20條對正當防衛的條件、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區分已經做了非常明確、具體的規定,立法意圖與目的亦非常清晰,但是司法實踐多年來一直沒有完整而準確地予以理解與把握,由此導致正當防衛條款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僵尸條款。就此,我圍繞正當防衛特別是防衛過當的認定與處理著重講以下幾點:
第一,正當防衛如何判斷,特別是防衛限度與防衛時間如何把握?我覺得,司法實踐中要注意避免四個方面的誤區:第一個誤區是對防衛人提出“客觀冷靜的圣人標準”,即以一個客觀冷靜的與己無關的圣人標準,要求防衛人面對突然而至、猝不及防的暴力攻擊,做出客觀冷靜、精確理智的反應;第二個誤區是“事后諸葛思維”,不是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換位思考,站在當事人所處的突發情景,斟酌他面對暴力攻擊時能夠做出什么樣的反應,而是以一個事后諸葛亮的標準去苛求防衛人;第三是“對等武裝論”,在判斷是否防衛過當時,總是要求防衛人采取在總體上或者基本上與不法侵害同樣的打擊方式,選擇同樣的打擊部位,實施同樣的打擊力度,造成基本相當的傷害結果,否則,就認定為防衛過當;第四是“唯結果論”,往往認為只要防衛行為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結果,特別是死了人,就要按防衛過當論處,甚至直接認定為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司法實踐如果不跳出這四個思維誤區,正當防衛制度就沒法真正被激活。
第二,正當防衛與天理、國法、人情。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法治理念與法教義學有一個誤區,認為無論是入罪還是出罪,只要嚴格依法裁判,形式上有法律根據就行。我們往往把復雜的定罪思維過程簡化為個案事實和法律規定對號入座的三段論演繹推理過程,導致司法實踐中機械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思維盛行,排斥天理、人情對國法的滲透與制約。關于這一點,我想提請大家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我們的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關于“天理國法人情”的那些東西到底是應當予以揚棄的糟粕,還是應當汲取的法文化精華。我最近拜讀了范忠信教授等著述的《情理法與中國人》。該書有一段歸納非常好,我在這兒念一下,跟大家一起分享。 該書指出:“國法是一個孤島,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橋梁,如以天為彼岸,人為此岸,則天理溝通了彼岸,人情架通了此案,國法居中連接兩岸”。有人可能會說這是糟粕,我們現在學習西方法治與西方法教義學,人家不講天理,不講人情。但是,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大家都知道自然法,自然法源于古希臘,在十七、十八世紀得到復興。自然法講得最多的是什么?是自然權利、普遍理性與公平正義,并且主張用自然法來審視、校正實定法、人定法。如果實定法、人定法違反了自然法的基本理念,就可能產生“惡法非法”的合法性危機。在自然法的終極審視下,當代法治觀念不再拘泥于純粹的規則自治,不是僅僅強調形式理性,而是強調良法之治與良法善治,追求具體法治與個案正義。這是在形而上的理念層面強調自然法對實定法的終極審視,這種意義上的自然法其實就是我們中國法文化的天理。在形而下的操作層面,德國、日本發展出來的刑法教義學一方面把自然法的理念,即天理融入到法教義學的價值判斷之中,另一方面則把對人情的關照和關懷融入到定罪思維模式之中,據此發展出區分不法與責任的階層犯罪論體系,在責任論中不斷地吸納人情對定罪的影響,在心理責任論的基礎上發展出規范責任論,在規范責任論范疇內進一步衍生出期待可能性、違法性認識可能性等旨在體現“法律不強人所難”這一法諺的新的責任要素。可見,中華法文化與西方法文化在解釋與適用國法的過程中都十分重視兼顧天理與人情,都特別強調解釋和適用刑法、處理個案時應當依據國法,上通天理,下達人情。
第三,防衛過當案件的解決方案選擇。方案之一是現實中比較通行且能夠接受的方案,即在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不區分不法與責任的理論前提下,對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作整合不法與責任內涵的統一理解,防衛過當是客觀上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結果、主觀上行為人具有過錯或者罪責的不法行為。因此,立足于鼓勵與保護公民行使正當防衛權利,對正當防衛應當從寬認定,對防衛過當則應當從嚴認定,能夠不認定為防衛過當的盡量寬松認定為正當防衛。但這并非最佳方案。其實比較理想的方案應當是基于不法與責任的二元區分,即在肯定防衛過當不法的前提下將防衛過當區分為有責的防衛過當與免責的防衛過當兩種形態。有責的防衛過當不僅客觀上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而且行為人對此具有罪責,主觀上對防衛過當不法行為具有可非難性,因此應當認定為犯罪,只是在處罰時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而免責的防衛過當則是,雖然行為后果上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但行為人于防衛當時不具有合理地把握防衛限度的期待可能性,因而不值得用刑罰對其防衛過當行為進行非難譴責,其防衛過當行為雖然構成不法,但因缺乏罪責,仍然不構成犯罪。“于歡案”如果按此方案處理,也許更加令人信服,效果更好。這種方案既維系了正當防衛制度的權威性,又結合了個案的具體情況,兼顧了當事人的特殊情況,把法律規定的一般正義與個案正義很好地予以結合,因而我們的司法實踐應當在接受不法與責任的區分的基本思維邏輯的基礎上,逐漸嘗試按照這種方案處理防衛過當案件。當然,處理防衛過當案件還有一個更為徹底而有效的解決方案,那就是借鑒德國刑法第33條的規定,在現有的刑法條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防衛人在反擊不法侵害時因驚慌、恐懼、憤怒而防衛過當的,不受處罰”。盡管我同樣認為,如果把現有的法律解釋到位并加以正確適用,原本不必在立法上引入類似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缺乏充分的正確理解與適用法律的能力的情況下,立法上明確規定免責的防衛過當不罰,也許具有更為明確的規范指引與政策宣示作用,更有利于司法實踐妥當地處理正當防衛案件,避免錯誤地將不該入罪的防衛行為認定為犯罪,從而促進刑事司法個案正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