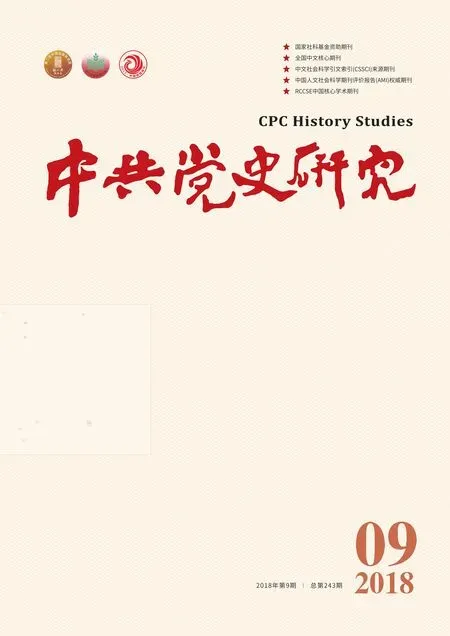“跨文化與地域”視野下知青史研究的新路徑
丘 新 洋
一、對地域性知青史研究的反思
近些年來,在當代中國史研究領域,基于地方檔案的個案研究開始蓬勃發展,諸多以往不為人所知的地方史圖景和地方性知識得到了很好的展現與建構。學界之所以有此反思與突破,既得益于地方史料的新發現,又得益于學者們對現有研究模式不滿而希望尋求一條理解當代史脈絡新路徑的努力。事實上,當代中國史研究中的知青史研究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想要有進一步的突破,除了應該做到從“走入知青”到“走出知青”外,還需要在地域性
① 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53頁。
知青史研究方面大做文章。
由于上層檔案開放程度有限,加之早有定宜莊、劉小萌、潘鳴嘯(Michel Bonnin)、伯恩斯坦(Thomas P.Bernstein)等人研究成果的珠玉在前,全國性知青史研究陷入低潮,相應地,地域性知青史的研究傾向卻日趨明顯。雖然地域性的個案研究極大細化和深化了知青史的內容,展現出全國各地知青運動的多元性和復雜性,但它也面臨著三大困境。其一,研究區域受到行政區劃界線的規制。地域性知青史的個案研究多囿于人為劃定的行政區域,而忽視了一些邊緣、交界地區客觀存在的橫向聯系。其二,研究內容難以進一步拓寬或延伸。雖然學者們在知青下鄉動因、回城安置、城鄉關系、閱讀經歷、個人記憶、生產勞動、家庭婚姻、醫療衛生、教育學習等內容上取得了較多成果,但仍未能跳出知青史研究,展現人類歷史中更為宏大的一面,如文化群體間的交流等。其三,研究成果同質化現象凸顯,“盡管地區不一樣,但關于知青運動的主題一樣,政策的貫徹一樣,形成的文獻也類似,由此而展開的研究也就難免‘千篇一律’”[注]易海濤:《資料·內容·理論方法:中國知青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期。。
由此可知,地域性知青史研究必須進行結構性和整體性的反思,比如,如何跳出知青史研究的范疇,以“文化地域”“社會移民”的角度將知青運動置于整個中國史乃至全球史的視域中去考察和理解?如何將地域性知青史研究的目光聚焦在邊區地帶和少數民族地區,在跨區域的視野下對比不同地區的知青運動,并對運動中鄉村社會的經濟、宗族等經典命題作一番探討?
二、“他鄉之客”:知青運動中的文化沖突
如果放在更為宏大的長時段中看,涉及上千萬人的知青史又何嘗不是一部人口移民史或文化交流史。人生而處于文化之中,并在社會交往中耳濡目染地習得和適應所處的文化。而中國自然、社會環境的極大差異使得各地城市、農村有著不一樣的文化形態。當城鎮知青群體脫離長期生活的主體文化區域,以主體身份進入到一個陌生的客體文化區域時,便會因語言、風俗、思維方式等諸多文化要素的差異而產生不適應感,進而造成文化沖突。
筆者以為,知青運動中農民群體與知青群體的文化沖突是多元的,并在兩個層面上得以體現:其一,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的沖突。農村文化是在農村社會生產方式基礎上,以農民為主體并建立在農村社區的文化,它是農民文化素質、價值觀、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反映。然而隨著新中國工業化戰略的啟動,逐漸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上出現了較深的隔閡,所以當來自城鎮的知青群體與長期生活在農村的農民群體相處時,兩者便因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在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而發生沖突。比如,來自沿海城鎮的女知青習慣在酷熱的夏天下海游泳,而當她們在另外一種文化場景內仍穿著泳衣在水庫或小溪游泳時,就與農村保守的思維觀念發生了沖突。又如,知青對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表示不滿,而農民則對知青男女之間的自由交往甚為反感,等等。其二,特定文化區域內主體文化與客體文化的沖突。文化區域是具有同種或相似文化特征、生存方式的地理區劃,其分布不以行政區劃為界線,如客家文化區分布在閩粵贛邊區,畬族文化區則主要集中于閩浙邊區等。當外地知青進入特定文化區域時,文化沖突便會在語言風俗、宗族傳統、婚姻觀念等方面得以體現。其中語言最容易表現族群間的聯系,特別是在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內,語言的巨大差異使得外地知青有種被圍困、被隔絕的感覺。日常飲食和節日習俗上的文化沖突亦復如是,例如廈門人有在中秋節玩“博餅”的習俗,然而當這一做法被知青帶入客家地區時,卻被當地農民誤解為賭博;又如,插隊在山西農村的外地知青對當地婚禮上的“鬧婚”習俗給予了抵制。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要關注知青運動中的文化沖突外,也要承認文化適應與文化融合的一面。比如,廈門知青積極主動地學習客家方言,福州知青在畬族地區插隊時入鄉隨俗地尊重當地文化風俗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城鎮知青在服飾、發式、婚戀觀念、生產方式等方面對農村農民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比如杭州知青在建德山區插隊時,周圍的一些農村青年在穿著上、發式上也悄悄地學著他們的模樣。
雖然文化沖突往往伴隨著文化交融,但潘鳴嘯對知青與農村關系的研究表明,兩者之間的影響是有限的,在文化上很難做到真正交融。事實上,知青群體之所以會有偷雞摸狗、斗毆打架等“消極抵制行為”,文化沖突所造成的邊緣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在以往解釋相關行為的動機時常常被忽視。
文化沖突何以導致知青群體被邊緣化?筆者淺見,可以從兩個維度進行思考:一方面,知青群體脫離了具有約束力的組織而成為“他鄉之客”。知青群體是在城市、社區、學校的嚴格規訓和家庭的監督約束下成長的,明確的組織關系使他們不敢有所逾越,而當他們進入農村社會時,這些外在的約束和規訓便消失了。加之農村社會對知青群體缺乏強有力的管制,一些知青便游走于農村與城市之間,比如有人長年累月地在其他地區串聯,拒絕下地干活,公社和大隊干部對此或者視而不見,或者無能為力。另一方面,農村社會中復雜的宗族關系對文化不同的外來知青群體有一種排斥力。特別是在南方的山區農村,多山丘陵的地理形態使得血緣型家族村落得以賡續。雖然宗族勢力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系列社會革命中遭受嚴重打擊,但其聚集的空間結構并沒有被完全破壞,甚至與此相關的傳統民俗也還在農村地區延續著,所以作為“外來人”的知青群體是很難真正融入其中的,有不少知青甚至還卷入了村內復雜的宗族關系中,最終造成的傷害反而增大了知青群體對農村社會的離心力。雖然筆者認為文化沖突是導致知青群體出現消極抵制行為和逐漸被邊緣化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否認的是,在很多時候,口糧、工分、返城、安置等關乎切身利益的因素在農民和知青的沖突中起著更具決定性的作用。
三、傳統交流的延續:邊區視域下的知青運動
地域性知青史的個案研究以省、市作為切入點,既易于操作又便于“解剖麻雀”,但對于一些特定區域,倘若仍以人為劃定的行政界線來研究,便會忽視行政界線之外的客觀聯系,誤將區域空間當作自足的封閉性實體。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在研究中國帝國晚期城市時已注意到,區域系統的研究要擺脫傳統的以行政單位為界線的方法[注]參見〔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第327—343頁。。筆者以為,在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中亦當如此,所以除了繼續拓寬和加深原有的地域性知青史研究外,還應該以“跨地域”的視野來關注一些容易被忽視的特定區域,如多個省份交界的邊區地帶和少數民族聚集地。
邊區視角在對1949年以前歷史的研究中是比較常見的,比如對革命根據地的考察往往圍繞著閩粵贛、鄂豫皖、陜甘寧、晉察冀等邊區進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加強了對地方政權的控制,超越行政區劃的邊區模式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不過,最近有研究成果表明,以邊區視角展開研究仍具可行性[注]參見溫銳、游海華:《勞動力的流動與農村社會經濟變遷:20世紀贛閩粵三邊地區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例如,閩粵贛邊區雖然被高山大嶺割裂成三個互不統屬的自然區域,但通過境內的贛江、汀江、梅江和眾多支流,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商業貿易圈。隨著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全國各地農村的商業貿易遭到強勢擠壓,農民也幾乎喪失了遷移往來的自由。然而,一系列社會革命下的閩粵贛邊區鄉村社會依然延續著舊有的一些傳統,即邊區內的人口流動和商業往來常常大于邊區外。比如在人口流動上,人口較為密集的粵東和閩西仍然會朝著較為稀疏的贛南遷移,具體來說,就是廣東梅縣地區的農民或前往贛南謀生,或嫁入贛南。當知青運動發生時,閩粵贛邊區的知青亦被卷入上述遷徙趨勢之中,如福建武平的廈門知青有時會前往贛州會昌串連,福建永定的廈門知青則會串連到隔壁的廣東梅州,而他們所串聯的路線與傳統的商路幾乎一致。
同時,人口流動促進了邊區各地的經濟往來。如廣東地區的手工業者常到福建知青聚集地生產衛生香,制作桌椅,而靠近粵贛的福建知青也會參與邊區經濟生活中。由此可見,雖然50年代中期以來的統購統銷已然成為國家政策,但是閩粵贛邊區的商業貿易在一定程度上依然繼續著過去的商業傳統,其中邊區內的墟市無疑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邊區墟市的分布,正如施堅雅所言:“行政區劃的邊界很少與集市和貿易體系的邊界相重合。”[注]〔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327頁。比如,在福建武平的大禾地區,每逢三、八墟期,臨近的江西永隆等地的村民都會前來赴墟。當然,除了邊區的知青運動值得關注外,少數民族聚集地的知青運動亦應得到重視,比如上海、成都、北京等地的知青來到云南少數民族地區,還有不少福建知青在閩東的畬族鄉村插隊。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極為顯著,加之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方式、政策傾向與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故而考察此類地區的知青運動是很有意義的。毋庸諱言,1949年以后,國家權力及其政治影響對于任何地域都是決定性的,對知青運動而言亦是如此。但筆者要強調的是,跨地域視角的知青史研究有利于發現行政區劃之外常為人所忽視的歷史存在,包括人際往來、人口交流和商業聯系等。
總而言之,對邊區地帶和少數民族聚集地的跨地域研究為地域性知青史研究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之所以需要引入跨地域研究的方法,主要基于如下兩個考慮:其一,跨地域知青史研究便于在各地區之間展開對比分析,比如閩粵贛邊區三地雖均為客家文化區,但知青群體來源上的差異導致三地知青在婚姻家庭、生產生活、文化交融與沖突,乃至后知青時代的書寫等方面都有著不一樣的表現,通過對比分析,或可梳理出是哪些因素導致了這些差異性;其二,跨地域知青史研究跳出傳統地域界線的框架,有利于注意到以往較少關注的邊區地帶和少數民族聚集地,還可以通過經濟貿易、人口遷徙等問題重新審視革命與鄉村、傳統與變遷等經典話題,并分析知青群體是如何參與其中的。
通過上述討論,筆者認為,地域性知青史研究若要有所突破,如下三點或許值得思考:
其一,應該從“走入知青”到“走出知青”,即以知青運動為研究對象,收集多重史料,在爬梳清楚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將其放置于諸如地域文化、社會移民、文化沖突等更為宏大的議題中去討論,進而與農民工在城市遭遇的文化沖突,乃至華人移民群體在其他國家遭遇的文化沖突進行學理上的對話,而非“就知青史談知青史”。其二,應該適當借鑒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比如,關于知青運動中文化沖突和交融的材料是很難見于檔案文件或報刊媒體的,正如曹錦清、張樂天在研究浙北鄉村時所言:“文化既有其有形的因素,更多的卻是無形的東西”,“純依靠表格、問卷,并不能統計出無形但十分重要的文化因素;走馬觀花式的大面積走訪雖能得到一些道聽途說的表面浮淺的材料,我們卻無法從中得到科學的結論。故而我們傾向于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注]曹錦清等:《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頁。。其三,應該在問題意識的導向下選擇研究案例。地域性知青史研究在本質上屬于個案研究,案例的選擇應該在明確的問題意識引領下進行,即要搞清楚想解決什么問題,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要做到何種程度的突破,等等。反觀近些年來的地域性知青史研究,雖然開創性地把一些從未探討過的省、市、縣作為研究案例,但因為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研究成果還是無法避免空泛、粗淺且趨于同質化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