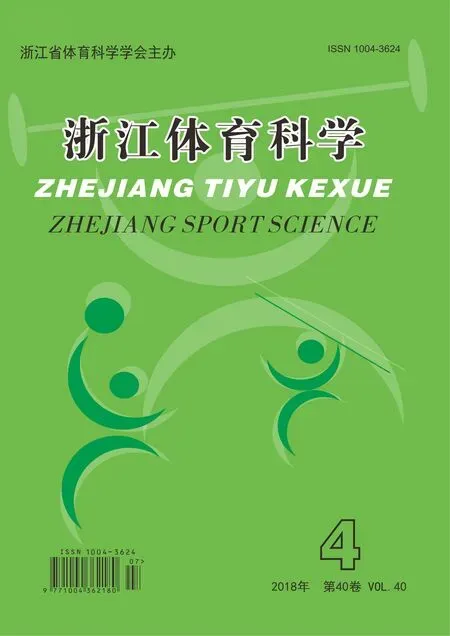清末民初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內(nèi)在訴求和當(dāng)代的啟示
徐 曼,林小美
(1.浙江大學(xué) 公共體育與藝術(shù)部,浙江 杭州 310058;2.浙江大學(xué) 教育學(xué)院體育學(xué)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清末民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社會劇烈變動、精神危機(jī)凸現(xiàn)而各種思想學(xué)說又百花齊放的時代。在這樣一個充滿憂患與動蕩不安的時代,武術(shù)作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個重要手段而逐步興起,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進(jìn)行了適時地轉(zhuǎn)型,不僅影響了中國傳統(tǒng)武術(shù)的發(fā)展,也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武術(shù)產(chǎn)生的基礎(chǔ),完善了中國武術(shù)的教育體制,繼而為中國武術(shù)的持續(xù)發(fā)展注入了新的動力。而當(dāng)代中國是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又一次深刻裂變的重要階段,雖然其內(nèi)涵頗難與清末民初時期同日而語,但同樣處于急劇變革的社會轉(zhuǎn)型期。此時,適時地重新審視清末民初的武術(shù),攫取清末民初武術(shù)在民族沉浮中發(fā)揮的作用及價值,以期為變革期的中國武術(shù)的轉(zhuǎn)型和發(fā)展注入新鮮的血液與活力。
1 從“三時段理論”解析清末民初武術(shù)的轉(zhuǎn)型
“三時段理論”是法國著名歷史學(xué)家費(fèi)爾南·布羅代爾所創(chuàng)立的史學(xué)理論與方法,它包含了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史學(xué)理論。運(yùn)用三時段理論審視清末民初武術(shù)的轉(zhuǎn)型將有助于對武術(shù)的全面把握、清晰認(rèn)識,以及客觀公正的評。按照布羅代爾的“三時段說”[1]的分析,中國武術(shù)從古至今的歷史發(fā)展,是一個“長時段”的貫通,在長時段中又有很多重要的歷史環(huán)節(jié)而構(gòu)成了中時段。如果將中國武術(shù)發(fā)展的歷程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清末民初的武術(shù)在新型傳統(tǒng)的形成過程中,恰恰處于轉(zhuǎn)型和構(gòu)型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其可謂是中國武術(shù)發(fā)展歷史長河中的一個“中時段”的主要階段,在此階段中,又存在著先后四個事件的“短時段”[2]。即武舉制的廢除;1909年霍元甲創(chuàng)建上海精武體育會;1914年馬良創(chuàng)辦武術(shù)傳習(xí)所,推廣“中華新武術(shù)”;1927年中央國術(shù)館的建立。這幾個具有歷史標(biāo)志性事件,不僅是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一種外在標(biāo)志,同時也反映出了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內(nèi)在訴求。將武術(shù)放置于長時段來看,清末民初武術(shù)的轉(zhuǎn)型既是西學(xué)沖擊與之結(jié)合的結(jié)果,也是中國武術(shù)發(fā)展的自省過程。
1.1武術(shù)中國歷史“長時段”的貫通
武術(shù)起源于人類的生存自衛(wèi)斗爭中,發(fā)展于中國古代的戰(zhàn)爭中,是古代戰(zhàn)爭的重要軍事手段,是國家暴力機(jī)關(guān)無上權(quán)力的代表。隨著火槍火炮逐漸登上歷史的舞臺,作為冷兵器時代配套的武術(shù)也與戰(zhàn)爭逐漸分野。20世紀(jì)初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使得當(dāng)時社會政治局面錯綜復(fù)雜,為振奮民族精神,弘揚(yáng)民族文化,武術(shù)以“國術(shù)”的角色進(jìn)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當(dāng)今,伴隨著高科技現(xiàn)代化信息時代的到來,武術(shù)以其健身、防身、修身、養(yǎng)身的特點(diǎn)不可替代地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代表在世界范圍內(nèi)得以傳播。縱觀武術(shù)在中國歷史長時段中的發(fā)展,我們不難看出,武術(shù)從起源到各歷史時期的演變和發(fā)展,它總是與當(dāng)時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息息相關(guān),由此可見,武術(shù)的發(fā)展始終貫通于中國歷史的“長時段”之中。
1.2中國武術(shù)“中時段”時期的整體轉(zhuǎn)型
清末民初,在中華民族即將面臨亡國、亡種、亡族、亡文化的時候,武術(shù)作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被重新推上了歷史的舞臺,武術(shù)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jī)遇,使武術(shù)從一種殺戮的手段慢慢淡化轉(zhuǎn)向成為提升內(nèi)在修為的途徑。
清末民初是中國武術(shù)發(fā)展“中時段”時期的特殊階段,由于社會環(huán)境的大變革迫使清末民初的武術(shù)進(jìn)入全面轉(zhuǎn)型時期。這種轉(zhuǎn)型不僅僅表現(xiàn)在技術(shù)上的改進(jìn)、觀念的轉(zhuǎn)換,更體現(xiàn)在武術(shù)與文化思潮的緊密結(jié)合,武術(shù)與民族精神上的高度統(tǒng)一。在名人志士的倡導(dǎo)下,在民族崛起和振興思想的指引下,武術(shù)的內(nèi)涵不斷地豐富,作為保家衛(wèi)國的手段其政治功能逐漸凸顯,最終被國人稱之為國術(shù)。其次,這一時期武術(shù)以一種嶄新的身份進(jìn)入了近代的教育系統(tǒng),并以此奠定了日后的武術(shù)教育制度。另外,這一時期武術(shù)由于西方科學(xué)的介入,使武術(shù)在西方科學(xué)研究的解釋下,得到了一種全新的嘗試和詮釋。第四,武術(shù)社團(tuán)的建立,使武術(shù)在民間得以衍生的同時,也使武術(shù)的整體運(yùn)行系統(tǒng)產(chǎn)生了巨大變化,繼而為今后武術(shù)發(fā)展的方向、框架與理論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chǔ)。
在社會背景下催生所形成的武術(shù)多元化功能,不僅是清末民初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產(chǎn)物,也是武術(shù)發(fā)展跨入新時代的里程碑。
1.3清末民初中國武術(shù)“短時段”的剖析
短時段主要指歷史上的突發(fā)事件,例如政治革命、戰(zhàn)爭、自然災(zāi)難等等內(nèi)容,相當(dāng)于傳統(tǒng)的政治編年史[3]。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及社會變革,使武術(shù)經(jīng)歷了一段從蒙醒到覺醒、再到醒悟的過程。
蒙醒期,1901年武舉制的廢除標(biāo)志著冷兵器的戰(zhàn)爭走向了黃昏,武術(shù)總體上退離了戰(zhàn)場,一直以軍事為主要功能的武術(shù)在時代的變化中逐漸磨滅了其與生俱來的暴戾之氣。是生是滅的抉擇,不僅是當(dāng)時武術(shù)所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同時也迫使武術(shù)為生存而發(fā)展,從而推進(jìn)中華武術(shù)進(jìn)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
覺醒期,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國民族精神的缺失,使具有愛國主義傳統(tǒng)的中國人民對武術(shù)有了重新的認(rèn)識。在新舊文化、中西文化之間沖撞、變革、交流、吸收、融合中,1909年上海精武體育會的創(chuàng)建以及1914年武術(shù)傳習(xí)所的創(chuàng)辦,為武術(shù)的改良創(chuàng)造了條件,為武術(shù)的傳承拓寬了路徑,促使武術(shù)從形式到內(nèi)容,從理論到實(shí)踐,以及武術(shù)的功能和社會地位,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醒悟期,如果說清末民初,武術(shù)與西方近代體育之間,更多的表現(xiàn)為一種抵制、一種抗?fàn)幍脑挘敲醋?927年中央國術(shù)館的建立開始,武術(shù)在傳承方式、競賽形式等方面上,開始反省自身的不足,并借助西方體育發(fā)展模式對武術(shù)的練習(xí)形式、練習(xí)手段以及競賽要求等方面進(jìn)行了科學(xué)的規(guī)范。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武術(shù)進(jìn)行了自我的改造,促進(jìn)了武術(shù)的近代化發(fā)展進(jìn)程。
清末民初中國武術(shù)的若干個“短時段”,不僅使武術(shù)文化體系逐歩趨于成熟,同時還使武術(shù)滲透于社會的各個角落和各個層面,進(jìn)而推動著武術(shù)的傳承方式、功能、價值等向多樣化方向邁進(jìn)。
2 清末民初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內(nèi)在訴求
清末民初武術(shù)的轉(zhuǎn)型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當(dāng)時西方體育及西方文化大量侵蝕的社會背景影響,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武術(shù)自身為尋繹發(fā)展、順應(yīng)適時而進(jìn)行的轉(zhuǎn)型,繼而使清末民初的武術(shù)更具有深度、廣延和包容性。
2.1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功能訴求
起源于軍事的武術(shù)由于冷兵器時代的結(jié)束,武術(shù)的軍事功能逐漸退化。然而,隨著民族主義與軍國民主義的迅速崛起,國人對具有本民族特征的軍事化訓(xùn)練內(nèi)容和手段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需求,武術(shù)作為舊時代軍事訓(xùn)練的遺存,無疑是國人進(jìn)行軍事化訓(xùn)練的最佳方式。為適應(yīng)民族特征軍事訓(xùn)練的要求,以德式兵操為參照的中華新武術(shù)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yīng)時而生,它是中國武術(shù)“兵操化”改良的產(chǎn)物。由此在清末民初武術(shù)的軍事功能再次顯現(xiàn)。
清末民初時期,在一些社會名流和教育家的組織下,以推廣和研究武術(shù)為宗旨的武術(shù)社團(tuán)應(yīng)運(yùn)而生,以育人為目的的學(xué)校武術(shù)得以回歸。隨著武術(shù)社團(tuán)的興起,以及現(xiàn)代武術(shù)競賽的出現(xiàn)等不僅使封閉保守的武術(shù)傳承方式被沖破,也使武術(shù)的功能從軍事為主逐步向健身、教育、娛樂乃至審美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的多元化方向發(fā)展。學(xué)校武術(shù)的回歸,使武術(shù)的傳承形式由家族式、師徒式,改為一對多的老師和學(xué)生的公開集體授課形式,將原來口傳身授、徒承師授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教育方式改變?yōu)檎n堂式的團(tuán)體教學(xué)的傳習(xí)方式,進(jìn)而使一些原來散存在民間靠口傳身授的武技,被整理成規(guī)范的圖解教材,繼而大大推動了武術(shù)理論體系的豐富和發(fā)展。武術(shù)現(xiàn)代理論體系的建立、武術(shù)功能多元化的發(fā)展以及武術(shù)教學(xué)形式的統(tǒng)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摒棄了武術(shù)固有的門派陋習(xí)和狹隘的地域觀念,促進(jìn)了武術(shù)不同門派之間、武術(shù)與西方體育項目之間、男女之間的和諧發(fā)展。
2.2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價值訴求
在歷史動蕩的清末民初,因各種思潮的不斷波及而使武術(shù)被賦予各種使命與價值,此時的武術(shù)發(fā)生了歷史性的升華,其社會地位得到高度的提升,甚至被國人美譽(yù)為國術(shù)。
在西方體育文化的影響下,武術(shù)從價值觀到運(yùn)動鍛煉思想, 從教習(xí)到表演和競賽方式, 都向著科學(xué)化與規(guī)范化的方向演進(jìn)。武術(shù)外延的轉(zhuǎn)變,是武術(shù)的文化價值、教育價值以及體育價值逐漸形成的一種過程。清末民初武術(shù)的內(nèi)外轉(zhuǎn)型,使武術(shù)逐漸勾勒出了武術(shù)與中國文化、武術(shù)與現(xiàn)代教育等多方面水乳交融的新面貌。
2.3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精神訴求
清末民初伴隨西洋體育涌入所產(chǎn)生的輻射和誘導(dǎo)效應(yīng),使得武術(shù)獲得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jī)遇。在以體育訓(xùn)練為手段,以民族精神為教育理念,以增強(qiáng)體質(zhì)、提升國家力量為目標(biāo)的武術(shù)救國論下,武術(shù)逐漸成為“強(qiáng)種與復(fù)興民族的工具”。在強(qiáng)種強(qiáng)國理念的倡導(dǎo)下,尚武成為當(dāng)時社會的流行。
在求得生存、汲取養(yǎng)分和重獲新生的土洋體育之爭中,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孕育下,武術(shù)進(jìn)行了演變和發(fā)展。清末民初武術(shù)自身的不斷演進(jìn)使武術(shù)與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得到了進(jìn)一步的融合,使這一時期的武術(shù)成為民族英雄的代名詞。
3 “變則通”清末民初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當(dāng)代啟示
中華民族從古至今,都是一個極富創(chuàng)造力和變革精神的偉大民族,這也是中華民族能夠不斷取得歷史進(jìn)步最根本、最深刻的思想精神方面的原因。然而任何事物的變革就如《易經(jīng)》所講,事物的變化都具有規(guī)律、道理,謂之變化之道,改革之道,變通之道,繼而揭示出“通則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及“變則通、通則久”等哲學(xué)思想。“通變”,是為會通古今而變之,側(cè)重點(diǎn)在“變”,而此“變”又非一味趨新求異,而是有因有革之變。因此,把繼承和創(chuàng)新結(jié)合起來,是“通變”的精義所在[4]。
當(dāng)代社會新舊鼎革的巨變,武術(shù)也霍然進(jìn)入了一個由近代武術(shù)向現(xiàn)代武術(shù)的歷史轉(zhuǎn)型。“體操化”、“非武術(shù)”是對現(xiàn)代武術(shù)的評價,這種錯誤的評價只看到了現(xiàn)代武術(shù)與傳統(tǒng)武術(shù)不同風(fēng)格的一面,沒有看到其內(nèi)在的精神脈動一面。現(xiàn)代武術(shù)不是“非武術(shù)”、“反武術(shù)”,而是在變通思想指導(dǎo)下的“變”、“通”,是一種多元化中的傳統(tǒng)武術(shù)型態(tài)的轉(zhuǎn)型創(chuàng)化,這種轉(zhuǎn)型性創(chuàng)化使中國武術(shù)走出國門,立于世界。同時,也發(fā)現(xiàn)在這種轉(zhuǎn)型性創(chuàng)化的過程中,內(nèi)在的震動,以及西方體育文化的侵入,商品化、普及化和快節(jié)奏的西方體育特質(zhì)使武術(shù)的民族文化內(nèi)涵以及技擊等價值、功能被逐漸淡化。在武術(shù)所蘊(yùn)含的中國文化、民族精神被邊緣化的當(dāng)下,武術(shù)需要自身的拯救。窮極而變、變而暢通、通暢而久之,現(xiàn)代武術(shù)的發(fā)展可以借鑒和攝取清末民初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可貴經(jīng)驗,以“變則通”哲學(xué)思想為指導(dǎo),在保持武術(shù)本質(zhì)不變的基礎(chǔ)上,明確現(xiàn)代武術(shù)發(fā)展的多元化路徑和核心價值,運(yùn)用現(xiàn)代化的傳播手段,突出傳播武術(shù)文化的深層底蘊(yùn),尋求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的傳承方式和健身標(biāo)準(zhǔn)化體系,爭取武術(shù)在錯綜復(fù)雜的社會變革中得到綿延。
3.1變革武術(shù)的傳承方式
1986年武術(shù)在高等學(xué)校專業(yè)目錄中正式立項,1992年中國大學(xué)生體育協(xié)會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分會的正式成立,以及武術(shù)碩士點(diǎn)、博士點(diǎn)的相繼設(shè)立,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武術(shù)人才培養(yǎng)的縱向發(fā)展。其次,隨著省市、全國、洲際、世界等各級別武術(shù)錦標(biāo)賽的不斷完善,競技武術(shù)達(dá)到空前絕后的發(fā)展。然而在武術(shù)不斷向著高、尖方向發(fā)展的同時,也發(fā)現(xiàn)武術(shù)習(xí)練者數(shù)量在逐年地減少、武術(shù)拳種在不斷地萎縮。另外,由于理論與實(shí)踐的脫節(jié),以及以競技武術(shù)人才培養(yǎng)為啟蒙武術(shù)教育的理念,造成了武術(shù)人才培養(yǎng)向著“理論教育厚實(shí)實(shí)踐教育薄弱型、實(shí)踐教育尖端理論教育平庸型”兩極分化的態(tài)勢發(fā)展。轉(zhuǎn)變武術(shù)人才培養(yǎng)模式,是避免武術(shù)人才的平行線發(fā)展趨勢。
首先,選擇廣闊厚實(shí)的武術(shù)啟蒙教育對象。武術(shù)啟蒙教育不僅僅包括競技武術(shù)訓(xùn)練的三級網(wǎng)點(diǎn)的運(yùn)動員,更應(yīng)該落到學(xué)校武術(shù)和群眾性武術(shù)社團(tuán)中,他們是武術(shù)啟蒙教育的主陣地。其次,樹立高端的武術(shù)啟蒙教育目的。武術(shù)不僅僅是身體鍛煉、休閑娛樂、社會交往的一種手段,更是傳承中國文化、民族精神的主要方式。最后,提升武術(shù)人才培養(yǎng)的檔次。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每個時代的精神孕育著每個時代所需的武術(shù)人才,每個時代的武術(shù)培養(yǎng)模式將誕生不同的武術(shù)家。在如今的時代背景下,將武術(shù)作為一種全民健身的運(yùn)動,一種民族的文化進(jìn)行教育,才能培養(yǎng)出全面的全新的武術(shù)傳承人。
3.2形成武術(shù)的健身標(biāo)準(zhǔn)化體系
隨著競技武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國家武術(shù)管理中心一直倡導(dǎo)武術(shù)運(yùn)動的標(biāo)準(zhǔn)化:競賽規(guī)則標(biāo)準(zhǔn)化,競賽機(jī)制標(biāo)準(zhǔn)化,教學(xué)標(biāo)準(zhǔn)化等等。武術(shù)要走向世界,讓世界認(rèn)可,僅僅從競賽標(biāo)準(zhǔn)化出發(fā)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競賽只是現(xiàn)代武術(shù)發(fā)展的一方面,武術(shù)的健身價值是武術(shù)被現(xiàn)代人群所認(rèn)可所接受的內(nèi)在因素。
在武術(shù)的良好健身價值逐漸成為人類增進(jìn)健康的手段時,武術(shù)健身的量及強(qiáng)度就不能依據(jù)自己的興趣或愛好而定。武術(shù)健身將如同藥劑丸,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劑量,何種量和強(qiáng)度會損害健康,何種量和強(qiáng)度是有利于健康,應(yīng)該有一定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目前上海體育學(xué)院已經(jīng)在對不同體質(zhì)人群太極拳鍛煉進(jìn)行相應(yīng)的運(yùn)動處方研究,這是一個極好的開端。隨著武術(shù)健身處方研究的深入,促使武術(shù)健身向標(biāo)準(zhǔn)化邁進(jìn),標(biāo)準(zhǔn)化的武術(shù)鍛煉時間、強(qiáng)度,是廣泛性普及性推廣武術(shù)的前提。同時武術(shù)健身標(biāo)準(zhǔn)化的形成是符合西方人體育運(yùn)動鍛煉的要求,同時它也將促進(jìn)武術(shù)健身價值的海外認(rèn)同度。
3.3完善武術(shù)的制己修身功能
“內(nèi)可以治身,外可以應(yīng)變,君子比德也。”這是司馬遷的《史記》中對于習(xí)武者信廉仁勇的“德”的要求。雖然武術(shù)自產(chǎn)生以來一直以技擊功能作為其主要功能,制人制敵是武術(shù)給人的第一印象。然而,通過長期的武術(shù)練習(xí),習(xí)武者可以體悟到技擊的最高含義在于通過技術(shù)的磨練和對自身極限的充分發(fā)掘來達(dá)到制己修身的良好境界。因此在武術(shù)傳承過程中,除了講究格斗制勝、強(qiáng)身健體之外,應(yīng)更多地融入自身潛力的發(fā)掘、性格的培養(yǎng)等精神內(nèi)涵的塑造,將武術(shù)原先以控制他人為主的技術(shù)衍變?yōu)榭刂谱约簽橹鞯募夹g(shù),讓武術(shù)成為修身養(yǎng)性的手段,這是武術(shù)不同于其他民族武技的文化個性之一,也是武術(shù)在現(xiàn)代社會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4加強(qiáng)武術(shù)的傳播功能
當(dāng)我們重新探究清末民初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原因和影響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所體現(xiàn)的不是文化交流上的先進(jìn)或是落后,而是一個民族從覺醒走向自強(qiáng)的狀態(tài)。
全球化日益加劇的今天,是聯(lián)系更為緊密、交流更加頻繁的時代,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相互影響,每天都在發(fā)生。一個民族若想要在全球化中不被淹沒,就必須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須有自己的文化代表。武術(shù)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豐富的武術(shù)動作是中華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圍內(nèi)傳播的肢體語言,其每一個動作的內(nèi)涵都可以成為解析中華民族文化精髓的途徑。在中西文化不斷碰撞及交融的今天,武術(shù)不應(yīng)單純地形而下的肢體動作的海外傳播,不應(yīng)過多地停留在為申奧、為迎合西方體育而進(jìn)行的改變階段。當(dāng)今武術(shù)的發(fā)展應(yīng)著眼于在吸收民族文化中優(yōu)秀成分的基礎(chǔ)上,提高習(xí)武者自身的素養(yǎng),促使當(dāng)代武術(shù)成為既具有時代性又保留民族性的中華民族文化傳播媒介。
21世紀(jì)的武術(shù)發(fā)展應(yīng)以幫助中華民族文化走出低迷、促進(jìn)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為主題,通過提升武術(shù)傳播者的內(nèi)涵,強(qiáng)化武術(shù)的傳播功能,使武術(shù)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向世界輸出的載體。
4 結(jié) 論
4.1 重溫清末民初武術(shù)先驅(qū)者經(jīng)過力求統(tǒng)新舊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的可貴探索之后,與西方體育文化碰撞后的清末民初武術(shù),不僅成為清末民初學(xué)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傳承和發(fā)揚(yáng)的重要途徑。
4.2 地球村、全球一體化思想的日趨深入,為武術(shù)的大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機(jī)會。當(dāng)代武術(shù)的發(fā)展應(yīng)有效地攝取清末民初武術(shù)轉(zhuǎn)型的有益經(jīng)驗,抓住發(fā)展的機(jī)遇,更新觀念,改革創(chuàng)新,與時俱進(jìn),在保持武術(shù)特質(zhì)和固有形式的基礎(chǔ)上,通過變革武術(shù)的傳承方式,以及武術(shù)的健身標(biāo)準(zhǔn)化體系的形成,使當(dāng)代武術(shù)的發(fā)展成為符合時代發(fā)展需要的應(yīng)有之義。
4.3 在人類文化差異減小而日益單一僵化的今天,探尋武術(shù)文化體系中的獨(dú)特風(fēng)格和特殊稟賦,深掘武術(shù)制己修身的獨(dú)特內(nèi)蘊(yùn),強(qiáng)化武術(shù)的傳播功能,使武術(shù)成為中西思想較量和觀念博弈后的一枝獨(dú)秀。
[1] 馬良.中華新武術(shù)·發(fā)起總說[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17.
[2] 國家體委武術(shù)研究院.中國武術(shù)史[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7.
[3] 姜義華.史學(xué)導(dǎo)論[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3.
[4] 栗勝夫,等.中國武術(shù)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3.
[5] 溫力.中國武術(shù)概論[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5.
[6] 宋志明,吳潛清.中華民族精神論綱[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6.
[7] 麻天祥.中國近代學(xué)術(shù)史[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7.
[8] 吳懷棋.中國史學(xué)思想史[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7.
[9] 陳晴.清末民初新式體育的傳入與嬗變[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
[10] 羅時銘.中國近代體育變遷的文化解讀[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xué)出版社,2007.
[11] 郭玉成.中國武術(shù)傳播論[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8.
[12] 林小美,等.清末民初中國武術(shù)文化發(fā)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2.
[13] 林小美,等.民國時期武術(shù)運(yùn)動文選[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2.
[14] 張正明.年鑒學(xué)派史學(xué)理論的哲學(xué)意蘊(yùn)[D].哈爾濱:黑龍江大學(xué),2010.
[15] 周保分.現(xiàn)代武術(shù)發(fā)展研究[D].濟(jì)南:山東師范大學(xué),2009.
[16] 林小美,厲月姣.清末民初中國武術(shù)社團(tuán)文化研究[J].體育科學(xué),2010,46(2):134-139.
[17] 李印東,李軍.從“土洋體育之爭”的歷史文化背景談西方體育對武術(shù)的影響[J].北京體育大學(xué)學(xué)報,2010,33(4):6-10.
[18] 陳其泰.關(guān)于“民族精神”內(nèi)涵的理論思考[J].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10(11):82-85.
[19] 楊建營,邱丕相.武術(shù)精神的歷史演變及21世紀(jì)發(fā)展的新趨勢[J].體育學(xué)刊,2008,15(10):92-95.
[20] 郭守敬,郭志禹.以武術(shù)弘揚(yáng)民族精神的歷史回顧與教育策略[J].體育文化導(dǎo)刊,2006(7):64-66.
[21] 邱丕相.全球文化背景下民族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的思考[J].體育科學(xué),2006,26(8):63-65.
[22] 倪依克,邱丕相.社會學(xué)視域下傳承武術(shù)文化的教育價值[J].體育科學(xué),2007,27(11):15-20.
[23] 謝建平.全球化背景下武術(shù)發(fā)展的文化思考[J].上海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04,28(1):33-36.
[24] 奮翩生(蔡鍔).軍國民篇(1902)[C].新民叢報癸卯匯編,1903: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