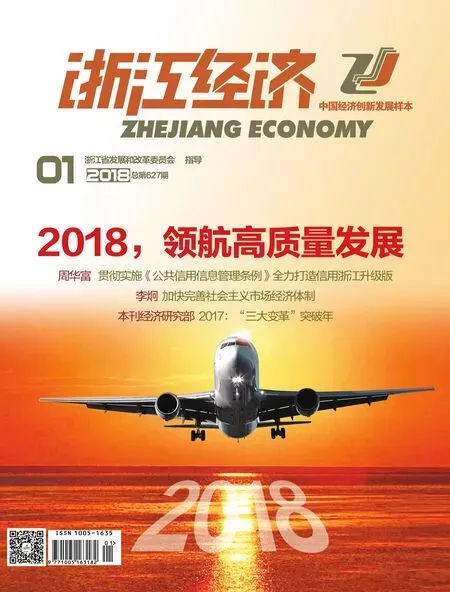重點生態功能區聚積綠色財富新路徑
□羅成書 周世鋒 倪毅 柯敏
重點生態功能區是指生態敏感性較強,生態系統十分重要,關系到區域生態安全,需要在國土空間開發中限制進行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城市化開發,以保持并提高生態產品供給能力的區域。省第十四次黨代會提出要實施大花園行動綱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著力探索重點生態功能區聚積綠色財富新思路、新路徑和新政策,對于全省重點生態功能區內跨越發展、建設好大花園、示范帶動全國重點生態功能區科學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成效與問題
基本內涵。從綠色財富的內涵構成上,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生態財富,也就是“綠水青山”,包括優質健康的森林、湖庫、土壤等生態系統及棲息在其上的生物群落。二是經濟財富,也就是“金山銀山”,包括建構的綠色產業、生產的綠色產品等。綠色財富的聚積,既是綠水青山保護與提升的過程,也是金山銀山創造與轉化的過程。“綠色財富”理念突破了以人本身發展為根本目的的局限,更加著眼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經濟與生態協調共贏,標志著人類從以掠奪資源破壞環境積累財富轉變為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創造財富。
主要特征。從綠色財富的創造過程分析,其主要特征可概括為“四綠”,即依托綠色資源,采用綠色技術,創造綠色財富,促成綠色福利。一是創造財富的資源是“綠色”的,即利用當地自然資源,或仰賴于當地優質的生態環境,提供生態產品,從而創造財富;二是創造財富的技術是“綠色”的,即采用的工藝是無污染少污染的,采用的環保處置技術和環保裝備是先進的,屬于“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對外部生態環境無損害和污染;三是財富本身是“綠色”的,即財富的表現形式產品本身是生態型、環保型、有益健康的,無公害和無污染是其基本特征,人們可以安全享用和支配,這是“綠色財富”的本質屬性,它推動了綠色生態產業的蓬勃興起;四是在財富運用方式上是“綠色”的,在保護生態與環境的前提下,不僅財富的積累不以掠奪自然資源為代價,并且在運用和享受財富的方式上具有公平、共享、協調的社會福利特性。
三大成效。一是生態財富聚積效應凸顯,構筑了沿海地區重要生態屏障。所謂生態財富,指的是綠色財富中難以經濟化的生態資源。主要包括:“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體協同保護,水、氣、土等生態產品質量處于沿海發達地區的領先翹首之位;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建設持續有力,成為生態財富富集區域;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推進“五水共治”,維護生態財富保護的血脈。二是經濟財富創造卓有成效,生態經濟發展成績斐然。所謂經濟財富,指的是綠色財富中可以經濟化的生態要素。主要包括:借區位之利,大力發展面向上海、杭州、寧波等長三角中心城市的鄉村旅游;借電商之媒,助力綠色有機農產品、資源精深加工品、文化創意產品等遠銷全國;借文化之魂,推動民俗、民風、民間藝術的復興與經濟價值的再現;借金融之新,開展林權抵押、農業保險、碳匯交易等綠色金融以協同生態財富的保護與經濟財富的創造。三是生態政策疊加效果初顯,積累了一批先行先試的重要經驗。生態發展的政策效果明顯。主要包括:生態公益林政策、國家公園改革試點、國家主體功能區建設試點、“兩山”專項財政扶持資金政策、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山區經濟政策、山海協作工程、生態獎懲制度、差異化考核制度、新安江跨流域補償機制等等。
三大問題。一是財富創造綠度不足。全省重點生態功能區仍有不少污染企業或污染環節,財富創造的過程和結果仍不夠綠。礦山開采對自然山體的破壞,帶來粉塵污染和水土流失;有的地方小水電產值占其工業產值的比重還較高,對河流生態影響較大。單晶硅和有機硅產業潛在的水污染,鈣產業帶來的山體破壞及粉塵污染,木玩行業造成的粉塵污染和油漆污染,冶煉行業存在的高能耗和粉塵污染。農業種植帶來的面源污染依舊較為嚴重,茶樹、果樹種植造成的水土流失也不小。二是政策供給精準不夠。浙江重點生態功能區的政策仍有不少提升空間,綠色財富創造的政策供給不夠精準。首先,從空間上,重點生態功能區的政策目前僅在開化、淳安、慶元、景寧、文成、泰順六個地方試點,試點到期后,急需有新的政策體系出臺。其次,從政策體系上,有的地方一方面不考核GDP和工業增加值,但另一方面又要考核固定資產投資,政策的矛盾造成地方無所適從。第三,從政策內容上,急需進一步梳理建立長期有效的機制,探索綠色金融、產業準入負面清單等有效實施的新抓手。三是績效考核差異不大。目前,差異化的績效考核覆蓋面還不夠廣。從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上看,只有開化、淳安等地實現差異化的績效考核。從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域內部空間上看,也只有少部分縣市對鄉鎮施行差異化的績效考核政策。特別重要的是,對績效考核結果的應用普遍欠缺,領導干部的提拔任用與績效考核的聯系度并不高。
思路和路徑
分析國內外類似地區聚積綠色財富的經驗可以發現,產業轉型以形成綠色產業結構、科技先行以實現綠色技術提升、政策支撐以引導發展方向、嚴刑峻法以確立法律權威是比較重要的幾點。
基于前文對重點生態功能區聚積綠色財富的基本認識,全省重點生態功能區綠色財富的聚積,不應該是生態財富單邊增長而不顧經濟財富,更不應該是經濟財富單邊擴張而犧牲生態財富。合理的聚積模式,是要達成生態財富和經濟財富在總量上增長、質量上提升、結構上更優化、空間上更集聚。
因此,聚積綠色財富的基本思路應為:深入踐行“兩山”重要思想,發揮浙江重點生態功能區區位條件、資源資產、創新精神等復合優勢,按照頂層設計、分類施策、分步推進、協同破障的思路,著力拉長“長板”、補齊“短板”,著力提升生態產品的供給能力和生態經濟的發展能力,著力建立正向激勵與反向約束同步發力的政策體系,推動浙江重點生態功能區加快走上聚積綠色財富科學新路。
為此,可從產業促綠、空間導綠、政策扶綠、合作聚綠等方面,考慮確立浙江重點生態功能區聚積綠色財富的差異化戰略路徑。
一是產業促綠,探索經濟財富新手段。面對空間新格局、產業新革命,針對部分縣市依然存在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在全省產業準入負面清單促產業轉型的基礎上,繼續探索實施一批具有“四綠”特征的產業培引新計劃,以產業的綠色化帶動綠色財富聚積,積極推動主客共享等新綠色經濟、綠色業態、綠色模式的涌現。
二是空間導綠,探索財富空間新格局。發揮財富創造的空間集聚規模優勢,全力推動小縣大城向小縣優城邁進,推動“山水林田湖”生態格局再梳理,積極引導生產、生態、生活空間合理布局,促進生態空間引領聚積生態財富、生產生活空間聚優經濟財富。
三是政策護綠,探索差異管控新制度。對于生態敏感性和重要性較為重要的區域,且短期內尚未形成有效綠色財富聚積的地域,應對地區特色化發展需求,探索加強生態獎懲、轉移支付、績效評價、空間管制、區域調控等新制度,通過政策扶持,保障該類地區生態財富的聚積和經濟財富的有效探索。
四是合作聚綠,探索各方協同新模式。面對發展新機遇、新挑戰,在全省“山海協作”等內外合力共促重點生態功能區綠色財富聚積的基礎上,繼續探索新的省市聯動、沿海發達地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協同的新模式,通過以外促內、內外聯動、內在為主的策略最終實現內生動力的厚植。
五是建立健全“六大機制”。以“六大機制”為抓手,衍生制定系列精準政策,為重點生態功能區聚積綠色財富保駕護航。分別是: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在11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制定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基礎上,下一步可以在科學合理評價的基礎上對重點生態功能區進行擴容調整,原17個生態經濟地區可以適時調為省級重點生態功能區,與此同時省級生態功能區也應建立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以此確保綠色財富聚積的技術、生產方式和產品的綠色化。綠色資產監測審計制度。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用制度確保生態財富量質齊升。資源要素生態化配置機制。建立用水、用地、環境容量生態化的配置機制,在泰順等地探索實踐的基礎上制定重點生態功能區資源要素生態化配置總體方案,因地制宜打造要素改革升級版,在依畝產效益排序競爭性獲取資源的同時,加強生態環境改善、環境污染排放等指標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引導資源要素向更綠的企業、更綠的生產環節、更綠的先進技術、更綠的產業集聚平臺傾斜。綠色金融創新機制。利用浙江民營資本充裕,金融市場運行效率高效的優勢,在綠色金融上加快探索,制定綠色金融創新行動計劃,引領示范全國。生態獎懲制度。加快開展開化、淳安等國家主體功能區建設試點效果評估,總結經驗與問題,制定更加優化的全省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獎懲辦法。差異化考核機制。省里制定針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統一考核辦法,在取消地區生產總值和工業產值考核的同時,聯動降低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考核,強化對綠色財富總量、質量和結構的考核,強化對社會民生的考核。相應強化對考核結果的應用,同干部個人績效獎金、政治前途掛鉤,確保考核嚴肅性和約束力,引導綠色財富聚積的行政管理者的行為符合重點生態功能區發展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