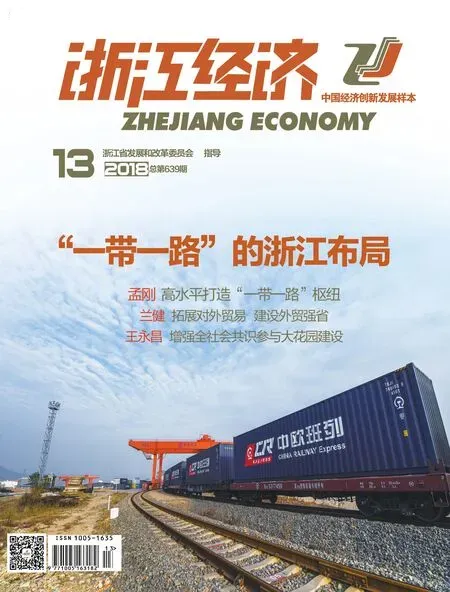“綠水青山”的價值實現
□陳嘯
農歷戊戌新年,離杭返鄉。短短一周假期,不僅有父母家人、同學老友相伴,更在車水馬龍、觥籌交錯間,耳聞目睹了家鄉農村之巨變。大伯家養的生態竹林雞供不應求;姐夫緊盯鄉村生態旅游,借助“互聯網+”做成了全市知名的旅游公眾平臺;初中老同學承包山水林田湖,建起了農業綜合體,節假日游客人山人海……種種現象背后似乎隱約有一個相似之處:在新的社會消費需求和市場機遇下,他們都借助“生態”實現了“價值”。
生態產品兼具環境價值與經濟價值,而當前困擾我們的主要是其經濟價值的轉化,也就是如何把“綠水青山”真正轉化為“金山銀山”。加快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化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綠水青山”的價值實現是保護生態環境的首要前提。從現實國情看,人口龐大且城市化水平低,大量人口分布于農村地區,加快推動共同發展是當前面臨的重大使命與迫切任務。保護是發展的基礎,但發展更是保護的依托。只有在綠水青山中實現價值,才能反過來更好地保護綠水青山,才能使保護“綠水青山”成為一種“全民自覺”。
二是“綠水青山”的價值實現是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長期來,國家各級涉農資金量大面廣,但是投入效果不盡理想。老百姓守著“金山銀山”等飯吃,“綠水青山”的價值沒有充分挖掘,轉化通道沒有有效打通。實現“綠水青山”的價值,將使支持農村從“輸血”走向“造血”,是鄉村振興的重大課題也是主要難題。
三是“綠水青山”的價值實現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根本途徑。加快實現“綠水青山”的價值,不僅有利于增加百姓收入、打贏扶貧攻堅戰、實現全民共同富裕,還有利于更好地貫徹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使區域空間布局、城鄉資源配置、地區功能分工更加清晰明確,全面提升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率。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具備可行性和操作性,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綠水青山”的價值可以被量化。對“綠水青山”價值的量化是轉化為“金山銀山”的基礎,與經濟生產總值GDP相對應的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近年來已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其價值體系主要通過生態系統服務來體現,包括防風固沙、洪水調蓄、氣候應對、凈化水質、生物多樣性乃至健康等方面,這個綜合價值可以通過科學模型量化計算得出,在美國等國家已十分成熟并廣泛運用到政府管理中。二是“綠水青山”價值既可以通過行政化手段達成,也可以通過市場化途徑實現。2012年以來,浙江與安徽省共同開展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是全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實例,也是通過行政手段實現生態價值的范例。從市場手段看,在國外“為生態系統服務付費”的制度設計和案例已十分成熟,生態地區從“生態補償對象”轉為“生態產品賣方市場”,產生了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
要實現生態產品的價值,重點在于三個方面:一是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值的“理論核算+市場核算”。當前,國家部委和中科院等科研院已推動制定GEP核算技術規范,并在貴州、青海兩省以及廣東、云南等省的市縣層面開展了一批試點探索。浙江可探索在部分重點生態功能區開展該項工作,并逐步將其納入生態文明建設考核體系。同時,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應與市場充分結合,要積極引導金融機構、企業參與核算,使理論的價值真正變為社會認可的“真金白銀”。
二是構建“全省縱向+局部橫向”的生態補償體系。從全省縱向看,隨著主體功能區戰略的深入推進、全省生態保護紅線的全面劃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體系的建立,建立健全差異化的財政生態補償政策條件已趨于成熟。差異化的財政補償政策,不僅注重各地劃定的生態保護紅線區保護面積等生態本底,而且與生態保護的動態質量、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執行情況等相掛鉤,可以充分激勵地方積極性。從局部重點區域橫向看,如浙江八大水系完整清晰,可以率先探索基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橫向補償機制。
三是打造“多元化+多主體”的生態產品價值轉化公共平臺。除了生態補償、生態付費外,“綠水青山”價值轉化的另一個關鍵在于打造價值轉化的公共平臺。如麗水、衢州通過打造“麗水山耕”“三衢味”等區域公用品牌,實現農副產品的整體溢價,德清構建高端洋家樂品牌帶動全縣民宿經濟發展,安吉兩山合作社打造農業全產業鏈服務平臺,都是通過公共平臺、公共品牌的構建,實現生態價值轉化受益面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