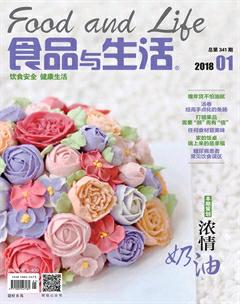兒時的小鋪
2018-02-07 18:03:55張金傲
食品與生活
2018年1期
張金傲
兒時的回憶永遠那樣美好,像窗外白雪那樣純潔,像爐里的火那樣溫暖……每年臘月,下雪的時候也是最懷舊的時候。
上世紀50 年代,家鄉的小街巷里遍布著許多小食雜鋪,有水果床子、菜床子、賣開水的、裁縫鋪、小人書鋪、猶太人的小診所和藥店……只要有人,這些小店就不關門,生活很方便。
小時候總是去一間小鋪給父親打酒。小鋪公私合營前是波蘭人開的,后兌給中國人改名叫“福發源”。鋪面也不大,20 多平方米,一直保持著俄羅斯風格。進門兩邊是厚重的實木柜臺,左邊柜臺賣酒、熟食和煙卷,柜臺中間擺著三個中式酒壇子,分別裝著60 度、50 度和40 多度的糠麩酒,蓋子用紅布包裹起來。一個玻璃柜放在柜臺的一頭,可以看到里面分兩層擺放的各種熟食。柜子后面的食物,是那樣誘人。
以前外國掌柜只賣適合僑民口味的熟食和各種面包,例如灌腸叫“力道斯”,現在又加兩字改叫“秋林力道斯”;茶腸叫“茶伊斯”,油脂腸就是松江腸,叫“意大連斯”,西班牙腸叫“依斯班斯”,現在又統一叫“哈爾濱香腸”,中俄混合叫“老巴克肉棗和老巴克火腿”,現在市場上也有,但香料味太重,絕不是過去的味道。還有“羊干腸”,是一種西式風干肉灌制品,多年不見了,與現在哈爾濱風干香腸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帶醬香,有很純的肉味。“羊干腸”制作成本高、周期長,因而很貴,上世紀50 年代,500 克就賣3 元多。中國掌柜根據哈爾濱人口味,保留了力道斯腸和茶腸,茶腸要的是嫩嫩的肉香味,力道斯腸則帶濃濃的煙熏味。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