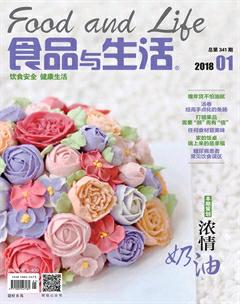本幫菜的風(fēng)格特色(二)
周彤
甜上口 咸收口
外地人看上海菜,往往就像文學(xué)作品中勾勒的 “左手醬油瓶,右手糖罐子”那樣,他們往往會(huì)直觀地表述為:“上海菜就是甜的”,但這種表述和“四川菜就是辣的”一樣膚淺,做菜要是真的這么簡(jiǎn)單,哪里還有什么中華美食文化了?
但是話(huà)說(shuō)回來(lái),本幫菜中的許多菜式,尤其是炒和燒兩大類(lèi)主流菜式中,口味偏甜的確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
那么,本幫菜的這種甜,到底有沒(méi)有一個(gè)所謂的“標(biāo)準(zhǔn)”呢?
這就不得不回過(guò)頭來(lái)看,推敲一下這樣兩個(gè)比較原始的問(wèn)題:一是上海人為什么喜歡咸中偏甜的味感,二是這種味感追求一種什么樣的效果。
江南一帶不產(chǎn)甘蔗,也不產(chǎn)甜菜,由于臨近東海,所以這里原本口味是以咸為主,寧波、紹興一帶至今還有“飯榔頭”這么一說(shuō)(意思是特別咸的菜就特別能下飯)。
江南人喜歡吃甜,始于北宋變?yōu)槟纤文菚?huì)兒,由開(kāi)封那幫跟著趙構(gòu)跑到江南來(lái)的官員們帶來(lái)的食俗。同時(shí)帶過(guò)來(lái)的食俗,還有吃羊肉,羊這種家畜同樣是江南一帶比較少見(jiàn)的,但如今江南一帶羊肉做得好的地方比比皆是。
這是中國(guó)美食文化的歷史決定的。
但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主要是清道光年間之后才成型的,本幫菜偏甜的味覺(jué)藝術(shù)特征要從這個(gè)歷史階段說(shuō)起。
上海開(kāi)埠后不久,中國(guó)就暴發(fā)了太平天國(guó)運(yùn)動(dòng),很快溝通中國(guó)南北運(yùn)輸?shù)膭?dòng)洋涇浜南側(cè)是法租界北側(cè)是英租界(1849 年)脈——京杭大運(yùn)河就淪為了戰(zhàn)區(qū),南北貨運(yùn)不得不從以?xún)?nèi)河為主,改為以海運(yùn)為主。受當(dāng)時(shí)造船水平的制約,海運(yùn)的貨船中,南船不能北上,北船無(wú)法南下,他們都要以上海為中轉(zhuǎn)站進(jìn)行倉(cāng)儲(chǔ)接駁。就這樣,上海開(kāi)始從十六鋪外灘迅速發(fā)展起來(lái)。
當(dāng)時(shí)上海的外來(lái)人口中,寧波幫、南通幫和蘇錫幫是最主要的三個(gè)群落,雖然現(xiàn)在看來(lái)這些地方相距不算太遠(yuǎn),但在道路交通條件還比較落后的晚清時(shí)期,這三個(gè)地方的文化還是有著不少差異的,表現(xiàn)在飲食習(xí)慣上也大不相同。寧波、紹興人偏咸、蘇州無(wú)錫人偏甜,而南通人的口味則比較中庸,就是咸鮮味。
那么問(wèn)題來(lái)了,這些口味不同的人在一起怎么個(gè)吃法?
上海美食史上的記錄是這樣的,到光緒年間,上海已經(jīng)有16 個(gè)幫別的風(fēng)味菜館進(jìn)駐,一般是哪里來(lái)的移民多,他們就會(huì)天然地找他們熟悉的風(fēng)味餐館去就餐,但對(duì)于各家餐館的老板們來(lái)說(shuō),他們想做所有人的生意,這幫小飯攤、小餐館的老板們是最急于要找到一個(gè)“江南味道的最大公約數(shù)”的。
我們以“老正興”(指“同治老正興”)為例來(lái)看一下。“老正興”一開(kāi)始是做無(wú)錫菜的,那么這家館子當(dāng)然會(huì)吸引來(lái)上海的蘇州人和無(wú)錫人,這種老家的味道會(huì)使他們感到親切,但錫幫菜太甜了,甜到連蘇州人都不太吃得消,更別提寧波人和南通人了,那么老板和廚師怎么辦?只能做個(gè)妥協(xié),少放點(diǎn)糖。接下來(lái)他們會(huì)發(fā)現(xiàn),比他們更老的一些餐館比如“老人和”這樣的店子里賣(mài)的上海本地風(fēng)味菜肴能吸引更多的客源,甭管是江蘇的還是浙江的還是本地的,都可以接受。那么“老正興”的口味特征就會(huì)自覺(jué)地向“老人和”的風(fēng)格看齊,也就是更為“中庸”,更為“廣譜”,更為“兼容”,否則生意真的做不大了。
比這個(gè)更有說(shuō)服力的一點(diǎn)在于,中國(guó)人吃飯往往都是一群人一去,既然這些人中哪里人都有,那么餐館的菜式就不能只照顧其中某一部分的人,否則就會(huì)有不習(xí)慣此種風(fēng)味的客人“翻毛腔”(滬語(yǔ),意為“反感”、“生氣”)。
當(dāng)時(shí)的上海餐飲界就是這樣一個(gè)逼著你做“和合”工作的市場(chǎng)。好在解開(kāi)這道題并不需要有多深的學(xué)問(wèn),看看市面上賣(mài)得好的菜是怎么回事,大家就清楚了。答案就是“咸中微甜”。
“咸中微甜”具體說(shuō)來(lái)是這樣的,它要求菜肴的底味是建立在咸鮮味的基礎(chǔ)上,而且還要比較濃郁,這樣才會(huì)使食材本來(lái)的美得到充分體現(xiàn),但在此基礎(chǔ)上,加入適量的糖,會(huì)使咸鮮味更為細(xì)膩和雅致,這是江南一帶的人普遍都愿意接受的。
這種“咸中微甜”的具體味感,應(yīng)該表述為“甜上口,咸收口”。
因?yàn)椤疤鹕峡凇保恳晃黄穱L到這道菜肴的客人都會(huì)有一種細(xì)膩、甜蜜而溫柔的味感,但這種甜不可太過(guò)濃郁,否則太甜的菜很快會(huì)麻痹味蕾,而“咸收口”指的是隨著口中唾液的分泌,微甜的味感很快被更為濃郁的咸鮮所取代。
這種“甜上口,咸收口”的味感是值得大書(shū)特書(shū)的,因?yàn)樗业搅艘粋€(gè)人類(lèi)味覺(jué)上最微妙的平衡點(diǎn)。人的舌頭上的味蕾分布是不均衡的,舌尖易品甜、舌根易品清中葉時(shí)的十六鋪碼頭20 世紀(jì)初的老正興苦、兩腮易品酸、舌苔面相對(duì)均衡一些,主要品各色鮮味。“甜上口、咸收口”正好與舌頭感知味覺(jué)的順序相同,它既保持了菜肴應(yīng)有的咸鮮特色,同時(shí)又給咸鮮底子勾勒出了一個(gè)美麗的味覺(jué)上的花邊。
上好的菜肴都是一種“掛口感”的,所謂的“掛口感”就是菜肴對(duì)口腔的味蕾進(jìn)行了有效的深度刺激,這樣持續(xù)興奮中的味蕾會(huì)使人產(chǎn)生某種持續(xù)的味覺(jué)記憶,即使你用茶水漱過(guò)了口,這種味覺(jué)的停留感覺(jué)還在,這就叫“掛口”。掛口的方式有很多種,但咸中微甜是最佳呈味方式之一。
常有外地人說(shuō),本幫菜甜得讓人受不了。雖然這里很可能有一個(gè)味覺(jué)習(xí)慣的問(wèn)題,但一般來(lái)說(shuō),這在調(diào)味上叫做“走偏”,掌勺的人還不會(huì)掌握放糖的“度”。很多“菜譜廚師”是很容易在這里犯錯(cuò)誤的,這就是“濃油赤醬”這種模糊語(yǔ)言和“左手醬油瓶、右手糖罐子”這樣的文學(xué)語(yǔ)言的不靠譜之處。
“咸鮮底、復(fù)合味”是咸鮮類(lèi)本幫菜的總體原則,這句話(huà)的重點(diǎn)在于本幫菜的這種所謂“復(fù)合味”該如何描述和定位,而“甜上口、咸收口”就相對(duì)比較清晰地表明了其藝術(shù)規(guī)律。
但“甜上口、咸收口”還不足以完全概括咸鮮類(lèi)本幫菜的藝術(shù)特色,它還有更細(xì)微和精妙的層面,這要再往下細(xì)分一節(jié)才講得清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