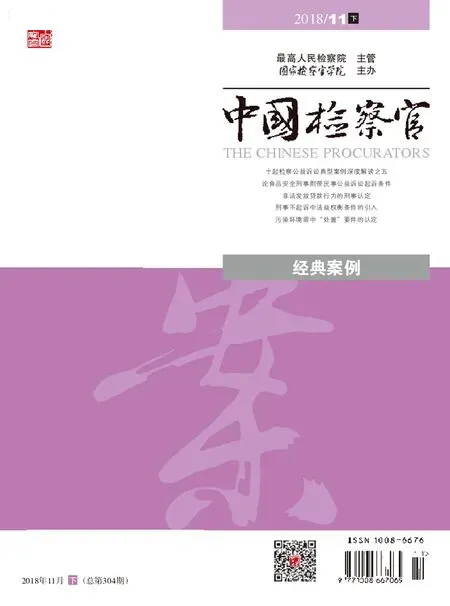論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起訴條件
文◎李桂明
近年來,公益訴訟成為檢察機關的一項新業務,[1]各地檢察機關都積極開展了公益訴訟實踐。其中,食品安全是檢察公益訴訟的一個重要領域,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是檢察機關辦理該類案件的常用手段。但是,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起訴條件并不明確,尚有待進一步探討。
[基本案情]張某系甲省乙縣人,2018年3月,張某從丙省購買了大量名為“A牌加碘食鹽”和散裝無商標鹽塊,長期在其住處乙縣城關鎮銷售。后在市場清理大檢查過程中,被乙縣市場管理局查處,并對其銷售的576公斤食鹽進行暫扣和封存,后經法定部門鑒定,張某銷售的“A牌加碘食鹽”和散裝鹽塊均不含碘。于是該案轉入刑事偵查程序,公安機關從乙縣城關鎮張某住處起獲未銷售的“A牌加碘食鹽”和散裝鹽塊共計632公斤,并從城關鎮其他村民家中提取了“A牌加碘食鹽”累計392公斤,均是從張某處購得,經鑒定與張某家中起獲的“A牌加碘食鹽”系同批次產品,也均不含碘。根據衛生部與工業和信息化部出臺的衛辦疾控發〔2009〕168號文件以及該省衛生廳文件的規定,甲省乙縣為嚴重缺碘地區。而按照《食鹽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條例》第15條第3款的規定,“在缺碘地區生產、銷售的食品和副食品,凡需添加食用鹽的,必須使用碘鹽”。由于銷售數額較大,對社會產生的危害程度較大,公安機關認為張某銷售無碘食鹽的行為已經涉嫌犯罪,于是按照刑事訴訟程序移送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過程中,檢察機關認為該案受害群體眾多,涉及公共利益,于是對張某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一、爭議焦點及法院的認定
本案刑事部分由于公安機關收集的證據非常扎實,足以證明張某構成犯罪,因此并無爭議,主要爭議在于民事部分是否能夠按照公益訴訟來處理。
(一)實體方面是否侵害公共利益
本案的關鍵問題是張某的行為是否侵犯公共利益。對于這一問題在檢察機關起訴的過程中有三種不同的認識:一是認為張某的行為不侵犯公共利益。這種觀點主要認為社會公共利益是一個宏觀概念,而不是一個具體的概念,需要有較為廣泛的受害群體,如果受害群體并不廣泛,則不能按照社會公共利益來評判。本案中,張某銷售的“A牌加碘食鹽”和散裝鹽塊當場被查獲的為576公斤,在家中查獲的為632公斤,在村民家查獲的“A牌加碘食鹽”有392公斤,其中未銷售的食鹽并不會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損害,而在村民家查獲的392公斤“A牌加碘食鹽”由于村民尚未食用,因而還未對村民造成損害。而真正造成實際損害的是已經被村民食用了的食鹽,而這部分損害究竟有多大,并沒有證據證明,因此并不能證明公共利益遭受損害。二是認為張某的行為與公共利益無關。此觀點認為張某銷售的食鹽是針對具體的客戶,而每一受害者又是具體的個人,無論人數多少,都與公共利益沒有直接關系,應當定性為受害者眾多的案件,因而張某的行為與公共利益無關。三是認為張某的行為侵犯了公共利益。這種觀點也是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的主流觀點,認為食品安全本身就屬于公共利益的一個組成部分,張某銷售無碘食鹽的行為是對食品安全公共秩序的一種破壞,無論銷售數量多少,都構成對公共利益的侵犯,因此張某的行為侵犯了公共利益。上述三種觀點在辦案過程中雖然有爭議,但是可以分為兩類:前兩種情況對張某的行為都不能按照公益訴訟來處理,而最后一種情況則可以按照公益訴訟來處理。最終辦案的檢察機關采納了第三種意見,按照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對張某提起訴訟,追究其民事法律責任。
(二)程序方面是否有起訴權
辦案檢察機關認為張某的行為侵害了公共利益,準備對張某提起公益訴訟,而如何對張某提起公益訴訟,也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另行起訴,該觀點認為,應當先將張某的刑事犯罪部分審判結束,然后對公共利益遭受損害的總量進行評估,再根據相關證據對張某另行提起公益訴訟。當然這在訴訟程序上會存在一定不便。按照2018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檢察機關民事公益訴訟案件辦案指南(試行)》(以下簡稱《辦案指南》)第1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一般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市(分、州)人民檢察院管轄”。基層人民檢察院一般情況下不能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所以對于張某應當由辦案機關的上級人民檢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追究其民事責任。二是一并起訴,也即由同一辦案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對張某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與刑事部分一并辦理。這種觀點也有法律支持,即“兩高”《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公益訴訟解釋》)中第20條規定的 “人民檢察院對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犯罪行為提起刑事公訴時,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由人民法院同一審判組織審理”。上述兩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而從法律程序來講,也都具有實現的可能性。第一種做法有利于使公益訴訟專業化,但是程序復雜;而第二種做法雖然程序簡單,也有直接的法律依據,但是由刑事審判組織審理民事案件其專業性并不一定得到全部彰顯。辦案檢察機關認為,本案案情較為簡單,所侵犯的公共利益也較為明顯,取證過程也并不復雜,不需要做復雜的技術鑒定,依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完全可以解決辦案中公共利益的認定問題。因此,最終辦案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向張某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求張某承擔民事法律責任。
(三)法院的認定結果
法院經過審理認為,張某銷售無碘食鹽的行為構成了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刑事部分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并判處罰金人民幣6千元。與此同時,法院還一并對民事部分作出了處理,認為張某銷售無碘食鹽時,購買者是社會不特定的公眾,并且已有大量的無碘食鹽流向了社會,食用這些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鹽的受害群體則更多,而且在社會中的未食用的無碘食鹽對社會所造成的危險也并未消除,隨時有可能會對社會公眾造成身體健康損害,因此張某銷售無碘食鹽的行為侵犯了社會公共利益。民事部分判決張某在緩刑期間不得從事與食品相關的生產銷售活動,在本地負責收回已銷售的食鹽,消除影響,并在本地媒體公開賠禮道歉。判決后,張某并未上訴。應當說法院的判決較好地保護了社會公共利益。
二、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起訴條件的限定
張某銷售無碘食鹽案,刑事部分并無爭議,而民事部分卻產生了一定的爭議,從實際辦案出發,也就引出了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起訴條件到底有哪些的問題。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加以限定。
(一)案件范圍限于食品安全領域
毋庸置疑,檢察機關提起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首要條件就是案件范圍必須屬于食品安全領域。案件是否屬于食品安全領域似乎根據生活常識便可以輕易判斷,但是對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而言卻并非如此。因為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首先要符合刑事訴訟的特征,而可以適用刑事程序處理的案件必須要達到刑事立案標準,由此可知,符合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前提條件必須是刑事法律規范中所稱的食品安全案件,而且需要達到刑事立案標準。因而,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案件范圍是狹義標準,限于《刑法》第143條規定的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第144條規定的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所限定的“食品”。由此可以看出,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案件范圍必須滿足下列條件:一是狹義標準,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屬于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食品”。二是程度標準,即需要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而所謂的情節嚴重是刑事標準而非民事標準。換言之,有些案件可能情節達不到刑事立案的標準,但是卻可以達到民事公益訴訟的標準,此種情況并不屬于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案件范圍。
(二)損害后果必須侵害公共利益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落腳點是公益訴訟,也就是說要想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必須是行為侵犯了社會公共利益。而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其實是一個較為模糊的概念,并沒有法律的直接界定,公共利益與公序良俗密切相關,包含了具體和抽象、現實與未來的相關利益,是由評價客體與評價標準構成。[2]一般而言,公共利益就是社會整體所認同的價值觀念和公共秩序,而并不一定是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可以通過代表人訴訟來加以解決,例如小區物業糾紛。從這一點來看,對公益訴訟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必須是社會主流價值觀所認同的社會公共秩序。例如,本案中張某銷售無碘食鹽的行為是被社會公序良俗所否定的,侵害的是社會食品安全的公共秩序,[3]因此可以按照公益訴訟來辦理,這也是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起訴條件之一。
(三)起訴條件不受主觀過錯的影響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解決的是民事部分法律責任如何承擔的問題,而民事法律責任確定的基礎是過錯原則,在特殊情況下,則可以是無過錯原則。公益訴訟應以何種歸責原則作為起訴的基礎,法律并沒有直接的規定,而按照《侵權責任法》的規定,食品安全的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原則,因此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訴訟也不必考慮侵權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問題。[4]另外,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是以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為前提的,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方面自然符合刑事法律規范中對主觀惡意的要求,這在民事侵權法律關系中也必然是存在過錯的行為。在收集證據方面,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對嫌疑人主觀過錯方面收集證據的方向也會因此而有所變化。
(四)嫌疑人的行為必須符合民事違法性的要求
行為違法性是確定侵權行為的必要條件,無論是一般侵權行為還是特殊侵權行為,均要確定侵權行為人的行為違法性,這一點是判斷侵權行為的關鍵要素之一。然而在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是否還要證明行為人的行為具有違法性,對這一問題也有兩種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不必收集嫌疑人行為違法性的證據。因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公安機關已經收集了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的證據,既然構成了犯罪,自然也就能夠證明其行為的違法性,因此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不必再行收集嫌疑人行為違法性的證據。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當收集嫌疑人行為違法性的證據。因為民事部分要求的行為違法性與刑事部分不同,證明犯罪行為的證據與證明民事違法的證據要求程度也不同,將證明犯罪的證據作為證明民事行為違法性的證據,有可能會遺漏一部分證據,因為有的證據未必能夠證明犯罪,但是可以證明民事行為違法。從這一角度來看,后一種認識更加符合法律邏輯。因為民事行為違法性的證明標準與刑事犯罪的證明標準并不一樣,前者標準較低,后者標準較高,且所需要的證據材料也是不同的。從這一角度來講,應當將嫌疑人的行為必須符合民事違法性的要求作為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起訴條件之一。
(五)公共利益的損害需與違法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是確定民事侵權法律關系的成立要件,也是刑事法律關系的重要基礎。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刑事部分需要證明的因果關系是行為人的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民事部分的因果關系則是要證明行為人的行為與公共利益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從侵權法的角度來講,只要符合相當因果關系,就可以證明侵權行為的成立。[5]具體而言,就是要證明沒有行為人的行為,損害結果就不會發生,而有了行為人的行為損害結果就非常有可能會發生。即只要證明有較大可能性,就可以使因果關系成立。這是民事因果關系與刑事因果關系之間的區別。
(六)案件管轄條件
案件管轄也是辦理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條件之一,根據《公益訴訟解釋》第20條的規定,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由同一檢察機關一并辦理,這一點是比較清楚的。但是有疑問的是跨區案件管轄問題。刑事訴訟一般由犯罪地法院管轄,必要時移送主要犯罪地法院管轄。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如果犯罪嫌疑人生產偽劣食品的犯罪地在甲地,銷售地在乙、丙等地,而產生影響地有可能還會波及丁、戊等地,此時刑事部分的管轄權是比較容易確定的。但是由辦案檢察機關一并辦理民事公益訴訟,很有可能會出現民事部分造成的公共利益損害最嚴重的地區并非是主要犯罪地,即辦案檢察機關所在地很有可能并不是公共利益受損最嚴重的地區,因此在最終法院判決的時候,若判決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措施時,很有可能會存在執行方面的困難,公益訴訟的效果難以得到最大化。而在當前法律狀態下,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管轄原則還應當堅持主要犯罪地原則,檢察機關是被動受案,選擇余地并不大。因此,建議依法確立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管轄規則為:一般情況下應當由公共利益主要受損地的檢察機關和法院實際辦理,如果抓獲地并非公共利益主要受損地的,可以將案件移送公共利益主要受損地檢察機關將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一并辦理。
三、結語
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是一項嶄新的業務,食品安全領域是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的重要領域,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則是檢察機關辦理此類案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對于這樣一類案件,起訴條件是檢察機關應當重點把握的,具體而言,要從案件范圍、損害后果、主觀過錯、行為違法性、因果關系、案件管轄條件等方面來把握起訴條件,這樣就可以將食品安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辦理扎實。
注釋:
[1]參見朱孝清:《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后檢察制度的鞏固與發展》,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4期。
[2]參見梁上上:《公共利益與利益衡量》,載《政法論壇》2016年第6期。
[3]參見周偉:《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檢察院訴吳明安等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載《中國檢察官》2018年第14期。
[4]參見郭明、謝厚群:《檢察機關提起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訴訟的現實困境與出路》,載 《法制博覽》2017年第33期。
[5]參見楊立新:《侵權責任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