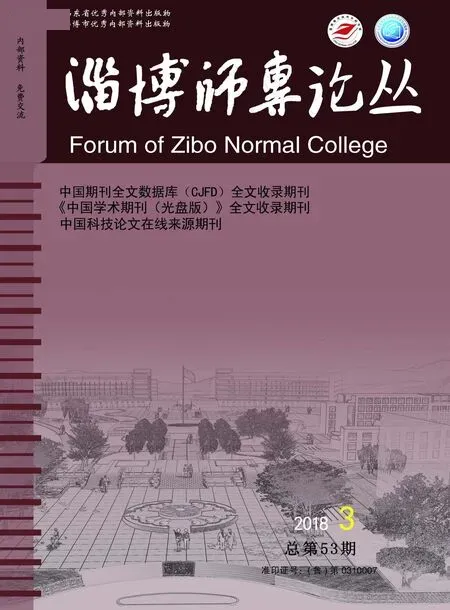吳澄的詩學性情觀
黃金葉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025)
引言
“性情”一詞最早出自《周易》之《乾》卦。在先秦諸子著作中,對性和情的認識各有特點。性情論是詩學中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命題,在詩學中,“性情”最早出自漢代《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1](P30)“吟詠情性”[1](P30)。從目前研究狀況來看,元代詩學研究相較于其他朝代詩學研究而言較少。研究元代詩學性情論的成果多集中在歷史層面的建構,對于個體的研究不多。因此,本文以元代吳澄為研究對象,對其詩學性情論進行討論。吳澄是宋末元初之儒學大家,有“北許南吳”之稱號,與北方大儒許衡齊名,開創(chuàng)了“草廬學派”,門徒眾多。吳澄還是元代重要的文學家,他在文學上有許多重要的見解。他的文學主張,特別是他詩學理論影響了元代中后期詩學發(fā)展。他繼承了宋儒哲學思想,其詩學也體現(xiàn)了較強的哲學思辨性。所以,本文從其儒家哲學思想層面出發(fā),闡釋其詩學性情論。
一、元代以前哲學性情觀發(fā)展情況
在詩學中,“情”是詩學核心觀點;“性”則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其核心思想為道德。二者在不同的闡釋下,則有不同的意義與內(nèi)涵,性時而與情相對,時而與情統(tǒng)一。
于孟子而言,人性乃善,人的情體現(xiàn)為仁義禮智,是完全道德化的“四端”之情,此處,情與性統(tǒng)一。對于荀子而言,人性本惡,性屬于天,天沒有理想,也沒有道德的原理,因此性中亦沒有道德的原理。而道德是人為的,也就是荀子所言之“偽”。他認為人天生就對聲色欲望有所追求,如果順著天性,那就會社會紛亂失去秩序,陷入欲望爭奪的戰(zhàn)爭之中。
到了漢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凸顯,性和情的關系是對立和統(tǒng)一兼具。他認為性相當于天之陽,情相當于天之陰,“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養(yǎng)而無其陰也”[2](P230),由于天人合一,人的性情對應著天的陰陽。人之質,是人的理性,相當于天之陽;人的情感相當于天之陰。人性不善不惡,性中有善端,就如同禾與米的關系,禾苗既生出米粒,也會生不出米粒,禾苗就是善端,米就是人的思想和行為。為了能保證善端能生善,就需要通過“王教”來規(guī)訓人性。
唐代韓愈為宋明道學的發(fā)端人物。在《原性》中,他認為,性由天而生,有五種,分別是仁義禮智信;情接于物而生,有七種,分別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性有分為上中下三品,上是善,中是可善可惡,下是惡;情亦可分為三品。上品善性恰如其分地掌控七情“動而處于其中”[3](P2502);中品有善惡的性,雖然不能完美掌握七情,但是仍能“求合與其中者也”[3](P2502);而下品惡性則是直接抒發(fā)泛濫或者是不足的七情,“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3](P2502)。李翱作為韓愈的徒弟,提出“滅情復性”,他認為情感是“邪”和“妄”的體現(xiàn),而性則是沒有不善的。因此,情感與道德人性直接對立,只有消滅情感,才能恢復人性。此處的性是指道德理性。他同意性是天的體現(xiàn),即“天命之謂性”,而情感則是“七情”之情。可見,李翱的性情論思想認為性和情是統(tǒng)一的。李翱的性情學說的意義在于為儒家理學人性學說提供了宇宙本體論的基礎,并將情感納入道德理性之中。
到了宋儒階段,開始從形而上的角度對性進行闡釋。程顥、程頤兄弟以及朱熹皆認為宇宙的本源是“理”,他們?nèi)藢τ谛郧榈挠^點保持一致。二程認為“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4](P204),性與萬物本源之“理”相關,性雖是由理所生,但也與氣的關系緊密。人作為具體的物,其生必依托于氣,氣有其不同的特質,也就是氣稟,不同的氣會影響性,因此性有善惡之分。二程認為理性猶如水一般,有的從源頭流向大海,終究沒有被污染,因此不需要人力去規(guī)訓。而有的水從源頭流向大海的過程,則被泥沙污穢所染,但是污水本質仍然是水,因此需要人力去加以整治,恢復其原本的面貌。可見,其繼承了孟子人性善的觀點,且將性分為兩層:一層為表面的性,有善惡之分,善惡由氣所影響;另一層則為宇宙之“理”,且宇宙之“理”之根本為善。氣生情,情亦有善惡之分。他們認為心為性、為理,人只要將情感展現(xiàn),情感便不屬于心,而是屬于情感。但是情感的表達始終表現(xiàn)著性,比如,惻隱之情屬于道德之情,從“四端”之情中可以發(fā)現(xiàn)性。對此,關于性與情的關系,二程和朱熹都認為是既包含又對立,當所發(fā)之情無法體現(xiàn)善,則與性對立;當所發(fā)之情是屬于道德情感,則體現(xiàn)了性。
二、吳澄哲學性情觀
(一)吳澄哲學性情論中的性
從吳澄的哲學維度出發(fā),闡釋吳澄的性情論。其性善論建立在“人之性是得天性之理”[5](卷2P20A)的基礎之上,而人有性善性惡之分,吳澄認為氣質有不清不美,致使人之本性難免不受到污壞。他堅持人性善,“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5](卷2P20A),并且強調(diào)人的內(nèi)在氣質雖不清不美,但天地之性從人誕生開始就存在于人的氣質之中并發(fā)揮著主宰作用,可以通過“學問”來恢復人之本性,恢復人之理氣,清除污壞之氣質。此觀點與二程、朱熹一致。吳澄認為本性污壞在于人的氣質受到外在環(huán)境影響,本性污壞在于氣質有清濁之分,氣質則是宋儒所說的氣稟,與“氣”內(nèi)涵并不相同。再進一步思考,筆者發(fā)現(xiàn),吳澄的“氣”論的前提是發(fā)現(xiàn)、承認個體具有獨特性,“理”論則是對儒家傳統(tǒng)思想的繼承,堅持社會性、道德性,為個體建造圍城。可見,吳澄作為朱子后學的一份子,接受了前人的影響。
(二)吳澄哲學性情論中的情
吳澄關于“情”,有兩種說法,一說為喜怒哀懼愛惡欲,即是“七情”之情;另一說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即是“四端”之情。在他看來,“天之生是人,其生也,有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是性,其發(fā)也,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6](P131)。可見,吳澄認為“四端”與“七情”之間是“發(fā)”與“未發(fā)”的關系,“四端”是仁義禮智,是天給予人的,是人天生便具有的,屬于道德意識和道德情感活動;“七情”則以仁義禮智為基礎,是人們表達、釋放出來的情感,屬于心理學意義上的情感活動,也就是情緒。
綜上所述,吳澄認為性情同一。吳澄性情之間的關系是既包含又對立,當所發(fā)之情無法體現(xiàn)善時,便與性對立;當所發(fā)之情是屬于道德情感的范疇,則體現(xiàn)了性。
理氣論哲學思想對吳澄詩學理論有所影響,筆者從吳澄的哲學思想出發(fā)研究其詩學中的性情論。真實和自然是吳澄詩學中與性情二字相配次數(shù)最高的兩個核心概念,因此,研究性情之真與自然性情此二者的內(nèi)涵意義是能夠闡釋吳澄詩學性情論的含義。
三、性情之真:個體性和社會性
吳澄的詩歌理論建立在其哲學思想之上,“詩也者,乾坤清氣所成也”[5](卷19P16B)。在吳澄的哲學邏輯下,詩歌作為萬物之一,由氣所生,并且包含著理。可見,詩亦是氣化生而來,其本身具有四端之情,具有自己的規(guī)律和存在的形式,因此性情之真則是指道德思想感情。但是詩歌不僅與世界本體“理氣”有直接關系,也與人有關,“人之有聲而成文者,詩也”[5](卷22P2B),不同的詩人具有不同的氣質,詩歌情感也會有所不同,而此時性情之真指詩人本真的情緒。詩歌相對比哲學而言屬于形而下,它同時受到同樣為形而下的人與屬于形而上的“理氣”的雙重影響。而性情之真在詩學中主要表現(xiàn)為性情的個人情感和社會情感的矛盾。
(一)真實的個人情感
“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人之辭,而后世文人不能及者,何也?發(fā)乎自然而非造作也”[5](卷17P16A)。吳澄認為詩歌應表達詩人的真情實感、真實性情,就如詩經(jīng)國風那般自然地表達出農(nóng)民婦人豐富的感情,不是人為地強迫感情流露。“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人之辭”[5](卷17P16A)中的情感屬于“七情”之情,是人本身的情感,不論是田夫對貴族的痛恨之情,還是婦人對愛情的向往之情,只要是發(fā)乎內(nèi)心,自然不造作,皆符合性情之真。“王實翁為詩,奇不必如谷,新不必如坡,工不必如半山,性情流出,自然而然,充實所到,雖唐元、白不過如是”[5](卷18P4A),自有獨特個性,詩人為詩,重在將真實情感表達自然到位,言己性情,而不是為了追趕前人腳步。黃庭堅之所以奇,蘇東坡之所以新,皆為其氣質決定,皆為其性情決定,詩歌情感絕不在于模仿他人或扭曲自己的性情。從哲學角度而言,性情之真具有個人性。性情由氣所化生,不同的氣化生為不同的性情。可見,氣不同,性情不同,人的性情具有獨特性,而這一切都是符合吳澄理氣論的哲學思想邏輯。吳澄同意詩人具有個人情感,具有個人的獨特感受,吳澄的思想仍然給個人性情留有余地。
(二)關乎政教的社會情感
古代儒家學者皆重視社會倫理政教。社會倫理政教本質則在于道德情感。吳澄作為儒家學者,繼承這一儒學傳統(tǒng),因此,吳澄在詩學中更重視的是社會性情。從社會功用而言,“詩祖三百篇,學者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5](卷18P2A),吳澄認為詩經(jīng)作為詩之祖,內(nèi)涵傳統(tǒng)的事父、事君的社會倫理規(guī)則。詩經(jīng)在孔子時期便被納入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孔子認為詩能夠陶冶性情、提高修養(yǎng)學識、讓人了解社會情況和其中的得失、可以批評政治、可以表達民情。對于儒家而言,社會的倫理和道德情感通過詩而闡發(fā),發(fā)揮其社會功用。從哲學層面而言,“理”主宰氣之運動,給予氣凝聚的力量,是氣之內(nèi)核。“理”代表的是“四端”之情,是人性善之根本,表現(xiàn)為人之德。因此,詩歌同為氣之所化,同萬事萬物一般,都以“理”為其內(nèi)核。詩歌的性之根本在于善,情之根本在于“四端”之情,詩歌性情根本在于道德情感。
(三)個人情感與社會情感的調(diào)和
吳澄通過品級觀、“性其情”的方法調(diào)和社會與個人之間的矛盾,并最終選擇突出社會,弱化個人。吳澄將詩分了品級“詩言志,寧高無卑,寧純無雜,寧正無邪”[5](卷23P1B),詩的性情在高低、純雜、正邪之間有所區(qū)分和舍棄。這就折射出吳澄在“理氣同一論”中更偏向于“理”的哲學思想,更側重于認為人的道德情感是性情之本真。
四、自然性情:表達方式和詩歌境界
“自然”在吳澄詩學理論中出現(xiàn)次數(shù)較多,常與性情相配。自然性情在吳澄詩學中可分為兩種意思。
(一)自然而然的表達方式
其言“夫詩以道情性之真,自然而然之為貴”[5](卷23P3A)。吳澄認為表達性情自然的詩才是好詩,重視詩歌內(nèi)容表達的方式,重視情感在文字上流動的方式,如潺潺流水般潤物無聲,是吳澄哲學理念和詩學性情論的體現(xiàn)。在詩歌創(chuàng)作過程中,吳澄認同“聲情自然,不事雕鐫”[6](卷56P1A),認為好的詩歌不在于極力追求詩文之工整,也并不在于鉆營詩之文字,而是毫不經(jīng)意地使用文字,詩歌宛如天成,情感緩緩流出。
(二)天人合一的詩歌境界
其言“純乎一真,心聲自然”[5](卷60第P3B)。 吳澄所言之性情自然中的“自然”并不是我們現(xiàn)代人所言的客觀存在的自然,而是儒家所言的天之規(guī)律,屬于詩學性情的一部分。儒家所言“自然”從哲學“天人合一”思想中產(chǎn)生,儒家認為“天”是一種最高的存在,它具有最高的道德情感和理性規(guī)律,是世間萬物所共有的同一之“理”。
因此,自然性情是由道德而生,此道德情感就是萬事萬物的普遍情感。天之氣理給予人類道德情感。而人的自然情感往往是由詩人個人氣質所決定,被外在事物觸動后,人的七情之情便會有所發(fā),人的七情是由人性所生,人性又由人之氣化生,外在事物觸動只是一個動力,卻不是源頭,只有理氣是根本的源頭。因此,人要實現(xiàn)詩歌的性情自然的目的,重點在于要達到與普遍情感、理性道德情感同一的境界。只有達到理氣層面的同一,也就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才能理解天之氣理,領悟自然的意義。
如何達到天人合一之境界?吳澄認為通過格物之學能夠最終服務于反身窮理的目的,帶來道德上的增益,去除氣質帶來的種種不良影響,恢復人之本性。通過對具體事物之理的了解,上升到對普遍天理的認識,達到天之氣理之高度,以便于作為本性的善能全面發(fā)揮出來。當詩人能夠表達自然性情之時,詩歌便能達到“心與景融,物我俱泯,是真詩境界”[5](卷16P15A),便談不上人被物所役或人役物的說法。此刻人的情感已經(jīng)達到最極致的道德化,對待外在事物的情感態(tài)度僅僅為“一笑”,這一微笑表達的是人將萬千情緒拋棄,與天、物融為一體,“天時物態(tài),世事人情,千變?nèi)f化,無一或同,感觸成詩,所謂自然之籟”[5](卷22P12A)。吳澄的自然性情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將人與物同化,類似于莊子所言“吾喪我”,但是吳澄所喪的是不美不清之氣,其使性回歸到本性,恢復到“乾坤之清氣”中去。
五、吳澄詩學性情論對后世的影響
吳澄的詩學扎根于理學,吸收了傳統(tǒng)詩教,吸收了陸九淵的心學,其中包含的新思想和新內(nèi)容對當時以及他身后的文人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主要是對虞集和明代性靈說的影響。
作為元代四大之首的虞集,他在延祐時期備受重視,在詩壇上也頗有影響力。他身為吳澄的弟子,在詩學理論更多地繼承了吳澄的朱子理學和傳統(tǒng)詩教的思想,多求雅正之風。其言:“古者君臣賡歌于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fā)諸音而成文著,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業(yè)。”[7](P2065)但是最終落腳點仍然是“善”,落到君子品德之上,虞集比吳澄更為深入地走向了傳統(tǒng)詩教,但他的理論仍未脫離吳澄以性情、創(chuàng)作主體為核心的詩學理論。
吳澄的詩歌理論主張影響了明代的性靈說,與他在明代心學的地位顯赫有關。王陽明推崇陸學和吳澄,明代性靈說又受到了王陽明的影響,因此,性情說可以說是間接地受到了吳澄的影響。公安派主張詩要表現(xiàn)詩人的主體精神,講究的是不落格套,對詩法的無視,這都與吳澄的詩學有著許多相同之處。吳澄主張其詩在我,其機在我,同樣也是重視詩歌展現(xiàn)詩人自我主體精神;其言自然而然、自然天趣,創(chuàng)作詩歌不應該扭曲性情,不應該追逐字句的精美精致,應該是不事雕琢、自然天成。而清代袁枚認為“作詩不可以無我”[8](P410)同樣突出一個“我”字,以 “我”來推重詩的個性。可以認為,吳澄的詩學性情論,不僅僅影響了元代時期重雅正的詩學追求,也為后人解放詩學思想奠定了基礎,由此也可以看出吳澄詩學的包容性。
結語
綜上所述,吳澄詩學性情論以吳澄“理氣”哲學本體論為基礎,含有性情之真和自然性情兩個方面。性情之真體現(xiàn)的是個人性與社會性兩個不同的含義的矛盾與調(diào)和,個人性情是人之氣的顯露,社會性情則是天之氣的顯露。吳澄從其哲學觀點出發(fā),更為重視性情的社會性。自然性情則是創(chuàng)作論和性情論共有的概念,吳澄認為若要達到自然地創(chuàng)作詩歌的水平層次,詩人需要提高自己內(nèi)在的道德情感,清除人心中污濁之氣,擴展內(nèi)心之理氣,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即性情與天同、與萬物同的境界,此時詩人的創(chuàng)作才能達到真正的不造作而理氣齊備的自然境界。吳澄詩學性情論吸收了儒家、詩家的詩學理念,既影響了元代延祐的雅正之風,也奠定了明清詩學解放思想的基礎。本文僅圍繞吳澄性情論中的性情之真與自然性情兩個方面進行探討,或有錯訛不足之處,希望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