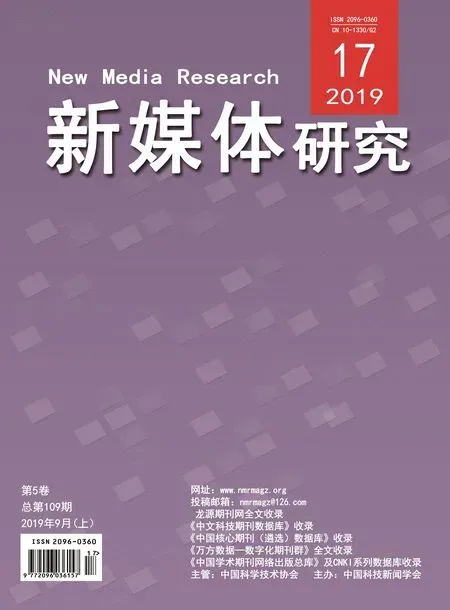新媒體輿情的生成與傳播
趙作為
摘要 微信和微博作為當(dāng)下我國影響力最大的社交媒體,日益影響著我國的社會發(fā)展和公眾生活。微信和微博作為時下網(wǎng)絡(luò)輿論的源發(fā)主要平臺,在網(wǎng)絡(luò)輿情生成和傳播過程中存在巨大差異,文章從輿論場域、輿論自凈化能力、輿情傳播差異和公共事件傳播等方面,對兩者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
關(guān)鍵詞 新媒體輿情;微博;微信;比較分析
1輿論場場域:開放VS封閉、顯性VS隱性
作為當(dāng)下最為流行的社會化媒體,微博與微信兩大信息交流的平臺在網(wǎng)絡(luò)輿論熱點生成和傳播中,呈現(xiàn)出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是基于微博、微信各自輿論場域的傳播特征,決定著輿情生成和傳播呈現(xiàn)出各自的特點。微博由于其相對開放的信息傳播特點,更像是一個大眾化媒體平臺,其輿論場相對開放。而微信是基于熟人關(guān)系建立起來的社交平臺,其輿論場場域(以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為主)相對封閉。
微博由于其信息相對開放,呈現(xiàn)的輿論場域較為顯性,普通民眾可以直觀感受到,而微信由于其信息傳播環(huán)境相對封閉,輿論場域呈現(xiàn)隱性特征。正是由于微博輿論場的開放特點,微博輿論更為多元化,帶來的問題是微博的輿論撕裂現(xiàn)象嚴重。由于我國微博用戶龐大,微博已經(jīng)成為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放大器,社會現(xiàn)實中的戾氣和沖突矛盾,在網(wǎng)絡(luò)匿名機制環(huán)境下,經(jīng)由微博發(fā)酵、傳播,又會引發(fā)輿情下線群體性事件。微博中由各興趣話題、“圈子”形成的各個階層和群體,對輿論議題的不同見解,常常引發(fā)輿論場的群體極化和輿論撕裂,甚至激化為網(wǎng)下不可調(diào)和的斗毆事件。
而微信輿論場表面看似平靜,實則輿論場暗流涌動。微信的傳播特性決定了輿論事件經(jīng)過微信平臺的聚集發(fā)酵,一旦爆發(fā),就會成為輿情熱點。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的裂變傳播方式,決定了微信輿論的傳播速度快、影響面廣的特點,微信的封閉傳播,使得微信輿論呈現(xiàn)出單一極化明顯的特征,2015年2月末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環(huán)境調(diào)查紀錄片《穹項之下》就是很好的例子。
微博的開放性還體現(xiàn)在其輿論監(jiān)督效能上。近年來,民眾的民主監(jiān)督意識空前高漲,社交媒體平臺特別是微博為普通大眾監(jiān)督政府官員提供了絕佳平臺,為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和政治表達提供了快車道,從一側(cè)面加速了我國法制化進程,起到了社會減壓閥、疏解負面社會情緒、推動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shè)、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作用。
2輿論自凈能力
網(wǎng)絡(luò)謠言作為網(wǎng)絡(luò)輿論的形式之一,在微博和微信各自平臺傳播中,呈現(xiàn)出迥異的自我糾錯和自凈化能力。微信對謠言缺乏自我糾錯能力,微博則具有很強的自凈功能。微信屬于熟人關(guān)系下的私人小眾圈,因為是熟人彼此信任度高。在微信這一強關(guān)系和信息傳播環(huán)境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下,好友問的信任度使得人們對謠言的免疫力下降。由于特殊的傳播生態(tài),謠言自澄清機制弱,外部真實信息難以進入,謠言的生命力、煽動性和欺騙性極強,謠言管理難度增加。
而微博作為信息公開的媒體平臺,謠言的自澄清能力極強,微博平臺的信息糾錯能力能夠很好地體現(xiàn)出來。當(dāng)網(wǎng)絡(luò)謠言出現(xiàn)時,微博用戶可以互相質(zhì)疑、印證、糾錯,在信息的良性互動中,事件不斷被去偽存真,接近真相,最終謠言會被真實信息所取代。
“微博是微信謠言的清道夫”這句話,形象生動地闡明了微信和微博各自平臺謠言傳播特點和自我糾錯能力的差別。
3輿情傳播差異
強關(guān)系和弱關(guān)系理論由美國社會學(xué)家馬克·格拉諾維特最早提出,強關(guān)系理論是指現(xiàn)實生活中人與人聯(lián)系緊密,弱關(guān)系是指人與人關(guān)系并不緊密,異質(zhì)性較強。微信是典型的強關(guān)系傳播,而微博則呈現(xiàn)弱關(guān)系傳播,微信中的關(guān)系是現(xiàn)實中人際關(guān)系的網(wǎng)絡(luò)延伸,輿論可以通過這種新型的“網(wǎng)絡(luò)人際傳播”進行迅速發(fā)酵、擴散;而微博用戶雖然彼此很少是現(xiàn)實中相互認識的人,表面上看是弱關(guān)系,但由于可以通過“共同關(guān)注”、興趣愛好進行分類,以及互相轉(zhuǎn)發(fā)、評論等形式互動,相對“弱關(guān)系”的環(huán)境下,也為網(wǎng)絡(luò)輿論生成和傳播提供了絕佳的平臺。
在微信“強關(guān)系”在輿論傳播中,更多地通過傳遞信任感與影響力左右輿論發(fā)展,輿論生成和傳播隱蔽,爆發(fā)性強;而微博“弱關(guān)系”更多地通過傳遞信息與知識形成輿論,輿論生成和傳播高效迅速、成本低、擴散面廣。
4“沉默的螺旋”效應(yīng)
“沉默的螺旋”是德國著名的傳播學(xué)學(xué)者諾依曼于1974年發(fā)表的論文《沉默的螺旋:一種輿論學(xué)理論》中提出的觀點。該假說認為:人們在表達自己的觀點之前,會判斷和比較別人的觀點,如果覺得自己的意見與群體意見一致處于“優(yōu)勢”時,就會果斷發(fā)表自己的觀點;相反,當(dāng)發(fā)現(xiàn)自身的觀點與大多數(shù)人所持觀點不一致,屬于“較少數(shù)”或者處于“劣勢”時,“擔(dān)心被孤立”的恐懼心理會促使他們選擇保持沉默。這樣,“優(yōu)勢”的意見和“劣勢”的意見就成螺旋態(tài)勢發(fā)展。
“沉默的螺旋”是基于人們的社會心理。在微博環(huán)境下,由于用戶匿名性這一特點,“害怕被孤立”心理極大弱化,基于微博的“弱人際關(guān)系”,人們發(fā)表意見時,不必在意是否被孤立,因為現(xiàn)實中沒人知道他們的具體身份。但由于有意見領(lǐng)袖、群體壓力的存在,沉默的螺旋效應(yīng)依然在微博輿論場中存在。
而在微信這一強關(guān)系下,“沉默的螺旋”效應(yīng)依然凸顯,人們發(fā)表與公眾多數(shù)意見相左的看法時,會考慮“被熟人孤立”“被嘲笑為另類”這一心理活動,從而不傾向于發(fā)表與其他人不同意見或觀點。
5公共輿情事件傳播
微信與微博基于不同的信息傳播架構(gòu),微信定向于社交、朋友圈,人際交流強于微博,而微博的基本功能是信息發(fā)布和獲取,具有的媒體屬性強于社交屬性。在公共事件,特別是突發(fā)性公共事件信息傳播方面,微博的傳播力和引爆力、話題制造能力以及信源等,都具有微信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
在2014年“馬航失聯(lián)”事件中,更多的人選擇從微博尋找有用的信息,而不相信微信中的謠言。一系列公共突發(fā)事件的實踐證明,微博的號召力和公信力得到公眾的認可,微博也借助一些公共事件,開始回暖,很多曾離開微博的人又重新回歸了這塊輿論場。在2016年媒體公信力調(diào)查中,受訪者認為公信力最強的是電視,其次是報紙,再次是微博,廣播和微信則分列第四、五位。
微信圈群較為封閉,容易導(dǎo)致信息傳播的偏向和極化。與微博相比,微信好友與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好友的契合度較高,彼此的信息來源更易被信賴。所以,微信用戶的信息交流者偏向于有共同興趣和價值取向的群體,導(dǎo)致信息傳播的過程中極易出現(xiàn)“群體極化”現(xiàn)象。
在公共事件線下動員方面,微信基于熟人的“強關(guān)系”,在發(fā)動線下活動時具有極強的號召力。在一些熱點事件中,微信公眾賬號中的觀點與微博、知乎等其他社交平臺觀點形成網(wǎng)絡(luò)共振,既易強化既有觀點,也大大降低網(wǎng)絡(luò)時代社會動員的成本。在近年來的諸多公共突發(fā)事件中,微信的“圈群化網(wǎng)絡(luò)動員”成為輿論場中的洶涌暗流,頻繁發(fā)生的涉及“訴求性群體利益”公共事件,在圈群化傳播環(huán)境下,輿論會聚集壯大,涉事主體如果回應(yīng)不力,則會演變成線下大規(guī)模群體事件或運動。
在當(dāng)前日益分眾化媒體時代,因共同興趣、話題分享而形成的新時代網(wǎng)絡(luò)社群,在風(fēng)險規(guī)避中會產(chǎn)生心理或身份認同,社群內(nèi)形成瞬時強關(guān)系,風(fēng)險信息會通過QQ群、微信群等“圈群”渠道擴散到其他社群,進而傳播到整個網(wǎng)絡(luò)輿論場域,從而加速輿情風(fēng)險的擴大和傳播。在2016年和頤酒店女孩遇襲、雷洋案、江蘇高考減招風(fēng)波等幾起典型輿情事件中,這些輿情風(fēng)險得以充分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