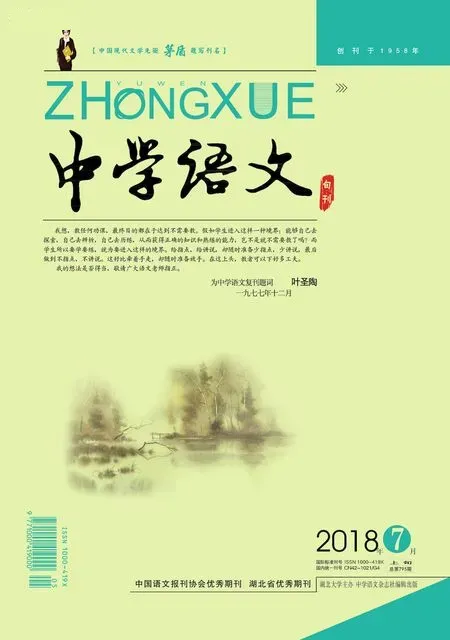著眼細節 讓寫作慢下來
胡嶺
著眼細節,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讓寫作盡可能地慢下來,不只是匆匆于敘事,汲汲于抒情,而是貼近人、事、物的本身,通過細微之處的呈現,從容而細膩、節制而真實地傳達更多的微妙的心理、豐富的情緒和深廣的思想。如果說,敘事與抒情,是文字向外的綿延,那么細節則是文字向內里的貼合,文字在內外上實現相對平衡時,文本才會有張力,才可以具備打動人心的力量。
對于寫作,真正的細節,是來源于生活的。典型的生活細節往往存在于觸手可及之處,卻常常被忙碌的疏于思索的人忽視,但一旦被人捕捉住,它又可以引發讀者共鳴,實現作者、讀者之間依賴于文本的心理共振。譬如有同學在《那一刻,我遇見他們的愛情》一文中,著力于表現父母的愛情。
父親出發去國外出差的那天,母親提起去送他的事。我因為下午有課而猶豫著,父親也表示不想耽誤我們中午休息,但母親卻用期待的目光看著我:“去送送吧,三個月呢,你都見不到爸爸了。”如果我說不去,母親也會因我留在家里,我于是同意了。點頭的瞬間,一抹喜悅與滿足從他們倆眼中流過。
……
他慢慢地放開我,腳步似乎遲疑而停滯了一秒,然后走到沒有看著他的母親跟前,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著。一如相冊里,那個溫柔地望著身著潔白婚紗的母親的青年,意氣風發,羞澀溫和。
“和你……也抱一下吧!”小心翼翼的語氣,帶著害怕拒絕的不安與小小的期待。然后仿佛下定決心,猛地上前,在母親開口之前,用更大的力道擁住了她。那是一個仿佛要將對方揉入自己血肉中有的擁抱,讓人在那一刻感受到一個男人全部的戀戀不舍與最深的柔情。
這種愛情又表現為人到中年情感冷熱交織的含蓄與不動聲色,其本身就很難通過大段的敘說去加以剖析與展現。但作者卻抓住父母告別之際,母親欲送父親卻先勸“我”去送,父親欲擁抱“母親”卻先擁抱“我”的細節,將父母之間淡于表達卻渴望表達而不得不以我為媒介去表達的“狡黠”與“深情”表現得如此鮮明,讓人在會心一笑中又深有體會。
再如有同學在大量的生活素材中捕捉到一個奇怪的現象。
奶奶在廚房炒菜,我是在客廳看電視,嗑瓜子時,總會猛然記起一件事,就像是讓漁桿將記憶深處的某個物件吊了上來,或是用撈網撈出一段記憶似的,她會突然眉頭一皺眼睛一亮,像似小孩發現零食似的狡黠目光,又像是阿基米德浴缸中的恍然大悟,她驚醒般的張開嘴,丟下手中的一切事,無論是鍋里的熱騰騰的菜,還是盆里擰到一半的衣服,拉長了聲音喊道“老——頭子——哎。”如果房子另一頭的爺爺應了一聲。奶奶便閉口不喊,也不做過多的交流,甚至也不隨意拉一句話,如果一聲過后沒有回應,他便會如此反復,直到喊了有四五遍,他就會急切的在屋里屋外找爺爺。出了門,看見了已在躺椅上鼾聲陣陣的爺爺。便會,“撲哧”一聲笑了,蝶笑罵道:“這個該死的”,眉間緊張的神色散去了。
文段中寫奶奶總會莫名其妙地喊一聲爺爺,如果爺爺應了一聲,奶奶便不再作聲,如果爺爺不應,奶奶就會急切地去找爺爺的細節,以此來觀照奶奶對于爺爺安危的關切之情,再妥帖不過了。
像這樣的生活細節在我們的課本中也有。例如《項脊軒志》中通過“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一句,以細節寫夫妻之間的親密,可謂傳神。一群小姑娘拉著回娘家的大姐詢問,大姐在向自己丈夫轉述時得意自豪的心理情態呼之欲出。其中也有歸有光自己的幾分得意。夫妻之間的得意恰恰便是彼此關系親密的證明。
找到典型的生活細節,只是寫作的第一步,重要的,還需要去表現細節。但是不得不承認,大多數高中生對于細節的表現力是比較弱的。這不能夠單純從技術層面去探討,或許跟他們曾經經歷的相關情境的記憶有關。情景記憶是對特定時間和地點發生的事件的記憶,而這也是高中生在記敘文寫作中的重要內容。
情景記憶既包括對單個事件的項目記憶,也包括對項目與項目、項目與背景信息之間的關系的聯結記憶。雙加工理論認為項目記憶和聯結記憶涉及不同的認知加工過程。項目記憶既可以通過熟悉性來完成,也可以通過回想完成;而聯結記憶只能通過回想來實現。熟悉性是一種基于熟悉強度連續變化的自動加工過程,發生速度較快,反映的是人們對單個項目的知道感,無法提取與事件相關的細節信息。回想則是一種全或無的閾限加工過程,發生速度較慢,能夠提取事件發生時的細節信息。學生在寫作過程中,根據所寫題目,勢必要從大量生活素材中選取相應的材料,但他們對于這些材料的記憶往往只是停留在熟悉性的層面,所以能夠很快地以線條的形式將其敘述出來,形成大概的事件輪廓,但若要將使事件飽滿、真實、有感染力的細節填充于其中,則必須通過發展速度慢的回想來實現。這樣,寫作者只有放下滿足于熟悉的心理,讓自己徹底回到曾經的某個時空中,以慢放的方式,恢復項目與項目、項目與背景之間的關聯,這也就是本文在開篇所說的,“著眼細節,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讓寫作盡可能地慢下來”。當然,這種慢,并非是物理時間上的慢,而是一種寫作的思維方式上的慢,是可以通過訓練而被寫作者熟練掌握的寫作方法。
不過,在訓練上,也不必急于求成,可以先引導學生先寫當天經歷的事情,消除時間上的隔閡,做現場的記錄或描寫。比如有同學就對作文課中自身的心理狀態做了全記錄,并以課堂作文的形式加以呈現。
早上,步頻無比迅速地匆忙趕到教室,待坐定后,目光集中在了黑板上的課表,心里暗暗盤算,八節文化課加上晚上的競賽,意味著一疊作業加上三小時的頭腦風暴,嗚呼哀哉!最終還是留意到了下午的兩節語文。在初中,連堂語文一般都意味著寫作的“災難”,講《鴻門宴》?好像學完了。寫作文嗎?作文!上周沒寫作文,周末沒寫周記,完了完了完了!我心中暗嘆不好,多半怕是又要接受考驗了。
……
預備鈴打響,胡老師大步邁上了講臺,跨立在講臺上,用他那一貫嚴肅的眼神和姿態等著我們做課前準備。拿著兩疊紙的左手似乎是刻意背在了身后。我瞥了一眼,一白(作文用紙)一綠(普通試卷),不應該都是綠的嗎?我心里又生起了不好的預料,卻依然懷著期待和僥幸的一絲念想。
……
胡老師在黑板上飛快寫下作文題目。我瞟了一眼題目,用雙手捂住了臉,即使做了很久心理準備,卻還是受到這最后一下重擊而崩潰,似乎感到心上有無數小蟲蠕動,心亂如麻,大腦一片空白,只記得曾經寫過一模一樣的題目,因結尾太低級被當眾批評。教室里再一次如爆炸了一般,同學們徒勞地掙扎著,卻又最終不得不順從命運的安排。我卻感到自己石化在座位上,看著作文紙的傳遞,有如窒息般絕望。那一刻,我自己似乎已不是自己,空氣都變得黏稠,無形的力量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這位同學在作文中,對于害怕寫作文,但又對今天是不是寫作文的揣測,到最后因為要寫作文而猶如窒息般的絕望寫得細膩真切,現實場感極強,可謂是對當天所發生的事情做了回放與現場直播。每一處細節的呈現都非常合理,很有情緒上的感染力,相信會引發不少作文恐懼癥者的共鳴。這樣以現場寫現場的訓練,實質上是降低回放的難度,讓學生更容易對事件的細節作更為全面的恢復,以養成寫細節的習慣,繼而,可以慢慢引導學生寫一周前、一月前、一年前的事情,如此循序漸進,一方面強化學生的回放意識,另一方面提升記錄細節的能力,最終達到可以讓學生針對不同的題目自由地從記憶中調取細節來進行寫作,或調取一定細節來做虛構的現實基礎。
至于在具體操作層面,不少作文寫作指導從外貌描寫、神態描寫、動作描寫、心理描寫、環境描寫等方面引導學生進行分類訓練,但這種機械的訓練形式,明顯不能再滿足高中階段記敘文寫作的需求,在高中階段更應該從出入、繁簡兩個維度來做細節方面的訓練,以適應高中階段更為復雜的寫作內容。
一、出 入
出入是針對心理狀態而言的。所謂“出”,即著眼于抽象的心理狀態,以細節描寫使內形于外;所謂“入”,即著眼于描寫外在的言語、動作、神態、外貌等,以切合特定人物、特定情境下的特定的心理狀態,達到以外寫內的目的。出入,皆指向于心理狀態,但不管是外化,還是內顯,細節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現形式。
我們首先來看一位同學在文章中表現的孤獨感。
“早點回去休息吧,今天晚上的晚自習到此結束了。”宿管老師催促道。我獨自一人走著,只見身邊的人們大都與我反向而行,與我漸行漸遠。我雖已在近兩個月的時間里慢慢習慣了寄宿生活,可心中仍泛起了一絲對溫暖的家的懷念。我打開了燈,光芒進入了寢室,讓我得以看清眼前的景象——好幾張床已經只剩光禿禿的木板或是已經卷好鋪蓋,恐怕今晚只有我一個人了吧?我失落地想,手中捧著一本書,可上面的文字卻同神秘的符號一般,讓我無法閱讀。這時,一個人走進了寢室,我的心頓時燃起了一支火苗。“你今天晚上住這里嗎?”他不假思索地搖了搖頭。我的心情頓時又跌入了低谷,我低下頭,盯著書本發呆。他父母也隨他來到了寢室,他們一同收拾好了東西,便一起離開了,只留下我一個人,我默默地望著三個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心中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上一次見到他們已是上一個星期的事了。他們好像除了督促我學習,提醒我準備軍訓的東西,也就沒再做什么了,于是又匆匆離開。我心中既有著一份不滿之情,又有一份沮喪。我悄悄地關了燈,閉上眼睛,可卻久久不能入眠,也不知道多久,才因過于疲勞而陷入沉睡。
孤獨感是很難描述的,許多人會采用比喻的形式,來使之具象化,這不失為一種好方法,但具象化的感覺似乎又不是感覺本身了,多少會給人隔閡之感。但這位同學在本段文字中抓住了一系列細節,如“反向而行”“漸行漸遠”的人、“光禿禿的木板或是已經卷好鋪蓋”、“不假思索地搖了搖頭”的同學、“慢慢消失”的背影,反復渲染孤獨的心境,其實質是以自己的心境觀人看物,而人和物都著上了作者心境之色彩,成為其心境的一部分,說是實,又是虛,虛虛實實間便有了心理變化的細膩和起伏。可謂處處寫內,但處處形于外。
再來看另一位同學在軍訓結束之時,寫教官送同學們上車離開軍訓基地的文章。
上了車,車門還遲遲未關,教官站在門口也遲遲沒有落座,他只是用眼神一個一個地掃過我們的臉龐,似乎想要說什么。看到這,我的心仿佛漏跳了一拍,頓悟了之前我是為何而不安。正想找旁邊的同學交流幾句,教官卻突然說話了:“嗯,就到這兒了吧……”他也顯得有些局促不安,呼吸有些不勻,胸脯隨著呼吸聳動著,又說了幾句話,在嘈雜的車里,我聽不清他說了什么,但此刻,我喉嚨里好像堵著了什么,想對他說句什么,卻怎么都說不出口。
教官卻也沒有給我們說話的機會,最后一句“再見”落下時,他也不知為何喘出了粗氣,臉色漲得潮紅,忽的,敬了一個無比標準的軍禮。
時間,仿佛定格在那一刻,教官的右手掌放橫在太陽穴旁邊,左手貼緊褲縫線,身子挺得筆直——正如他教我們的那樣。平常板著的面孔終于“軟”了下來,臉上仍留著那張略有尷尬的笑臉,金色的陽光順著他臉上剛硬的線條流進一條條笑紋間,如同嵌了一條金色的鍍邊,他的眼里分明含著淚光,卻努力忍住不流露出來,外表再如何強裝鎮定,微微顫抖的行軍禮的手還是暴露出他心中的不舍。
這三段文字中,作者的觀察可謂細致。教官的眼神、呼吸、胸脯、臉色都盡在筆下,以“掃”寫眼神,有檢閱之感;以“不勻”寫呼吸、以“聳動”寫胸脯,則顯不安;以“潮紅”寫臉色,則寫情緒上的激動。繼而寫教官敬禮,從左手到右手,從身子到面孔,從笑紋到淚光,處處寫外,但又處處照應內心。既形成畫面,給人以視覺上的沖擊,又以視覺打開通向心理狀態的通道,以窺探更為隱秘的世界。
二、繁 簡
繁簡是針對描寫細節的文字量而言的。繁,則是用大量的文字從各個角度、甚至是融合大量細節去寫相關對象,形成一種飽滿、豐富、厚實之感;簡,則是用少量文字簡潔地去寫細節,實現以少馭多、以簡馭繁的目的。繁簡的選擇,是以文章的表達需要為標準的,大到通篇皆寫細節,綿密繁細,如針線穿織,小到粗粗幾筆,點到為止,卻在全篇之中有眼波閃動之妙。
我們先看一位同學以繁筆寫細節。
朝陽不似正午的驕陽似火,也不像下午的殘陽如血,它溫暖而明媚,從天上傾灑而下,給世間萬物都鍍上了一層金黃的光輝。我的心情也如它一樣,洋溢著希望。今天第一天上學,也是留了五年的短發終于可以扎起來的時候。媽媽搬了小凳,坐在庭院溫暖的日光下,開始為我梳小辮。我坐在小木凳上,偏過頭去看媽媽,只看見她專注而溫柔的側臉,臉上細小的絨毛在陽光下閃著金色的光輝,嘴唇噙著一抹柔和的笑意,眼睛認真地看著梳子。她在陽光下好像一個神圣的天使。察覺到我過大的動作,媽媽輕敲了一下我的頭,責備:“別亂動!等會頭發梳得不好看可別哭鼻子!”眼里卻盛著笑意,我朝她吐了吐舌頭,擺頭坐正。暖洋洋的陽光從頭頂曬向全身,我半瞇起眼睛,感覺自己好像浸在溫水里,舒服極了。媽媽手上動作極輕,木梳子小心地挑起一撮發,用手攏住細軟的發絲,梳高,梳齊整。往日不羈的頭發此時在媽媽手上服服帖貼,仿佛被施了魔法。陽光透過樹枝投下細碎的光影,這幅景象美好得像一幅畫。
本段文字寫媽媽為我梳頭發時的溫馨與美好。作者先以環境描寫起,一“傾灑”一“鍍”,前者由上而下,后者由眼前到遠方,創設了一個立體的布景;接著寫媽媽的外貌神態,臉上的絨毛,唇間的笑意,認真的眼神,既寫實,又寫意;然后寫媽媽的動作,“輕敲”“挑起”“攏住”,可謂精細入微;最后,再寫環境,與起始處呼應。文字中,幾乎每一句都是細節,眾多的細節有條理、有層次地組織在一起,多而不亂,處處體現著溫馨和美好。
我們再看另一位同學以簡筆寫細節。
作者在學習上屢受挫折,無意中走到一個廟中,便去求簽,“我握住簽筒,斷定不會是什么好簽,微微顫了顫手,一只簽便從筒中偏斜了出來,稍稍地翻轉后落在地上,撞出了一聲清脆的響聲”。結果,作者求得了一支上上簽,在簽的鼓勵下,努力學習,最終走出了困境,人也變得昂揚而有自信了。之后,再次來到廟中求簽,“我想,一個上簽應當是順理成章的。雙手大幅度地揮劃幾下,一支簽在有節奏的震動下,挪出簽筒,在簽筒口停留了幾秒,伴著清脆的響聲敲在地上,與半年前如出一轍”,結果卻是一支下下簽。全文以敘事與抒情議論為主,最終闡明“至于絕處逢生、再接再厲則不把握在簽中,而把握在那雙握著簽的手中”的道理。文中的兩處細節用墨雖少,但極為傳神,在困境中,人不自信,故而求簽時也格外謹慎,用了一個“顫”,寫盡了內心的復雜,在順境中,人尤顯自信,故而求簽時帶著幾分急切,用了“揮劃”一詞,將自己的心態表露無疑。
當然,不管是出入,還是繁簡,其實都要求跳出片段、零碎、孤立的細節描寫,訓練學生從構段謀篇、情節設置、情感表達、文學審美等方面對細節做整體布局,讓細節描寫以細微的變化流動于篇章之中,使情節前后勾連呼應,各種表達方式榫合交融,形式與情感高度統一,以寫出文質兼美的作文。所以說,寫細節,是一種慢功夫,是以慢的思維方式烹制的一道鮮美的菜肴。